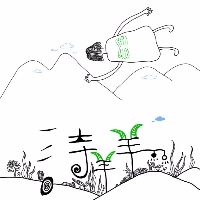柴静:山西临汾人,1976年出生。曾在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主持“夜色温柔”,在湖南卫视主持“新青年”。2001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先后在“时空连线”“新闻调查”“24小时”“面对面”等栏目担任主持人与记者。央视一套专题节目《看见》主持人。公益纪录片《穹顶之下》制作人。
非 典日记
4月22日
我不知道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发生什么了,只知道很可怕。
看着病人全身蒙着白布,被轮椅推上救护车,然后是二十多个人,被担架抬着,被搀着,还有自己手里拿着输液瓶,一个一个从门口出来。
我问了在场的被他们称为副院长的人,在杂乱的现场,他说到一个叫“天井”的地方,说那里是最多人倒下的地方。
4月24日
今天拍完东西回来的路上,开过人民医院,才发现那里被封了。我们的车急调头。
几个护士坐在大门口的石阶上,有一个摘下蓝色护士帽,长发垂在胸前,非常年轻。她们就那样一语不发地坐着。
我们用长焦拍了10分钟,谁都不说话。车开动的时候我向她们举起大拇指。不知道她们能不能看到。
这是一所与卫生部只有一街之隔的医院。
5月21日
我知道自己有几分侥幸,毫发无损地穿过了“非典”时期,回到恒常的生活里来。
可是,老是忘不了人民医院的那些人,天贺、晓鹏他们也是。
看到了《财经》的“人民医院感染调查”和王志对吕厚山的专访,心里难受。 一是觉得慘烈,205人感染啊: 一是觉得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点儿做这个题目,自责很久。
吕也在节目中提到“天井”,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还有一点很重要,今天节目组收到了一封人民医院医护人员的信,他们看过了院长吕厚山的采访,希望我们能够去现场调查,揭开更多的谜底。
我开始联络这次采访,不能再晚了。
5月22日
终于要做人民医院了。
报题、联络都很顺利,吕说他不接受采访,没关系,我要找的是一线的当事人。
这个雷雨交集的夜。
5月23日
人民医院的事有些周折,我打电话给急诊科主任朱继红,说:“你不用做判断和结论,只需要向我们描述你在4月看到、听到、感觉到的,就可以了。”
他沉默一下说:“回忆太痛苦了。”
“是的,”我说,“但是痛苦也是一种清洗,是对牺牲的人的一种告慰。”
我对他说,不采访没关系,见到他可以表达我的敬意。4月24日那天经过人民医院的时候,我一直希望有机会见到他们。不管决策者有多少失误,火线的人,那些用身躯挡炮弹的人,应被致以敬意。
“没有人会忘记,没有人会被忘记。”在最后我说,发自心灵深处。
5月24日
在人民医院,当朱继红蹲下身,打开急诊窒“天井”的铁索时,我难以形容自己内心的震动——这就是历史,所有的椅套上都是“星期四”的字样。
那是4月17日,“天井”关闭当天的时间,之前发生的一切就凝结在这里。那些凌乱不堪的床,堆积在桌上纸张发脆的病历,每一页翻开都是“发热”、“发热”、“发热”……
黑板上写着22个病人的名字。其中有19个名字的后面,都用粉笔写着“肺炎”。
“我们没写SARS”,朱继红说,“其实就是。”
“那另外三个不是的人呢?”
他沉默了一下说:“没有办法,只能在这里沤着。”这只是一家医院的急诊科的一间临时输液室的感染数字。他带我去看了留观室改成的SARS病房,我只看到几间普通的病房,迟疑地问他:“你们的清洁区、污染区呢?”他指了指地上,“只能在这儿画一根线。”我不能相信地问了一句,“在哪儿?”他指了指胸口:“在这儿。”
在这儿工作的人,连隔离衣都保证不了。
当4月20日我穿着三层隔离衣,进胸科医院,进佑安医院,消毒30分钟的时候,我不知道就在这个城市的另一家医院,他们的病房是这样的状况。
我问他那几天是什么状态,他说:“我很多天没有照过镜子,后来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胡子全白了。”
最后在发热门诊那儿,看到了露天的椅子和输液架。病人多的时候就坐在空地上,树上、车里也都挂着点滴。
这一切都被镜头记录下来,在26日被彻底清理之前。
这就是现场。
拍完,坐在人民医院的台阶上,喝一口冰水,心里非常寂静。有很多人都说“非典”过去了,真的吗?如果我们不回头来看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就难以避免下一次的悲剧。
5月27日
急诊科的王晶昨天去世了。
我们去看了她的家人,她丈夫给我念妻子的短信,每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着心。
第一条是:窗前的花儿开了,我会好起来的。
他不能探视妻子,只能每天站在地坛医院门口,进不去,就在世界上离她最近的地方守着。
她写:回去吧,你不能倒下,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
她开始知道自己不好了,在短信里交代存折的密码了。
最后一条,她要他系上红腰带:本命年,你要平安。
他一边恸哭一边念,我的眼泪也满脸地流,做记者哪能这样呢?可是你是你就不能摆脱人的情感。
女儿大宝才六岁,她在门上贴张条子,条上说:妈妈爱我,我爱妈妈。
我问她为什么贴在门上。
她不说话。
我轻声说:“你是想让妈妈一回来就看见,是吗?”
她点点头。
临走的时候,她在床上叠幸运星,说装满一整瓶子妈妈就回来了。
我在暗淡的光线里沉默地站了一会儿,很想拥抱她一下,但是什么也说不出来。
她也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我忽然明白,她其实已经知道妈妈过世了,但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的难过。
出来后,车行驶在二环,满天乌黑的云压着城,暴雨马上就要下来。我们一车的人,谁也不说话。
不知道这期节目能不能播出,我只希望保留下这些素材,20年之后,大宝长大了,我可以放给她看一看,让她明白,她的母亲是怎样牺牲的,是什么让这么多人付出了惨烈的代价。
这是2003年,春夏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