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路
作者简介:王路,阴昭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北京 100084
人大复印:《逻辑》2019 年 03 期
原发期刊:《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20193 期 第 15-23 页
关键词:奎因/ 逻辑观/ 一阶逻辑/ 量词/
摘要:奎因是20世纪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逻辑的理论和方法是奎因哲学的基础。他强调一阶逻辑的重要性,甚至认为模态逻辑不属于逻辑。他对许多传统哲学观念提出挑战,包括关于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区分,有关个体的本体论承诺等等,在哲学研究中产生广泛的影响。王路教授赞同奎因的逻辑观,认为从弗雷格到奎因,他们的逻辑观是一样的,尽管他们使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奎因的逻辑观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观是一脉相承的。这种逻辑观在理论上体现的是关于量词的研究,实质则是对普遍性的追求。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与哲学是一致的,因此,能够在哲学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阴昭晖:您是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研究专家。但是,我发现,除弗雷格以外,您研究最多的是威拉德·冯·奎因(W.V.Quine)、迈克尔·达米特(Michael Dummett)和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您还翻译了他们三个人的书。①在课堂上,您也经常谈论这三个人。我还发现,这三人中您谈论最多的是奎因。在您的“语言哲学”和“逻辑哲学”课上,您让我们读的文章最多的,除了弗雷格的,就是奎因的。在您最近的新书《语言与世界》②中也还是这样。我觉得您对奎因的文献非常熟悉,甚至不亚于对弗雷格文献的把握;您对他的思想有深刻的认识和把握,而且您对奎因本人也很推崇:您经常强调奎因很重要。但是,您很少写研究奎因的文章。假如不上您的课,我根本不可能听到您那么多关于奎因的精彩论述。所以,我首先想问您,为什么您常常谈论奎因,但是却不写关于奎因的研究论文呢?
王路:奎因这个人很重要,也比较特殊,他的生命历程差不多是整个20世纪。他有一个显著特点:他与他同时代的很多人都有直接的对话和交锋,比如达米特和戴维森。还有一点,奎因和罗素不太一样,奎因是美国人,20世纪分析哲学一开始主要来自英国,主要人物是罗素等。但是,分析哲学到了美国之后,从奎因开始发展起来了。可以说,美国的分析哲学的发展,奎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读奎因的东西,但是没有写研究文章。这是因为二手文献读得不够。我一直认为,写研究性文章,只读一手文献是不够的,一定要读别人的相关研究,这就是我说的二手文献。我总是强调:一手文献是研究的基础,二手文献是研究的起点。如果你没有读过二手文献,写什么写?别人说过什么,你都不知道,写出来充其量也就是你的读后感嘛!读后感就没意思了。但是,课堂上不一样。比如,我讲奎因,可以直接讲奎因本人的思想,也可以讲他与别人的比较:奎因怎么说的,弗雷格怎么说的,达米特怎么说的。这与写论文是不一样的。这样讲课可以给学生以启示,能够引导学生进一步阅读文献就够了,因此,讲课可以随意一点。论文不同,它要基于别人的研究成果,要说出新东西,要有严密的论证。
阴昭晖:您见过奎因,也见过达米特,和他们都通过信。您能从自己的亲身经历比较一下这两位哲学家吗?
王路:这个问题挺难说的。我和达米特有过一次比较深入的交谈,我在他家待了两个多小时,后来他开车带我去教师餐厅(faculty club)去吃饭,然后还请我喝了咖啡,实际上我和他前后一共待了4个小时。这次经历是令我难忘的。我和奎因见过面,当时是1996年在日本京都大学一个会上,他获得一个大奖,他去领奖时作了一个报告,结束后我上去和他说了几句话。其实当时和他说那几句话也不应该,因为他年纪已经比较大了,报告后也有些累。我当时主要因为事先已经和他通过信了,我想当面请他为我翻译的《真之追求》写个序。后来我2000年去美国也没有见到他,他生病在家,圣诞节前去世了。所以,我和奎因没有什么更多的接触。奎因去世之后,2001年3月份,我参加了哈佛大学哲学系举办的一个奎因追思会,许多名人讲了话,通过这个追思会对奎因有很多了解:奎因的人缘很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这我以前写过的。③所以,我在读奎因的时候会想到奎因,想到我和他的这些交流。但是,我和奎因在思想上的交流是没有的。这一点和达米特不一样,因为我和达米特是有直接对话和思想交流的,因此,在读达米特的书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好像达米特是在和你说话,这样可以帮助你去理解他的思想。但是,奎因太重要了,所以我一直读奎因的东西。如果非让我对这两人评价一下的话,我认为:在思想的敏锐程度上,奎因可能要比达米特强;但是,在思想的深刻程度上,达米特可能要比奎因强。这完全是我从读他们的著作中感觉到的。
阴昭晖:您多年以前出版过一本书《逻辑的观念》,④这本书尽管篇幅不很长,但是,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本书中您提出过很多鲜明的观点,比如归纳不是逻辑,辩证逻辑不是逻辑。您认为逻辑的性质就是亚里士多德说的“必然地得出”。而在弗雷格的研究中,您又总是强调他说的“真这个词为逻辑指引方向”。⑤此外,我看到,奎因的逻辑观被很多人总结为“逻辑就是带等词的一阶逻辑”。在奎因看来,模态逻辑、高阶逻辑以及集合论等都不属于逻辑,有人曾把这种逻辑称为“奎因式逻辑”(quinine logic)。我的问题是,您是否同意这种对奎因逻辑观做出的总结?您的逻辑观和奎因的逻辑观是一致的吗?
王路:我先回答你的第二问题,简单说,我的逻辑观和奎因是完全一致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对于第一个问题,应该这么说,我的逻辑观主要来自亚里士多德和弗雷格。亚里士多德是逻辑的创始人,弗雷格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我在《逻辑的观念》那本书中说,他们二人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出来以后,很多人都想发展逻辑,比如,像培根的《新工具论》发展出了归纳法,黑格尔的《逻辑学》发展出来了辩证法。但是,我认为这些都不是逻辑的发展,其实都是背离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
阴昭晖:什么叫“背离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
王路:就是观念出问题了。因为他们的工作都涉及什么是逻辑这样一个观念的问题。这也就是我在《逻辑的观念》里面特别强调的,逻辑就是“必然地得出”。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亚里士多德说的话:推理是一个论证,在这个论证中,一些东西被规定下来,由此必然地得出另外一些与此不同的东西。这段话我在课堂上、在文章中引用过很多遍。亚里士多德当时的描述是很直观的。他描述了一个推理的结构,他只是说从前提到结论这个推理的过程是“必然地得出”,至于什么是“必然地得出”,他没有进一步说。但是,他提供了一个三段论系统,也就是说,只要满足了三段论的那些格和式,就能保证从真的前提得出真的结论。但一阶逻辑不这么说了,一阶逻辑说逻辑是研究推理的有效性的:“有效”就是保真,就是保证从真的前提一定得到真的结论。这是一个语义说明,这样的说明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一致的。当弗雷格说真为逻辑指引方向时,他也是从语义的角度来考虑的。所以,亚里士多德说的“必然地得出”、弗雷格说的“真(这个词)为逻辑指引方向”以及一阶逻辑说的“有效性”,这三者之间都是一致的。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逻辑的观念,有了这样的观念之后,再讲归纳不是逻辑,辩证逻辑不是逻辑,就是很正常的了。
你刚才提到一点,奎因认为模态逻辑、高阶逻辑和集合论不属于逻辑。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奎因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一阶逻辑才是逻辑。而一阶逻辑就是弗雷格所建立的逻辑。所以,奎因的思想在这一点上和弗雷格是一致的。一阶逻辑与模态逻辑是有区别的。弗雷格有一个说法:像“必然”这样的表达只起暗示作用,与判断内容无关。因此,在弗雷格的逻辑中是没有对模态词的考虑的,弗雷格也就没有构造出模态逻辑。严格地说,我们把弗雷格的逻辑叫做一阶谓词演算,因为现在所说的一阶逻辑比它丰富多了,但是,一阶逻辑的基本思想、内容和方法都是弗雷格提供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奎因说的一阶逻辑与弗雷格的逻辑是同一的,他们两人的逻辑观是一致的。从亚里士多德到弗雷格到奎因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样说是没有问题的。因此,我认为我在强调逻辑的观念时强调这一点,也是和他们一致的。
所以,当奎因不赞成把模态逻辑这样的东西弄进来,或者说他不赞成搞模态逻辑、至少不赞成搞模态谓词逻辑的时候,他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是和弗雷格一样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弗雷格引入全称量词时,他给的名称不是我们现在叫的“全称量词”,而叫“普遍性”。就是说,一阶逻辑的实质是与普遍性相关的,而这种普遍性是由于我们借助量词达到的。在这一点上很多人不理解,甚至许多学逻辑的人也没有认识到。而这一点我认为对于逻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弗雷格建立的这个逻辑是能够达到普遍性的,奎因对它有非常明确的认识,他知道借助这样的逻辑可以帮助他进行哲学讨论,并在哲学讨论中获得有关普遍性的问题的认识和说明。所以,表面上奎因是坚持一阶逻辑,实际上他是坚持一种与普遍性相关的认识,坚持一种达到认识普遍性的思想和理论。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奎因是非常睿智的,他和弗雷格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阴昭晖:我赞同您关于量词的说明,我也认为一阶逻辑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关于量词的研究。您说奎因借助逻辑来研究哲学,是不是指他关于本体论问题的研究呢?本体论问题作为最古老的哲学问题,主要是研究存在本身的。奎因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出名。他说:存在是由存在量化所表达的东西。类似说法很多,像表达存在的最佳语词就是量词。我想请您结合本体论问题再进一步谈谈量词理论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奎因甚至要把本体论问题归结到量词上?
王路:一阶逻辑中量词为什么重要,这就涉及对量词本身的认识。现在我们学习逻辑,初始语言里面有两个量词:一个全称量词,另一个存在量词。刚才我们说了,弗雷格最初定义量词的时候,它不叫“量词”,而叫“普遍性”,并且弗雷格在相关讨论中有一个明确的说法:量词是我们可以达到普遍性的唯一方式。什么叫普遍性呢?普遍性在逻辑中是通过量词域来说明的。
阴昭晖:请您举个例子说一说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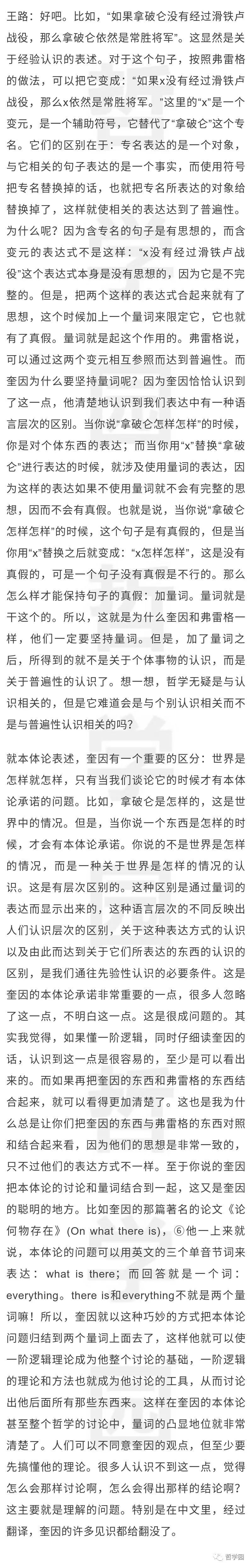
阴昭晖:您提到中文的翻译,我就接着再问一个相关问题。您一直认为应该将being译为“是”,比如,奎因那条著名的本体论承诺:“to be is to be a value of a variable”,⑦学界译为“存在是变元的值”,而您译为“是乃是变元的值”。您这样做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王路:being这个词应该翻译为“是”,而不应该翻译为“存在”,这个问题我已经讨论很多了,这里就不讨论了。⑧简单地说,我的观点被称为“一是到底论”,既然如此,我就必须把它坚持到底呀。(笑)所以,我要把它翻译为“是”。当然,你也可以说:你有点矫情,你没说出道理来。所以,还是要说一说其中的道理。当奎因说“to be is to be a value of a variable”时,后面的“to be a value of a variable”是关于前面“to be”的解释,那么,他说的这个“to be”是什么?这个“to be”一定是传统所说的那个“to be”,也就是西方哲学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讨论的那个being。它一定是这个东西;否则的话,奎因的讨论就没有意义了。如果把它翻译为“存在是变元的值”,问题是很明显的。从现代逻辑的角度看,我们有两个量词:一个是存在量词,一个是全称量词。“存在是变元的值”相当于只涉及一个量词,难道奎因的讨论只涉及存在量词吗?显然不是。奎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把there is和everything并列在一起说的,他没有只说一个。并且他明确说existence(存在)这个词不好,我们不用,我们可以用is(是)。无论是不是有道理,这样他就很容易谈到量词。something is such that…,everything is such that…这两种表达也是他经常在一起说的,它们与前两种表达显然是对应的。这样的表达是什么?量词和系词表达嘛!所以,我觉得一般地说说“存在是变元的值”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认真讲述奎因的思想,按照这个翻译就把奎因的思想曲解了。非常保守地说,这样的翻译至少容易对他的思想造成曲解。所以,我主张他的话要翻译成“是乃是变元的值”。
阴昭晖:等词在奎因逻辑观中似乎很重要。等词是表达同一性的。奎因经常批评别人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比如混淆符号和对象的关系。“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实体”也是他的一个非常出名的本体论承诺,这与他关于等词的认识相关。请问,奎因关于等词的认识与他关于量词的认识是相关的吗?
王路:我觉得不仅是相关的,而且是完全一致的。首先,等词是什么?我认为奎因对于等词的理解和弗雷格是一致的。弗雷格和罗素的逻辑都是带等词的,因为他们的那个逻辑是要推出数学的,要表达数的,而数之间的相等必须用等词,所以等词是两个项之间的关系,是两个指称个体的符号之间的关系。但是,后来人们讲逻辑的时候做了简化:不加等词了。如果这样的话,就需要用二元谓词来表示同一性了。用谓词表示同一性,同一性只能是谓词的一种语义解释。而谓词之间的关系是用逻辑联结词表示的。这样一来,谓词的作用保持不变,但名字之间的相等关系就含糊了。也就是说,由于没有等词,也就缺少了直接表示同一性的方法,而相应表达需要采用其他方式。所以,从弗雷格到奎因,带等词并不妨碍整个量词理论是一致的,它只不过表明等词是表达个体之间的一种同一性的关系。量词有量词域,量词域中都是个体的东西,在这里,个体之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同一性也是其中一种关系。用等词是一种表达方式,不用等词就需要考虑其他表达方式。将这样的认识用到哲学讨论中,奎因才提出:“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实体”,按照这个标准,实体一定是个体的东西,而同一性是个体之间的关系,它是需要用等词或相似于等词的方式来表达的。
阴昭晖:奎因的逻辑观还有一个比较鲜明的观点,认为“模态逻辑不属于逻辑”。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但没有展开。奎因的这个观点遭到很多人反对。比如我们熟知的奎因和露丝·马库斯(Ruth Marcus)之间的论战。我看到,奎因的一些观点发生过一些变化,但他关于模态逻辑的观点似乎始终没有变。这是为什么呢?
王路:这个问题说起来比较麻烦。我就直接跟你说说我现在的看法吧。我赞同奎因的观点,但是,我又与他的观点不完全一样。逻辑学家得有一个逻辑观,也就是当问什么是逻辑的时候,你要给出正面回答。假如用举例的方式来回答:一阶逻辑是逻辑,或者逻辑就是一阶逻辑,也是可以的。我们都承认一阶逻辑是逻辑。问题在于,逻辑是不是等于一阶逻辑。奎因认为模态逻辑不属于逻辑,似乎是赞同这种看法的。在这个讨论中,奎因有很多具体的说法,比如,他认为,按照模态逻辑,一阶逻辑的很多东西就要改变,如存在概括规则就会失效。因为从“□Fa”得不出“x□Fx”。奎因认为一阶逻辑是没有问题的,是要坚持的。人们都说,奎因的观点涉及他的本体论承诺,在我看来,这涉及他对普遍性的认识。修正一阶逻辑的东西势必影响到关于普遍性的认识。在这一点上我是赞同奎因的,我认为奎因的看法是对的,要坚持一阶逻辑的东西。又比如关于本质主义的讨论。按照模态逻辑,“□Fa”的意思是:“a必然具有F这种性质”,这样就使F这种性质成为a的本质,因而模态逻辑的说明与本质主义联系起来,而奎因是坚决批判本质主义的。关于本质主义我就不展开讨论了,我只说一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与奎因有不一样的地方,我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固然有它说不清楚的地方,但是,“本质”这个概念依然是亚里士多德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对认识的一种说明,比如亚里士多德说的十范畴中第一个范畴就是本质,它是亚里士多德关于认识的一种说明,和其他范畴形成区别:其他范畴都是与感觉相关,但是,本质一定不是与感觉相关的。用康德的话说,本质一定是与理解相关的。这等于说,本质与其他范畴的区别是亚里士多德对于认识层次的一个划分。而奎因不赞成这个,他有他的道理,没关系。后来凯特·法恩(Kit Fine)在讨论中就区别了本质的和必然的:本质的可以是必然的,而必然的不一定是本质的。所以,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奎因强调一阶逻辑和模态逻辑的区别,一阶逻辑是外延的,与本质的东西没有关系,而模态逻辑会引起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说他有他的道理。
这里我可以关于我自己的看法再多说几句。我认为一阶逻辑是普遍的,而其他逻辑不是普遍的,比如模态逻辑就不是普遍的。以前我这样说时有人立即就问为什么,还要我举例说明。我说,数学就不用模态逻辑啊!这些年来我反复强调弗雷格那段话:“逻辑关系到处反复出现,人们可以选择表示特殊内容的符号,使得它们适应概念文字的框架。”⑨弗雷格说的概念文字就是一阶逻辑,他的意思是说,他把这样一种逻辑做出来了;逻辑并不限于这种形式,还可以有其他形式,但是,一定要以他的逻辑为基础。模态逻辑的发展以及今天各种广义模态逻辑的发展都说明,弗雷格的论断是正确的。在这一点上,我比较赞同弗雷格的说法,后来那些逻辑也可以做,只要把它加在一阶逻辑上就可以了。但是,用这种方式做得太泛以后就可能会出问题。我认为,奎因不仅看到了模态逻辑中的问题,而且可能看到了后来可能要出的那些问题。今天有很多所谓类似广义模态逻辑的东西,大概在奎因看来都不是逻辑。所以,奎因才激烈反对像模态逻辑这样的东西。刘壮虎老师近年来几次谈到,现在有很多所谓逻辑系统,它们的算子其实都不是逻辑算子,也是这个意思。我认为这里归根结底仍然是一个逻辑观的问题。
现在我可以明确地说,我的逻辑观就是奎因的逻辑观:逻辑就是一阶逻辑。奎因可以说“加等词”,我不说“加等词”,意思也一样。
阴昭晖:那模态逻辑呢?
王路:模态逻辑可以说是一阶逻辑的应用,因为它不过是把“必然”“可能”等算子加到一阶逻辑上,它的语义与一阶逻辑是一致的,比如它关于“必然p”的解释:p在任一可能世界中都是真的。而且在模态逻辑中,逻辑本身的性质没有变,比如“必然地得出”或推理的有效性、“保真”这些基本的东西没有变,以及逻辑系统所要求的基本性质如可靠性、完全性也没有变。所以,我赞同说逻辑就是一阶逻辑,而其他逻辑是一阶逻辑的应用。这种说法跟奎因的说法可能有点不一样,显得比奎因宽容一些,但是,基本思想和精神是一致的。
阴昭晖:下面的问题与您相关,有些观点可能对您的看法提出质疑。第一个问题,奎因认为专名可以消去,而您在《语言与世界》中认为专名最终是不能消去的。我对您的这个看法是有疑问的。这个问题涉及专名和摹状词的区别,以及可能世界语义理论的相关说明。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您能说一说您和奎因的分歧吗?
王路: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首先要知道奎因为什么这么说。刚才我们也说了,奎因非常强调量词,他把所有本体论问题都归结到量词上去,他要用量词来解释一切,或者是要基于量词理论对世界作出解释,这是奎因的一个基本思想。他自己有一个逻辑系统也是不含名字的。
专名表示对象。摹状词也有这种作用,因为它表达唯一性。奎因说可以把一个专名划归为一个摹状词,因为一个摹状词也表示一个对象,然后再用罗素的方法把这个摹状词消掉,这样就没有摹状词了,因而也就没有专名了。这个意思很清楚:专名变成摹状词,摹状词被消掉,结果专名和摹状词都没有了。那么,奎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把摹状词消掉以后,句子中就只剩量词了。⑩所以,这个想法与奎因把本体论问题归结到量词上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我认为奎因这个思想是清楚的,想法是有道理的,他的描述表面上也成立。但我不能完全同意,因为我认为专名是消不去的。把一个专名划归为一个摹状词,表面上看是消去了专名。其实并没有做到:因为摹状词除自身的定冠词外,它还隐含着名字或定冠词。这里就可以看出弗雷格不区别专名和摹状词的重要性以及它给我们的启示了。定冠词自身只表达唯一性,但是,要达到指称一个对象的目的就一定要借助一些起说明作用的东西,而这样的说明也要表达唯一性才行。举个例子:当我在教室里说:“前排穿红衣服的那个女同学”这句话时,我没有说女孩子的名字,但是,大家都知道我说的是谁。因为我只是把她的名字转化为这样一个摹状词“前排穿红衣服的那个女同学”。在这个摹状词中,好像没有名字,其实不是这样。“前排”是什么?它含一个指示词,即“前”,它的意思是“第一”,相当于定冠词。此外,这个“前排”一定是我们上课的这个教室,比如“6A318”。所以,它相当于“6A318第一排”。名字表达唯一性,不借助名字表达不了唯一性。摹状词可以替换名字没有问题,但摹状词也必须表达唯一性。所以,在替换的过程中,表达指称的方式可以改变,但是,表达唯一性的功能保持不变。所以,我认为,专名实际上是不能被消去的。
阴昭晖:第二个问题,量词理论确实重要。但是,我看到您指导的学生中有好几个做的论文都与量词研究有关。以前杨红玉、现在戴冕的论文都是专门研究量词的,我的论文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涉及量词理论,而且您总是特别强调这部分内容的重要性。我想问您,量词理论尽管重要,但是,如今已是非常成熟的理论。您允许这么多人做量词理论研究,难道不重复吗?这与您一贯倡导的研究理念不是相悖的吗?
王路:不是的。杨红玉的论文最开始是要写奎因研究,最后把题目改成了量词理论研究,因为她对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中量词理论之间的关系、替换量化和对象量化之间的关系、一阶逻辑和模态逻辑之间的关系感兴趣,所以最后她就把她的论文集中到这部分了。戴冕做的研究是“量词与数词”。他考虑的不是现代逻辑和传统逻辑之间的关系,也不是考虑对象量化和替换量化的关系,而是量词与数词之间的关系。在日常表达中,量词和数词很相似,都作为形容词出现,比如“所有人怎样怎样”,“两个人怎样怎样”。量词和数词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形容词。不同之处在于,数词可以做专名,如“2+2=4”,而量词是不能的。数词可以表达确定的量,而量词可以表达普遍性。此外,数词又与概念相关。弗雷格说,数的给出包含着对概念的表达。数词与量词之间的关系,量词与谓词之间的关系,数词与概念之间的关系,这是很复杂的。戴冕主要是做这个研究。而您做的论文是奎因逻辑思想研究,在这其中量词显然又是很核心的东西,因此,您也会涉及量词。虽然你们都会涉及量词,但是,你们研究的重点又都是不一样的,这就再次说明量词和一阶逻辑的重要性。我们经常说要学逻辑,老这样说别人都烦我们了,就像祥林嫂一样。但是,实际上,如果不懂逻辑,不懂量词,现代分析哲学中的很多东西是看不懂的,传统逻辑中和量词相关的,也是看不懂。看不懂怎么办,就稀里糊涂,或者回避,或者不懂装懂。比如,奎因的本体论承诺,字面上没有量词,但是,实际上最核心的思想就是量词理论。刚才提到的罗素的摹状词理论也是基于量词的,最开始谈到的弗雷格所说的普遍性还是量词。如果不懂量词,那么,如何读懂这些理论呢?如果不懂这些理论,那么,又怎么能说懂现代哲学呢?所以,以量词为基础,可以讨论许多问题,可以进入很多不同领域。认识到这一点对于传统哲学研究也是有帮助的。康德的范畴表第一行不就是“量的范畴”吗?它难道与量词没有关系吗?所以,奎因强调量词,甚至把它强调到极致,是有他的道理的。我强调这部分研究在你的论文中的作用,也是希望你能够对这个问题有充分的认识。
阴昭晖:第三个问题,您翻译奎因的唯一一本书是《真之追求》。这并不是他的代表作,似乎也不是他的名著。您为什么会选这本书翻译呢?
王路:主要是这本书最薄啊!我大概很多年不做翻译了,翻译是件很麻烦的事。要翻译一本书基本上一年其他什么事都不能干了。但是,如果我们不看书的话就会落后。必须要看文献。所以,我后来就不愿意翻译了。奎因那本书是晚年写的,基本上是他早期思想的简写,比如,他早年的Word and Object(11)书里面的很多表述和论证都是很比较复杂的,到了《真之追求》这本书中,线条很清楚,表达也就很简单:从观察句开始,到句子涵义,最后达到真。思想和观念梳理得非常清楚,最后他的所有理论几乎都装进去了。所以,这本书虽然薄,却能够体现出奎因一生思想的总结性的东西。而且我非常喜欢这本书的书名“真之追求”,它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真理的追求”是根本不同的。
阴昭晖:第四个问题,学界一般把Quine译为“蒯因”,我在论文中也这样做,而您总是把它译为“奎因”,这是为什么呢?
王路:这里有一个拼音规则的问题。翻译人名通常要遵循韦氏拼音法。在用中文翻译外文人名时尽量避免使用中文中已有的姓氏。Quine这个名字是姓,所以,“奎因”是姓,他并不是姓“蒯”,“蒯因”看起来就好像他姓“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不过像我的文章,我写成“奎因”,编辑非要改成“蒯因”也无所谓。不过就是个名字嘛。但是,这里面实际上涉及人名的翻译规则。
阴昭晖:谢谢您回答了那么多问题。再请教您最后一个问题。牛津大学的蒂莫西·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教授最近在一篇文章(12)中提到了奎因的影响,他说那时大家都对奎因感到“恐惧”,因为很少有人能与奎因在哲学争论中使用的逻辑技术这个武器相匹敌;那时哲学家们对一些日常语义概念的使用也会感到“紧张”,比如同义性、意义等:因为大家害怕受到奎因理论的“指责”。但是,威廉姆森又认为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种“紧张”和“恐惧”就逐渐消失了。他的意思是奎因的影响力在那个时候下降了。但是,就我阅读的有关奎因的研究文献而言,我感觉到最近一些年讨论奎因的文章明显增多,有人甚至提出“回到奎因”。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王路:简单地说,这其实就是对逻辑的理论和方法的把握和应用的问题。上个世纪开始的时候,奎因所讨论的都是传统哲学中的重大问题,如分析和综合命题的区分,本体论承诺等问题,这些问题当然会受到人们的重视,所以,奎因在这些问题讨论中提出的观点和质疑马上引起了哲学界的轩然大波,很多人都要和他讨论。但是,不少人在讨论中遇到了困难,因为奎因讨论问题的理论工具完全不一样,他的这种理论工具主要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阶逻辑。这样就导致一个结果,假如不懂一阶逻辑就没法和奎因进行讨论。所以,你说威廉姆森说当时的人们“恐惧”是很正常的,因为人们对这个工具的掌握是不够的。西方人对现代逻辑的掌握也是有一个过程的,约瑟夫·鲍亨斯基()在20世纪30年代参加过世界哲学大会,他说在那次大会上,维也纳学派全体出席,他们在黑板上书写逻辑符号进行论证,对传统哲学家进行围攻。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哲学家们是讲究论证的,如果一个论证充满了符号,而你是看不懂的,那么你如何跟别人去讨论?哲学不是大批判,只说你是唯心的,他是唯物的,这是不行的,得论证。达米特说,20世纪50年代,有一次他身边的人奔走相告,说今天奎因要来做报告,我们得去好好修理修理他。那时牛津是哲学中心,看不上美国来的哲学家,这是很正常的心态。达米特说,我读过奎因,只有我知道奎因的思想深刻,和他辩论是很难占便宜的。结果那些人根本就不是奎因的对手。达米特还说,约翰·奥斯丁(John Austin)作为报告主持人也只是就奎因某一本书的某一个脚注中的一个词提了一个小问题,因为奥斯丁知道奎因的本领。奎因是一个非常敏锐和犀利的人,他又有理论武装。按照达米特的说法,那些人修为不够,是辩论不过他的。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逻辑的普及,大家都知道这套方法了,因此,再讨论的时候恐惧感就没有了,你说的东西,你所使用的理论和方法,大家都理解,差异只是认识的差异而不是方法的差异,这个时候就可以平起平坐的讨论了。所以,威廉姆森说情况好转了。这就是为什么在国内我一直强调要学习现代逻辑,你学会了以后才能读懂人家的东西,才能和别人在同一个层次上讨论;否则,你怎么讨论啊。做不到这点就只能是恐惧。现在国内很多人老说“你是搞逻辑的”,“我不懂逻辑”,表面上这好像是开玩笑的话,其实也是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惧”。当然,国内许多人这样说时并不是恐惧,而是无畏。金岳霖先生以前说过一句话“过去说人不懂逻辑那是骂人话”,就是说,你研究哲学却不懂逻辑,还搞什么搞。大概也有相似的意思。
至于你说有人说要“回到奎因”,我没有看到这话具体是怎么说的。但是,我在阅读中注意到一个现象:最近文献中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倒是被人们提得很多。不管是重提卡尔纳普还是你提到的“回到奎因”,我认为,这大概主要是因为现如今人们对意义问题、真之理论等问题讨论很多,它们都是20世纪后期语言哲学所讨论的问题,与前期的讨论并不完全一样。所谓回到奎因,回到卡尔纳普可能是要重新思考他们以现代逻辑为工具所提出和讨论的那些问题,重新关注他们讨论问题的方式,从中发现新的思路和思考方式,甚至重新发现新的问题。比如,法恩是一个逻辑学家,他研究模态逻辑,由于涉及与本质相关的问题,他还构造了一个本质逻辑,可是,最后他居然去讨论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又比如今天人们研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研究康德、黑格尔,都是用现代逻辑的方法,这说明,应用现代逻辑进行研究在今天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事情了。而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奎因又是运用这种方法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因此,现在如果有人说出“回到奎因”,我觉得这个说法至多可能有些夸张,但大概是不会错的。
①三本译著分别是:奎因:《真之追求》,王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达米特:《分析哲学的起源》,王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戴维森:《真与谓述》,王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
②王路:《语言与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③王路:《寂寞求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3—234页。
④王路:《逻辑的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⑤弗雷格:《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王炳文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29页。
⑥Quine,W.V.O.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Cambridge Mass.:Harvard,1994.
⑦Quine,W.V.O.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p.15.
⑧参见王路:《“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王路:《一“是”到底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
⑨弗雷格:《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第45页。
⑩以罗素的摹状词理论中“《威弗列》的作者是司各脱”这个例子为例,其中的“《威弗列》的作者”这个摹状词可以表述为:“至少有一个人写了《威弗列》并且至多有一个人写了《威弗列》。”“至少有一个”和“至多有一个”就是量词表达式。
(11)Quine,W.V.O.,Word and Object,Cambridge Mass.:MIT Press,1994.
(12)威廉姆森:《近40年来分析哲学的转变》,徐召清译,《世界哲学》201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