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明代话本戏剧和小说演义中有关流沙河的故事地域可能受宋元明文献中四川汉源流沙河与三藏的传说的影响,也可能受明代文献中将西北唐代大流沙沙漠、沙河戈壁荒漠演变成流沙河的影响。明代西北和西南的火焰山见于记载,但将其与唐僧取经联系起来的首先是在明代戏曲、话本之中,并不是在历史文献之中。火焰山与唐僧取经联系起来,反而是受《西游记》等明清戏剧话本、小说演义的影响才附会到景观上的。通天河的地名出现较早,曾特指有三条河流,早期并没有与唐僧取经联系起来,更没有晒经石的传说和遗存,在西南地区反而是早在明前期就出现唐僧取经的晒经石的传说和遗迹。历史上很早就有白马驮经的历史与传说,后来在元明以来文学叙事中开始出现白龙马的传说,而在历史叙事与民间景观附会中,明代前期以来白马同时也演变成白马和尚山和白马护经的故事。《西游记》的白马和白龙马故事,可能受此影响。《西游记》女国主要是受汉唐历史语境的葱岭以南的东女国和文学语境的宋代女人国的影响而来。通过唐玄奘取经历史的演绎个案,发现中国古代的景观附会呈现“地域泛化”和“情节神化”两个特征,其中“地域泛化”对中国古代文本叙事、景观附会的影响很大。历史事实的“源文化”会直接衍生出真实的历史景观、民间口述传说、民间附会景观三种“前文化”,进而影响到文本叙事,而文本叙事又会产生新的景观附会和口述传说,形成“后文化”,反过来又会再影响文本叙事。
关键词
《西游记》;南北丝路;文本叙事;地域泛化;景观附会
从唐代玄奘到印度取经,《大唐西域记》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问世后,历代关于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与传说屡屡见于文献,并附会成各种景观留在各地。明代吴承恩以玄奘取经故事为原型的小说《西游记》面世后,更使西天取经的历史得以靠文学叙事的演义流传广泛。不过,在世人的眼里,不论是《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还是《西游记》,都是以中国西北地区、南亚地区的历史叙事、文学叙事和景观遗址为地域原型,今天这些地区也确实留有许多相关的历史遗迹、传说和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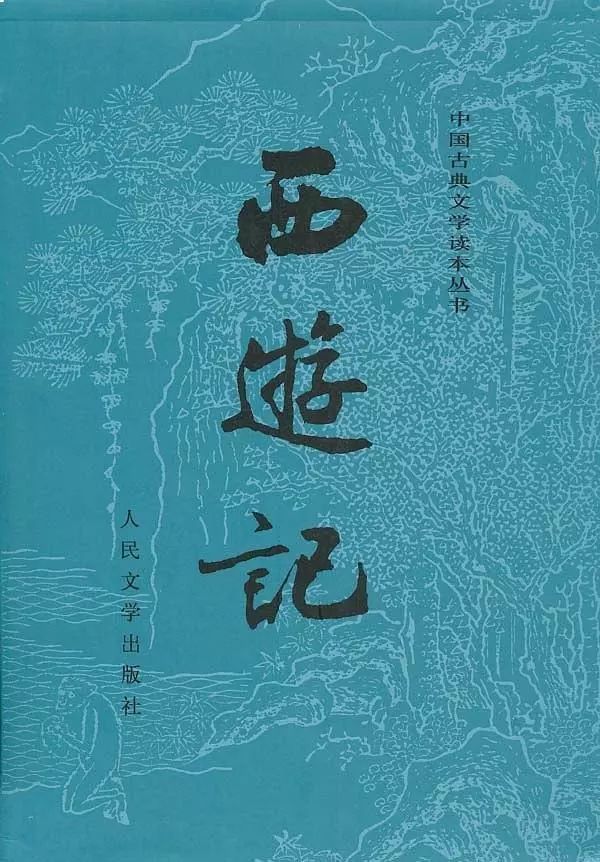
《西游记》
不过,我们发现《西游记》中的几个故事的地域原型较早也出现在西南丝绸之路上,因为我们在研究西南丝绸之路时,在四川西南部、云南西部、缅甸地区也发现了许多唐僧三藏取经经过的所谓历史遗迹和历史记载。现在的问题是,这些遗迹真是与唐僧三藏玄奘取经有关吗?其与西北地区的唐僧取经的遗迹是何种关系呢?又与《西游记》中的历史故事是何种关系?这是我们需要去破解的。我们注意到此前杨国学先生已经提出了“前《西游记》文化”和“后《西游记》文化”的概念,对于我们理解这种关系是一个较好的切入口,但在中国古代,书写叙事与景观附会的关系的实际情况可能要比杨先生谈到的复杂得多。
现在看来,要搞清楚这些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在中国古代,历史叙事、文学叙事、景观附会之间的关系。其实,在中国古代一直有两种历史存在,一种是作为科学的历史,一种是作为文化的历史,有时两种历史是难以区分出来的。这里,我们需要先将《西游记》故事的地域原型与历史叙事、文学叙事和景观附会的关系作一番具体梳理,以此为案例分析文本叙事与景观附会关系的互动机理,讨论景观附会中历史地域原型的流变,总结中国古代作为科学的历史与作为文化的历史的关系。
蓝勇编著《中国历史地理》
一、《西游记》中“流沙河”的历史地域原型
我们知道,《西游记》第二十二回“八戒大战流沙河”中谈到在黄风岭流沙河边的石碑上有“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十个字。在明代杨致和《西游记传》“唐僧收伏沙悟净”中也谈到“又见岸边有石碑,横纂‘八百流沙河,三千弱水深’”。历史上与这个故事有关的流沙河地名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今四川汉源县的流沙河,一个是今新疆吐鲁番境内的流沙河。
首先,今汉源县的流沙河得名于何时呢?据宋代《太平寰宇记》《方舆胜览》等文献记载,当时今天的流沙河仍叫汉水,并没有流沙河之名。如《太平寰宇记》卷七七《黎州》:“汉水,在县西一百二十里,从和姑镇山谷中经县界至通望县入大渡河,不通舟船,每至春冬,有瘴气生,中人为虐疾。”再如《方舆胜览》卷五六《黎州》:“汉水,发源自飞越岭,寰宇记云:在汉源县西百二十里,地名通望,合入大渡河,夏秋常有瘴气,中人为虐疾。”我们注意到《方舆胜览》主要是沿袭《太平寰宇记》的记载,也无流沙河之称,可见宋代仍无流沙河之名。但到明景泰《寰宇通志》、天顺年间《大明一统志》和万历、嘉靖《四川总志》等记载中,汉源县的汉水开始有了流沙河之名的记载。如《寰宇通志》卷七〇:“黎州汉水,源出飞越岭,流经城南二十里,东流入岷江,一名流沙河。”《大明一统志》卷七三《黎州安抚司》:“汉水,源出飞越山,流经城南二十里,东流入岷江,一名流沙河。”正德《四川志》卷二四《黎州安抚司》:“汉水,源出飞越山,流经城南二十里,东流入岷,一名流沙河江。”嘉靖《四川总志》卷一五《黎州安抚司》:“汉水,源出飞越山,流经城南二十里,东流入岷江,一名流沙河。”总的来看,明代文献中汉源汉水已经有流沙河之名了。不过,单纯看这些历史叙事的文献中并没有将流沙河与唐僧取经联系在一起。
《西游记传》
其实,西北地区的流沙河记载也肇源于明代,如永乐年间陈诚《西域番国志》记载:“出川至流沙河,河上有小冈,云风卷流沙所积。道北有山,清红如火,名曰火焰山。”陈诚《西域行程记》也记载:“道北山青红如火焰,名火焰山。道南有沙冈,云皆风卷浮沙积起,中有溪河一派,名流沙河,约有九十里,至鲁陈城。”嘉靖年间李日华《六研斋笔记》卷二记载:“(高昌)东行三千里至流沙河,即沙漠碛是也。”万历年间《图书编》卷五一:“(鲁陈)出川西行至流沙河,河上有小冈,云风卷浮沙丘所积,道北火焰山,色赤如火,城方二三里。”万历年间《咸宾录》:“(鲁陈)西行出流沙,河北出火焰山,山色如火,气候和暖。”万历年间何乔远《名山藏》:“出大川渡流沙河,有山青红如火焰。”同样,明代文献中对西北流沙河的记述也没有与唐僧取经直接联系起来。不过,在时间上西北地区的流沙河出现的时间要比西南地区更早一些,当然从表述上看这个西北的流沙河是河流还是流沙还游离不定。
中国西北与西南的流沙河地名均最早出现在明代文献之中,有对三种历史地域的重塑可能。一可能是对上古《尚书·禹贡》中“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历史记忆与当时环境感应的命名表述,这里谈到远古时期的流沙,并没有具体的地望可指。一可能是对《大唐西域记》中《大流沙及以东行路》中“从此东行入大流沙,沙则流漫,聚散随风”的大流沙(今塔克拉玛干沙漠)后代重新现实命名。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对《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古沙河(莫贺延碛)的重新塑造,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记载“沙河阻远”、“从此已去,即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 、“至沙河间”。这里的沙河本是指狭长的莫贺延碛,今位于罗布泊和玉门关之间,称“哈顺戈壁”,只是后人将本是指狭长戈壁演义成一条可能在当时并无名称的河流上。显然,明代文献中有一个将西北地区远古不能确指的流沙、唐代大流沙沙漠、沙河戈壁荒漠演变成流沙河河流的过程。在近代,西北地区甘肃流经张掖、临泽、高台的黑河和在临泽县的大沙河、酒泉市清水镇的白沙河也有流沙河之称,但出现时间较晚,命名的原因待考。另称云南西双版纳也有流沙河的地名,起源可能也较晚。
《大唐西域记》
但很有意思的是历史文献中最早将流沙河附近与唐僧三藏取经牵扯在一起的却不是在中国西北,而是在中国西南四川汉源流沙河一带。早在宋代人们就将唐三藏取经的故事附会在汉源一带了,如在南宋《舆地纪胜》中就有记载:“宝盖山,在梵音水之东。”《蜀中广记》卷三五引《方舆胜览》佚文称:“有梵音水,亦云三藏至此,持梵音而水涌出,故名。水色如米潘而甘,在今南半舍。”为此,宋代冯时行在黎州还专门写有一诗名《题梵音水野亭》,收录在《缙云文集》中。另万历《四川总志》卷一八《黎州安抚司》:“梵音水,司治南一十五里,俗传唐朝三藏至此,持梵音而水涌出,故名。水色如米潘,味甘。宋政和间,太守宇文侯过而饮之曰佳泉也,易名粲玉泉。”也就是说北宋政和年间易名,显现这个故事可能早在北宋年间就存在了,在明代人们认知中也十分相信此说。直到现在,据《四川省汉源县地名录》记载这个梵音水,在今汉源县河南乡,今称观音水,至今相传唐僧取经东返时滴观音赠水成泉,1986年我在汉源县考察时曾发现遗址仍存,有具体景观可寻。又比如南宋《方舆胜览》卷五六《黎州》记载:“藜厅,在州治小厅之东隅,世传唐三藏师游西域,经行植梨杖于此,云他日州治在此。后果迁如师言。杖成株,高五十尺,围九十尺。余授诗:神僧曾西征,目览江山异。深林植杖黎,他日成州治。”《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卷中《黎州》下也记载:“藜厅,州治。”万历《四川总志》卷一八:“三藏黎,旧黎州治,世传唐三藏游西域,经行植梨杖于此,云他日州治在此。后果迁如其言。其后梨成株,高五十丈,围九尺末。天圣间,州治大火,人取其枝以接他枝。”从《四川总志》的记载来看,《方舆胜览》的围九十尺显然是围九尺之误。《大明一统志》也有类似的记载。也就是说,宋代黎州今四川汉源县一带,民间已经有较多的唐三藏取经的传说和遗迹存在了,并在明代一直流传。
我们注意到,元代李孝光《五峰集》卷九《次三衢守马昂书垒韵》中记载:“我垒何所有,而无白马骑。群书汗牛马,不涉流沙河。”已经将流沙河与佛教东来牵扯在一起来唱叹,只是没有谈及流沙河的具体地望。我们知道,南宋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代院本有《唐三藏》《蟠桃会》,元杂剧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大圣》,明代有朱鼎臣的《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杨致和《西游记传》等,这些都是《西游记》的创作基础话本,但宋元话本中并没有涉及上面谈的流沙河、火焰山、晒经石等故事。我们发现也只是在明代话本中才涉及流沙河、通天河、火焰山的故事,如明万历年间吴承恩《西游记》和杨致和《西游记传》中已经将西北流沙河融入西游记的收沙僧的故事之中。
看来,不论是吴承恩直接传承杨致和的故事或是杨致和缩写吴承恩的故事,都可能受宋元明文献中四川汉源流沙河与三藏传说的影响,也可能受明代文献中将西北地区唐代大流沙沙漠、沙河戈壁荒漠演变成流沙河河流的影响。如果仅从这个过程来说,显现了历史文献对文学叙事的影响,但历史文献中的许多记载不过也是一种作为文化的历史文本化的结果。
吴承恩像
二、《西游记》中火焰山的历史地域原型
《西游记》第五十九回中“唐三藏路阻火焰山,孙行者一调芭蕉扇”开始,一共三回都是孙行者三次调芭蕉扇的故事。一般人们认为这个故事原型目前最早见于元末明初的戏曲昆曲折子中,称:“保护大唐师父往西天取经,路过此间,只见火焰冲天,有八百余里,问及土人,说此乃火焰山,若要过此山,须向翠云峰芭蕉洞铁扇公主借她的芭蕉扇,扇灭此火方能过。”然而,我们发现这些昆曲折子戏虽然传为元代吴昌龄所作,但留传下来的戏本历代可能多有增补,现在我们发现的唱词和道白中反而是多有近百年来的语言味道,昆曲可能存在后来据吴承恩《西游记》故事增补的可能。所以,我们还不敢断定这些戏曲中火焰山故事在元末明初就已经成型。但是,这个故事在明代的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中已经有“忽至火焰山”的表述,只是只有孙行者一拐芭蕉扇的故事。另杨致和《西游记传》在“显圣弥勒佛收妖”中谈到“忽至火焰山”,也只有孙行者一拐芭蕉扇的故事。当然,吴承恩《西游记》出现前并没有后来《西游记》中的三借芭蕉扇的故事,三借芭蕉扇是吴承恩的原创。
从历史地域的来源看,流沙河往往与火焰山的历史来源相关相近。据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二《大流沙及以东行路》记载:“从此东行入大流沙,沙则流漫,聚散随风,人行无迹,遂多迷路,四远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来者聚遗骸以记之,乏水草,多热风,风起则人畜昏迷,因以成疾。”另慧立、彦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也记载:“(尼壤城)又从此东放流沙,风动沙流,地无水草,多热毒,鬼魅之患。”实际上这里记载“多热风”“多热毒”的环境背景是后人命名火焰山、火山、火州的历史环境因素。我们发现,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岑参在《使交河郡》中写道“暮投交河城,火山赤崔巍。九月尚淌汗,炎风吹沙埃。何事阴阳工,不遣雨雪来”。另一首《经火山》诗更是直接称“火山今始见,突兀蒲昌东。赤焰烧虞云,炎氛蒸塞空。不知阴阳炭,何独燃此中。我来严冬时,山下多炎风。人马尽流汗,孰知造化功”。看来唐代吐鲁番一带已经有火山的称呼。所以,元代设置哈剌火州,明代称火州、和卓。
明代文献中对西北火焰山与流沙河的记载表明两者是在一起的,如明代陈诚《西域番国志》记载:“出川至流沙河,河上有小冈,云风卷流沙所积。道北有山,清红如火,名曰火焰山。”《咸宾录》也记载:“(鲁陈)西行出流沙,河北出火焰山,山色如火,气候和暖。”何乔远《名山藏》记载:“出大川渡流沙河,有山青红如火焰,山下城屹然,广二三里,即鲁陈城。”
不过,有的明清文献往往将火焰山与中古时期的赤石山联系起来,如《读史方舆纪要》记载:“火焰山,在柳陈城东,连亘火州,宋史:‘北庭北山中出硇砂’,山中当有烟气涌起,无云雾,至夕光焰若炬火,照见禽鼠皆赤。或即此山也。”清代祁韵士《西域释地》称:“火山,在城东肃州志载作火焰山,自吐鲁番东至喀喇和卓诸回城,山皆赤色如火焰形,故明时有火州之名。按《魏书》云高昌郡东西三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国有八城,多石碛,气候温暖,北有赤石山,所载与今正合。”《钦定续通典》卷一四九:“火州,地多山青,若火故名。”显然,以上文献认为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赤石山即后来明清时期的火焰山,实则是错误的。首先,据《魏书》卷一〇一、《隋书》卷八三、《册府元龟》卷九六一、《文献通考》卷三三六等有“北有赤石山”的记载,与今天火焰山在吐鲁番以东不合。据明代《寰宇通志》卷一一七《火州》记载:“火焰山,在柳陈城东连亘火州,山色皆如火因名”,但同时记载:“赤石山,在土鲁番西北,峰峦秀美,石多赤色”。《寰宇通志》卷一一七《火州》,玄览堂丛书续集本。《大明一统志》卷八九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如称:“火焰山,在柳陈城东连亘火州,宋史云北庭北山中出硇砂,山中当有烟雾涌起,无云雾,至夕火焰若炬火照见,禽鼠皆赤采者,疑即此。”“赤石山,在土鲁番西北,峰峦秀美,石多赤色”。所以,明代赤石山与火焰山完全是两座不同的山。在清代的大多数文献中,火焰山与赤石山也是分开的,如嘉庆《回疆通志》卷一一:“火焰山,自喀刺和卓历吐鲁番喀刺沙尔库车北一带,山皆赤色,如火焰形,其中产铜砂,常有烟雾涌起,至夕光焰照见,禽鸟皆成光彩。”不过,明清历史文献历史叙事中对西北火焰山的记载中并没有将其与唐僧取经联系起来。另还有甘肃张掖武当山到内蒙古马鬃山一带也有火焰山名,但出现时间应该较晚。张掖大佛寺中《西游记》连环画壁画中也有“路阻火焰山”画面,但也是出现在清代。将西北地区的火焰山与唐僧取经联系起来,在历史文献的历史叙事中也出现较晚,如清人袁栋《书隐丛说》中认为:“吐鲁番有火焰山……土人云,唐僧元奘西游过此,《西游记》火焰山事非无因也,而火焰山且不止一处也。”
《回疆通志》
在西南地区,也是在明代就开始出现火焰山的记载,天启《滇志》:“沿溪而上,十里升火焰山,其高三十里,峰回路转,陡险之处,翼以木栈。”《读史方舆纪要》中也记载云南元谋县西北又有火焰山。清代雍正《云南通志》:“火焰山,在城北一百二十里,高可三十里,峰回路转,陡绝崎岖。”同治《会理州志》卷一《山川》:“火焰山,一百八十里,为川南丛险要隘。”在明代《谭襄敏奏议》卷四《剿贼计安地方疏》中也有这个火焰山记载。不过,明清文献中并没有将这个火焰山与唐僧取经联系起来,我们并不知此处火焰山与唐僧取经故事联系在一起是何时?1986年我在云南元谋县考察,从江边渡金沙江到姜驿,翻越火焰山,当地人传说就是唐僧师徒取经经过的火焰山,上面还雕刻有唐僧师徒取经场面的石龛。但2016年底我们再次考察时,已经发现取经的石龛不复存在了。
从以上可以看出,历史文献历史叙事中将火焰山与唐朝三藏取经联系在一起,不论西北或是西南,相对较晚,反而是历史文献的文学叙事的戏剧、话本中早在明代就将火焰山与唐僧取经联系起来了。
显然,在明清时期文献的历史叙事中,西北和西南的火焰山都见于记载了,但将其与唐僧取经联系起来首先是在明代文学叙事的戏曲、话本之中,并不是在历史文献的历史叙事和口述传说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讲,今天西北和西南地区的火焰山与唐僧取经联系起来,可能反而是受《西游记》等明清戏剧话本、小说演义的影响而重新附会到景观上的。这个案例反而显现了文学叙事对历史文献叙事的影响也是存在的。
玄奘负笈图
三、《西游记》中通天河与晒经石的历史地域原型
《西游记》第四十七、四十八回中,唐僧遇阻通天河,夜宿陈家村,巧遇灵感大王祭祀,孙悟空与其斗法通天河,救得童男童女,后得老龟相助,渡过通天河。《西游记》第九十九回中又记载了唐僧取经回程中在通天河过渡覆舟经书打湿而晒经的故事。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传》中并没有一点通天河故事的影子,但杨致和《西游记传》中有类似的唐僧收妖过通天河故事之说。
在历史文献的历史叙事中通天河之名起源较早,宋明时期就有通天河的记载,但地望并不能确定。在清代的文献中,通天河的地望有时是指一个大的范围,即在西北青海、甘肃、新疆一带,主要存在三个称通天河的河流:一是在今新疆自治区和静县的开都河、海都河,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一:“海都河……谚曰通天河。”愈浩《西域考古录》卷一一:“开都河,亦曰海都,土人呼为通天河。”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四:“开都河,或作海都,回语谓曲折也,俗称通天河,水经注谓之敦甍水。”二是指今青海省玛多县黄河上的通天河,愈浩《西域考古录》卷一六:“由星宿海渡通天河,西南行有河不深广,策马可渡。”康敷镕《青海志》卷一:“黄河星宿海迤南通天河,与格尔吉河上下一带东接四川西南,与西藏所属土司界接壤。”三是指金沙江上游的青海省玉树县一带的通天河,黄沛翘《西藏图考》卷二:“木鲁乌苏即木鲁河,华言通天河,乃西宁西藏之界。”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四“渡木鲁乌素河,俗呼通天河。”姚莹《康纪行》卷九:“木鲁乌苏河,番人又名通天河,即大金沙江上流也。”嘉庆《卫藏通志》卷四:“一日始至木鲁乌苏,名通天河,乃金沙江之源也。”特别是在《大清实录》《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有关大量通天河的记载,主要是特指青海、四川交界的通天河,今长江源头的通天河一带。如《清德宗实录》卷三四四记载:“通天河,系四川地界……通天河距四川穷远,去西宁仅二十余里。”《清宣宗实录》卷二九五:“上年西藏贡使堪布等行至通天河岐米加纳、并托逊诺尔地方,被四川所属格尔次暨果洛克番两次抢劫。”又卷二五〇:“其失事之区,每在西宁所辖通天河一带。”民国《玉树县志稿》卷三记载:“金沙江上游,蒙名乌鲁木苏河,番名州曲,普通名通天河。”这里的通天河主要是指今青海玉树地区的金沙江段,在明代一般称毕力术江。
《卫藏通志》
总的来看,通天河在宋元文献历史叙事出现后,地望指向并不明确,到了明代戏曲、话本中出现的通天河也没有具体地望可指。只是到了清代历史文献历史叙事中才开始有特指。不过,不论是历史文献历史叙事中,还是戏曲、话本的文学叙事中,并没有记载今西南丝路上有通天河存在。但是,与通天河有关的晒经关、晒经石的历史根源却在西南地区源远流长,故迹众多。
今天来看,取经途中晒经的故事原型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
《大唐西域记》卷三《迦湿弥罗国》:
沙门至国西界,渡一驶河,济乎中流,船将覆没,同舟之人互相谓曰“今此船覆,祸是沙门,沙门必有如来舍利,诸龙利之”,船主检验,果得佛牙。
这段故事倒是在慧立、彦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的记载中更为成型:
(迦湿弥罗国)又西北行三日至信度大河,河广五六里,经象及同侣人并坐船而进,法师乘象涉渡。时遗一人在船看守经及印度诸异华种,将至中流,忽然风波乱起,摇动船舫,数将覆没,守经者惶惧堕水,众人共救得出,遂失五十夹经本及华种等,自余仅得保全。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不过,这里虽然记载了过河经书损失之事,但在唐宋元时期的文献中并没有晒经石的有关记载。目前,明中叶《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中的今四川汉源县晒经石记载是最早的有关记载了。明景泰年间编的《寰宇通志》卷七〇《四川行都司》称:“晒经石,在越嶲卫城北三十里晒经关旁,相传唐玄奘三藏禅师晒经于此。”同时在卷七〇《黎州安抚司》梵音水条下记载:“(黎州粲玉)泉南数十步,有二巨石,一号袈裟石,五色相间;一号晒经石,皆三藏遗迹。”又如明天顺年间编的《大明一统志》卷七三《四川行都指挥使司》:“晒经石,在越嶲卫城北三十里晒经关旁,相传唐玄奘三藏禅师晒经于此。”万历《广舆记》也记载:“晒经石,越嶲卫,相传唐玄奘三藏禅师晒经于此。”在许多地方文献中也有类似记载,如正德《四川志》卷二四《四川行都司》山川:“晒经山,在(越)治北二十里,相传谓唐三藏曾晒经于此。”另在津梁处记载有:“晒经关,在治北百八十里。”嘉靖《四川总志》卷一五《四川行都司》记载:“晒经石,越嶲治北三十里晒经关旁,相传唐三藏晒经于此。”万历《四川总志》卷一八也有类似的记载。明末《蜀中广记》卷三四引《土夷考》:“李子坪七里至晒经关。志云,晒经关在越嶲卫东三百里,高岭山关旁广石,即三藏法师晒经处,未详。”《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四:“晒经关,卫东北三百里有晒经山。山岭高峻,四声关其上,关旁有广石,相传唐僧三藏晒经处也。”明代万历陈耀文《天中记》引《地志》:“(黎州玉粲)泉南数十步,有二巨石,一号袈裟石,五色相间;一号晒经石,皆三藏遗迹。”
清代以来有关晒经石的记载越来越多。雍正《四川通志》卷二七:“晒经石,在卫北二百里晒经关旁,相传唐三藏晒经于此。”嘉庆《宁远府志》卷一一越嶲厅有晒经关,咸丰《邛嶲野录》卷五:“晒经关,旧志在卫北一百九十里,新志在厅东北一百里晒经山,峰峦高峻,置关其上……晒经山,新《通志》在厅东北,山有晒经石因名,《明统志》在厅晒经关旁,相传唐元装(玄奘)三藏禅师晒经于此。”总的来看,明清时期文献中有关晒经石的记载大同小异,都深信与唐玄奘晒经有关。
光绪《越嶲厅全志》卷二之四《山川》:“晒经关顶,治北三百六十里,南北悬亘,各十余里,山形浑厚,顶一巨石,即晒经文石,十景之一,上修关帝庙,唐国师有:狮象前面走,文星守水口。若问真龙穴,晒经关下有。”光绪《越嶲厅全志》卷二之九《古迹》:“晒经石,治北二百六十里,旧志载唐三藏西天请经回晒于此,山有巨石,即晒经处,地遂以石名,今建关帝庙于上。”从这里可看出,清末开始在晒经石上建有关帝庙。这个关帝庙在《虚云和尚自述年谱》中有明确记载:“过流沙河,适水涨……天寒下雨,行抵晒经关,旅店不宿僧人。街外有一庙,一僧住守,求宿再三,不许。”早在1986年我在汉源晒经山实地考察就发现,晒经石仍然存在,但石上的关帝庙已经早已没有了踪影。应该看到,早在明代,就有人对晒经石的背景提出了疑问。明代顾汝学《晒经石》诗:“一片晒经石,云是唐僧留;何人能说法,致使石点头。”据咸丰《邛嶲野录》卷五记载晒经石上有一明代石碑,碑上刻的就是顾汝学的这首诗。据光绪年间顾汝玉《过晒经山观唐三藏晒经石》诗记载当时还竖立有木栅护碑,但我们两次考察都不见碑的踪影。曹学佺对唐僧玄奘到过汉源提出了怀疑,只是没有提出怀疑的原因。后来,清代咸丰《邛嶲野录》卷五谈到晒经石时,也引用了《蜀中广记》的这则记载。另清代许亮卿《步晒经石原韵》也感叹到:“佛于元奘去,诗人顾况留。墨光兴禅迹,千载晒关头。宋元明几载,光怪久淹留。笑尔真顽性,多年不点头。”
当然,在中国西北地区也出现过所谓通天河和晒经台故迹,如杨国学等人谈到的甘肃天水甘棠、夏河县大夏河畔、临泽县、高台县、青海玉树县通天河大桥和新疆和静县等就有相关传说,但传说普遍出现较晚,大多没有进入文本书写的历史叙事中,大多连民国的县志都没有记载,故可能更多是“后西游文化”景观。具体如甘肃民间认为洪武年间设立的高台县,传说是因为境内有唐僧玄奘过河将经书打湿而放在高台晒放而来。我们发现,虽然记载明洪武五年设立高台站,但正史中并无这种得名的传说。另在甘肃嘉峪关附近,有一块洁白的晾经石,传说是玄奘晾经的地方。再如新疆和静县开都河岸晒经岛和青海玉树县结古镇通天河畔的晒经石,都是认为唐三藏取经所留。整体西北地区有关唐僧晒经的故事与附会景观反而很少,并大多不见于明清地理文献中,且出现的时代较晚,可能更多是后西游记文化。
总地来看,虽然在中国西北地区通天河的地名出现较早,但有特指出现在清代,并没有与唐僧取经联系起来,更没有晒经石的传说和遗存,反而是在西南地区四川汉源县一带早在明前期就出现唐僧取经的晒经石传说和遗迹,在明代景泰、天顺、正德年间的文献中就出现了汉源晒经石和唐僧取经的传说记载和遗迹,但现在《西游记》版本年代多是在嘉靖、万历年间出现的,才有有关晒经石与唐僧取经的故事。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西南丝路上的这些通天河和晒经石历史传说和遗迹对吴承恩创作《西游记》是有较大影响的。
陈耀文著《天中记》
四、《西游记》中白龙马与白马护经的历史地域原型
《西游记》第二十三回中有关于白龙马的故事,如果我们今天要研究这个白龙马的历史原型,可能要从汉代的白马驮经的历史说起。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四:“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佛教入中国之始。寺在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帝梦金神,长丈六,项背日月光明。胡神号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经像焉。时以白马负经而来,因以为名。”可以说,白马从一开始就与佛教东来有较大的关系。另《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有这样的记载:“明日日欲下,遂入草间,须臾彼胡更与一胡老翁乘一瘦老赤马相逐而至……胡翁曰:‘师必去,可乘我马。此马往返伊吾已有十五度,健而知道。师马少,不堪远涉。’法师乃窃念在长安将发志西方日,有术人何弘达者,诵咒占观,多有所中。法师令占行事,达曰:‘师得去。去状似乘一老赤瘦马,漆鞍桥前有铁。’既睹所乘马瘦赤,漆鞍有铁,与何言合,心以为当,遂即换马。”这是老瘦马的典故,显现在唐僧取经过程中马的运输作用。到了宋代志磐《佛祖统记》叙述了“祗罗国王赐(玄奘)青象、白马,以助驮载”的历史,明确记载了有白马运输的历史。
在西北地区,早在西夏时期安西榆林窟中的壁画就出现唐僧取经的白马形象,另山西稷山县青龙寺壁画中也有白马的形象,一般认为也比《西游记》早,应该都是属于“前《西游记》文化”范围内的原型。但张掖佛寺《西游记》连环画中的白马形象出现得较晚,一般认为是在清代才出现,应该是“后《西游记》文化”的产物。
《洛阳伽蓝记》
从白马到白龙马的嬗变是在文学叙事中通过话本、戏剧完成的。南宋时期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记载:“女王遂取夜明珠五颗、白马一疋,赠与和尚前去使用。”这里仅是谈白马,并无白龙马的身影。但据传元杨景贤《西游记杂剧》木叉售马的故事有南海火龙三太子化为白马的故事。于是乎,在吴承恩的《西游记》中出现了白马演义成白龙马的故事。不过,白龙马名称在明代众多小说演义中都有存在,也大多是在万历年间出现的,如明万历诸圣邻《大唐秦王词话》、万历年间许仲琳《封神演义》、明末诸人获《隋唐演义》、清代钱彩《说岳全传》中都有白龙马的身影,万历年间成书的《西游记》中的白龙马形象与他们关系一时还无法说清。
但在历史文献的历史叙事记载中,今四川汉源县一带早在明代前期就有将白马驮经的历史附会成白马和尚山与白马护经堡之说,并逐渐与唐僧取经牵扯到一起了。如天顺年间《大明一统志》卷七三:“马跑泉,在和尚山,俗传肉齿和尚创奄山上,乘白马至山半,马渴而跑地,泉为之涌。”万历《四川总志》卷一八也记载:“马跑泉,在和尚山,俗传肉齿和尚乘白马至山半,马渴跑地,泉为之出。”在《蜀中广记》卷三四中记载晒经关附近就有白马堡,到了清代开始演变成白马护经堡,如《大清一统志》卷四〇一:“白马堡,在越嶲厅东北一百九十里,东去晒经关十里。”光绪《越嶲厅全志》卷二之六也记载:“白马堡,治北二百五十里,在晒经关北十里,有营兵塘房。”据《四川省汉源县地名录》记载此地名是因唐僧返唐经过此遇雨,白龙马奋起护经而得名。1986年我在汉源考察时,在晒经山下发现白马堡的地方,地名仍存,惜堡已经不存。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总地来看,历史叙事中很早就有白马的历史与传说,元明以来在文学叙事中开始将白马演义成白龙马的传说,而在历史叙事与民间景观附会中,明代前期以来在西南地区白马同时也演变成白马和尚山与白马护经的故事。在这一点上,如果从时间上来看,历史叙事、文学叙事、景观附会之间互有影响,《西游记》的白马和白龙马故事,可能受元代以来话本戏剧中白龙马故事的影响,也同时有可能受历史叙事和景观附会的白马护经的影响。
另外,在《西游记》第五十四回“法性西来逢女国,心猿定计脱烟花”中记载了西北的女国,这个女国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早就有原型存在。具体地讲,在历史研究的语境和文学创作的语境中都有女人国的话语。就历史研究的语境来看,中国古代有关女国的记载很早就出现了,如《山海经》《淮南子》《三国志》《后汉书》《异域志》《太平广记钞》等文献中都有记载,但所记女国地域众多,相当混乱。据石硕考证,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女国有两个,一个是在今川西高原,一个是在今葱岭之南。一般认为《隋书》《北史》首先记载了葱岭下的女国,后来《大唐西域记》《释迦方志》中也有记载,而川西高原还有一个女国,首见于《旧唐书·西南蛮传》中的东女国,据考证是早在唐人苏冕、崔铉《唐会要》之中就将许多葱岭南的女国资料误串到川西高原上的女国,后人又不断将其混乱搞在一起。在文学创作语境中的女国,早在宋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经过女人国处第十》中已经有记载了,但明代朱鼎臣的《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杨致和《西游记传》中并没有经过女人国的记载,所以,可能文学创作所依据的就是历史语境的女人国,只是历史研究所据拥有的文化背景不同,故创作中对此有所差异。吴承恩在撰《西游记》时正是依据自己对历史语境和文学创作语境中的女国的理解演义出来了女儿国。所以《西游记》中的女国主要是受汉唐历史语境的葱岭以南的东女国和文学语境的宋代女人国的影响而来。
五、兼论中国古代景观附会中的“地域泛化”与文本叙事
前面已经谈到在中国古史上有两种历史,一种是作为科学的历史,一种是作为文化的历史。正因此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叙事中,传说、神化往往杂糅其间,而文学叙事往往也受历史叙事的影响,以历史的大脉络为宏观主线去演义。其中作为文化的历史在中国民间下层社会中广泛流行,通过戏剧小说、景观附会、口述传说等形式扩大着作为科学的历史的社会影响程度,但也使一般人眼中的中国历史充满传奇和迷茫。
从玄奘《大唐西域记》和慧立、彦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流行以来,唐僧三藏取经的历史故事在中国流传较广,人们将唐僧三藏取经的故事往往附会在中国许多地区,融入自己的文学臆象,付入传奇和故事,一是通过文学叙事由话本、小说演义开来,一是直接附会在地面的山川、景观之上,一是通过口述传说在民间传播,一是景观附会和口述传说往往也会载入历史叙事的史书,特别是地理志之中,而这四者之间往往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糅合。前面我们谈到的有关流沙河、火焰山、通天河与晒经石、白龙马的故事,在历史叙事、文学叙事、现实景观、民间口述中往往都存在,只是时间或早或迟、内容或详或略。
《西游记》英文版
其实,在南北丝绸之路上还有许多有关唐僧三藏取经的故事附会,并没有在明清话本、戏曲之中,只是在历史文献历史叙事和民间口述、景观附会之中,如前面谈到的梵音水和黎州藜厅。
很有意思的是,南北丝绸之路的沿途,这类的记载和遗迹还十分多。如四川荥经县有晒经寺。明代云南大理就有晒经坡,见于倪辂《南诏野史》和嘉靖《大理府志》,据记载是由唐僧取经回国经过点苍山遇雨,打湿经书、晒经于坡而得名。另据明代《两浙轩续录》卷四记载楚雄无为寺也有晒经坡,为“世传唐朝高僧晒经处”。另云南祥云县有晒经坡,牟定县有晒经松,出现时间早晚都有。据明代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记载滇缅一带准古还有金塔大寺,相传为唐僧所寄宿,而都鲁濮水关有唐僧的晒经台,板古流沙河为唐僧取经故道等。《皇朝经世文编》卷一一八《工政》中记载缅甸温板又称流沙河,相传唐僧取经过此渡。其实,在中国西部其他地区有关唐僧取经的传说和遗迹都较多,如四川大邑县就有晒经寺,建于明代正统年间,旧传是唐僧取经中途遇雨打湿经书而晒经。四川江油也有晒经寺。在西北地区的晒经石就有6处之多,其中新疆1处、甘肃4处、青海1处,甘肃省张掖市童子寺出现了清代唐僧取经的壁画。
问题在于,我们明知唐朝玄奘取经是经过西北地区,并没有行经西南地区,又为何在宋元明清有如此多的唐三藏西天取经的故事流传在西南丝绸之路上呢?其实,这种现象是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相似历史背景下景观附会中存在的“地域泛化”的杂糅有关,而且这种“地域泛化”现象往往是与“情节神化”相同步,显现中国古代景观附会中“地域泛化”和“情节神化”的两个基本特征。
《大理府志》
(一)相似历史背景下的“地域泛化”杂糅——西南丝路的佛教东传与唐僧文化遗迹
这里我们所指的所谓“地域泛化”,是指中国古代在某种传统和背景的影响下,人们将历史上本来有特定具体地域的事件、人物附会在其他有相似自然和文化背景的地域上的行为。这里的“相似自然和人文背景”表明中国古史上的景观附会虽然往往是无中生有的,但多多少少都会是在自然相同、区位相近、历史相似、文化相近的背景影响下产生的。历史上西南丝绸之路唐僧文化景观附会的产生,自然是以西南丝绸之路与西北丝绸之路历史上同为佛教文化传播通道的历史相似为基础的。
从佛学西来的历史过程考察来看,以前人们对西北白马驮经为佛教东传之始的历史坚信不疑。近几十年来,阮春荣、何志国等学者提出佛学东来存在一个南传佛教系统,甚至早于西北地区从缅印、云南传入中国,主要根据是在西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发现了许多汉代的摇钱树、佛像、白毫相、梵文符号等遗物,从风格上与北方的犍陀罗风格有异。当然,对此学术界还有许多分歧和争论。
不过,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确有许多僧人开始来往于西南丝绸之路上求法传教,这是不争的事实。如道宣《释伽方志》卷下记载:“宋元嘉中,冀州沙门惠睿游蜀之西界,至于南天竺,晓方俗音义,还庐山,又入关,又返江南。”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也记载:“有一故寺,但有砖基,厥号支那寺,古老相传云是昔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僧所造。于是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牱道而出,向白莫诃菩提礼拜,王见敬重,遂施此地,以充停息,给大村封二十四所。”另慧皎《高僧传》卷七也有类似的记载。
义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到了唐代,天竺僧人取这条通道到蜀地更是众多。孙光宪《北梦琐言》:“先是,唐咸通中,有天竺三藏僧经过成都,晓五天胡语,通大小乘经律论,以北天竺与云南接境,欲假途而还,为蜀察事者识之,系之于成都府。”这则记载在《蜀中广记》中也谈到。志磐《佛祖统记》卷四三又记载:“(贞明)四年,西天竺三藏钵恒罗至蜀,自言从摩伽陀国至成都益州,途经九万九千三百八十里,时蜀主王建光元元年也。”唐代也有许多中国僧人取这条通道到天竺。据梁启超统计,南北朝隋唐时期留学印度的中国僧人中有九分之一都是取这条通道的,故僧人对这条通道多有记载,如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从那烂陀东行五百驿,皆名东裔。乃至尽穷,有大黑山,计当吐蕃南畔。传云蜀川南行一月余,便达斯岭。”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〇《迦摩缕波国》:“此国东,山阜连接,无大国都,境接西南夷,故其人类蛮獠矣。详问土俗,可两月行入蜀西南境。”释慧林《一切经音义》卷八一:“说此往五天(竺)路径,若从蜀川南出,经余姚、越嶲、不喜、永昌等邑,古号哀牢王……西过此蛮界即入吐番国之南界,西越数重高山峻岭,涉历川谷,凡经三数千里,过吐蕃界,更度雪山南脚,即入东天竺东南界伽摩缕波国……是大唐与五天(竺)陆路之捷径也。”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志磐《佛祖统纪》卷三二、释道宣《法苑珠林》卷二二、道宣《释迦方志》卷下。
可以说,宋明以来西南丝绸之路上有如此多的僧人故事传说、遗迹,自然是有其南北朝隋唐真实的佛教传播历史作为背景的。只是宋代由于宋挥玉斧,以大渡河为界,不与外域往来,宋代僧人往返此道由此大减。对于宋人来说,一方面对于这条通道开始生疏起来,知晓不多;一方面,以前又确有众多僧人来往于此道,留下片片鸿迹。所以,在迷惑朦胧的地理认知下,受“地域泛化”与“情节神化”传统的双重影响,西南丝路上许多唐僧三藏取经的记载和遗迹便不断出现。
志磐著《佛祖统纪》
(二)“地域泛化”与“情节神化”的杂糅——唐僧文化遗迹与历史上的景观附会现象
前面谈到中国古代景观附会中有“地域泛化”和“情节神化”两个基本特征,其中“地域泛化”的出现一是受传统乡情左右下的理想寄托的影响,二是受中国古代民间地理空间认知不足的局限的影响;而“情节神化”的出现往往一是受中国古代民间神化张扬夸大习性的影响,二是客观上受民间历史名物知识缺乏缺陷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前贤信仰十分发达,黄帝、大禹、二郎、孔明、关公、山谷、东坡遗迹遍地开花,呈现为将传说人物和历史人物附会在乡土景观上,形成历史文化的景观附会。可以说,历史文化的景观附会,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特殊的现象,如历史上黄帝陵、涂山、二郎庙、武侯祠、关公庙、涪翁亭、东坡庙,大多数不过是乡人对前贤仰慕以寄甘棠之志的一种景观附会,以此来寄托乡人的理想诉求。所以,遍布中国的唐僧三藏的遗址也多是这类景观。我们自然可以看到,出于知识的局限和乡情的因素,许多传说、故事本身与地域事实、名物相去甚远,有的谬误百出,有的荒诞不经。
具体到唐僧取经的历史和故事来看,我们知道,佛教东来的中国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逐渐向世俗化发展的过程,民间百姓真正对佛教深刻教义、名物上了解的人并不多。如将唐僧、三藏这种本来是对僧人的通称误为特指唐僧三藏玄奘、国师,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对此,早在明代《蜀中广记》中就认为造成这种误会的根源是人们将唐僧三藏误认为玄奘的特指,明代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三五在谈到藜厅、梵音水均为唐三藏所遗时称:“按玄奘西域记取经经由凉州出塞,似未入蜀,而三藏者乃僧之通称也。孙光宪《(北梦)琐言》云,唐咸通中有天竺三藏僧经过成都,晓五天胡语,通大小乘经律论,以北天竺与云南接境,欲假途而还,为蜀察事者识之,系之于成都府。其得所记朝廷功第文字,盖曾入内通场者,或即其人耶。”所以,上面许多文献中的三藏、唐僧本是对唐代僧人的一种泛称,并非特指玄奘,但却被许多人用于特指。同时,我们前面谈到北宋时期西南地区有关唐僧取经的记载和遗迹很少,只是到了南宋才开始有记载,这会不会是南宋只拥有半壁河山,南宋民间对西北地区知识缺乏了解所致。南宋至明末以来关于唐僧取经的梵音水、藜厅、晒经石、流沙河、白马护经堡传说和遗迹,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南北混杂、真伪相兼演义发展的。在其间,可能难免有望文生义的附会。早在明代就有人指出黎杖的故事“恐非实事”,认为“古称黎杖,黎则菖蓿,养之历霜雪,经一二岁,其本修直生鬼面可杖,取其轻而坚,非梨木也”。不过,我们发现在清代以前,多是谈唐僧、三藏、三藏师,还不敢直言是玄奘。到了吴承恩写《西游记》时,爱读怪书的吴氏的脑中充满了南宋以来南北的种种演义,他将其提炼升华,融入了《西游记》之中。而《西游记》的广泛传播,更使民间对唐僧取经的传说与遗迹不断演义发展,融入了更多的多元文化的色彩,所以,清人可能也乐得直接称这些遗迹为玄奘、国师所遗了。这种附会显现了民间传说的随地随人而异,故事的随意性明显,如对于晒经的故事本身就出入较大,有的称是过河打湿经书,有的则称下雨打湿经书。至于“情节神化”也杂糅在这种“地域泛化”之中,如其中的宝盖山梵音水“持梵音而水涌出”、白马转变为白龙马、白马护经等情节,明显就是一种“地域泛化”过程中的“情节神化”现象。
孙光宪著《北梦琐言》
(三)历史与文化之间——景观附会、口述传说与文本历史叙事、文学叙事的关系
从学理上来看,中国古代的景观附会、口述传说与历史上的历史叙事文本、文学叙事文本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这里文学叙事的戏曲话本、小说演义所起的作用相当特别,一方面这些戏曲话本、小说演义撰写过程中往往会夹杂一些以往的口述传说和景观传说,一方面这些戏曲话本、小说演义形成后也会附会到景观上,形成新的文化景观。同时,历史叙事的史书往往兼糅传说,不断对文学叙事中戏曲话本、小说演义产生影响,也直接会形成景观附会。
就《西游记》的创作来看,吴承恩等人以玄奘《大唐西域记》和慧立、彦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为源文化,做到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杂糅了民间之前的附会的有关唐代僧人的传说、景观,融入了自己的文学想象原创,形成了今天的《西游记》传奇故事。其中,历史文献中万历以前中国南北方已经存在的有关唐僧三藏玄奘取经的故事和附会景观对于《西游记》故事的形成影响可能较大,这包括真实的历史景观,如西北地区火州火山、西流沙、信度大河、白马等。但明万历以后《西游记》成型后对后世的文化影响也相当大,所以我们发现清代以来文献中的一些晒经石或留存的三藏景观也可能是从《西游记》的故事演化出来的。这种双向的互动,使中国古代民间作为科学的历史与作为文化的历史互相杂糅,在老百姓心中难以分出真假,往往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故事作为真实的历史来叙述。
即使在中国古代的许多志书中,许多学者在历史叙事中往往也杂糅传说,严谨的最多加上“据传”“俗传”“世传”,而不严谨的往往直接作为真实历史来表述,让我们一头雾水而难以分辨。所以,中国古代上的景观附会中的“地域泛化”往往也使历史形成许多地域迷案,不仅使社会上对历史产生种种误读,也使我们的史学工作者面对许多地域文化之争苦于难解,愁于无奈。所以,在作为科学的历史与作为文化的历史之间,我们历史学工作者如果不深入分析,有时也是难以区分的。
本文作者著《中国川菜史》
总的来看,这种历史叙事、文学叙事与景观附会、口述传说间可以形成以下关系:
图1
从图1的理论关系来看,宏观的历史事实我们称为“源文化”。这种“源文化”会直接繁衍出三种影响文本书写的“前文化”,即真实的历史景观、民间口述传说、民间附会景观,这三种“前文化”会影响到文本书写(文学叙事、历史叙事),而文学叙事、历史叙事又会产生新的景观附会和口述传说,形成“后文化”,反过来又会再影响文学叙事和历史叙事。所以,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叙事中,传说、故事往往杂糅其间,历史文献中往往会有传说、故事的成分,如众多典籍记载的流沙河;而文学叙事往往也受历史叙事的影响,也是以历史的大脉络为宏观主线去演义,作为一种文化的历史出现在历史长河之中。中国民间的景观附会更是相当复杂,历史发展中一般会有真实的景观遗存下来,如火州火山、大沙河,久之演变成为历史景观,但历史叙事往往也会在民间附会出景观,久之演变成为历史的文化景观,而文学叙事的故事往往也会附会在景观上,久之也会演变成文化的历史景观,如万历以后众多的火焰山、晒经寺。同时,民间的历史景观或是文化景观,可能也会反过来进入历史叙事或文学叙事之中,影响我们的历史书写和文学书写,如白马护经堡景观、晒经石等等。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作者:蓝勇,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编辑:若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