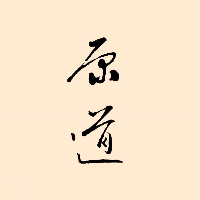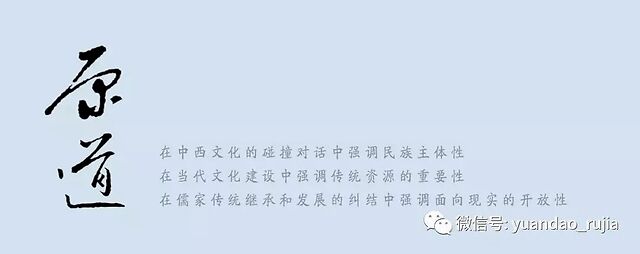
辨析“工夫”与“功夫”
汪 俐
(【宋】黄士毅编:《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内容提要: “工夫”与“功夫”是一对异体同义词,学术研究中经常可见两者混用的情况。研究“工夫”“功夫”的同异,要依照两者呈现出的不同词义状态,从日常义和义理义两个维度来做区分考察。
在日常义上,“ 功夫”出现时间早、语义丰富度和成熟度发展较快;“工夫”则体现出后来居上的发展态势。
在义理义上,经由对朱熹作品中二者从使用频次、用法到涵义种类及其偏向的对比分析,可以基本得出“工夫”“功夫”能够通用的结论。
基于“工夫”“功夫”在历史上的发展特点,本文主张:除“工夫”所独有的“工人、夫役”义以及“功夫”独有的“武术”义外,在表达相同涵义时,无论用哪一个“工(功)夫”都是对的,但用“工夫”比用“功夫”更好一些,尤其是研究义理层面的“工夫”与中国哲学范畴的“工夫论”的时候,应用“工夫”为宜。
关键词:工夫;功夫;日常义;义理义;朱熹;工夫论;
一、引 言
“工夫”和“功夫”从古到今一直为时人所混用。日常生活中,有“下工夫”“下功夫”的不同说法;学术研究中,也有“工夫论”“功夫论”的不同表达。
学界对于“工夫”和“功夫”是否有区别以及是否应对二者进行涵义和范围上的明确分界等问题,曾进行过一些讨论,但到目前为止尚无确切结论。
本 文拟通过对历史文本中出现的“工夫”“功夫”词条,从涵义到具体用法、再到整体的发展情况,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对比剖析与梳理,从而基本解决“工夫”“功夫”有何同异的问题。
同时希冀能以此为案例,对以后的学术规范和研究提供一些方法上的帮助与论据上的支持。
二、辨析的维度
通过对“工夫”“功夫”语义演变史的简单梳理,可以发现,“工夫”和“功夫”在语义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词义状态。
一种是单一涵义的日常义,如单指工程、工作;工人、夫役;本领、造诣;时间;努力;武术等;另一种则是复合了好几重涵义、用来描述义理范畴的义理义,如理学家所讲的“工夫”“功夫”,就是涵括了时间、空间、方法、境界四层内涵的义理概念。
因此,辨析两者用法、涵义的同异,要从日常义和义理义两 个维度来做 区分考察。
考察之前,须界定“工(功)夫”日常义和义理义分别涵盖的范畴,以便于材料的分类选择与研究。
日常义的描述对象比较具象,有“实”感,切近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无涉及义理层面的内容指向,具体到“工(功)夫”上,就包括早期就已形成的工人、夫役义;工程、工作义;本领、造诣义;时间义;努力义,还有明清之际引申出的武术义。
如果说日常义是概念,那么义理义则是指囊括相关义理内容的一整个概念范畴,其中所包含的层次、内容非常丰富,因此,同一个义理用语,在不同的语境中会体现出不同层面的涵义,以“工(功)夫”为例,它有时指整体的修炼过程,有时又指修炼过程中所用的方法、所耗费的时间与精力、所达到的人生境界。
(佛教修行)
按照“工(功)夫”义理化之后有涉及个人培壅以及自我实践的内容特点,可以认为,但凡与儒、释、道三家个体修炼相关的“工(功)夫”,才具有义理层面的涵义,其他包括儒家著述、佛道宗教典籍中不涉及个体修炼的日常用语的“工(功)夫”,都应划入日常义的范畴。
三、日常义辨析
“工夫”“功夫”的日常义发展贯穿整个古今,从魏晋之前的口语时期,到之后至今的文本时期,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发展情况都不一样,具体体现在二者在文献中的出现频次、具体用法、词义种类的丰富程度及演变等方面。
西汉时,“功夫”的用法就已出现,《广汉长王君治石路碑》中有“功夫九 百余日,成就通达”[1]一句,其中“功夫”指的是土木水利一类的工程。
魏晋时期,“功夫”已经为文献所广泛使用,并有了两种新的涵义:做一件事的过程中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经过努力积累而获得的某一方面的本领、能力、造诣。
这一时期,“工夫”也始见于文献中。值得注意的是,两个“工(功)夫”此时已有为同一文献使用的情况,比如道教典籍《抱朴子》,其中“工夫”和“功夫”分别出现两次。
现将有关例句摘录于下: ①“ 闻甲乙多弟子,至以百许,必当有异,便载驰兢逐,赴为相聚守之徒,妨工夫以崇重彼愚陋之人也。 ”[2]
②“既生值多难之运,乱靡有定,干戈戚扬,艺文不贵,徒消工夫,苦意极思,攻微索隐,竟不能禄在其中,免此垄亩。”[3]
③“或飞苍走黄于中原,或留盃觞以羹沸,或以美女荒沈丝竹,或沉沦绮纨,或控弦以弊筋骨,或博弈以弃功夫。”[4]
④“先所作子书内外篇,幸已用功夫,聊复撰次,以示将来云尔。”[5]
句①“工夫”应理解为时间与精力。句②“工夫”在被理解为时间、精力的基础上,按照后面突出主体努力程度的语境,应该更偏向精力层面。
句③“功夫”与句①“工夫”的语境、涵义完全一致。句④的“用功夫”与句②“工夫”的用法也基本一致,也是更多偏向描摹做事过程中所用的精力之多、努力程度之大。
由此可见,“工夫”“功夫”在《抱朴子》中,就用法而言,都是前接动词以构成短语的形式,“工夫”是“妨工夫”“徒消工夫”,“功夫”则是“弃功夫”“用功夫”;就涵义来说,也几无区别,都是指做一件事所耗费的时间和努力。
南北朝时,“工夫”在文本中出现仅有几例,涵义也仅限于“时间、努力”义这一种。而“功夫”的文例已非常之多,涵义上除了有上面所说的三种之外,还有从“时间、努力”义中分离出的单独的“时间”义出现。
因此,这一时期的“工夫”与“功夫”相比,无论在使用频次上,还是涵义的丰富度与具象度上,都远远不如。无怪乎有学者认为,“工夫”的出现,是由于古人懒写笔画,才将“功夫”的“功”简写为“工”。
唐代开始,“工夫”的涵义在种类和细致程度上都有很大发展。前朝就有的“时间、努力”义也同“功夫”一样,分离出了专指“时间”的涵义,诗人方干的诗集《玄英集》也讲“半日工夫斸小庭”[6],就是指“时间”的专门义。
《玄英集》中还有“要见工夫在笔端”[7]的诗句,此处“工夫”却是指另外一种涵义:(书画方面的)“本领、造诣”。而史部类文献主要反映了“工夫”的“工人、夫役”义,譬如《晋书·范宁传》“夺人居宅,工夫万计。”[8]
(王羲之《兰亭序》)
最后,还有从五代时一张雇工契上所写“工夫忽忙时”所反映出的与单字“工”同义的“工作、事务”义。“功夫”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发展出新涵义,而且自西汉时就有的“工程”义在此时已经鲜为提及,有了逐渐式微的趋势。
“功夫”的其余几种用法中,时人更偏好用到其中的“本领、造诣”义,来表示在文学、艺术方面所取得的高水平成就。
两相比较,除了“工”与“夫”结合而成的“工人、夫役”义为“工夫”独有的涵义,在其余四种“工夫”“功夫”共有的涵义(“时间、努力”义;“本领、造诣”义;“工程、工作”义;单独“时间”义)上,两个概念的使用情况区别不大,几乎可以通用。
宋代及以后,“工夫”在文献中的使用频次大大增加,涵义方面却无显著变化。历史上出现过的“工夫”的所有涵义,在这一时期都有所呈现,此时堪称“工夫”涵义的大全时期。
其中,儒家所讲的“工夫”,在表达“时间、精力总称”和“本领、造诣”的涵义时,已或多或少带上了义理色彩,故不列入日常义的讨论范围,只有表达单独的“时间”义时,才予以考虑其为日常义。
元明清之际,“工夫”成为所有部类文本中的高频词汇,内容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农业、文艺各个方面,而涵义还是上述五种,只是使用频次越来越高,成为常用词汇。
同期的“功夫”与之相比,在使用频次上远不如“工夫”。举一个例子,在中国基本古籍库的数据库里分别输入“工夫”和“功夫”词条,对从宋代到清代所有文献进行检索,出来的结果是“工夫”总共有29304条,而“功夫”是7462条,总数量大概只有“工夫”词条的四分之一左右。
至于涵义方面,除了没有“工夫”特有的“工人、夫役”义之外,其它四种涵义,都由“功夫”延续下来,内容上与“工夫”几无区别。除此之外,在晚清的兵书与武侠小说中,“功夫”还由“本领、造诣”引申出了一项新的特指涵义——“武术”义,就是描写棍棒拳法等武术招式及造诣成就。
“武术”义为“功夫”所独有,这一涵义发展到今天,在普及程度上超过了“功夫”的所有古义,以“中国功夫(Kongfu)”之名而为古今中外所熟知。
总的来说,“工夫”“功夫”的整体发展各有其特点。“功夫”在文本中出现的时间早,频次随着时代发展逐渐升高,用法的成熟度和语义种类的丰富度也发展得较为早和快,但整体的发展势头到了后期不如“工夫”。
而“工夫”的文本出现虽晚,初期的使用频次较“功夫”为低,用法和语义的发展也较“功夫”为晚和慢,但中后期发展起来则呈现出后劲足、势头猛的特点。 自宋代开始,“工夫”在使用频次和语用习惯上已大大超过“功夫”。
因而我们可以说,“工夫”的独有义是“工人、夫役”,“功夫”的独有义是“武术”,而当两者在表达同种涵义(总的“时间、努力”义;单独的“时间”义;“本领、造诣”义;“工程、工作”义)的时候,基本可以通用。
四、义理义辨析
两晋至唐,是“工(功)夫”义理化的初步阶段,此时在佛、道两教著述的带动与普及下,“工(功)夫”已经有了义理化的趋势。真正发展并完成“工(功)夫”概念的义理化,则是由宋代儒家实现的。
(一)两晋至唐
东晋时,一本道教修仙炼丹册子《铜符铁券》中,就同时采用“工夫”和“功夫”的用法,这两处“工(功)夫”已经开始初步具备义理倾向:
①“我将三段工夫指,片言无隐付降君。”[9]②“每一鼎之功夫,俱合天地日月、三才四时、五行六气、七政八卦、九宫十干、十二支二十四炁、七十二候二十八宿,万象生成。”[10]
结合前后文句来看,句①中 “三段工夫”并无明确所指,是对炼制丹药过程的一个整体描述。句②是写炼丹之鼎与放鼎之室的各种讲究,鼎室的置办达到一定条件后,每一鼎的“功夫”才能与天地日月等宇宙精华全部合宜,因此“功夫”指的是用鼎炼丹的过程。
(道士炼丹)
后者描述的对象较前者为具体,但在涵义上并无区别,都是指道教炼丹的过程。到了南北朝,“功夫”出现新的用法,即与道教话语诸如“真人”“神仙”等相结合,成为新的具有道教特色的复合词。
此时,“功夫”的涵义变成了道教修炼的最高目标——“真人”“神仙”所拥有的造诣与达成的境界。
至于唐代,在前朝已形成“造诣、境界”义的复合词的基础上,道教又将“工夫”“功夫”与本门的一些具体修炼方法相结合,使“工夫”和“功夫”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涵义——“方法”义。同时佛教兴盛,一些佛经中也用“工夫”“功夫”指代佛教的修行过程与境界。
由上可以看出,“工夫”与“功夫”是同时开始出现义理化倾向,最早是单词用法,涵义上是“过程”义,指道教修炼的过程。
后来,“功夫”先“工夫”一步,发展出了复合词的新用法,涵义上则是“境界”义,由日常义中的“本领、造诣”义衍化而来。
之后,二者以复合词的形式,同时发展出了新的涵义——“方法”义。在指代第一种涵义“过程”义的时候,“工夫”“功夫”出现的频次是一样的;而在指代第二种“境界”义和第三种“方法”义的时候,两个“工(功)夫”的频次明显不一,“境界”义用的都是“功夫”,而“方法”义则多用“工夫”。
这就说明,截至唐代,两词在指代“境界”义和“方法”义时,在涵义上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向,“工夫”主要用来指修炼、修行的具体方法,“功夫”则主要指经过修炼、修行获得的造诣与达成的境界。
(二)宋及以后
宋代,受佛、道的影响,儒家也将“工夫”与“功夫”援引进儒学话语体系,并在不断应用与诠释的基础上,最终将两者演变成蕴含丰富义理内涵的哲学用语。现以朱熹主要作品为例,来分析儒家话语里的“工夫”和“功夫”在使用频次、具体用法和涵义上是否不同。[11]
1.使用频次的不同。现将朱熹作品中有“工夫”和“功夫”词条的书名及词条出现次数列表如下:
书名 |
工夫(次) |
功夫(次) |
《仪礼经传通解》 |
0 |
1 |
《通鉴纲目》 |
0 |
4 |
《杂学辨》 |
1 |
0 |
《近思录》 |
4 |
0 |
《小学集注》 |
5 |
0 |
《论孟精义》 |
8 |
0 |
《延平答问》 |
15 |
0 |
《四书章句集注》 |
1 |
2 |
《四书或问》 |
5 |
3 |
《伊洛渊源录》 |
13 |
1 |
《晦庵续集》 |
6 |
29 |
《晦庵别集》 |
7 |
19 |
《晦庵集》 |
269 |
384 |
《朱子语类》 |
1599 |
118 |
总计 |
1933 |
561 |
表1 朱熹主要著作中“工夫”与“功夫”的出现次数
从表1可以发现,朱熹的不同作品中,“工夫”与“功夫”的出现频次并不一样。有些只有“工夫”而无“功夫”,如《杂学辨》《近思录》《小学集注》《论孟精义》《延平答问》;
有些只有“功夫”而无“工夫”,如《仪礼经传通解》《通鉴纲目》;有些“工夫”频次高于“功夫”,如《四书或问》《伊洛渊源录》《朱子语类》; 有些“功夫”频次高于“工夫”,如《四书章句集注》《晦庵集》《晦庵续集》《晦庵别集》。
需要注意的是,《朱子语类》由当时朱子门人辑录、后人汇编而成,虽不能代表朱熹本人对两个“工(功)夫”的使用习惯与态度,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朱熹前后那一段历史时期中,一部分儒家学者对“工夫”与“功夫”的使用情况,因而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朱熹本人所著的作品,“功夫”在总数上较“工夫”是占优的,但优势不是很大。 而由门人辑录的《朱子语类》,“工夫”却在总频次上对“功夫”有压倒性的优势。
出现这种情况,一则由于在仓促记录间,“工”字确实比“功”字简洁易写; 二则由于朱熹及时人并未对两个“工(功)夫”做出界限明确的涵义上与表述上的分类,因而使得门人认为无论用哪个“工(功)夫”,都是对的。
至于朱熹本人对于“工夫”和“功夫”的使用,是否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程度的偏好? 他早期所写的《四书或问》《论孟精义》《延平答问》以及《杂学辨》,其中“工夫”出现的频次都比“功夫”要高; 而中后期成书的《四书章句集注》《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近思录》《仪礼经传通解》等则是两者频次各有高低。
由此可以推知,朱熹在早期更习惯使用“工夫”,但总体上,他用“功夫”比用“工夫”在频次上要略高一点。 而朱子门人使用“工夫”的频次比“功夫”要高出十几倍,朱子所用的“功夫”比之“工夫”多出的数据放在《语类》中如此大的差异面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因此可以认为,发展成义理概念之后,“工夫”在使用频次上,确实已经大大超越了“功夫”。
2.具体用法的差异。义理化之后的“工夫”和“功夫”有两种不同的用法:一是以单词的形式前接动词构成短语,如“下工(功)夫”“做工(功)夫”;二是与前接的名词或形容词共同构成复合词,如“圣贤工(功)夫”“彻上彻下工(功)夫”。
第一种用法,是在没有具体前缀限定的情况下,“工夫”和“功夫”作为名词单独使用,或是前接动词用作短语,此时“工夫”“功夫”都是综合性的义理概念,指主体为了实现内圣外王的最高理想所进行的自我修炼,其中包含了修炼过程中的项目节次、所使用的具体方法、达成的阶段性成果、所实现的人生境界等等丰富深广的义理内涵。
纵览朱熹著作中的“动词+工(功)夫”的短语用法,可以发现,除了个别字词有差异,两者的前缀动词在种类上几无区别,涵义也完全一致,都是没有具体所指的综合性泛指义。而这种用法下的“工夫”比之“功夫”,从数量上看,整体要高出很多。
第二种用法, 是“工夫”“功夫”前有名词和形容词对两者做出语境和涵义上的限定,使“工夫”“功夫”偏向于其中某一层涵义,比如“彻头彻尾工夫”“接续功夫”偏向于时间与空间合构而成的“过程”义、“致知工夫”“主敬工夫”偏向于“方法”义、“成汤工夫”“颜子工夫”又偏向于“境界”义。
“工夫”相对“功夫”,在数量和组词的丰富度上都有一定优势。“功夫”的复合词大部分都能在“工夫”复合词中找到完全一致或词义相近、相对的,反之则不然。
譬如学者功夫、博文功夫、格物功夫、克己功夫、涵养功夫、彻头彻尾功夫、细密功夫等,这些都能在文献中找到同样的“工夫”复合词用法;词义相近的例子则有圣人功夫与圣贤工夫、持养功夫与存养工夫、朴实功夫与磨砻工夫等;词义相对的则有一刀两断功夫与确实静定工夫、诙广功夫与遁闷工夫等等。
反观“工夫”的一些复合词,却是自身所独有,找不到对应的“功夫”用法,如知行工夫、博文约礼工夫、戒慎恐惧工夫、养气工夫等等。
3.涵义上的区别与偏向。先来看同一语境下,在同一文段或文句中同时出现的“工夫”和“功夫”是否涵义有别:
①“曾再到晋辅处否?后生知所趣向,亦不易得。且勉与成就之,令靠里着实做工夫为佳。季章近读何书?作何事业功夫?意思比旧如何?无疑亦久不得信,不知后来于鄙说能信得及否?”[12]
②“来书云:‘今且反复诸书以收心,至涵养工夫,日有所夺,未见其效’,此又殊不可晓天。……且胡为而不移此读书工夫向不读书处用力,使动静两得,而此心无时不存乎?然所谓涵养功夫,亦非是闭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后谓之涵养也。”[13]
③“修省言辞等处,是刚健进前,一刀两断功夫,故属乎阳,而曰乾道。敬义夹持是退步收敛,确实静定工夫,故曰坤道。”[14]
④“或问:‘由求所以未仁,如何?’曰:‘只为它功夫未到。’问:‘何谓工夫?’先生不答。久之,乃曰:‘圣门功夫,自有一条坦然路径。……所谓功夫者,不过居敬穷理以修身也。由求只是这些功夫未到此田地,……功夫到此,则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15]
句①句②都出自朱熹文集,句③句④则出自《朱子语类》中由同一人记录的文段,由此可见朱熹本人及其门人董铢对两个“工(功)夫”的使用习惯与态度。
句①中有“做工夫”与“作何事业功夫”的用法,“做工夫”是“动词+工夫”的短语,“工夫”是没有特别偏向和具体所指的综合涵义,其中包括了过程、方法与境界;
“作何事业功夫”虽然乍一看是“事业功夫”的“名词+功夫”用法,但前面还有个“作”字,因而整体来看还是应该理解为“作(事业)功夫”,也就是“作功夫”的“动词+功夫”形式,所以“功夫”也是包含了过程、方法、境界的综合义理概念,与前面的“工夫”涵义一致。
句②中有三处“工(功)夫”,分别是“涵养工夫”“读书工夫”“涵养功夫”,读书是问学、求知的方法之一,涵养则是心性工夫的方法之一,因此这三处“工(功)夫”都是偏向“方法”义的“名词+工(功)夫”的用法,涵义也是完全一样的。
句③是“形容词+工(功)夫”的复合词,其中,“一刀两断 功夫”对应“确 实静定工夫”,两者都是表示“工(功)夫”在不同情形下显示出的不同状态,此时“工夫”和“功夫”不仅用法一致,涵义也一样,都偏向于“过程”义。
句④中有一处“工夫”与五处“功夫”,其中“工夫”“功夫”依各自语境的不同而显示出了好几个不同层面的涵义:
“何谓工夫”与“圣门功 夫”指的是涵括了修炼过程、内容、方法、境界的综合性涵义;“所谓功夫者,不过居敬穷理以修身也”的“功夫”,则是“方法”的偏向性涵义;“功夫未到”和“功夫到此”则是“造诣、境界”的偏向涵义。
单从这一句来看,似乎“功夫”用来指向“境界”层面的偏向义比较多,五处中有三处都是如此。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或者说,义理概念的“工夫”与“功夫”,在具体使用过程中,是否真如一些学者所言,有更为偏向其中某一涵义的现象存在?
现将书中“工夫”与“功夫”在表达不同涵义时,其中几组最常见的短语、复合词及其频次分列如下:
工夫(次) |
功夫(次) |
|||
综合涵义 |
做工夫 |
436 |
做功夫 |
30 |
下工夫 |
147 |
下功夫 |
63 |
|
用工夫 |
77 |
用功夫 |
42 |
|
日用工夫 |
21 |
日用功夫 |
34 |
|
“过程”偏义 |
下手工夫 |
2 |
下手功夫 |
1 |
外面工夫 |
1 |
外面功夫 |
1 |
|
“方法”偏义 |
格物工夫 |
11 |
格物功夫 |
4 |
穷理工夫 |
9 |
穷理功夫 |
8 |
|
克己工夫 |
24 |
克己功夫 |
3 |
|
“境界”偏义 |
颜子工夫 |
7 |
颜子功夫 |
1 |
工夫未到 |
10 |
功夫未到 |
7 |
|
工夫至到 |
6 |
功夫至到 |
2 |
|
表2 朱熹主要著作中“工夫”“功夫”不同涵义常见词组及其频次对比
由表格可窥知:纵向对比的话,“工夫”和“功夫”都是在表达无偏义的综合涵义时,频次为最高,大约占到各自总数目的80-90%,这即是说,两个“工(功)夫”最常用来所指的就是同时包括过程、方法、境界的总的涵义。
而其他三种偏义中,指“过程”偏义的频次最低,不到总数的1%;“方法”偏义最高,约占6-8%;“境界”偏义次之,约占4-7%。横向对比,则可见除去“日用工夫”等个别用法,在用法、表述和涵义都相同的词组中,“工夫”显然要比“功夫”在频次上要高一些。
尤其要注意的是,不仅“做工(功)夫”“下工(功)夫”的综合涵义和“过程”偏义、“方法”偏义是如此,就连在被宋儒正式义理化之前已呈现出“境界”义偏向的“功夫”,在此时表达“境界”偏义的时候,总的频次也已不如现阶段的“工夫”了。
(阳明静修)
由此可知,在成为义理概念之后,“工夫”不仅在整体的使用频次和具体用法的丰富程度上都已经大大超越“功夫”,在进行同样涵义的表述时,无论是无特指的综合涵义,还是有各自偏向层面的“过程”偏义、“方法”偏义、“境界”偏义,各自的频次也已超越“功夫”。
同时,两个“工(功)夫”在表述综合涵义时的用法,在总数所占比重上相对于三种偏义都有压倒性的优势。
这就说明,在宋以前,义理化初期的两个“工(功)夫”的发展特点:“工夫”偏向过程与方法、“功夫”偏向过程与境界,并没有随着时代发展而留存下来,而是在“工(功)夫”正式实现义理化之后发生了相应的改变。
两个“工(功)夫”都更多地用来表达统括过程、方法与境界的综合涵义,同时也没有出现哪个“工(功)夫”更为偏向其中某个涵义的情况,以往指“方法”多用“工夫”、指“境界”多用“功夫”的现象不复存在。
五、结 论
“工(功)夫”在历史上的涵义形式分为两类:所指对象单一、较为简单的日常义,与综合了好几重涵义、相对复杂的义理义。
两类形式中各自的涵义种类也有很多,日常义的“工夫”下辖五种不同涵义( 总的“时间、努力”义;单独的“时间”义;“本领、造诣”义;“工程、工作”义;“工人、夫役”义),“功夫”也有五种(总的“时间、努力”义;单独的“时间”义;“本领、造诣”义;“工程、工作”义;“武术”义);
而义理义的两个“工(功)夫”,则可依照具体语境的不同,而有综合涵义、“过程”偏义、“方法”偏义、“境界”偏义之分。
“工夫”与“功夫”就涵义的复杂程度来说,在整个中国语系中也是非常少见的。因此,辨析两者的不同,就需要每一个层面、每一种涵义都涉及到,不然就无法得到完备、准确的结论。
日常义上,“功夫”的各项指标都比“工夫”发展的早和快,出现时间早、频次发展快、语用成熟度早、语义丰富度也发展得快一些;义理义上,两者同时出现义理化倾向,语义演变也几乎同时进行,初期还出现了各有偏义的情况。
但无论是日常义还是义理义,后期的“工夫”在语义发展方面已经迎头赶上,在使用频次和具体用法的丰富程度方面更是逐渐超越了“功夫”,以至于到了现代,“功夫”词条最广为人知的涵义是明清之际才姗姗出现的最后一层日常义——“武术”义,而那几层先于“工夫”发展出的涵义与用法却鲜少为人所知。
(传统武术)
这就说明,“功夫”的发展趋势是由盛转衰,而“工夫”正相反,是越来越盛。
而“工夫”“功夫”之所以一直被混用,一是由于两者在涵义上的界限确实非常模糊,除了日常义中的“工人、夫役”义和“武术”义为各自所独有,其余五种日常义和所有义理义都为两者共有,在表述这些共有义的时候,“工夫”“功夫”完全能够通用。
二是由于从古至今,从未有人对两个“工(功)夫”做出过用法、涵义上的具有权威性的分野与规定,这种权威性要建立在对历史上两者发展演变特点的梳理与总结之上,需要有完整足够的材料与数据作为论据,方能让人信服。
因此,在文献资料丰沛、数据检索系统日渐完善的今天,我们有条件、也有必要以辨析的方式来对这个问题暂时做出回应。
基于“工夫”“功夫”在历史上的发展特点,本文主张除去“工夫”所独有的“工人、夫役”义以及“功夫”独有的“武术”义之外,在表达相同涵义的时候,无论用哪一个“工(功)夫”,都是对的。
但用“工夫”比用“功夫”更好一些,尤其是研究义理层面的“工夫”与中国哲学范畴的“工夫论”的时候,应用“工夫”为宜。
一来是考虑到两者义理义的发展趋势和特点,在“工(功)夫”彻底实现义理化之后,“工夫”不论在同样涵义的使用频次上,还是具体用法的丰富程度上,都对“功夫”有相当程度的优势,这种优势一直延续至今。二来则是出于一些外部因素的考虑。
目前不论中外,在谈到“功夫”的时候,第一反应总是会将之与“武术”联系在一起,因此,在哲学领域用另一个“工夫”,则是避免与人们普遍熟识的武术“功夫”相混淆的有效方式。
[1] 严可均辑:《全后汉文》下册,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91页。
[2] 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4页。
[3] 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03页。
[4] 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4页。
[5] 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45页。
[6] 方干:《玄英集》,《四库全书》第108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8页。
[7] 方干:《玄英集》,《四库全书》第108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0页。
[8] 《晋书·范宁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88页。
[9] 许逊受:《铜符铁券》,《道藏辑要》卷五缩印本,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207页。
[10] 许逊受:《铜符铁券》,《道藏辑要》卷五缩印本,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208页。
[11] 本文选择朱熹的主要作品为研究对象,是由于朱熹作品是为宋及以后儒家义理类著作中,在体裁文例、义理内容、整体体量各方面都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个案。现存的朱熹著作中有“工(功)夫”词条共2494条,为宋及以后所有儒者作品中数量最多。
[12] 《晦庵集》,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492页。
[13] 《晦庵集》,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8页。
[14]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17页。
[15]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20页。
汪俐,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
主编:陈明
选题:任重
编辑:陆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