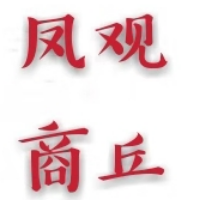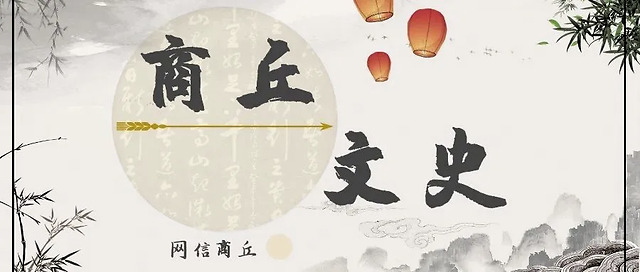
编者按
“微文化”有时候比“大文化”更易于将韧性的触须深深探进人心,更易于在瞬间砰然打动人们的情感。事实上,“微文化”不“微”,只不过似乎已生长在人们的思想中,虽不常被提起,却也不曾被忘记。
在商丘蔚为壮观的文化资源中,“毛主席‘在’商丘”可谓这样的文化记忆,如同“老家”给予每一个人刻骨的守望一样,是一种温暖,一种光荣,更是一种启迪。
文化是不是产业?这是当下文化体制改革进入深化阶段后,再次凸显出来的一个见仁见智的炙热的焦点之争。然而,发展却让我们看到,仁者让文化成为精神,智者让文化成为产业。
“文化创意”其实不神秘,很多时候它就是小发明般的小创新、小创造。如同纳百川成海,小的力量不一定闯不开大世界。
网络上广为流行的“后舍男孩”只是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的两个男孩子,他们借鉴国外网络流传的搞笑视频模式,仅仅利用一台电脑、一部摄像头,几件简单的道具创作出了一些网络MV作品,这些作品风靡网络后,他们将版权卖给了太合麦田音乐公司,从而成为名利双收的明星。
前不久,记者在市火车南站见到一个女孩子,她自己创建了个音乐工作室,刻录车载光碟,全是网络上最具人气的歌曲,励志的,怀旧的,民族的……成本不高,效果却很“原版”,她的小摊前总是围满了人,一本20元。记者问女孩子收入怎么样,她笑笑说比打工强。
相比于“后舍男孩”,这女孩子还似乎难以成为名利双收的明星。但她的举措叫“创意”,她的行为叫“创业”。
明码标价的都是商品,“智慧”标不出确切的价格。
“双八”的光荣与启迪
中国人喜欢“8”,古人喜欢是因为其寓意深远,隐指向四面八方展延,如“思接千载,心鹜八极”;现代人喜欢则多半因为与“发”谐音,意为“发财、发达”。其间又听说有些人开始不喜欢“8”了,看它字形太酷似一副打开的手铐。
仅仅于一个无辜的数字,竟不是喜欢和不喜欢那么简单,其中折射出时代变迁、社会转型、人心百态等,真是留心处皆见学问。
但对于商丘市一个叫“双八”的乡镇来说,“8”这样一个数字,有且只有一个纯粹的朴素的光荣的定义,那就是“纪念”。
“双八”,意为“8月8日”。日子回溯到1958年8月8日,毛主席到达商丘,视察原商丘县道口乡黄楼村“七一”试验站的红薯、水稻、高粱等试验田庄稼生长情况。毛主席视察走后的第二天,原道口乡决定以毛主席视察的日期作为乡的名字。
商丘多“道口”,一是古黄河改道前流经商丘,隋唐大运河贯穿全境,如同星辰的遗落一样,这是曾经繁忙了几个世纪的水上运输业馈赠给这块土地的“美丽遗落”。
原来的道口乡也是一个中州古镇,因地扼古宋州通往齐、鲁要道而得名。目前位于商丘市梁园区北5公里,105国道东侧。同样都已积淀成文化矿藏,但名字的变更,并非数典忘祖,更意味着一种史无前例的光荣,一种难以忘却的纪念。
毛主席视察10周年时,当地政府在视察现场建起了纪念亭和纪念馆。纪念馆全称为“毛主席视察黄楼纪念馆”,是一座半工字型建筑,共有主房28间,总建筑面积2200平方米。共5部分组成,正中大厅和东西四个展厅,正中大厅毛主席特大巨幅画像七米多高,两侧是毛主席1958年视察黄楼时的两幅巨型彩色照片,大厅中间是毛主席的一樽1:1塑像。各展室内布置着毛泽东青年时期到建国后至逝世一生的革命活动的珍贵照片200余幅。纪念馆外有毛主席视察过的井和试验田。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商丘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商丘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毛主席视察黄楼纪念馆接待过的前国家领导人和知名人士有李德生、杨得志、费孝通等。毛新宇和他夫人也来过。
毛主席来到咱农庄
键盘的敲打声中,一首老歌的旋律轻轻萦绕起来。记者在网上“百度”一下,歌名叫《毛主席来到咱农庄》,歌词如下:
“麦苗青来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千家万户齐欢笑呀,好像那春雷响四方。毛主席来到咱们村,跟咱们社员来谈心;一问咱们除四害呀,又问咱生产大跃进。毛主席呀关心咱,又问吃来又问穿;家里地里全问遍呀,还问咱们夜校办没办。主席的话儿呀像钟响,说得咱心里亮堂堂;主席对咱微微笑呀,劳动的热情高万丈。鼓足干劲大跃进哪,齐心建设咱新农庄。”
原本没想把全部的歌词“摆”在这里,一遍看下来,感觉词作者是在用“白话”一样的诗、诗一样的歌在传唱“毛主席来到咱农庄”,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就能引人穿越在一个又一个场面里,字里行间就能“看到”手拉手的问询,“听到”心贴心的谈笑。
彼农庄虽不是此农庄,但情景、关怀、温暖应该是一样的。
记者曾经读到时任道口乡乡长徐家麟的一篇回忆录,回忆当年毛主席视察黄楼村的详尽经过,文字不加任何粉饰,不见一处雕琢,而于平白的叙述中,尽见朴素的感情:不可遏制的激动,热烈的敬仰,和深切的缅怀。
那篇文章记者没找到,好在“百度”出原京九晚报记者李海军的《中州名镇双八 伟人视察得名》一文,内中有当初场面的淋漓呈现。
毛主席是1958年8月8日下午3:20时到达原商丘县道口乡人民委员会大院,身边由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中共商丘地委书记任秀铎、县委书记刘学勤等人陪同。
在黄楼村东头“七一”试验田里,10多个小伙子正在田间干活。看到有领导走过来,他们站成两排,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在参观“跃进门”时,人群中有一名小学生认出了毛主席,很快,人们像潮水般涌来,并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
在黄楼村打井工地,16名打井队员干得热火朝天。这个打井队已有两年打井经验了,建队以来完成15眼井。毛主席听了汇报后,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这眼井打多深,需要多少天完成?”毛主席问。“打12丈深,20天可以完成。”18岁的打井队员黄诗开走到毛主席身边,边回答边用手比画着,“用锥打一个小眼,然后用翅刷泥。刷泥之后,用五寸锥把泥掏出来,再往下打。”
在路过一块红薯地时,毛主席问:“这是谁搞的试验田?”站在旁边的道口乡乡长徐家麟回答:“乡、社干部搞得试验田。这2亩多麦茬红薯,翻地2尺深,每亩5000株,计划亩产1.39万斤。”
“好。”毛主席边说边往前走,在路过旁边的一块稻田时,毛主席摸了摸稻穗问:“稻田里怎么没有水?”徐家麟解释说:“今天刚断水,现在正在拔草。”毛主席又问:“1亩栽多少墩?亩产多少斤?”徐家麟回答:“3万墩,计划亩产1500斤。”
毛主席又来到稻田北头,仔细看过稻子生长情况后说:“北边的稻子长势不错,中间的有些稀。”
在参观黄楼村的积肥时,群众朝前拥挤,毛主席挥着手说:“不要掉进粪池了。”
下午5时,毛主席要坐上汽车走了。这时,群众再也不听干部的指挥了,有的扛着铁锨,有的握着锄头,潮水般地朝这边涌来。霎时,有200多名群众围住汽车,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毛主席呀关心咱,又问吃来又问穿;家里地里全问遍呀,还问咱们夜校办没办……”读过这样的文字,再回过头来听听《毛主席来到咱农庄》,如临其境,感同身受。
因为铭记 所以难忘
近几年,记者常去“双八”摘草莓,就有了顺便到毛主席视察黄楼纪念馆看看的理由和时间,也就认识了杨光福、黄诗云、李西坤们,因为一次“相见”,便有了一生无悔守望的“下里巴人”来。
因为有“故事”,他们成了村里的“功臣”,成了多此采访聚焦的“新闻人物”,他们是见证者,是讲述者,也是多种意义上的传承者。
一次握手让他光荣了一辈子,这个人叫杨光福。当年毛主席视察黄楼村时,杨光福说他正在打井,听说毛主席来了,他赶紧从井下爬了上来,那时毛主席正准备上车离开,他三两步跨到主席车前,与毛主席迎上来的大手紧紧握在一起。杨光福这一生最让他引以为荣的,不是吃饱穿暖的安定生活,不是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而是他那一双被主席紧紧握过的沾满泥巴的手。为此,他7天没有洗手。村里不少人没有握上主席的手,就来握握他的手。后来“文革”时,红卫兵也以握他的手表达自己“永远与伟大领袖毛主席站在一起”。
一次坚守让他后悔一辈子,这个人叫黄诗云。黄诗云是毛主席视察时的“中华第一合作社”的会计,毛主席视察的前3天,县里召集他们合作社的干部去开会,说最近有中央领导要来,要他们把各方面工作做好,各自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因为他是会计,工作岗位就是会计室。因为这次坚守,他没有见到毛主席,这让他后悔一辈子!
他想守护毛主席纪念亭一辈子,这个人叫李西坤。对于黄楼村来说,李西坤是一个“外来户”,如今他却成了这里最坚定的守望者。李西坤原是被邀请来的小麦技术员,下岗后把户口迁至黄楼村,看护毛主席纪念亭。他每天早上一起床,就会拿起扫帚扫地,将院子打扫干净。纪念亭前“毛主席视察井”的水泥标示牌,被他天天擦拭得干干净净。平常有人来参观,他就自觉担当讲解员,把他了解到的毛主席视察时的情景讲给人们听。
只为心中那一种最朴素的敬仰,我们谁也不会一任心灵之门紧锁。打开这扇门,无论我们推介的是文化,是精神,还是产业,只要是收获,何怨耕耘深。
作者简介
班琳丽,笔名班若,1973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出版长篇小说两部,诗集两部,中短篇小说集一部。作品发表在《文艺报》《中国作家》《北京文学》《诗选刊》《星星》《绿风》等刊物。《一腔白菜》获《中国作家》文学奖;《小日子》获第一届浩然文学奖等。现居商丘。
(来源:网信商丘 作者 班琳丽)
编辑:张梦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