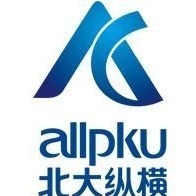来源 | 坤元辰兴不动产观察(kycxRE)文 | 圭也

列车跨过武汉长江大桥
交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是深远而全面的。城市的经济活动、空间发展乃至兴衰演替均与交通密切相关。纵观全球著名城市,几乎皆因交通起兴。我国亦如是,几千年的中国城市发展史,可称一部交通连结史。回首过去,从驿道、江河运输到铁路、航空运输,多少城市链、城市群此消彼长、各领风骚,共同促成我国今日城镇体系的形成。
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交通主要依靠水运。直至晚清,我国城市之间的交通方式才由驿道、江河运输向铁路运输过渡。期间,因铁路而兴盛的城市不胜枚举,因铁路而黯淡的城市亦比比皆是。然而,有一些幸运的城市,无论在水运时代还是铁路时代,均秉承地利成为交通枢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江汉汇流、九省通衢的华中名城——武汉。
武汉主要节点位置提要:武汉处于长江、汉水交汇之地。今武汉主城区主要位于三环以内。长江以东:黄鹤楼位于武昌老城内;今中南路、中北路位于武昌老城东部;武大位于中南中北路以东的湖畔;光谷则通过珞喻路向西沟通老城区。长江以西,汉水以北:汉口老城区大部分位于一环内;江汉路位于江畔;汉口站位于二环上。长江以西,汉水以南:汉阳老城位于一环以南。
以转运贸易为核心的外生动力发展阶段
(1938年以前)
江汉汇流之地
武汉起于江汉汇流之地。在长江、汉水长期冲击形成的平原湖沼区域,汉阳、武昌、汉口相继形成。得天独厚的地理格局使得武汉三镇自古以来便沟通了关中平原、四川盆地以及长江中下游平原,奠定了九省通衢的自然基底。
武汉是周边众多入江口形成的最大的城市聚落
《山海经》有云:“幡冢之山,汉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江。”汉水自秦岭汉中地区向东汇入长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亦培育了长江中游地区最大的城市聚落——武汉三镇。
武汉三镇周边水系
汉水是长江中游地区贡赋钱粮北上的最佳通道,亦是动乱年代代替京杭运河完成物资北上任务的战略通道。夏商周直至北宋,我国都城多位于关中平原及中原地区。西南、中南地区的贡赋钱粮多沿汉水北上,至汉中盆地转秦岭栈道至关中,或过南阳,水陆转运至洛阳、开封、北京。
动乱年代,汉水作为转运物资命脉的作用显现
每至动乱年代,如安史之乱、黄巢起义等,江南贡赋无法经过京杭大运河北上,亦西溯江、汉北上。汉水成为物资北上的命脉。
依托长江、汉水,武汉三镇在我国中南、西南地区的转运贸易中走向繁盛。其城市发展以转运贸易主导的外生动力为主。武汉的转运贸易时代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阶段一:双城时代
(明成化年间以前/1467年以前)
汉阳、武昌古城位置
“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
明代以前,汉阳、武昌长期隔江相峙,各自发展。汉阳位于长江西岸,起于西汉江夏郡沙羡县,经却月城、鲁山城等,逐步发展为汉阳城。武昌位于长江东岸,兴于东吴夏口城,经鄂州城等,逐步发展为武昌城。
双城时代,武汉形成了“龟蛇锁大江”的十字山水格局。汉阳东临长江,北靠龟山、南至汉水故道;武昌西临长江,纵跨蛇山,南至白沙洲,“扼束江湖,襟带吴楚,控接湘川”,周边九湖十三山环绕。
汉阳、武昌城池
汉阳、武昌均为典型的封建城池,承担着军事城堡、行政治所的功能。汉阳城墙开东、西、南三门,内部路网以丁字街道组织,城内府署、城隍庙、鼓楼等建筑居于城池中央。汉阳城受汉水故道影响沿河东西向发展。武昌城内蛇山横亘东西,黄鹤楼坐落在蛇山西端,中部有鼓楼使南北互通。山北官署、书院林立;南部主要为寺庙、军营。武昌城受到长江的拉力,城市发展偏重西部,城市东南部待开发。
长江、汉水形成的江中沙洲造就了南市的繁荣
城池之外,汉阳、武昌南市商业皆因长江、汉水的转运贸易而兴,因长江、汉水形成的沉积沙洲而盛。唐宋时期,武昌成为江汉漕运的起点以及东南贡赋的储存地,促使武昌及隔江而望的汉阳商业贸易走向繁荣。长江、汉水冲击泥沙形成的江中沙洲,如鹦鹉洲、白沙洲、金沙洲、刘公州、新鹦鹉洲等为武昌、汉阳提供了天然良港,使得两古城南门外的南市繁盛一时。
南宋范成大在《吴船录》中描述了武昌南市的盛景:“鹦鹉洲前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宋代诗人胡寅在《登南纪楼》中描述了汉阳南市的繁荣:“平时十万户,鸳瓦百贾区。夜半车击毂,差鳞衔舳舻。”
随着沙洲的沉没、汉水改道,武昌、汉阳城南市的转运贸易繁荣不在,武昌、汉阳的商业中心收缩至城池内部。武汉地区的转运贸易进入汉口时代。
阶段二:汉口时代
(明成化年间/1467年-汉口开埠/1861年)
“五百年前一荒洲,五百年后楼外楼。”
明成化年间(1467年),武汉大雨,汉水于汉阳决堤,改道汉口。至此,汉口成为汉水唯一的长江入江口,故称汉口。
汉水改道
在武昌、汉阳沙洲沉没、连年淤塞的背景下,汉口接过区域转运贸易的重任,逐步发展为“居奇贸化之贾,比廛而居,转输搬运,肩相摩,踵相接”的“楚中第一繁盛处”。
一统武昌、汉阳两城的转运贸易,至清代,汉口已发展为闻名全国的商业巨镇,“江湖数千里,商帆估舶,千万成群。”明末清初,汉口已成为中南、西南物资的中转集散地、漕粮交兑点以及淮盐转运中心。清初《广阳杂记》记载:“汉口为楚省咽喉,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输。”
本阶段,汉口汉正街、袁公堤已形成(图示黄颜色)
繁荣的转运贸易使得汉口从荒滩自下而上形成了繁荣的街市:汉正街。明嘉靖年间(1545年),汉口地区人口达到7,000人。汉阳县在汉口设立居仁、由义、循礼、大智四坊,共同形成了汉口正街,即今汉正街。昔日汉正街的繁荣,可见《汉口丛谈》:“西则居仁、由义,东则循礼、大智四坊。廛舍栉比,民事货殖,盖地当天下之中,贸迁有无,互相交易,故四方商贾,辐辏与斯。”
由于汉口地势低洼,屡遭江汉水患。1635年,汉阳城袁通判由硚口修建长堤至堤口,形成袁公堤,即今长堤街。袁公堤的修建,使得汉口城市形成南河北堤夹一街的城市空间格局。“在袁公堤的保护下,汉口地区快速发展。
阶段三:开埠时代
(开埠/1861年-汉口沦陷/1938年)
“驾乎津门,直逼沪上。”
开埠前,在繁荣的转运贸易中,汉口逐渐形成了“六大行”商品:盐、当、米、木、花、布、药材。至1861年汉口开埠,茶叶成为汉口仅次于盐的贸易中转商品,吸引了大量西方人深入长江中游腹地,至汉口经商。
汉口是长江中上游及中西部地区的转运中心
开埠使得汉口的转运贸易达到顶峰。汉口承载着中外贸易进出口货物的双向转运功能,在上海与长江中上游城市之间充当了国际贸易的桥梁。如果说上海是长江乃至全国经贸活动的总集散地,而汉口则是长江中上游或中西部地区的转运贸易中心。全盛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形成了以汉口为核心,以宜昌、沙市、岳阳、长沙等为二级转运港的转运体系,其中水运占贸易总值的90%左右。
汉口出口货物以间接出口(转运贸易)为主、茶叶出口占比高
汉口成为以出口贸易为主的转运贸易城市。根据海关总册统计,1867年至1931年的65年间,汉口以转运贸易为主的年份为59年,其中出口额占当年贸易总量的70%以上达52年。汉口的转运贸易主要为土货的出口以及洋货的进口。茶叶、桐油、棉花、蛋品、牛皮的出口占汉口贸易额的80%以上。1885年至1905年,汉口土货出口总量扩大3倍,达到6400万海关两。至辛亥革命,汉口出口额占全国25%以上,其中茶叶占全国出口比重超过60%,桐油超过90%,棉花超过50%。
转运贸易的繁荣推动了汉口城市、人口的大发展。
人口集聚于汉口
汉口堡及八门
由于汉口地位的提升以及太平军、水患的侵扰,1864年,汉口始建城堡并开八门:便门、通济门、大智门、循礼门、由义门、居仁门、便门、玉带门。堡内袁公堤改为街道,即今长堤街。汉口堡的修建提高了汉口的防御性。
汉口五国租界
1858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汉口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
开埠以来,英、德、俄、法、日五国先后于汉口东部沿岸获取租界。类似于近代上海租界,汉口五国租界中,英、德租界以金融贸易为主、法租界以娱乐商业为主、俄租界为旧汉口的高级住宅区及娱乐商业区为主,日租界商业气氛较为薄弱。五国租界与华界之间的道路江汉路不久即发展成武汉最繁盛的商业街,其尽头为著名的以《威斯敏斯特》旋律为钟声的江汉关大楼。
刘歆生为家人展示汉口规划图
提及江汉路,不得不提及汉口房地产大亨——刘歆生。
刘歆生,与上海的哈同、天津的高星桥齐名的近代地产大王,人称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出生于汉阳,少年时放过鸭、喂过牛,后与汉口天主堂神父金宝善相识,在神父的支持下开牛奶坊,并学会了英语、法语。随后,他通过教会的关系进入汉口太古洋行(即今太古集团)当练习生,逐步升为写字兼跑街,随后在法商立兴洋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工作,积累了投资经验。
刘歆生先后投资了大量实业、商贸公司,如矿厂、铁厂、榨油厂、转运公司、电话公司等,为进入地产行业积累了资本。
五国开埠以来,刘歆生敏感地意识到汉口市区必然会逐步扩大,果断将全部资金以及银行高息贷款用于购置汉口城郊土地。他创造性地发明了土地划船计价法,即在所购土地的四角立上旗杆,在旗杆之间划船,以划桨的次数来计价。如此,刘歆生收购了汉口城郊约2万亩的土地,成为汉口地皮大王。二十世纪初,刘歆生出地、英租界出资,共同建设了彼时汉口最繁华的商业街——江汉路。
民国时期江汉路
江汉关大楼(1930年)
江汉关大楼建设于长江中游地区内陆关卡以汉口关为准的背景下,侧面体现了汉口转运贸易之盛。
湖广总督张之洞督办京汉铁路
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生于官宦世家,15岁中解元,26岁点探花,随后入翰林,放学政,擢巡抚,升总督,屡任封疆,敭厉中外,晚年入阁拜相,卒谥文襄,一生荣宠备至。
张之洞被称为“武汉城市之父”,在武汉兴办铁路、堤坝,创办新式教育、民族工业。张之洞督鄂期间,武汉三镇城市迎来大发展:武昌向南北、东部拓展;汉口向西北拓展至张公堤(今三环);汉阳在铁厂的带动下向西延伸。张之洞拉开了武汉城市发展的骨架,造就了大武汉。
1898年张之洞督鄂后,在汉口堡外的后湖北侧修建张公堤(今三环)并将汉口堡改为后城马路,涸出田地10万余亩,汉口腹地初显今日规模。1906年,京汉铁路通车(即今京汉大道)。汉口先后建设了江岸车站、玉带门车站、大智路车站和循礼门车站。
张公堤极大拓展了汉口城市发展的腹地
京汉铁路四个车站及在汉口堡基础上建设的后城马路
张公堤、后城马路、京汉铁路的修建,使得京汉铁路以北的后湖附近地价猛涨。清政府将铁路外、张公堤内十万余亩土地分成九等,梯度收租,三两至六十两不等。后城马路西侧硚口一带土地1906年春每方售价银3两,两个月后涨到9两,初冬涨至50两。大智门一带土地,由于毗邻车站,涨至160两。据《夏口县志》记载:“自后湖筑堤、卢汉(即京汉)通轨,形势一年一变,环镇寸地寸金。”
随着火车站的相继建立,老城区与铁路之间的地带亦迅速发展起来,玉带门、循礼门、大智门车站附近的民房逐渐改为商店,出现了新的商业区,商业中心从汉江沿岸往后城马路一带转移。1915年出版的《汉口小志》载:“繁盛极矣,南北要道,水陆通衢,每届火车停开时候,百货骈臻,万商云集,下等劳动家藉挑抬营生者,咸廉集于此。”
张公堤的修建改善了堤内环境,堤内产生大量居住需求。大量整齐平直、契合地形的新式住宅里分在后城马路、京汉铁路之间建设。里分类似于上海石库门住宅,融合了西方联排住宅与中国合院式住宅的特点。民国建立后,汉口大规模建设里分达500多个。武汉最早里份为1901年建成的大智门车站附近的三德里。
汉口里分住宅分布(1930年)
大智门车站附近的三德里
伴随着汉正街、袁公堤(长堤街)、汉口堡(后城马路)、京汉铁路、张公堤的建设,汉口逐渐向内陆腹地圈层拓展。
1904年起,伴随着长沙、宜昌、重庆、沙市、万县等城市先后开埠,汉口转运贸易的地位开始下降。武汉城市以转运贸易为核心的外生动力发展阶段进入尾声,以工业制造为核心的内生动力发展阶段在京汉、粤汉铁路的先导下悄然开启。
以工业制造为核心的内生动力发展阶段
(汉阳铁厂建立/1890年至今)
在汉口水运转运贸易地位下滑期间,京汉铁路、粤汉铁路的贯通使得长距离、大规模的陆路转运贸易成为了可能。京汉、粤汉铁路巩固、捍卫了武汉转运贸易的地位,同时为武汉城市发展转向以工业制造为核心的内生动力机制拉开序幕。武汉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发展时期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阶段一:培育时期(1890年-1938年)
“蛰伏多年”的汉阳率先拉开工业制造的序幕。1890年,张之洞于地势较高的汉阳龟山北建设汉阳铁厂等重工业厂,服务于京汉铁路的钢轨生产。在一战急需钢铁的背景下,武汉冶金业产销两旺,进而促使武汉钢铁机器设备制造业大发展。蒸汽机、布机、碾米机等钢铁机器设备的生产,进一步促进了武汉纺织、粮油加工业的发展。武汉工业体系由此初步形成。
1894年,张之洞视察汉阳铁厂
武汉快速发展为我国重要的民族工业中心。1894年至1904年期间建立的武汉工厂及其资本金均居全国第一。至1920s,武汉形成了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四大纱厂,成为仅次于上海的棉纺织工业中心。伴随着军阀混战、钢铁价格攀升,武汉一度超过天津,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业化城市。这一时期,武汉为湖北省的工业中心,1936年,武汉工厂数、资金额、年产值分别占全省的94%、99%、92%。
这一阶段,武汉三镇的民族工业沿汉水、长江、铁路快速发展。汉口着重发展砖茶、蛋品制造、卷烟、制革、面粉等工业,以食品加工业为主;武昌重点发展近代纺织工业、造纸工业;汉阳则形成了冶金、机械制造业集群。
汉阳近代工业分布
汉阳形成了从南岸嘴沿汉江南岸上行10余里的冶金、兵器、机械、建材等重工业制造带。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机器厂、钢轨厂、铸铁厂、锻铁厂、钩钉厂、官砖厂等大小工厂鳞次栉比、烟囱林立。南岸嘴则集中了翻砂厂、米厂、造船厂、瓦厂等二十余家工厂。汉阳古城主街西延线则产生了大量的毛巾厂、毛绒工厂。染织厂布置于长江西岸。
武昌近代工业分布
武昌由于是政治、军事中心,早期禁商于城内,开埠前一直以传统的手工制造业为主。张之洞督鄂后,武昌沿长江修建南北长堤,从城南白沙洲至城北新河一带形成了沿江集中工业带。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由南至北绕过武昌老城,穿越沙湖,沿长江直抵徐家棚,进一步带动了武昌长江沿线的工业发展。随着时局的动乱以及武昌政权的松动,武昌城内轻工业得以发展,并与城内居住区、商业区高度融合。由此,武昌形成了大型工厂于城外沿江分布、小型轻工业制造厂散布于人口密集、商业贸易繁荣的老城区的工业格局。
汉口则效仿五国租界内的工业,建立起以民营轻工业为主体的、以纺织粮油加工等为主的工业制造体系。
租界时期,外商工厂平和打包厂、英商和利冰厂、英商电灯公司、德商砖瓦厂等分布于汉口五国租界、京汉铁路沿线。汉口的民族工业则分布于外商工厂的外围,布局在城郊开阔地带。在繁荣的转运贸易的带动下,汉口的工业制造快速发展,工厂高密度排列,工厂、住宅高度融合、混杂,从早期租界外围的铁路沿线,快速布满整个汉口城区。至1930s汉口的中小型民营工厂占据了武汉近代工厂的80%。
工业制造主导武汉三镇城市拓展
这一时期,武汉的城市发展开始受到以工业制造为主导的内生动力的深远影响。其中,汉阳以工业发展主导,工业化迅速推动新城区的建造,形成汉阳城、铁厂双核;武昌城蔓延至长江以及粤汉铁路沿线,主要向北延伸;汉口城在工商业互促下走向大繁荣,城市快速沿江、沿河、沿铁路发展。
沿江、沿铁路的近代民族工业带动了武汉新式教育的发展,成为武汉城市内生动力新的增长点。明清时期,武昌作为巡抚、总督和总兵驻地的“湖广会城”, 为湖广学子聚集的教育文化中心,拥有江汉书院、两湖书院等12所书院。在此基础上,张之洞在武昌城及东郊地区兴建新式学堂百余所,强化了武昌作为湖广教育、文化中心的地位。随后,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高等专门学堂——自强学堂逐步与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湖北省立医科大学、湖北省立法科大学、湖北省立文科大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等合并,在今东湖珞珈山一带组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即今武汉大学,带动了武汉东进,向东湖一带发展。
武汉大学带动城市东进
武汉大学与东湖(1930s)
1938年,抗战爆发,因战乱内迁至武汉的工厂以及武汉本地工厂继续西迁,武汉工业暂时下行。民族工业培育时期进入尾声。
阶段二:复苏、发展时期
(1949年-21世纪初)
建国后武汉城市空间结构
经过日占时期的全面破坏,建国后,武汉的城市空间及工业体系开始逐步恢复。在“先生产、后生活”方针的指导下,武汉城市建设的重点由“恢复经济,改造旧城”转移到“为大型工业建设服务”。以大型工业区为先导,武汉城市快速在武汉三镇城市既有基础上,沿长江、汉水、武汉长江大桥东延线十字展开,并将大型工业布置于外围郊区,如青山工业区等。这一时期,以武汉重型机床厂(1953年)、武汉锅炉厂(1954年)、武汉钢铁集团(1955年)为代表的钢铁及装备制造业开始成为武汉的骄傲和支柱。
1988年城市规划分区
为服务于改革开放,1982年、1988年,武汉两次修编城市规划,确定汉口以商业贸易、金融服务和对外交通为主;汉阳以汽车、旅游为主;武昌地区以科研、教育和新兴产业为主;青山地区以钢铁工业为主。1988年,在武汉工业制造、科研机构的优势基础上,光谷(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在武汉东湖成立,为武汉新世纪以来的产业转型奠定了基础。
这一阶段,武汉兴建跨江大桥、汉口火车站、武汉客运港、天河机场以及大批货运站场,强化了武汉九省通衢下城内的交通条件,将汉口、武昌、汉阳整合为统一的整体。
阶段三:转型时期(21世纪初以来)
新世纪以来,武汉传统重工业面临困难,拖累工业增加值增速放缓。武汉开始缩减传统工业产能,并结构升级至新型产业。2008年以来,武汉的钢铁及深加工行业的总产值占比持续下降,从19%回落至8%;装备制造业占比由17%回落至14%。高新技术产业在工业增加值的比例由10%提升至50%。武汉主要工业产品:光缆、空调、显示器的产量在全国占比超过10%,汽车产量占比升至4.7%,生铁、钢材等重工业产品在全国占比下降至2%。
卓有成效的产业转型有赖于自近代便逐渐形成的工业基础、新式教育基础。扎实的工业基础和完备的工业产业链为武汉储备了领先的工业硬件设备以及高素质的产业工人群体;领先的教育资源为武汉的产业转型提供了研发先决条件。二者为武汉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内生动力。
武汉核心区与光谷、车都、临空、临港板块
在武汉产业结构趋向精细化、高端化的背景下,武汉围绕着主城区的两江四岸,积极布局光谷、车都、临空、临港先进制造业板块,并通过高强度的交通基础设施将主城区与各板块连结。
1924年,《东方杂志》这样描述武汉的交通、商贸、工业地位:武汉居全国中心、内地交通的总汇,昔日为九省通衢者,谓西北由汉水以大陕甘,西由长江以达川滇,南由洞庭以达湘黔,东由长江以达赣皖江苏,盖仅以水道为交通唯一之利器;今则北循京汉以达河南、直隶,间接可达晋鲁,内蒙之绥远,关外之三省;粤汉通后,两广俱便。武汉以四通八达之地,处原料产区之中,予取予求,供无不应,输入输出,通无不便。故以工业论武汉,实为中部工业之中心。国内贸易久长、国外贸易出超,以商业论武汉,实为中部最大经济中心、内地贸易最大埠也。
一百年来,武汉以江汉汇流、九省通衢的外生优势为基础,培育民族工业、新式教育,发展重工业,建设国之重器,积累高等教育人才,进而转型发展精细化、高端化的制造业,培育城市发展的不竭内生动力,“虽深居内陆,亦领风气之先。”同时,武汉积极发展区域交通、城内交通,将相对独立发展、各领风骚的武昌、汉口、汉阳三镇整合成统一的整体——武汉,将通衢之地的特点推向极致。
最后,难能可贵的是,武汉并未自恃江汉汇流、九省通衢带来的城市发展外生动力而停止进取的脚步,而是在每一次城市大发展的时期为下一次城运转折点做准备,成为独具韧性、傲立长江中游的“楚中第一繁盛处”。
因此,我们也充分相信武汉这座韧性之城将克服疫情,“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继续书写武汉城市发展的“宏图”。
黄鹤楼
文中观点仅为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