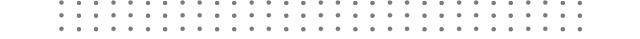1820年10月,意大利那不勒斯爆发斑疹伤寒。英国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和他的画家朋友约瑟夫·塞文(Joseph Severn)乘坐的船只在那不勒斯港口摇摇晃晃地停留了十日,这远远达不到“quaranta giorni”(意大利语,意为40天)政策要求的停泊40天方可靠岸的规定,而如今的“隔离”一词便是衍生于此。
此行之前,济慈一直愁肠郁结。他在《初见额尔金石雕有感》(On Seeing the Elgin Marbles for the First Time)一诗中写道, “……催命的无常沉重地压着我,像无可奈何的睡眠。” (他还在五音步诗《夜莺颂》(Ode to a Nightingale)中写道:“我几乎爱上了静谧的死亡。”)
济慈和朋友此番离开英国,启程前往意大利并非为了度假,而是寄希望于意大利温暖的气候能够帮助济慈恢复健康。他的咳嗽越来越厉害了。自从某天早晨看到枕头上的血迹之后,他便知道,病入膏肓的自己能够挺过肺结核生存下来的几率微乎其微。罗马成了他此行的最后一站。而在抵达罗马之前,他就这样一直流落在海上。
济慈作品《夜莺颂》的手稿
我猜想,后来的传记作者一定会对济慈心怀感激,因为他利用这段空闲时光撰写了一本简短的回忆录,记录了他不那么富有诗意的成长历程:幼年时,他所爱之人几乎都离他而去,他居无定所、穷困潦倒,还要对抗那些总是嘲笑他身高的霸凌者。度过艰难而悲惨的少年时期,14岁的济慈给医生当学徒,接受医学培训,这是一段可怕的经历,而在那之后,有好几年的时间济慈都在Guy Hospital医院接受令人毛骨悚然的其他培训。
在此期间,他爱上了诗歌,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学习写诗。他一步一步奋斗着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而他所求不过是“跻身英国诗人之列”。他确实做到了。
济慈这一段短暂的隔离期深深吸引了我。 当时,快25岁的济慈只剩下四个月的寿命,他觉得自己“虚无缥缈,仿佛我的整个生命已经是死后的存在”。他创作了双关语;他阅读拜伦的诗。一位同样患有肺结核的女性乘客让他感到恼火。之后他把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写下来,想要弄清个中意义。这份记录让人不忍卒读。
当然,他不会知道,对于像我的后世读者来说,他关于生平事迹的记录也获得了巨大成功。
诗人济慈的肖像画
隔离期间,只有一封写给布朗夫人的信得以留存下来。济慈深爱着布朗夫人的女儿范妮,此番离去,已是诀别。“啊,若我还能感受到自己是这个世界上的公民,我会向你好好描述那不勒斯湾。”他写道, “帮我问候范妮,告诉她如果我身体康健,我要用一叠纸来书写那不勒斯港,但这看起来就像是我的梦想。”
一叠纸。四大张羊皮纸折叠成了24页。想象一下,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济慈在纸上描述了近在咫尺的这座城市。
意大利。一弯月亮爬上来,于穹顶投下银色的光芒,远处的钟声响彻大海,呼吸之间是温暖而潮湿的空气。我看见他倚在栏杆上。“几乎爱上了静谧的死亡”这样的诗句已经抛诸脑后。他在这段隔离期间面临着人生的终止。他找到了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望。他留下了一个充满活力和浪漫主义的年轻人的形象,而他的诗歌中充满了忧郁。这个壮丽的海湾就在他的眼前。他却没有精力在一叠纸上留下匆匆片语。
从Maria Crowther号下船后不久,济慈在一封信中写道,他如同被困在房间里的鸟一样惊慌失措。他无法想象自己再也见不到范妮。“我不敢给她写信,也不敢收到她的来信,我怕看到她的笔迹会心碎,哪怕只是听到别人口中的她、看到她的名字,都让我无力承受。”
200年过去了,这种痛苦依然挥之不去。我好奇的是,如果他得以康复,他的诗会不会有所不同。
那不勒斯(《孤独星球》)
居家隔离已是第六日,我一直都在品读济慈。
他写道:“我游历了很多金色的国度。”
我也是。读大学那会,我以为“金色”意指梦想,但我发现,金色指代是的书本侧面的镀金。我购买的济慈书卷并不是镀金精装书;这些书已然泛黄,让人有些尴尬的是上面还有我标注的下划线。我的猫匍匐在沙发上,我对着他念了许多隽永的诗句,但他盯着窗外,根本不在意我们的处境:一场病毒如同圣经中的蜂群在世界各地肆虐,随心所欲、反复无常,就像侵袭诗人肺部的病菌一样,落下、锁定、繁殖。
我们不知道我们会隔离10天还是40天。抑或更长时间。到此为止。维苏威火山会爆发吗?我们不甚了解。
维苏威火山
这让我又联想到了济慈。他对他的“消极能力”一说心生向往: 一个人“能够安于不确定、神秘与怀疑,而非性急地追求事实和原因”。 这也是我今日的收获。
事实和原因都会发生变化 。色彩浓重的“有能力”、积极主动的“存在”,还有“不确定”这种流动的状态,让你在其中漂浮、游动、欣赏美景。
《夜莺颂》 译·穆旦
我的心在痛,困顿和麻木
刺进了感官,有如饮过毒鸠,
又象是刚刚把鸦片吞服,
于是向着列斯忘川下沉:
并不是我嫉妒你的好运,
而是你的快乐使我太欢欣——
因为在林间嘹亮的天地里,
你呵,轻翅的仙灵,
你躲进山毛榉的葱绿和荫影,
放开歌喉,歌唱着夏季。
哎,要是有一口酒!那冷藏
在地下多年的清醇饮料,
一尝就令人想起绿色之邦,
想起花神,恋歌,阳光和舞蹈!
要是有一杯南国的温暖
充满了鲜红的灵感之泉,
杯沿明灭着珍珠的泡沫,
给嘴唇染上紫斑;
哦,我要一饮而离开尘寰,
和你同去幽暗的林中隐没:
远远地、远远隐没,让我忘掉
你在树叶间从不知道的一切,
忘记这疲劳、热病、和焦躁,
这使人对坐而悲叹的世界;
在这里,青春苍白、消瘦、死亡,
而“瘫痪”有几根白发在摇摆;
在这里,稍一思索就充满了
忧伤和灰色的绝望,
而“美”保持不住明眸的光彩,
新生的爱情活不到明天就枯凋。
去吧!去吧!我要朝你飞去,
不用和酒神坐文豹的车驾,
我要展开诗歌底无形羽翼,
尽管这头脑已经困顿、疲乏;
去了!呵,我已经和你同往!
夜这般温柔,月后正登上宝座,
周围是侍卫她的一群星星;
但这儿却不甚明亮,
除了有一线天光,被微风带过,
葱绿的幽暗,和苔藓的曲径。
我看不出是哪种花草在脚旁,
什么清香的花挂在树枝上;
在温馨的幽暗里,我只能猜想
这个时令该把哪种芬芳
赋予这果树,林莽,和草丛,
这白枳花,和田野的玫瑰,
这绿叶堆中易谢的紫罗兰,
还有五月中旬的娇宠,
这缀满了露酒的麝香蔷薇,
它成了夏夜蚊蚋的嗡萦的港湾。
我在黑暗里倾听:呵,多少次
我几乎爱上了静谧的死亡,
我在诗思里用尽了好的言辞,
求他把我的一息散入空茫;
而现在,哦,死更是多么富丽:
在午夜里溘然魂离人间,
当你正倾泻着你的心怀
发出这般的狂喜!
你仍将歌唱,但我却不再听见——
你的葬歌只能唱给泥草一块。
永生的鸟呵,你不会死去!
饥饿的世代无法将你蹂躏;
今夜,我偶然听到的歌曲
曾使古代的帝王和村夫喜悦;
或许这同样的歌也曾激荡
露丝忧郁的心,使她不禁落泪,
站在异邦的谷田里想着家;
就是这声音常常
在失掉了的仙域里引动窗扉:
一个美女望着大海险恶的浪花。
呵,失掉了!这句话好比一声钟
使我猛醒到我站脚的地方!
别了!幻想,这骗人的妖童,
不能老耍弄它盛传的伎俩。
别了!别了!你怨诉的歌声
流过草坪,越过幽静的溪水,
溜上山坡;而此时,它正深深
埋在附近的溪谷中:
噫,这是个幻觉,还是梦寐?
那歌声去了:——我是睡?是醒?
撰文:Frances Mayes
翻译:唐尘
编辑:任芳慧
编辑助理 :于洋
标题图摄影: Susan Wright
维苏威火山摄影:Fulvio An iel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