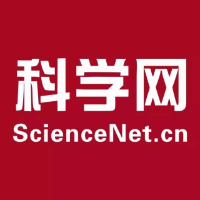2011年8月,傅伯杰(中)在黄土高原指导学生观察生态恢复。
2011年8月,傅伯杰(左一)在陕北黄土高原指导学生开展水土保持研究。
1996年,傅伯杰(左一)主持欧盟国际合作项目,与国外合作者在黄土高原安塞水土保持综合试验站。
“坚持一个研究方向,不断深入;坚守一个区域,逐渐扩大。”在5月9日在线举行的中国科学院大学院士大讲堂上,自然地理和景观生态学家傅伯杰如是激励学子。
戎马科研半生,这是傅伯杰的心里话。30多年来,他与团队一起,围绕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植被与生态恢复等问题展开攻关,让昔日的荒山秃岭变成一片“绿海”,并把中国的景观生态学研究推向了国际前沿。
“黄土高原生态修复具有中国的特殊性,也具有世界普遍性的意义。”傅伯杰说。如今,他与团队又把目光着向黄土地上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以及全球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以期为区域科技、经济发展以及未来地球科学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从“玩笑”到热爱
几年前,傅伯杰在给北京市中学生做科普时候,曾劝尚未选定专业的学生学地理,因为这是一门探索自然规律、昭示人文精华的综合性学科。“偏向于理科的,可以选自然地理;偏文科,就学人文地理;想学技术方面的,可以学地理信息系统。”他说。
不过,谈起与地理学的缘分,傅伯杰却一度认为那几乎是“命运的玩笑”。
1977年恢复高考后,傅伯杰在咸阳机器制造学校(中专)的选拔考试中拔得头筹,拿到了该校寥寥无几的高考参试“通行证”。当年,全国有570万考生,录取名额仅27万,占比仅4.7%,傅伯杰又“幸运”地成为被录取者之一。
然而,拿到陕西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傅伯杰,在打开通知书那一刻却懵了。
“学校是不是把‘物理系’错写成了‘地理系’?”这是傅伯杰当时的第一念头。因为他报考的自动控制、无线电等专业均与地理系毫不沾边。
后来,傅伯杰了解到,当年陕西师大地理系招收的七十名学生中,除了两人,其余都是被调剂过来的。有同学不愿服从调配,因为当时地理学并非“高大上”的学科。一些人调侃:“认识五百汉字,就能学地理,还需要学四年?”
带着这样的偏见,傅伯杰踏入了地理学领域。随着深入学习,他才发现,地理学是结合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门交叉学科,涉及地貌、土壤、植物、人文、工业、气象等各方面内容,这个“综合”的特点非常符合他的兴趣。
这也让傅伯杰越钻越深。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本科毕业以后,他考上了陕西师大自然地理专业攻读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然而他却没有停止继续探索的脚步,一年后便师从我国著名地理学家林超教授到北大读博。此后又先后到英国、比利时联合培养和做博士后。
坚守黄土三十年
从1982初年读硕士算起,一晃傅伯杰从事自然地理学研究已经38年。他把这些年的研究总结为三个阶段:1982~1995年,黄土高原土地类型和土地评价研究;1995~2008年黄土高原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研究;2008年至今,黄土高原的生态系统过程与服务研究。
尽管研究方向在变,但傅伯杰的目光从未离开过黄土高原。作为土生土长的陕西咸阳人,这里不仅是傅伯杰的故乡,也是他科研的根。
黄土高原横跨我国青、甘、宁、内蒙古、陕、晋、豫7省区,总面积64万平方公里,其水土流失面积接近43万平方公里,是我国乃至全球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加剧,导致土地肥力减退,农业和经济收益下降,陷入‘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傅伯杰说。
出于关切,1983年,读硕士二年级的傅伯杰就发表文章探讨黄土高原的生态平衡,他提出在摸清水土流失规律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建立不同的生态区,以林牧业为主、农林牧全面发展,恢复生态平衡。此后,这也成为他研究的主要内容。
同样在1983年,傅伯杰还在《生态学杂志》发表了另一篇题为“地理学的新领域——景观生态学”的短文。这也为他此后向景观生态学进军埋下了伏笔。
上世纪80年代,景观生态学作为地理学和生态学的交叉研究方向刚刚兴起。基于对黄土高原生态失调的观察研究,接触到相关知识的傅伯杰对此进行了初步的思考:“景观生态学是当代综合思想在地理学研究中的反映,是生态学向地理学的渗透,也是地理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不过,直到1995年,从比利时回国的傅伯杰与欧洲科学家合作申请到欧盟的一笔70万欧元的经费,他才开始带领团队进入这个新的领域,并把延安市宝塔区羊圈沟作为研究黄土高原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的“根据地”。
在这个有着典型丘陵沟壑的陕北农村,傅伯杰与团队开展了长达十多年的观测研究,他们在小流域尺度上对土壤水分、养分和土壤侵蚀以及土地利用变化等开展了系统的研究。这是国内首个较系统的流域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长期观测研究,同时也受到了国际瞩目。
世纪之交,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指出,全球生态系统服务有60%的服务功能在退化,影响了区域和全球的生态安全。该报告把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推向了新的国际研究前沿。联合国和英、美等国先后提出相关生态行动计划。
傅伯杰又带领团队开始生态系统服务研究,走出羊圈沟,把研究拓展到不同尺度的生态系统过程和服务中,在黄土高原实现了地理学“新的综合”。他们开展了黄土高原南北、东西样带调查,测量了不同地区的降雨量、植被覆盖和固碳、固氮等特点,明晰了影响黄土高原产流产沙和黄河泥沙含量变化的影响因子。
研究发现,在黄土高原南北、东西样带上降水量不同的地方,存在着种树和种草的分界线。比年均降水530毫米以下更干旱的地方,不适合大范围种树,更适合种草和灌木。
研究还发现,上世纪百八九十年代,坝库、梯田等工程措施是黄土高原产沙减少的主要原因,占54%。而2000年以来,植被恢复则是土壤保持和产沙减少的主要贡献者,占57%。
更需要关注的是,目前黄土高原植被恢复已接近该地区水资源植被承载力的阈值。
“可见,维持一个可持续的植被生态系统,对防止水土流失反弹和黄河泥沙具有重要的作用。” 傅伯杰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因地制宜,调整黄土高原的植被恢复结构。
从黄土高原走向全球
三十多年的黄土高原研究,傅伯杰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也让他斩获了很多荣誉。
如果不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今年5月初,傅伯杰原本要到奥地利维也纳领奖——2020年度欧洲地球科学联合会“洪堡奖章”。该奖章的授予对象是在发展中地区开展造福人类和社会的研究,在地球科学、行星或空间科学领域取得卓越贡献并产生重要国际影响的科学家。
评奖委员会在授奖词中表述:“2020年洪堡奖章授予傅伯杰,以表彰他在中国和非洲关于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效应以及平衡农业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的杰出研究并付诸实践。评审委员会一致认为,傅伯杰的研究经历和成就使他成为洪堡奖章最优秀的高水平人选,他享有很高国际声誉。”
傅伯杰获得这一殊荣,正是因为他在黄土高原土地利用结构与生态过程、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恢复方面的创新成果,以及领导全球干旱生态系统研究的卓越成就。这让他成为继中科院院士刘东生之后第二位获得该奖章的中国科学家。
荣誉背后,更多的是遇到困难时的坚持与坚守。单是在羊圈沟,傅伯杰就有无数记忆:
“我们一些学生一年中大半时间待在沟里,每到下雨天,老乡们往回跑,他们却往山上跑收集数据。
“一位学生在沟里观测了三年的数据投稿,期刊审稿后回复数据不够,他一待就又是一年。”
“很多学生传言傅老师‘不收女学生’,其实是因为初期野外住宿条件不允许。我们从老乡那里租来的只有两间窑洞,一间住人,另一间放仪器设备。”
几年前,傅伯杰“不收女学生”的传言被打破了。2014年底,黄土高原生态恢复与水土保持观测研究站在羊圈沟揭牌。让傅伯杰高兴的是,以后再去沟里做实验,研究团队就可以住在新建的二层实验小楼了。
“我们不是因为看到希望而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看到希望。”回顾走过的路,傅伯杰说。他嘱托青年学子,做研究不是“一口吃一个胖子”,而要循序渐进,扎扎实实不断开拓,勇于创新,不能套翻别人的东西。
当前,地理学研究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研究主题日益聚焦人地系统与可持续发展。去年9月,傅伯杰申请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研究黄土高原社会—生态系统演变机理与可持续性。以此为依托,他正在领导全球干旱生态系统研究国际大科学计划,以期为区域、全国乃至全球的生态保护、资源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