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导言的前四部分,康德层层深入,从宏观的目标入手,逐渐的找到了达成其目标的核心关键,也就是“先天综合判断”。此前已经确定了“先天综合判断”的存在,接下来,康德开始着手去寻找它,看看“先天综合判断”究竟都在哪儿。
在寻找的过程中,康德发现,在理性的一切理论科学中都包含先天综合判断作为原则,我们来看一下他是如何论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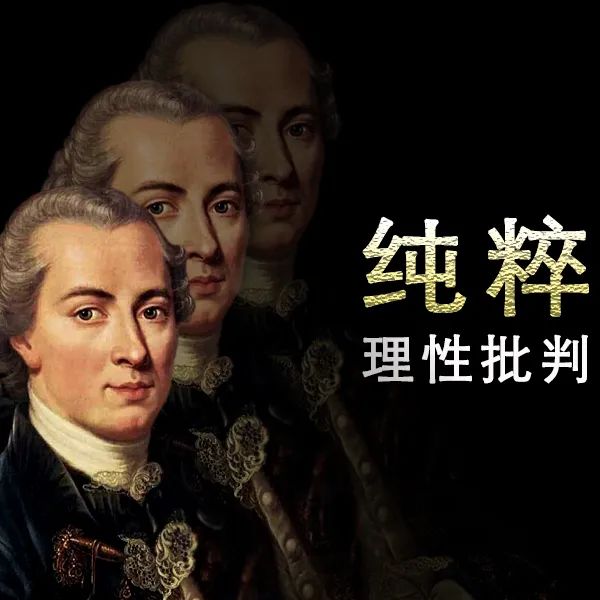
Day 10-2020年5月20日
康德所说的理性的一切科学理论科学,主要就是三类:数学、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哲学),既然做了判断,那就要一个个的去分析,康德还是首先选择了数学。
1. 数学的判断全部都是综合
这条定理似乎至今尚未被人类理性的分析家们注意到,甚至恰好与他们一切推测相反,尽管它具有无法反驳的确定性并有非常重要的后果。
这里康德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在康德的那个时代,大多数哲学家都会把数学看作是由分析判断构成的,而不是综合判断构成的。例如康德主要回应的怀疑论的代表休谟就认为人的一切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关于对象的知识都是综合的,唯独数学和逻辑学除外,因为数学和逻辑学不是关于自然对象的知识,而仅仅是关于观念和观念之间的关系的知识。
数学的观念都是人造的,跟自然对象没有关系,然后人们根据构造的概念,去分析数学的原则。为什么康德要另辟蹊径,认为数学是先天综合判断呢?实际上承认在一门科学里,先天综合判断的位置,本质上就是承认了人的认识能力以及能动性,在这门科学里将会发挥作用。
如果一门科学都是分析判断,那么判断的过程和结果都在这个判断当中,就不需要任何人的参与也会得出,这样人作为认知主体的价值又怎么体现呢。而作为所有科学中最成熟和近乎完美的典范,数学这个堡垒必须要攻克,如果数学是先天综合判断,那么就会解决认知论当中的绝大多数问题。接下来康德就会深入的论述为什么他会跟其他的哲学家看法不同。
这是因为,人们由于看到数学家的推论全部都是依据矛盾律进行的(这是任何一种无可争辩的确定性的本性所要求的),于是就使自己相信,数学原理也是出于矛盾律而被承认的;他们在这里是弄错了;因为一个综合命题固然可以根据矛盾律来理解,(它只是应用矛盾律来展开自身,)但只能是这样来理解,即有另外一个综合命题作为前提,它能从这另外一个综合命题中退出来,而绝不是就其自身来理解的。
在之前的小结中,我们已经大概了解到,分析判断实际上是依照矛盾律来最终确定的,比如“A是B”这个判断,由于在A的概念里已经包含了B,所以这个判断就近似于“A是A”,那么这个判断就是成立的,否则A是A,A又不是A,就会产生矛盾。
所以在这康德先说的是,虽然数学基本上也都是出于矛盾律的,但不能因为数学原理和分析判断都是出自矛盾律而就认定数学原理是分析判断。康德还进一步解释到,如果非要说数学原理跟分析判断一样的话,那也是因为在原理的传导中,应用到了分析判断,比如“A=B,B=C,那么A=C”这样一个综合判断,由一个命题传导到另一个命题时,分析是奏效的,但对于A=B这个判断自身还是综合的判断。
首先必须注意的是,真正的数学命题总是先天判断而不是经验性的判断,因为它们具有无法从经验中取得的必然性。但如果人们不愿意接受这一点,那么好,我将把自己的命题局限于纯粹数学。这一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它不包含经验性的知识,而只包含纯粹的先天知识。
这一部分实际上是康德做了一个铺垫,他马上要进行详细的论证,但在这之前,首先明确数学命题一定是先天的而不是经验的,他觉得这应该不会引起太多的反驳,就算有反驳,那他就把范围再缩小一些,就看纯粹数学,也就是不包含经验的部分,接下来康德就开始举例子来论证数学原理是先天综合判断而不是分析判断。
虽然人们最初大约会想:7+5=12这个命题是个单纯分析命题,他是从7+5之和这个概念中根据矛盾律推出来的。然而,如果人们更切近考察一下,就会发现,7+5之和的概念并未包含任何更进一步的东西,而只包含这两个数结合为一个数的意思,这种结合根本没有使人想到这个把两者总合起来的唯一的数是哪个数。
康德用了一个最简单的算数等式作为例子,他的关键点就是在于,分析判断的核心是在主词提出来之后,人们就会直接或者简洁的想到谓词是包含在其中的,也就是可以联想到这个谓词。比如5+7=12这个命题中,5+7作为主词,究竟是不是可以让人直接联想到12呢?康德认为不能。
这部分的论断其实并不是非常的确凿,因为对于我们熟悉加减法的人来说,看到5+7就会直接得到12,所以这个判断应该是包含在5+7当中的。但康德不是这么认为,他的想法应该是假设,如果一个没有算过5+7的人,即一个初次计算的人,根据数学规则是无法将其跟12联系到一起的,那么这个人的思维过程是什么呢,康德接着解释到。
12这个概念绝不是由于我单是思考那个7与5的结合就被想到了,并且,不论我把我关于这样一个可能的总和的概念分析多么久,我终究不会在里面找到12。我们必须超出这些概念之外,借助于这两个概念之一相应的直观,例如我们的五个手指,或者五个点,这样一个个地把直观中给予的5的这些单位加到7的概念上去。
因为我首先取的是7这个数,并且由于我为了5这个概念而求助于我的手指的直观,于是我就讲我原先合起来构成5这个数的那些单位凭借我手指的形象一个一个地加到7这个数上去,这样就看到了12这个数产生了。要把5加在7之上,这一点我虽然在某个等于7+5的和的概念中已经想到了,但并没有想到这个和等于12这个数。
这两段话,看似有些复杂,实际上如果我们让自己回到童年,想象自己第一次做算术题的时候,看到5+7,并不会直接得出12,比如先拿7作为基底,然后想象7加上自己的5个手指,一个一个的数下去,最终会得到12。所以虽然我们可以想到5+7这个两者之和的概念,但我们想象不到12这个数。
所以算术命题永远都是综合的,对此我们越是取更大的数目,就越是看的更清楚,因为这样一来就明白地显示出,不论我们怎样把我们的概念颠来倒去,我们若不借助于直观而只借助于我们的概念作分析,是永远不可能发现这个总和的。
就此康德给出了结论:算术命题永远都是综合的。隐含的概念就是在算数等式的两边,数字的关系不是自明的,并不是从等式的一边就能看到另一边的结论,而是需要借助人直观的中介。所以它是综合的判断。
其实在此并不需要绕太多弯去琢磨这个问题,就像之前所说,综合判断实际上是一种需要人参与的判断,所以康德在此明确的意思是,即便是算数这种最简单的纯粹数学问题,都需要人的先天直观参与,仅靠等式是无法自证的。这也就能强化人的能动性在数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了。
但是,但凭这个论断,实在是过于牵强,很难说到底是分析还是综合,与其说这是个论证,不如把它看作是康德的一种信念,我们也是只有理解了这种信念,才能在康德的理论体系中继续下去。
紧接着康德又用纯粹几何学的原理做了例证。
同样,纯粹几何学的任何一个原理也不是分析型的。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这是一个综合命题。因为我的直的概念决不包含大小的概念,而只包含某种性质。所以“最短”这个概念完全是加上去的,而决不能通过分析从直线这个概念中引出来。
在这里,康德用“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这个命题作为纯粹几何学的原理是综合命题的例证。他的意思是,直线的概念是直,它不包含长短的这种度量概念,所以最短这个概念是外化于直线的,也就是说是后加上去的,所以这个命题就一定不是分析的,而是综合的。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天然的觉得这种判断是一种分析判断呢?康德接下来就还原了这种想法。
在这里,通常使我们以为这种无可置疑的判断的谓词已经寓于我们的概念之中、因而该判断似乎就是分析性的那种信念,只不过是用语含混所致。因为我们应该在一个给予的概念上再想出某个谓词来,而这种必要性已经附着于那些概念身上了。但问题不在于我们应该想出什么来加在这个给予的概念上,而在于我们在这个概念中实际想到了什么,即使只是模糊地想到了什么,而这就表明,这谓词虽然必然地与那概念相联系,但并非作为概念本身所想到的,而是借助于某个必须加在这个概念上的直观。
康德的意思就是,造成我们认为这种命题是分析命题的原因是在于语言的混乱。他提出了个判断标准就是,在谓词还没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词是不是能够在实际中想到谓词。比如“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我们看到直线之后,似乎有些模糊的感觉,但是一定不会直接想到最短,一定是通过某种直观之后才能做出判断,所以这就能证明其不是分析判断而是综合判断。
在此个人的理解,依然是我们要把这个当作是康德的信念,而不要去过多的浪费经历分析,康德可以为综合提出解释,但我们同样也可以让分析成立。比如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这个判断究竟是什么,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直线这个概念,以及如何给它下定义,因为如果我们给直线的定义就是平面上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那么这显然就是一个分析判断。
所以还是那句话,在读康德的时候,我们先把这些当作他的信念基石,这样才能跟着他一起构建理论大厦,否则在还没有看到他的大厦之前,就把他的地基否定掉,我们就会错失在这个时代读康德的意义——并不是去钻研其理论的正误,而是去了解他的思维方式以及他所构建体系的逻辑结构。
几何学作为前提的少数几条原理虽然确实是分析的,并且是建立在矛盾律之上的;但它们正如那些同一性命题一样,也只是用于方法上的联结,而不是作为原则,例如a=a,即全体与自身相等,或(a+b)>a,亦即全体大于其部分。并且即算是这些原理本身,尽管仅仅按照概念来说是有效的,但它们在数学之中之所以行得通,也只是因为他们能在直观中体现出来。
最后康德还是顽强的继续把他的论证说完,对此我们就不再纠结其中的问题,因为他的大意已经足够清楚。接下来就看看自然科学的论证。
2. 自然科学(物理学)包含先天综合判断作为自身中的原则。
我只想举出两个定理作为例子,一个定理是:在物质世界的一切变化中,物质的量保持不变;另一个定理是:在运动的一切传递中,作用和反作用必然永远相等。
自然科学——康德特指的是物理学——中的情况比较明朗,争议不是很大,所以康德只是举了两个例子,进行了简单论证,一个就是物质不灭定律,一个牛顿第三定律。
显然,在这两个命题上,不仅仅存在着必然性,因而其起源是先天的,而且它们也是综合命题。因为在物质概念中,我们并没有想到持久不变,而只想到物质通过对空间的充满而在空间中在场。
所以为了先天地在物质概念里再想出某种在它里面不曾想到的东西,我实际上超出了物质的概念,因此这条定理不是一个分析命题,而是综合的,但却是先天被想到的,而且自然科学纯粹部分的其他一些定理也都是如此。
对于这两个定理,康德的论证方式实际跟数学当中是一样的,即首先判断,是不是先天的,其次判断在主词中我们是否能想到谓词。很显然这两个定理都是先天的,因为它们的判定里,明确了必然性,在前文中我们了解到康德对于先天的判定,主要是在普遍性和必然性这两点上。
那么对于物质不灭定律,在物质的概念里,我们是想不到持久不变的,物质最本质的概念是对空间的占有,除此之外都是额外附加的概念,所以这个判断也是需要给物质附加一个不变的量的概念,所以它是综合判断。同样牛顿第三定律中,主词是运动物体的相互关系,但谓词是一种量的相等判断,这个概念也不存在于主词当中,所以同样这也是综合判断。
由此康德下了一个结论,子啊让你科学纯粹部分的其他一些定理也都是综合判断。随后他把目光转向了形而上学。
3. 在形而上学中,即使我们把它仅仅看作一门至今还只是在尝试、但却由于人类理性的本性而不可缺少的科学,也应该包含先天综合的知识。
实际上康德是没有信心将之前的形而上学称之为科学的,所以他谨慎的说这是一门可以当作正在尝试的科学,但对此他也充满信心,就是形而上学由于是关于人类理性的本性的科学,所以就应该包含先天综合的知识。
并且它所关心的根本不是仅仅对我们关于事物的先天造成的概念加以分解、由此做出分析的说明,相反,我们要扩展我们的先天综合知识。
为此我们必须运用这样一些原理,它们在被给出的概念上增加了其中不曾包含的某种东西,并通过先天综合判断完全远远地超出了该概念,以至于我们的经验本身也不能追随那么远。例如在“世界必然有一个最初的开端”等命题中那样。
康德对形而上学的理解就是这门科学不是对我们已有的那些概念进行分解,就如他之前所说的,这种分析的方式虽然可以让人认识的更清晰,但是产生不了任何新的洞见的。所以形而上学应该是我们通过理性扩展先天综合知识,扩展我们的概念,可以在更大维度,更大的整体中去思考更大问题的一门学问。
所以形而上学至少就其目的而言是由纯粹先天综合命题所构成的。
对于形而上学,康德在此更像是在表达他的愿望或者说之前提到的信念,他认为形而上学就应该是为了扩展人类思维可能性服务的,而不是去分析某一些具体的对象,把它们搞得清楚明白。总的来说这一小节的论证力度略微偏软,但信念感很强。与其说康德在论证,不如说他在宣誓,宣告着一种人能够更为主动参与的哲学的出现,宣告着人可以作为同自然规则一样的,甚至是在某些程度上要高于自然规则的更本质的东西生存在这个世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