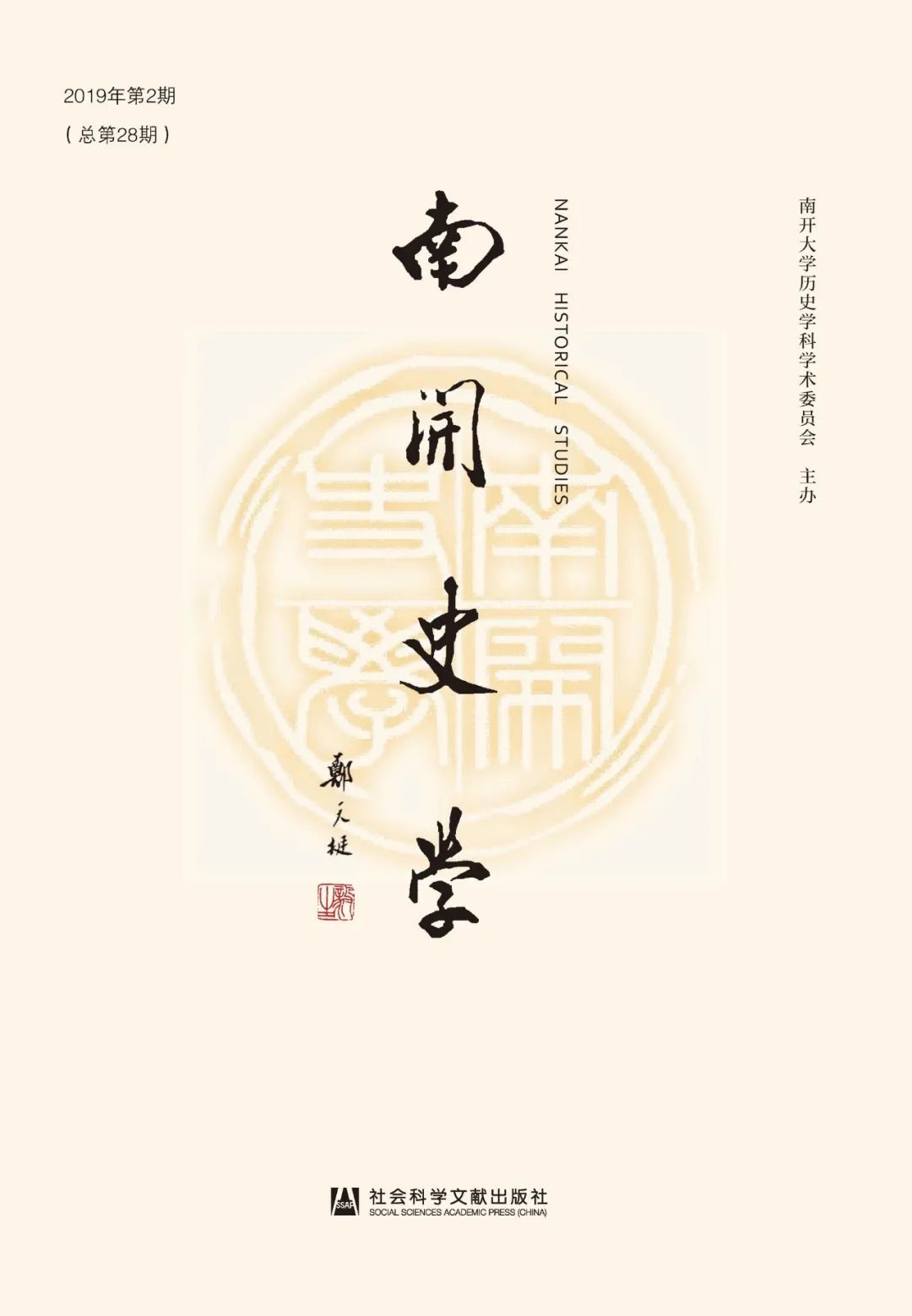
摘要:“华夷之辨”主张“内诸夏而外四夷”,或“内中国而外夷狄”的“里外分层”与“内外有别”的差序格局。中国古代汉人政权一直都将维护中原汉地“基本盘”的长治久安作为政治的首要目标,而将开拓边疆视为次要目标,甚至细枝末节,乃至危害政权的政治方式,对边疆的开拓与统治,呈现有所节制的“有限”特征。与之不同,崛起于东北草原—森林交界之地的东北政权,由于居于生态、经济多样之地,因此对于不同形态的边疆地区都充满兴趣,为了统治经济、文化远高于自身的汉人地带,东北政权强调“华夷一体”,倾向于利用政治方式将内地制度推广于边疆地区,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广阔疆域的整齐化管理。两种性质的政权虽在边疆政策上呈现历史分途,却从不同角度,利用不同方式,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过程中扮演着同等重要的历史角色。
关键词:华夷之辨华夷一体东北政权边疆整合
绪论
边疆政策的制定除受经济、政治因素的影响之外,还与思想观念具有密切的关系,并非一个完全客观的过程。在中国古代,汉人政权与北族政权在边疆政策上存在很大差异,导致这种差异的思想观念根源,是两种族群及由其所建立的两种政权在族群观念上有所不同。[1]具体而言,便是汉人政权虽在势力强盛时,有以“华夷一体”作为政治宣传,招抚边疆族群之举,但其族群观念的基本立场与核心内涵一直是“华夷之辨”,主张有差别地对待边疆族群,有条件地经略边疆地区。与之不同,本来便来自边疆地区的北族政权,不仅对开拓、经营边疆无所顾虑,而且为统治汉人地区,竭力消除自身征服者的形象,从而在政权设计中,虽有族群本位立场,但一直倡导“华夷一体”,致力于整合不同族群与地理空间。那么,“华夷之辨”与“华夷一体”的历史内涵及其差别,对汉人政权、北族政权的边疆政策有何历史影响,又如何从整体上影响了中国古代历史进程,值得深入考察与讨论。
一 中国古代“华夷之辨”的产生、发展与内涵
华夏政权及后来的汉人政权,控制着生态环境最为优越、经济最为发达的黄河、长江流域。与之相比,四裔边疆生态环境较为恶劣,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地理、经济上的优越感,促使华夏政权及后来的汉人政权,在族群、文化上形成对于四裔族群的优越意识,这便是中国古代的“华夷之辨”。如战国时期,公子成对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政策持反对态度,所依据者便是华、夷有所区别,即华夏优越而“夷狄”落后的“华夷之辨”观念。指出华夏文明十分优越:“中国者,聪明叡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2]由此指出赵武灵王不应仿照北族之俗,“今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臣愿大王图之!”[3]
在远古时期,“华夷之辨”伴随着经济方式、族群的分化,甚至对立,而逐渐产生、发展并昂扬。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经济形态,是原始农业、畜牧、渔猎等各种经济方式混合的状态,不同族群之间的经济差异及由此而导致的文化差异都较小,族群之间相应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界限。可见,用后来的术语来讲,早期中国社会实呈现“华夷一体”的历史格局。
当社会逐渐发展,步入高级文明阶段之时,经济方式开始分化,由此进一步导致族群与文化的分化。当中国步入文明社会之时,已存在农耕与畜牧两种经济形态的分工,在文化面貌上也有一定区别,于是两大经济体与族群分别被称作“华夏”“蛮夷”。但最初两大族群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族群之间的流动与融合也十分普遍。《史记》便记载了尧帝流放四位首领至四夷的传说:
讙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4]
所反映者实为远古时期农业族群、畜牧族群之间的流动与融合。对于在西汉前期对汉人形成最大威胁的匈奴,司马迁持同源之立场,认为匈奴是夏朝后裔,“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5]
远古时期,两大族群之间虽存在竞争与冲突,但由于当时两种经济方式尚有各自扩展的足够空间,相应并未产生大规模、长期的紧张关系,“华夷”尚可共存于同一秩序之下。记载两周史事的《逸周书》,指出只有将统治延伸至边疆者,才能称作“王”或“帝”。“善至于四海曰天子,达于四荒曰天正。四荒至,莫有怨訾,乃登为帝。”[6]西周具有与“蛮夷”维持积极关系的制度。《周礼》亦载:“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7]职方氏职责在于管理包括边疆族群在内的全国疆域之图。“职方氏掌天下之图,辩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蓄之数。”[8]西周诸侯国也常使用“以夷制夷”之策,率领部分边疆族群征讨另一部分边疆族群。“用天降大丧于下国,亦唯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内。”[9]“会杞夷、舟夷,雚,不,广伐东国。”[10]
可见,虽然三代中国在疆域观念上呈现差序特征,将地理空间上的边疆族群划为政治上的边缘层次,但尚未产生华夏、“四夷”两大族群的截然划分与对立,无论在族群观念还是国家制度上,基本仍保持“华夷一体”的历史格局。
这一历史格局在东周时期逐渐被打破。春秋战国时期,伴随周天下秩序逐渐瓦解,“四夷”逐渐内压,西北族群开始大规模进入关中地区。“自周衰,戎狄错居泾渭之北。”[11]甚至东周王都洛阳附近也成为“夷狄”所在。“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12]华夏政权之腹心从而为“夷狄”所占据。“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于卫,侵盗暴虐中国。中国疾之。”[13]并不断遭到西北族群的进攻。“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郑之氾邑。”[14]华夏政权从而面临腹背受敌的局面。“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15]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齐国丞相管仲辅助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口号,率领华夏政权共同抵御“四夷”的进攻。鲁闵公元年(前661),“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齐人救邢。”[16]在“四夷”的持续压力下,华夏国家中实力强大者,沿着齐国开创的道路,不断举起“尊王攘夷”的旗帜。鲁僖公十一年(前646),“夏,扬、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王子带召之也。秦、晋伐戎以救周”。[17]华夏政权从而不断结成联盟,互相拯济,共同对外,逐渐形成了惯例。鲁僖公元年(前656),“夏,邢迁于夷仪,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18]春秋时期由此形成华夏、“四夷”的二元对峙。
这一对立形势随着深入边疆腹地的楚、秦逐渐壮大与崛起,并先后成为霸主,从而打破了传统的华夷界线,而有所淡化。但春秋战国时期,“华夷之辨”观念不仅一直存在,而且经由各种学派的不断阐述,进一步理论化。进入帝制时期,伴随着汉人与边疆族群,尤其与北方族群形成长期、大规模对峙,并不断引发战争,“华夷之辨”观念从而不仅成为这一时期族群关系的真实写照,而且成为汉人或以中原地区为统治重心的北方族群所建立的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族群的政治口号与处理边疆问题、开展对外关系的政治立场。
“华夷之辨”观念产生之后,并未取代、消除“华夷一体”观念。帝制时期,中原王朝一方面与边疆族群维持了长期的对峙,另一方面却一直致力于通过武力战争或政治招抚,将边疆族群纳入统治秩序中来,恢复三代中国“华夷一体”的历史格局,从而建立理想中的“天下秩序”。因此,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一方面在族群冲突严重之时,在“华夷之辨”上持严格立场,从族群上区分华夏、“蛮夷”不同之处,强调二者之间的“异质性”,即中国古代所谓的“严夷夏之防”,从而为自身不勤远略加以辩护,可称之为“华夷之辨族群论”;另一方面在族群关系缓和之时,在“华夷之辨”上持弹性立场,从文化上区分华夏、“蛮夷”不同之处,强调二者之间的“同质性”,认为二者之间的差异源于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从而为二者之间的流动与转换预留了渠道与空间,部分实力强大的汉人政权甚至标榜“华夷一体”,从而为自身的边疆经营提供理论支持,可称之为“华夷之辨文化论”。甚至同一政权,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地区的边疆族群,交替使用“华夷之辨族群论”与“华夷之辨文化论”。可见,“华夷之辨”的两种立场与论调,为中原王朝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依据不同地缘形势灵活处理边疆地区与对外关系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是中国古代汉人文明得以长期屹立不倒,最终形成以汉人文明为核心与主体,吸收了周边文明甚至外来文明,最终形成中华文明的思想基础。
二 北方族群的长期压力与汉人政权严格的“华夷之辨族群论”
春秋战国时期,在“四夷”的持续压力下,华夏政权昂扬“华夷之辨”观念。其中最为激进的反应,是从族群观念出发将“四夷”视为与华夏截然对立、不可接触的族群。周襄王时,富辰称:“狄,豺狼之德也……狄,封豕豺狼也,不可厌也。”[19]晋国地处北部边疆,与北戎接壤而居,相应在北戎南下潮流中一直受到直接威胁。晋国魏绛便从族群论的角度称:“戎,禽兽也。”[20]认为忽视中原地区之争夺,致力于进攻“夷狄”的做法,实质上是“得兽失人”,将会得不偿失。“魏绛曰:‘劳师于戎,而失诸华,虽有功,犹得兽而失人也,安用之?……’”[21]周定王称:“夫戎狄,冒没轻儳,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22]孔子著《春秋》,维护正在瓦解的东周正统秩序,不仅对当时“夷狄”侵逼华夏提出批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23]而且坚守“华夷”的界限,“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24]否定了华夏、“四夷”在文化上的共通性。释《春秋》而成书的《左传》记载,季文子提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点。[25]
战国以降,面对“四夷”进一步紧逼,华夏政权仍坚持“华夷”之别。秦国尸佼以边疆族群为“禽兽”。“程,中国谓之豹,越人谓之貘。”[26]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礼记》,主张华夏与“夷狄”本性不同,不可推移: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通。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27]
西汉前期面对匈奴咄咄逼人之势,由于实力不逮,出于维护族群自尊,从“华夷之辨族群论”出发,将“蛮夷”视作不断抢掠汉朝的“寇贼”。比如,孔安国伪作《古文尚书》称:“蛮夷华夏,寇贼奸宄。”[28]武帝对于因国力不逮而导致的输币结盟[29]与嫁女“和亲”[30]深感耻辱,从而积蓄实力、培育骑兵,最终采取北征大漠、封狼居胥的军事战争,取得了军事层面的辉煌胜利。鉴于这一时期汉匈之间严重的族群冲突,主父偃以“禽兽”称谓匈奴,认为上古先王“禽兽畜之,不比为人”。[31]
“华夷之辨族群论”一方面成为西汉发动对匈奴战争的政治舆论,另一方面却使汉人对边疆族群的隔阂进一步加深。受到这一影响,西汉虽在军事上不断取得对匈奴作战的成功,却将边疆腹地视作不同于汉人地区的远方异域,从而欠缺在制度上深层整合的政治心理驱动,满足于与被征服边疆族群建立羁縻关系,维持间接统治。武帝时期,在汉军的多次打击之下,匈奴各部不断内附,西汉仿照政权内部实行的分封制度,将匈奴各部安置于近边地区,将其作为“属国”。“居顷之,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32]在这一制度下,匈奴各部仍保持了部落本身的完整性,汉朝因此未能在分割各部的基础上,实行直接统治。宣帝时期,匈奴呼韩邪单于来降,围绕接待礼仪,西汉君臣进行了讨论。虽然都是从“内华夏而外夷狄”的族群政治观念出发,但由于视角不同,官僚集团形成了不同的意见。丞相黄霸、御史大夫于定国从华夏优越于四裔族群的视角出发,认为应将呼韩邪单于置于西汉诸侯王之下:
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国议曰:“圣王之制,施德行礼,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诗》云:‘率礼不越,遂视既废;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圣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单于向风慕化,奉珍朝贡,自古未之有也。其礼仪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33]
御史大夫萧望之却从对边疆族群保持松散统治的视角出发,主张对呼韩邪单于实行羁縻统治,与之达成宗藩关系。
(萧)望之以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书》曰:‘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后嗣卒有鸟窜鼠伏,阙于朝享,不为畔臣。信让行乎蛮貉,福祚流于亡穷,万世之长策也。”[34]
宣帝最终采纳了萧望之的意见,下诏曰:“盖闻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单于称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35]
宣帝君臣中,以御史大夫萧望之态度最为消极,他认为汉朝应尽量减少与匈奴的往来。在应对策略上,既不与之达成和议,也不主动征伐。“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36]既在地理上与之隔绝,也在政治上保持距离。“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37]当其进犯之时,采取防御立场。“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38]在其归附之时,达成松散的宗藩关系。“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39]
西汉在西域地区,也实行间接的羁縻统治。西域各国皆保持政权独立,西域都护府仅监临其上,在作战时调发各国军队一同参加。在这种松散的边疆体制下,西汉对北方族群的统治较为宽松,相应在国力下降时,很快就会失去对北部边疆的控制。
东汉不仅与匈奴不时展开大规模战争,而且面临着西羌的长期威胁,族群冲突仍然十分剧烈。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华夷之辨族群论”观念进一步昂扬。班固著《汉书》,受到萧望之的影响,将边疆族群视为中国的对立面与祸患。“夷狄者,中国之阴也。”[40]从而再次重申“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族群地理观念,主张保持与边疆族群的隔绝状态:
《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41]
东汉和帝时侍御史鲁恭也秉持同样的族群观念,并将“气”之哲学理论附会于“华夷之辨族群论”。“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是以圣王之制,羁縻不绝而已。”[42]献帝时期,蔡邕则将长城视为“华夷”界线:“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分别内外,异殊俗也。”[43]
相比于两汉,魏晋汉人政权在汉地多年内乱之后,实力严重下降,北方族群遂进一步向中原地区呈现内压之势。鉴于此,西晋太子洗马江统著《徙戎论》,对西晋内徙北方族群的做法表示深深的忧虑,从而再次重申“内华夏而外夷狄”的族群地理格局:
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44]
唐武则天时期,鸾台侍郎狄仁杰认为“华夷”之分根植于地理环境。“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东拒沧海,西阻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45]
经过安史之乱冲击之后,唐朝实力大为下降,中晚唐时期遂呈现四裔族群不断内压的历史潮流。[46]两宋时期,北有契丹、西夏、金朝,西有吐蕃,南有大理,北方族群对汉人所构成的压力尤大。汉人虽然在北宋初年有北进以收复幽云十六州的计划,但在连遭败绩之后,除与实力较弱的西夏展开百年战争之外,对其他北方族群改而采取“事大”立场,纳币称臣。[47]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反对边疆开拓的政治舆论占据了上风,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便完全否定了汉武帝边疆开拓的功绩。指出汉武帝所行与秦始皇十分相似:“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48]但西汉并未如秦朝那样快速灭亡,源于西汉前期实行了正确的治国方针,而汉武帝也及时改正了错误,促使西汉再次返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秦之祸乎!”[49]
在这一地缘背景下,北宋士人为抵制边疆族群内压之势,便昂扬“华夷之辨”观念,以之作为激发汉人族群的政治舆论工具。北宋初年,石介鉴于辽国占据幽云十六州,形成对中原汉地威逼之势,从而撰写《中国论》,再次重申“内华夏而外夷狄”的族群地理格局。“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50]认为华夷之间应保持畛域,各守本分。“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如斯而已矣。则中国,中国也;四夷,四夷也。”[51]从而从族群地理的角度,论证契丹南下之不合理。
北宋虽然经济、文化发达,但在军事上一直较弱,不仅要向契丹交纳岁币,而且也无法形成对于西夏的军事优势。北宋士人尝试从思想观念上化解这一地缘形势的尴尬。苏轼作《王者不治夷狄论》,认为“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之也,譬如禽兽然”。[52]即通过倡导严格的“华夷之辨族群论”,标榜北宋不治“夷狄”符合汉人政权的政治原则。北宋末年安抚使安尧臣为化解这一现实困境,甚至开始挑战“华夷之辨文化论”所秉持的同化观念,认为华夏文化即使发达,也不一定能感召“夷狄”,使之归化。安尧臣再次重申“内政为本”的政治观念。“臣闻中国内也,四夷外也;忧在内者本也,忧在外者末也。”[53]但与之前学者秉持君主修德便可抚远人、王天下的观点不同,安尧臣得出了较为悲观的结论:“夫天下无内忧必有外惧,盖古夷狄之于中国,有道未必服,无道未必不来。”[54]他之所以如此主张,在于走上了“内政为本”政治观念最为内敛的道路,即既然以内政为本,那么,边疆及边疆族群便在政治治理中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圣人以一身寄乎巍巍之上,安而为泰山,危而为累卵,安危之机不在于夷狄之服叛去来也。”[55]从而再次重申“王者不治夷狄”的观点:
王者不治夷狄,春秋亦内诸侯而外夷狄。非谓中国之力不能制之,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通,种类乖殊,法俗诡异;居于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山谷、险阻之地,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56]
总之,安尧臣的核心观点是“有道未必服”,认为北宋内政已经获得了治理。“今四海之内非有乱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天时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至广之天下,无一间隙之端。”[57]但仍然无法统治边疆族群,“而南夷敢杀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崛强之王,北夷敢有抗礼之帝者,何也?生齿之数日益众,土地之产日益广,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国不尊,天下不实者,何也?”[58]便源于四裔族群与汉人具有本质不同,“有道未必服”。这一观点实反映出时人对北宋无法取得对于北族政权的地缘优势的无奈心理。
在北族政权不断内压的地缘背景下,北宋末年发生了“靖康之变”,造成了汉人从未有过的巨大耻辱。基于这一时代背景,南宋时期“华夷之辨族群论”达到高潮。《满江红·怒发冲冠》“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59]宣泄了当时汉人的仇恨情绪。鉴于北宋之灭亡与联金灭辽的失败策略具有直接关系,胡安国于是重申不与“夷狄”相盟的古老规训。在《春秋》“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条下,胡安国注云:“按《费誓》称‘淮夷’、‘徐戎’,此盖徐州之戎,久居中国,在鲁之东郊者也。韩愈氏言‘《春秋》谨严’,君子以为深得其旨。”[60]认为韩愈所主张之“谨严”,意在严格华夷之辨。“所谓谨严者何谨乎?莫谨于华夷之辨矣。”[61]指出孔子著《春秋》特意在鲁隐公与戎结盟于唐之事上注明日期,即表示出反对与批评立场。
中国而夷狄则狄之,夷狄猾夏则膺之,此《春秋》之旨也。而与戎歃血以约盟,非义矣。是故成于日者必以事系日,而前此盟于蔑则不日、盟于宿则不日,后此盟于密则不日、盟于石门则不日,独盟于唐而书日者,谨之也。[62]
在此基础上,胡安国对汉、唐与北方族群结盟而反遭祸患之事进行了梳理,实影射了北宋与金结盟反而导致政权灭亡。“后世乃有结戎狄以许婚而配耦非其类,如西汉之于匈奴;约戎狄以求援而华夏被其毒,如肃宗之于回纥;信戎狄以与盟而臣主蒙其耻,如德宗之于尚结赞。虽悔于终,夷将奚及?”[63]最终感叹道:“《春秋》谨唐之盟,垂戒远矣。”[64]
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也称“中国结昏夷狄,自取羞辱”。[65]而南宋与金朝的长期对峙,从现实格局上进一步彰显了“华夷之辨”的合理性。林之奇认为:“严华夷之辨,万世不易之治也。”[66]
明朝北上征伐元朝,宋濂在北伐檄文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政治口号,并认为“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明军北上灭元是“雪中国之耻”[67]的举动,显然延续了两宋“华夷之辨族群论”立场。但也正是在“华夷之辨族群论”影响之下,明朝如同两汉一样,在军事进攻之后,对于进一步建立边疆体制,实现长期、固定的统治,缺乏足够的政治动力。在明中后期明蒙长期对峙的时代背景下,明人也多持“华夷之辨族群论”立场。正统时期,李贤仍将边疆族群视作“禽兽”,认为其与汉人“赤子”具有本质的不同,明朝不应与边疆族群保持密切关系。“臣闻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兽夷狄。夫黎民而赤子,亲之也;夷狄而禽兽,疏之也。”[68]弘治时期大儒丘濬延续了两宋“华夷分治”的政治思想,在上呈皇帝、用作经筵教材、供皇帝施政参考[69]的《大学衍义补》中指出,“华夷分治”是自然之理:“天地间有大界限,华处乎内,夷处乎外,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70]相应远古圣王在治理天下时,便已注重区分华夷,比如舜便窜三苗、禹进攻四“夷”。“帝舜授禅之初,既首窜之于三危,至禹治水时,其窜者既丕叙,其留者犹不即工,故帝命禹徂征,然犹逆命。及禹班师而后来格,于是考其善恶而分背之焉。”[71]“华夷之辨”观念实已出现。“由是观之,可见圣人为治,拳拳于华夷之辨。盖有虞之世,固已然矣,非但始于春秋也。”[72]“禹服周畿要荒蛮夷,邈然处于侯甸采卫之外。当是之时,华夏之辨,截然有一定之限。”[73]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天下秩序瓦解,“华夷分治”格局才被打破,逐渐呈现以“夷”乱华的历史潮流。[74]因此,君主治理天下的基本原则与方案便是再次复归与维护“华夷分治”。“天生人类有二焉,华也,夷也。华华夷夷,各止其所,然后生人安而世道清。若夷有以乱乎华,则人生为之不宁矣。虽有政教,何自而施?”[75]
在明中后期国力逐渐下降的时代背景下,明朝也囿于“华夷之别”,长期缺乏处理边疆问题的变通方案。丘濬对汉唐“和亲”政策、两宋岁币政策,明确表示了讥讽态度。“其(董仲舒)言之与厚利和亲,后世亦有用之以弭祸息争者矣,然而无益焉。唐人之遣公主,宋人之纳岁币,徒费民财,损国威,其后效果何如也?后之人尚鉴之哉!”[76]弘治时期,尽管明朝由于逐渐丧失对河套的控制,在西北边疆面临蒙古越来越大的军事压力,但明人仍多坚决反对与蒙古议和。“或偷安忍耻,则主于和议,和议则紊我纲常。”[77]嘉靖时期,面对蒙古在核心边疆全线压制明朝之势,部分明人开始尝试采取灵活变通的方案,以解决这一地缘政治困境。比如顺天巡抚王大用以易马方式与朵颜达成北徙协议,但遭到这一时期主流舆论的强烈批评,王大用也因此被罢免。赵时春在批评王大用时,首先追溯了“华夷之辨”传统观念。“《书》称戎狄荒服,周公兼夷狄以宁百姓,孔子内中国外夷狄而成《春秋》,圣人之虑深矣。”认为王大用的这一做法会动摇“华夷”秩序,“亵国威以启戎心”。而赵时春提出的边疆方案仍是当时主流的长城防御:“莫若垣山堑谷,结庐屯戍,乘高瞰下,而田其中,置为永业。”[78]御史杨继盛弹劾武将系统所主张的与蒙古开展“互市”的方案,认为这一方案是汉人政权长期视为耻辱的“和亲”政策的别名,“以堂堂中国,与之互市,冠履倒置,不可”。[79]杨之立场与气节也得到当时舆论的普遍赞同。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围困北京,史称“庚戌之变”。在这一军事危机下,赵贞吉仍将互市视作耻辱,反对与俺答达成和议。[80]隆庆时期,以平定“倭寇”闻名的俞大猷,也从中国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地理封闭性角度论证了“华夷之辨”的合理性。指出天地初开之时,便赋予了中原地区与四裔边疆不同的气性。“天地开辟之始,其有深意于华夷之间乎?观其清淑秀淳之正气,凝而为中华之土。驳杂粗厉之偏气,列于中华之外为四夷。”[81]为保障中原“正气”不被边疆“杂气”所污染,上天在四周设置地理险阻加以隔绝。“若六合浩荡,华夷无限,则偏得以混正,夷得以杂华。天地独厚我中华之意,于是乎塞矣。是故于南东西三方之夷,并以溟海波涛数千万里不测之险限之,非但曰风马牛不相及也。”[82]长期以来,四裔族群大都未能对中原地区构成实质威胁。“自古及今,不能为中国大患,是不足深虑。”[83]仅有北方族群对中原地区构成了长期威胁,“所可虑者,惟东北一带万里之沙漠耳,然亦不可谓天地无意于此也。北之西偏,有黄河一水迂迤之限;北之东偏,有太行一山迂迤之限,人能因其险而守之,亦甚易也”。[84]
隆庆时期,明朝鉴于嘉靖时期北部边疆长期的军事冲突所造成的沉重压力,借助俺答汗之孙把汉那吉主动来投的偶然事件与蒙古达成和议,史称“隆庆和议”或“俺答封贡”,在一段时间内结束了明朝与蒙古之间多年的战争局面,时人甚至称这一时期为“全盛之世”。“国家数全盛,屈指必隆万。汪住既藁街,王杲亦俘献。辽疆比内地,轩盖历程顿。”[85]但包括推动“隆庆和议”的阁臣高拱与大同巡抚方逢时在内的明朝官员,仍将和议视作权宜之计,并不因此而将推动与蒙古的政治联络作为未来的长远规划。高拱首先从“华夷之辨族群论”的角度,指出明朝与蒙古存在本质差别:“夫夷狄之性,譬之禽兽,适其欲则摇尾乞怜,违其愿则狂顾反噬。为中国计,惟当顺所利,而因以制之,固非可以礼乐驯服,法度绳约也。”[86]高拱指出之所以与蒙古达成和议,一方面借鉴了嘉靖时期军事征战导致“帑储竭于供亿,士马罢于调遣”的“往岁失计”,认为当前“因而受之”,[87]可免蹈覆辙;另一方面指出了“隆庆和议”与嘉靖互市的不同,借助将互市纳入朝贡体系之中,维护了明朝的政治权威。[88]方逢时也认为开展互市是不得已之举。“贡市原系不得已之举,卫边境而救民命,贤于十万师远矣。”[89]即使如此,明朝仍然坚守了自身立场,“虏服”后才让其“贡”,[90]这与前代所采取的征伐、和亲、岁币政策相比,更是重大的胜利。“御戎无上策,狂征祸也,和亲辱也,赂遗耻也。今曰贡,则非和亲矣;曰市,则非赂遗矣。”[91]
明朝由于并未有借助“隆庆和议”进一步开拓、整合北部边疆的打算,而只是满足于停战的现状,因此对进一步整合蒙古高原,实现明蒙一体化缺乏兴趣。方逢时便秉持这一立场,反对将明制推广于蒙古的做法。“启近得报,见兵部议,欲将北虏节年所授官职分为四卫,各设司所,如中国之制,分别造册,以为他年承袭之地也。”[92]对此,方逢时之意见是“愚窃以为过矣”,依据是“夫虏贪饮食,冒货利,不可以话言晓,不可以礼义训,不可以法度绳,历代以来,鲜有能戢其心、制其暴者”,[93]即仍将北方族群视为不可“理喻”的“野蛮人”。可见方逢时也持“华夷之辨族群论”。
其实,蒙古接受“隆庆和议”,并不单纯地是俺答为保全爱孙之命或自身年老力衰,不复战争野心,而是由于当时蒙古草原遭受了严重旱灾,不得已而为之。“此时北庭荒旱草少,俺酋不复过青山,悉众屯牧威宁海之东,去大边可二百余里。其党永邵卜、朵落土蛮更苦饥困,易子而食,俺酋调之不至。昨降人云,止调到把都儿者,乃独石之外贼也。”[94]如果明朝此时以经济、政治等方式进一步援助、分化与笼络蒙古部落,那么有可能实现对蒙古的大体控制与初步改革,明末蒙古族归附、协助清朝入关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但事实是,晚明士人对边疆族群普遍持严格而消极的“华夷之辨族群论”立场。如罗汝芳称:“盖夷,兽类也,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之也。”[95]万历时期,明人仍称:“天下之大防莫严于华夷之辨。”[96]可见,在明中后期北部边疆愈来愈沉重的军事压力下,明人一直秉持的“华夷之辨族群论”立场,虽有鼓舞对蒙古、女真作战之效,却导致明朝缺乏灵活变通的政策,是造成明中后期军事困境的重要因素。
而在西域地区,明朝不仅在军事上持消极立场,而且在政治上也显得僵化,缺乏积极经营的愿望,长期与之保持松散的宗藩关系。弘治八年(1495),鉴于哈密为吐鲁番所据,明朝“乃闭嘉峪关,绝西域贡”,引发了西域各国的反向。
时西域诸胡皆言:“成化间,我入贡,皇帝先遣中贵人迓我河南,至京宴赐甚夥。今不抚我,我泛海万里贡狮子,谓我开海道,却不受。即从河西贡者,赏宴亦薄。天朝弃绝我,相率从阿黑麻,且拒命,中国能奈我何。”[97]
经过多次反复,明朝最终在嘉靖时期关闭嘉峪关,从而将本与明朝保持朝贡关系的西域诸国推向了敌人。
明朝灭亡后,汉人在国土再次沦于北族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激发与昂扬“华夷之辨”。吴三桂以叛明罪臣发动“三藩之乱”却能获得广泛响应,与这一普遍存在的族群意识具有密切关联。清末汉人再次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所获得的社会反响也反映出,“华夷之辨”思潮在清代社会虽然一直遭受压抑,却潜伏不断。
可见,在“华夷之辨族群论”影响下,中国古代汉人政权一方面倾向于对北方族群保持强硬立场,在实力足够之时发动战争,从而有助于边疆开拓的进行;另一方面,汉人政权在实力不足时,仍缺乏灵活变通的观念,从而造成军事困境。不仅如此,“华夷之辨族群论”对汉人与边疆族群异质性的强调,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汉人政权在边疆地区长期、固定统治的政治愿望,使其缺乏在边疆地区实行与内地类似的政治制度,推进边疆与内地一体化进程的政策措施,是制约中国古代汉人政权边疆开拓与经营的思想瓶颈,是促使“有限扩张主义”中“有限”内涵长期保持的主观原因。
三 汉人的边疆开拓与弹性的“华夷之辨文化论”
但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华夏政权及后来的汉人政权不断地向四隅拓展,不断接纳边疆族群,与“四夷”的关系也并非如“华夷之辨族群论”所主张的那样一直很强硬。这一方面源于农业族群与畜牧族群本来就是同出一源,存在先天性的历史联系;另一方面与“四夷”在华夏、汉人逐渐壮大扩展之时,不断凝聚势力,从而与华夏、汉人形成长期的对峙格局,逼迫华夏、汉人逐渐修改自身的心理定位,形成“华夷”在一定程度上“同质”,可以共存、流动,最终一体化的“华夷之辨文化论”。
“四夷”的强势一方面激发了“华夷之辨”观念,另一方面也开始迫使华夏国家为“华夷共存”留下了可能与空间。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政权在“四夷”压力之下,为了壮大自身实力,与边疆族群采取结盟政策。比如鲁国多次与戎人结盟,[98]齐国、卫国曾与狄人结盟,[99]楚国曾与夷人结盟,[100]晋国、秦国曾借援戎翟势力。晋惠公时期,姜戎在秦国驱逐之下东进,惠公认为其为共工之后,属华夏分支之一,将之接纳进来,并安置于南部边疆,使之成为拱卫晋国的军事力量。
楚、秦两国的相继崛起与逐鹿中原,在相当程度上冲击、改变了春秋时期的“华夷”格局与“华夷”观念。楚、秦两国本居“蛮夷”之地,处于九服中的“镇服”,不属华夏,但两国随着经济、文化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发展,对春秋时期地缘版图形成了巨大冲击,华夏各国遂允许其参与盟会,将之纳入华夏国家行列,甚至奉之为霸主。对于这一由“夷狄”进于华夏的历史转变,华夏政权尝试从文化角度加以解释,从而借鉴周朝代商的“德运”观念,认为“夷狄”积“德”便可以摆脱原来的身份,而进入华夏的行列,甚至可以成为华夏盟主。[101]
面对北戎威胁,鲁襄公四年(前569),晋国大夫魏绛与晋悼公讨论处理北戎威胁之事,虽一方面持“华夷之辨”的立场,另一方面在其威逼之下也从现实出发,主张与之达成和议,并借援其力。魏绛由此而阐发出著名的“五利”理论:
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102]
晋悼公接受了这一主张。“公说,使魏绛盟诸戎,修民事,田以时。”[103]借此将晋国霸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104]可见,春秋时期华夏国家已开始谋求与“四夷”在边疆地区的共处、互利之道。
鉴于春秋时期华夏各国与“四夷”之间的密切关系,孔子也从学理层面论证了这一格局的合理性,指出华夏与“四夷”具有交流的空间。“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105]“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106]孔子周游列国,以儒学改造现实政治的努力一再遭遇失败,甚至曾有转向四裔边疆的打算。“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107]这一时期,不仅儒家表达出“华夷”可以共存的理论旨趣,其他学派也是如此。比如道家代表人物之一文子便指出:“道德之备犹日月也,夷狄蛮貊不能易其指。”[108]
战国时期,北方赵、燕、秦国,由于长期与北方族群接壤而邻,受其影响甚至借鉴其军事优长,呈现“胡化”潮流。鉴于此,孟子虽采取批判态度,“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109]但对于“以夏变夷”却保持认可态度。秦国杂家尸佼认为远古圣王普施恩泽,甚至遍及“禽兽”。“尧养无告,禹爱辜人,汤武及禽兽,此先王之所以安危而怀远也。”[110]“汤之德及鸟兽矣”。[111]指出舜治理天下时,德泽便惠及“夷狄”:“舜之方陶也,不能利其巷下,南面而君天下,蛮夷戎狄皆被其福。”[112]这一时期,墨家代表人物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倡导天下之人应无差别地相爱、相利,其中便包含“夷狄”。墨子认为大禹治水,是出于为华夏、“夷狄”共谋福利之目的。“北为防、原、泒,注后之邸、嘑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楚、荆、越与南夷之民”。[113]指出尧舜曾分别向北、向西教化“八狄”“七戎”,并死于途中。[114]稷下道家学派的慎到,也认为华夏、“夷狄”在价值观念上有共通之处。“治水者,茨防决塞。虽在夷貊,相似如一。学之于水,不学之于禹也。”[115]先秦时期各家学说所倡“华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交流、沟通的“华夷之辨文化论”主张,为帝制中国灵活而富于弹性地应对边疆族群,开拓、治理边疆提供了理论支持。
西汉前期国力不逮时,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西汉借此休养生息,培育出强大国力,为后来发动汉匈战争奠定了基础。借助长期开展的边疆战争,西汉中后期与东汉形成了对于边疆族群的威势,边疆族群从而不断归附两汉政权,两汉政权也从“华夷之辨文化论”立场出发,积极招抚边疆族群。
唐朝既系胡化汉人所建之政权,相应在应对边疆族群时,较少纯粹的汉人政权思想顾虑。从“华夷之辨文化论”立场出发,通过军事作战、政治安抚,相对于两汉,更为主动、积极地利用联姻政策,与边疆族群皆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推动了唐代广阔疆域的形成与族群之间的密切交流。受此影响,唐代士人多有持“华夷之辨文化论”者。比如韩愈便称:“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116]
北宋虽然无法在与契丹的竞争中占据上风,却在国力上明显强于西夏,从而一直致力于运用战争方式经略西北边疆,并在政治上倡导“华夷之辨文化论”,注重对西北族群的同化。比如神宗时期,北宋便积极地推动西北族群的汉化进程。“王安石以王韶书进呈,韶言:‘已拓地千二百余里,招附三十余万口……’安石白上:‘韶如此诚善。今三十万众若能渐以文法调驭,非久遂成汉人,缘此本皆汉人也。’”[117]
明朝在秉持“华夷之辨族群论”的同时,也长期标榜“华夷一家”,[118]彰显出“华夷之辨文化论”的立场。这不仅源于明朝疆域一直保持了多种族群共存之格局。还在于明朝不断招抚边疆族群,乃至藩属国的政治策略。明初虽然标榜“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但所辖疆域一直是多种族群共存之格局。这不仅源于明初基本占据了除蒙古高原北部之外的元代旧疆,永乐之后虽然逐渐丧失对漠南部分地区的统治,但在疆域之内一直有大量滞留的旧元势力,主要居住于西北地区,被明人称作“土达”;而且在东北地区实现了对女真各部的长期羁縻统治,而蒙古部落也不断有南下归附明朝者。为安抚境内非汉人族群,明朝需要在政治舆论上弱化“华夷”之间的区别与界限,这是明朝长期秉持“华夷之辨文化论”的内因。明朝与蒙古形成了长期对峙与冲突格局,为招抚蒙古各部归附以及维持与藩属国的宗藩关系,明朝也时有宣扬“华夷一体”者,这是明朝秉持“华夷之辨文化论”的外因。
总之,中国古代汉人政权秉持“华夷之辨”。在族群冲突严重之时,秉持严格的“华夷之辨族群论”;在族群关系缓和时,转而采取富于弹性的“华夷之辨文化论”,在相当程度上致力于打通“华夷”之间的界限,甚至宣扬“华夷一家”,从而在坚持汉人本位的同时,灵活而富于弹性地应对边疆族群。这是汉人政权得以不断开拓、经营边疆的思想根源,是中国古代“有限扩张主义”中“扩张”得以长期保持的主观动力。相对而言,北方族群实力强大,且长期与汉人政权保持敌对态势,因此“华夷之辨族群论”被更多地运用至北部边疆,这也是北部边疆战争不断的根本原因。而其他边疆族群则由于较为分散、实力弱小,呈现不断归附中原王朝之势,相应“华夷之辨文化论”被更多地运用至其他边疆地带,这些边疆地带的族群从而逐渐成为中原王朝的羁縻势力或者藩属国。但无论是“华夷之辨族群论”,还是“华夷之辨文化论”,汉人政权的边疆经营都呈现“有限”特征。
四 中国古代汉人政权边疆经营的“有限”特征
中国古代“华夷之辨”观念,无论是族群论立场,还是文化论立场,都以汉人本位为前提,一直坚持“华夷有别”,只是在“差别”的强调程度与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秉持不同的观点而已,所追求的理想疆域秩序都是“内华夏而外夷狄”或“内中国而外夷狄”[119]的差序格局。这一差序格局并非单纯限于族群地理的“内外分层”,还主张在族群政治上的“内外有别”,即认为汉人与四裔族群并非平等关系,而是差等关系,所主张的也非双向交流,而是单向汉化。因此,“华夷之辨”从根本上而言,是一种“汉人中心论”,一直仅将汉地视作真正的中国,而将边疆地区视作附属地带,甚至是与汉人地区具有本质不同的无用之地。
在“华夷之辨”观念影响下,华夏政权及后来的汉人政权,一直都将实现中原汉地“基本盘”的长治久安作为政治核心目标;而将开拓、统治附属地带的边疆地区视作次要目标,甚至细枝末节、无用之举,乃至会危害政权的反向行为。丘濬认为汉人政权在政治建设上,应将主要精力投射于“华夏文明之域”,而将边疆地区视为瓦砾。“惟西与北及西南之地,尚未底于海耳。然皆限以重山叠嶂,大荒绝漠,地气既恶,人性复犷,非复人所居之处。有与无,不足为中国轻重焉。惟明主宝吾华夏文明之域,以瓦砾视之可也。”[120]相应不以招徕边疆族群,而是将保障中原汉地作为政治的最高目标。“自古帝王,皆以能致外夷以为盛德,殊不知德在华夏文明之地,而与彼之荒落不毛之区无预焉。固所谓‘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真知焉哉!”[121]
相应,中国古代汉人政权在管理疆域时,皆秉持由内而外的政治立场。成书于战国、秦汉时期的《春秋公羊传》,便指出孔子著《春秋》秉持的便是这一政治观念。“《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122]相应在边疆开拓与统治上,缺乏强烈的政治动力,且长期满足于维持对边疆地区的间接统治与松散关系,以最低成本实现天下秩序。
故而,在“华夷之辨”观念下,中国古代汉人政权的边疆开拓与统治并不强调积极进取,而是倾向于在地理上保持“内外分层”,在政治上维持“内外有别”。在四裔族群构成威胁或主动联系时,被动性开拓与经营,缺乏积极主动的热情。在边疆开拓时,倡导在具备一定条件下有节制地开展,在边疆经营时,注重将边疆族群与汉人相区别,在具体方式上也较为推崇非战争方式,相应在力度上便有所保留,呈现“有限”特征。
中国古代汉人政权边疆政策的“有限”特征,在边疆开拓方面,体现为在“华夷之辨”观念影响下,长期主张“内外分层”,将维护中原汉地“基本盘”的稳定,而非开拓边疆作为保持政权统治的首要方案。相应地,防御而非进攻,便成为中国古代汉人政权的主流军事立场,“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便是这一军事立场的典型体现。在这一军事立场之下,中国古代汉人政权为开拓边疆而发动战争,容易遭受一定的政治舆论压力,甚至巨大压力。汉武帝即位之初,西汉政权的主流边疆观念仍视经营边疆是劳而无功之事,倾向延续“和亲”方案,以维护与匈奴的和平关系。建元六年(前135),“匈奴来请和亲,天子下议”。[123]大行王恢反对和亲,主张进攻匈奴。“大行王恢,燕人也,数为边吏,习知胡事。议曰:‘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倍约。不如勿许,兴兵击之。’”[124]大司农韩安国却表示反对,指出匈奴凭借蒙古高原的广阔空间,流动作战,汉军难以与之形成决战。“千里而战,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125]而且蒙古高原生态环境与汉地截然不同,难以直接统治。“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强,自上古不属为人。”[126]汉军千里北伐,消耗极大,发动战争面临极大风险。“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且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冲风之末,力不能漂鸿毛。非初不劲,末力衰也。击之不便,不如和亲。”[127]由于这是当时大多数官员的主流意见,汉武帝便也只能听从。“群臣议者多附安国,于是上许和亲。”[128]
汉武帝虽然积极开拓边疆,但反对声音一直存在。比如司马相如便称:“天子之于夷狄,其义羁縻勿绝而已……仁者不以德来,强者不以力并。”[129]反对西汉通西南夷的做法。
东汉时期,政治舆论中的防御观念仍然十分盛行。何休注《公羊传》也称:“王者不治夷狄,犹录戎者,来者勿拒,去者勿追也。”[130]章帝时期,窦宪议征匈奴,户曹吏乐恢上书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边疆为无用之地,不应为此发动战争,而应维持羁縻关系:
《春秋》之义,王者不理夷狄。得其地不可垦发,得其人无益于政,故明王之于夷狄,羁縻而已。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以汉之盛,不务修舜、禹、周公之德,而无故兴干戈,动兵革,以求无用之物,臣诚惑之。[131]
和帝时期,窦宪再次发动北征。“和帝即位,窦太后临朝,后兄车骑将军宪北击匈奴。”[132]儒士群体仍对此普遍持反对态度,认为不当无故而征,耗费财政:
(司徒袁)安与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诣朝堂上书谏,以为匈奴不犯边塞,而无故劳师远涉,损费国用,徼功万里,非社稷之计。书连上辄寝。宋由惧,遂不敢复署议,而诸卿稍自引止。惟安独与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争者十上。太后不听,众皆为之危惧,安正色自若。[133]
班固著《汉书》,对昭帝改变武帝政策,在内与民休息,对外停止战争,给予了高度评价。
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尊号曰“昭”,不亦宜乎![134]
三国曹魏文帝在攻占河西走廊,重新与西域建立朝贡贸易关系后,曾有主动与西域建立商贸往来的意愿。“文帝问则曰:‘前破酒泉、张掖,西域通使,燉煌献径寸大珠,可复求市益得不?’”却被侍中苏则所阻:“则对曰:‘若陛下化洽中国,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贵也。’帝默然。”[135]
与两汉相比,唐朝开拓边疆的力度更大,唐太宗也持“华夷一家”政治观念,但这一时期的政治舆论,仍多有反对边疆开拓者。贞观十四年(640),黄门侍郎褚遂良鉴于安西都护府耗费较大,上奏称:“臣闻古者哲后临朝,明王创制,必先华夏而后夷狄,广诸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返;始皇远塞,中国分离。”[136]
近世时期,汉人不仅受到北方族群的长期压制,而且儒家思想对政权的影响愈来愈深,宋、明两朝不仅在边疆开拓上采取了更为谨慎与保守的立场,而且在政治舆论上也呈现同样的思想取向。北宋欧阳修重申“内华夏而外夷狄”的族群观念,指出中原王朝不应“勤远略”,“先王肇分九州,制定五服,必内诸侯而外夷狄,姑务息民,弗勤远略”。[137]而应对外采取防御立场:“其来也,调戍兵以御之;其去也,备战具以守之。修利隄防,申严斥堠……盖圣人制御戎之常道,严尤所谓得其中策,古今大概,在乎谨边防、守要害而已。”[138]如果四裔族群自动归附,则维持松散的宗藩关系,“或来献贡,得以羁縻”。[139]明丘濬同样秉持“内华夏而外夷狄”的族群观念,认为“华夷分隔”为自然之理。“夫内夏而外夷,天地之常经。荒服之外,礼教所不及者,圣王所不臣,古今之大义也。”[140]汉人政权不应将一统“华夷”、招抚远人作为政治最高目标,指出这是好大喜功的做法。“必欲腥膻之丑类,侏离蓝缕之夷,皆冠带以列位,稽颡而来朝,以此为遗后之策,以此为足以慰神灵之所想望,是乃秦皇、汉武夸大喜功之私心,非帝王内夏外夷、大中至正之道也。”[141]
中国古代汉人政权边疆政策的“有限”特征,在边疆统治方面,体现为在“华夷之辨”影响下,长期秉持“内外有别”,强调将边疆族群与汉人相区别,从而在边疆地区长期保持与内地不同的政治制度,推崇间接统治,维持松散的政治联系。
在先秦时期形成的五服、九服疆域观念中,四裔边疆在地理上处于遥远的“荒服”“蛮服”,在政治上属于远离王化之地,不应积极地直接统治,只需维持消极的间接统治。东汉马融释“荒服”,称“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释“蛮服”,称“蛮,慢也。礼简怠慢,来不距,去不禁”。[142]虽然五服、九服疆域观念是一种理想化的疆域管理模式,中国古代汉人政权的疆域治理并非如此整齐一致,[143]但在边疆地区的统治方式上,在“华夷之辨”的影响下,并不强调边疆与内地的一致性,而是主张保持差异性,也即所谓的“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144]倾向于在军事征服之后,借助当地原有统治体系,因俗而治,[145]实行间接统治。“蛮者听从其俗,羁縻其人耳,故云蛮。”[146]三国吴国孙权鉴于公孙渊归附之后再次反叛,打算亲征。士人陆瑁加以劝谏,指出应遵循圣王所持对边疆实行间接、松散的羁縻统治方式,不应为之发动战争,认为这是“弃本逐末”的做法。[147]
丘濬追溯了先秦时期形成的“五服”差序疆域制度,指出中原王朝在疆域治理上,应详内而略外。“先儒谓《禹贡》五服,甸、侯、绥为中国,要、荒已为夷狄。圣人之治,详内略外,观五服名义可见。”[148]应在边疆因地制宜地设定不同于内地的制度,这样“惟其势异而情殊,故帝王所以治之也,修其教不易其宜,随机而应变,因事而制宜,要在使之各止其所而已”,[149]以维护“内华夏而外夷狄”的族群地理格局。“虽然,其所以渐被暨及者,风闻之声,神化之教,使之闻而慕之,振而动之而已。未尝体国经野,设官分职,而以内治治之也。此无他,天地间有大界限,华处乎内,夷处乎外,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150]因此,归根结底,丘濬主张中原王朝应不治边疆。“治中国则法度宜详,治以必治也;治夷狄则法度宜略,治以不治也。观至于五千,见德化之远;及观要、荒二服,见法度之不泛及,圣人不务广地而勤远略也如此。”[151]而令其自治,“王者驭夷狄,以自治为上策”。[152]这样才能将边疆族群限于四裔边疆,而不会进攻中原汉地,汉人便能获得地缘安全。“彼既止其所而不为疆场之害,则吾之内地华民,得其安矣。”[153]在丘濬看来,汉人政权在与四裔政权的来往中,也应秉持静态、被动的立场。“曹操谓羌欲与中国通,自当遣人来,慎勿遣人往,此诚练达事体,通晓夷情之语也。”[154]不应与四裔政权积极联络:“盖中国之与夷狄,气类不通,疆域殊隔,无事时,政不必屑屑相与通往来也。非甚不得已,决不可以通使。”[155]
丘濬尤其反对汉人政权与边疆族群密切接触的出发点之一,是担心两种族群与文明发生的交流会导致“以夷变夏”现象的发生,认为这是导致“内华夏而外夷狄”族群地理格局遭到破坏,最终促使汉人文明遭到巨大冲击的历史根源。丘濬指出北方族群第一次对华夏构成严重冲击,是西周末年申侯联络犬戎,杀死周幽王。“自古夷狄为中国害,莫甚于犬戎之弑幽王也。然旋即远遁,未有据中国之地,臣中国之人,僭中国之号,而至于数十年之久也。”[156]北方族群长期统治中原地区,始自西晋末年的“五胡乱华”。而这一历史潮流之形成,根源在于汉晋内徙北方族群于近边地区。“有之,始自刘渊焉。原其所以致此者,岂夷狄之罪哉!中国之人有以感召之也。”[157]而丘濬将汉明帝迎佛视作这一现象的感性原因:
当汉明帝时,无故以梦寐恍惚之思,遣遐荒绝漠之使。迎胡鬼,致胡书,构帝王之宫以居之,屈帝王之尊以事之,其所以尊崇敬奉之者,不止被发野祭而已也。以夷召夷,遂有五胡乱华之祸,滥觞于北朝之分治,滔天于蒙古之混一,而中国之土地、人民尽为胡有矣。呜呼!不有圣人复生,则中国帝王所自立之天下,几何而不尽沦于夷哉![158]
明茅坤也认为中原王朝在治理国家时,应将边疆置于边缘地位,不应加以经营。“独不闻天子有道,则守在四夷乎?尝闻魏徵曰:‘朝廷,心腹也;州邑,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是故国势有常尊,治地不与焉;国威有常信,服远不与焉。”[159]这一观念一直延续至清代。“故先王名之(榆林)为荒服,荒者,忽也,简略也,得之矣。”[160]
可见,在“华夷之辨”观念影响下,中国古代汉人政权将边疆地区视作与内地有所差异,甚至本质不同之地,无论在边疆开拓,还是在边疆统治上,政治动力都有所欠缺,从而呈现明显的“有限”特征。在“华夷之辨”观念下,只有边疆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到与内地大体一致的程度,汉人政权才开始将之视为与内地同质之地,实行与内地相同的政治制度。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汉人政权统治之下,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主要不是依靠军事与政治自上而下地推动,而是主要依靠经济与文化自下而上地推动。这种有所局限的“有限”特征,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与制约了中国古代汉人政权的边疆开拓,是其长期保持“有限扩张主义”,维持“差序疆域”的主观根源。
五 “华夷一体”观念与中国古代北族政权的疆域扩展
与汉人政权立足于农业经济便可自保不同,北方族群所依赖的游牧经济,或者混合以渔猎、原始农业的混合经济,都收益较低,北方族群只能借助军事优势,不断抢掠人口与资源,才能维持大规模社会的长期存在。因此,相对于汉人政权,北族政权开拓边疆的动力更为充足。在中国古代,崛起于草原腹地的游牧族群虽然武力强盛,但缺乏对汉地的统治兴趣与统治能力。与之不同,北方族群中的东胡系族群所建立的政权,可称为“东北政权”,因崛起于生态、经济多样之地,对具有不同生态环境、经济形态的广阔地区,皆充满兴趣,从而不断整合汉地与内亚,建立起规模更大、内涵更为丰富的农牧国家。
在族群观念上,东北政权由于崛起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地区,因此能够在保持自身族群本位的前提下,以相对平等的姿态对待其他族群。而为了统治经济、文化远高于自身的汉人地带,东北政权强调“华夷一体”,以消除汉人的敌视意识。辽道宗指出辽国崇尚儒学,不异中华。“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161]有学者认为,辽国曾实行汉契一体的族群政策。[162]在其统治下的汉人士人,也受这一影响,秉持同样的族群立场。[163]西夏也尊崇儒学,将之作为招徕汉人士人的措施之一。“西夏盛强之时,宋人莫之能御也。学校列于都邑,设进士科以取人,尊信仲尼以‘素王’之名号,为未极于褒崇,则文风亦赫然昭著矣哉!”[164]金朝推行汉化,曾实行国人、诸色人不加分别的族群政策。[165]元朝为维护在中原汉地统治的政治合法性,倡导“华夷之辨文化论”,以打破华夷界限。元代郝经出使南宋,致书南宋两淮制置使李庭芝称:“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166]受到这一影响,元朝时期汉人士人普遍奉行“华夷之辨文化论”立场,这一观念甚至延续至明初。如朱升便为“四夷”进入中华秩序留下了可能,指出华、夷皆为人,在这一点上并未有分别。“钟五行之秀者为人,吾同胞也,奚有华夷之分,内中国而外四夷也?”[167]只是汉人加强修养,而人性完备;边疆族群在文化程度上有所不及,人性因此而不完满。“唯中国尽其性而修其行也,夷狄戕其性而亏其行也,与禽兽奚择焉?此所以严华夷之辨,天必眷中国而子之,远夷狄而外之也。”[168]
可见,近世时期,由辽、金、元、清构成的北族政权脉络,不仅在地理空间上逐渐蚕食、占领中原汉地;而且在政治观念上也逐渐挑战、颠覆汉人政权狭隘的族群意识,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169]的最终形成提供了强大推力,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疆域的开拓与经营。但具体而言,东北政权内部又有不同。辽朝在进入华北腹地遭遇挫折之后,对统治汉地有所畏惧,从而停止了继续南下的脚步,未能在整合汉地上实现更大的突破。金朝在灭亡北宋之后,由于内部政治变乱,失去了进一步统一中国的有利时机,长期呈现与南宋沿淮河对峙的地缘态势;而由于实行汉化政策,将地缘重心逐渐转向中原,对亚洲内陆的经营相应逐渐松弛,为蒙古崛起提供了历史空间。与以上两个政权不同,元朝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不仅开拓出中国历史上最为广阔的疆域,而且在地缘政治上长期保持了中原汉地与亚洲内陆的平衡,甚至更为偏重亚洲内陆,因此在政权灭亡于汉地叛乱后,却退回蒙古高原长期生存下来。而清朝借鉴之前东北政权疆域政策的经验教训,既极大地推进了边疆开拓进程,又极大地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有效治理。
对比明、清两个王朝,可以清楚地看出汉人政权、东北政权由于秉持不同的族群观念,从而在经营边疆时造成了明显的历史差异。
明朝作为驱逐北族政权而重建之汉人政权,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政治口号,在自我定位上,仍以传统汉人政权为旨归。在族群观念上,朱元璋为安抚疆域之内的非汉人族群,招抚边疆族群,虽标榜“华夷一家”,但在根本立场上,却继承了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重申“内中国而外夷狄”的族群观念,[170]相应在开国之初便明确表达了对外实行防御的基本政策,并将之著录于祖训之中,从而长期确立下来。指出四裔边疆及其族群,在本质上与汉地及汉人有所不同,无法直接统治。“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171]因此不应主动开拓边疆。“若其自不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172]对于势力强大、一直与中原王朝为敌的北方族群,加强防御便可以了。“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173]洪武十五年(1382),晋府长史桂彦良上《太平治要十二条》,也再次重申“天子有道,守之四夷”的传统理念。“驭戎狄之道,守备为先,征伐次之,开边衅、贪小利,斯为下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以德怀之,以威服之,使四夷臣服,各守其地,此为最上者也。”[174]在此基础上,批评了汉武帝、隋炀帝、唐太宗开拓边疆之举。“若汉武之穷兵黩武,徒耗中国而无益;隋炀三伐高丽,而中国蜂起;以唐太宗之明智,后亦悔伐高丽之非,是皆可以为鉴,非守在四夷之道也。”[175]主张明初应通过政治形式招抚四裔族群,而不应发动战争。“今海内既平,车书混一,蛮夷朝贡,间有未顺,当修文德以来之,遣信使以喻之,彼将畏威怀德,莫不率服矣,何烦勤兵于远哉?”[176]对于北元残众,加强防御便已足够。“惟北狄遗烬尚烦圣虑,当选将练兵,分屯镇守,谨其关防,俟其衅隙,一举而殄平之未晚也。”[177]朱元璋对此甚为赞同。“彦良所陈通达事体,方禆于治道,世谓儒者泥古而不通,今若彦良可谓通儒矣。”[178]因此,在边疆开拓与治理上,针对不同的边疆空间与边疆族群,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朱元璋虽不断在“华夷之辨族群论”与“华夷之辨文化论”之间徘徊,但一直坚持华夷界限,而对于边疆族群之间的内部战争,也表达出尽量不加干涉的政策与“慎战”的思想。[179]
永乐时期,朱棣为弥补得国不正的政治合法性缺陷,致力于大规模开拓边疆,不仅连续五次北征蒙古高原,而且向南进占交趾,并派遣郑和下西洋,开拓海洋边疆,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呈现继承元帝国历史道路的历史取向。但与元帝国在军事征服之余,致力于政治进占,从而建立了立足于亚洲、影响及于欧洲的庞大帝国不同;永乐时期的边疆开拓,除对交趾实行政治进占之外,其他都仅限于军事征服或外交联络。朱棣五次北征大漠并未取得彻底的胜利,也未设计长期、固定统治蒙古高原的相关制度。同样,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并未有将明朝势力扩展于海洋边疆的政治愿望,而只是将宗藩体系进一步推广于海洋世界。[180]永乐七年(1409),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朱棣的敕谕明确表明了这一历史内涵:
皇帝敕谕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人等: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致失所。今特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遵朕言,循理安分,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摅诚来朝,咸锡皆赏,故兹敕谕,悉使闻知。永乐七年三月 日。[181]
宣德六年(1431),郑和、王景弘等在第七次下西洋之前,在福建长乐南山重修天妃行宫,立碑以彰显天妃神迹,同样表明了这一政治目的:
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固远矣而程途可计。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琛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迄今七次,所历番国,由占城国、爪哇国、三佛齐国、暹罗国,直逾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域,迥隔于烟霞缥缈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者,诚荷朝廷威福之致,尤赖天妃之神护佑之德也。[182]
跟随郑和一同出使的费信,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夫王者无外,王德之体,以不治治之。夷狄之邦,则以不治治之。”[183]伴随明前期开拓边疆的行动,明朝再次在东亚、东南亚、中亚建立了松散的区域国际秩序——“中华亚洲秩序”,形成了“万邦来朝”的盛世局面。
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万方,遣使四出招徕。由是西域大小诸国莫不稽颡称臣,献琛恐后。又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抵日出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自是,殊方异域鸟言侏之使,辐辏阙廷。岁时颁赐,库藏为虚。而四方奇珍异宝、名禽殊兽进献上方者,亦日增月益。盖兼汉、唐之盛而有之,百王所莫并也。余威及于后嗣,宣德、正统朝犹多重译而至。[184]
明前期既然未在武力强盛之时,利用军事征服确立对边疆地区长期而固定的统治体制,相应在明中后期国力逐渐下降之后,便很快失去了对边疆地区的有效控制,尤其是在北部边疆,逐渐处于战略劣势地位。
相比而言,明朝更为积极地开拓、统治南方边疆。伴随历史进程的发展,秦汉、隋唐、两宋等中原王朝不断开拓、开发南方边疆。元朝绕道大理,灭亡南宋,相对于前朝,尤其注重对南方边疆的经营。明朝崛起于南方,接续元朝历史脉络,以空前之力度经营南方边疆。
南方边疆中,云南处于最南,先秦时期华夏政权尚未对这一地区有所经营。“况滇南乃靡莫之遗墟,而西南之僻壤,毛实不登于《禹贡》,职方未入于《周官》。”[185]帝制中国时期,中原王朝虽不断经略云南,但这一地区在元朝之前,一直保持着相对独立。“秦皇、汉武,斥土开疆,极其力方得西域,遣使通道置官;唐疲河北,而南诏无功;宋偏江左,而画斧自限。”[186]“呜呼!汉之斥土名越嶲者,以斯地实越嶲水,以彰休盛。然特为僻土服远言尔。武侯南征,天威赫著,而文治犹未遑。唐则先服后叛,宋则画界陆沉。”[187]从中原王朝角度而言,也就是所谓的“古惟以不治治之”。[188]元朝在武力征服云南高原后,借鉴唐宋土官制度,将之普遍推广于云南地区。明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云南的控制与开发。“元虽合为一统,而胡俗无讥焉。国家以纲常为治,礼乐为教,云南虽去神皋万里,而气厚风和,君子道行,洪武初元,已入荣被天言之褒矣。”[189]
对于南方边疆其他地区,朱元璋也同样加强了统治,在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比如明前中期,尚在福建许多地区实行土司制度。“闽中成、弘以前,山寇多而海寇少;正、嘉以来,山寇少而海寇多。国初州县仍宋、元旧,山林深阻,菁棘蒙密,奸宄时窃发,至乎蔓不可图。”[190]明朝经过多次军事征伐与政治经营,逐渐在这一地区推广内地的郡县制度,完成了福建内地化的历史进程。“今其地芟夷之后,悉置县司,即欲啸聚,靡所藏寄。此山寇多少所由异也。”[191]
可见,明朝在开拓、治理南方边疆方面,呈现相当的历史活力。“迨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趋调,而法始备矣。”[192]但另一方面,明代“改土归流”力度有所不足,对于广大南方边疆的统治仍大体限于实行间接的羁縻统治。“然其道在于羁縻。彼大姓相擅,世积威约,而必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惟命。”[193]嘉靖后期,李开先称:“今虽郡县其地(云南),然犹以夷处夷,流官土官仍其旧。”[194]在军事征发时,时常不服从明朝管束,甚至发动叛乱。“然调遣日繁,急而生变,恃功怙过,侵扰益深,故历朝征发,利害各半。其要在于抚绥得人,恩威兼济,则得其死力而不足为患。”[195]
明朝之所以在南方边疆大体维持间接统治,一方面与“华夷之辨”观念有关,另一方面也源于在蒙古长期压力之下,从中国古代中原王朝“重北轻南”的传统出发,渐放缓对于南方边疆的经营。“古之治夷狄者,称西南夷为最难。故当时有议罢西南夷,专事朔方;罢珠崖,以为劳师远攻者。国初法重北防,远南服,漫焉疏阔,弗经意,渐成羁縻。”[196]
与明朝相比,清朝作为北方族群建立的中原王朝,明确标榜包括“满汉一体”“满蒙一体”在内的“华夷一体”的族群观念。顺治四年(1647),顺治帝谕称:“朕出斯民水火之中,统一天下,满汉一家,同享升平,岂有歧视之理?”顺治六年(1649)重申:“满洲、汉人俱属吾民,原无二视之理。”[197]雍正帝在与曾静反复问难时,批评了汉人政权“华夷之辨”观念,指出:“曾静蛊惑于华夷之辨,此盖因昔之历代人君,不能使中外一统,而自作此疆彼界。”[198]指出清朝实秉持“华夷一体”观念。“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199]相应汉人也应转变族群意识,不应再秉持“华夷之辨”。“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孝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200]从而维护“天下一统,华夷一家”[201]的大一统格局。
清朝在使用武力不断开拓边疆的同时,也充分利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手段,致力于实现对边疆地区长期、固定的统治,并将其作为进一步开拓边疆的基础与支撑。这样,清朝的边疆开拓便如同滚雪球一样,拥有源源不断的支持与动力,从而开辟出越来越广阔的疆域。乾隆帝便指出清朝不仅在南疆获取了军事胜利,而且在这一地区推广农业经济,实现了财政自足。“况堂堂大清,兵力全盛,而回部之赋税、屯田之收获,以及沿途贸易、城仓积贮、储胥充裕,不独内地毫无飞挽馈运之劳。而陕甘两省蠲赈之恩,有加无已,闾阎初不知有军兴征发。”[202]相对于此前汉人政权完全依赖内地财力,无法长期稳定地推进边疆开拓,这是一种实质性的飞跃。“岂汉唐宋明诸代疲中国之财力,而不能得地尺寸者可比。”[203]相应边疆开拓收获巨大:“今统计用兵,不越五年,而西陲万余里,城无不下,众无不降。”[204]不仅取得了军事胜利,而且实现了政治统治。
清朝不仅开辟了广阔疆域,而且在充分观照边疆不同地区的差异,因地制宜设定相关制度的基础上,将内地制度不断向边疆地区推广,从而极大地推进了帝国疆域的一体化进程,加强了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推动了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使中国不同地区空前地凝聚起来。无论是疆域规模,还是统治效果,清朝都达到了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巅峰,成为世界近代边疆开拓潮流中的重要一环。[205]
但另一方面,在世界近代时期,欧亚大陆其他文明掀起海洋扩张潮流,海洋有取代陆地成为世界地缘政治版图核心区域与主导势力的历史趋势。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清朝由于崛起于内亚,在地缘政治上呈现重视陆疆、忽视海洋的历史选择,从而与世界近代潮流有所分歧,最终成为其政权衰亡、制度瓦解的历史根源。
结语
在远古时期,中国不同地区经济分化尚不明显,不同族群之间并未形成大规模对峙的地缘态势,相应也未形成截然对立的族群意识。这一族群格局如果用后来术语加以描述,便是所谓的“华夷一体”格局。伴随历史的发展,居于中原地区的族群依托这一地区较为优越的生态环境,逐渐发展出专业而发达的农业经济,在文化上逐渐形成先进的华夏文明,并借助武力不断向四方开拓,从而与四裔族群形成长期的对峙、冲突态势。由此不仅逐渐产生出更为明确的族群意识,而且形成了相对于四裔边疆族群的优越感,华、夷二元对立的族群意识由此产生,并借助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学派不断的理论阐述及帝制时期汉人与北方族群长期对峙的地缘态势,长期延续下来,这就是所谓的“华夷之辨”。
在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华夏或汉人政权根据不同的地缘政治形势,对“华夷之辨”内涵进行相应的阐释。在族群冲突严重时,华夏或汉人政权秉持严格的“华夷之辨”立场,从族群上区分华夏、“蛮夷”不同之处,即“异质性”,可称之为“华夷之辨族群论”,从而为抵御边疆族群的进攻提供政治口号,并为自身不勤远略提供政治解释。在族群关系缓和时,华夏或汉人政权秉持弹性的“华夷之辨”立场,从文化上区分华夏、“蛮夷”不同之处,强调二者之间的“同质性”,认为二者之间的差异源于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从而为二者之间的流动与转换预留了渠道与空间,部分实力强大的汉人政权甚至标榜“华夷一体”,可称之为“华夷之辨文化论”。甚至在同一时期,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对于不同的边疆族群,汉人政权并用“华夷之辨族群论”与“华夷之辨文化论”两种观念。“华夷之辨”的两种立场与论调,为汉人政权根据不同地缘形势,灵活处理边疆问题与对外关系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是中国古代汉人文明得以长期屹立不倒,最终形成以汉人文明为核心与主体,吸收了周边文明甚至外来文明,最终形成中华文明的思想基础。
无论是“华夷之辨族群论”,还是“华夷之辨文化论”,本质上都是一种“汉人中心论”,一直坚持“华夷有别”,只是在“差别”的强调程度与是否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秉持不同的观点而已,都主张“内诸夏而外四夷”或“内中国而外夷狄”的“里外分层”与“内外有别”的差序格局,都仅将汉人地区视作真正的中国,而边疆地区一直被视作附属地带。由于中国古代汉人政权一直都将维护中原汉地“基本盘”的长治久安作为首要政治目标,而将开拓边疆视为次要目标,甚至细枝末节,乃至危害政权的政治方式。因此,对边疆的开拓与统治都呈现有所节制的“有限”特征,边疆开拓与经营呈现被动而非主动的立场,在具体方式上也更为推崇和平方式,而非战争方式,从而在力度上有所保留。
这种“有限”特征,体现在边疆开拓上,是汉人政权更为注重对中原汉地“基本盘”的保障而非边疆地区的开拓;体现在边疆统治上,是汉人政权更为注重在边疆地区实行与中原汉地有所差异的间接统治方式,只有在边疆经济、文化发展至与内地大体接近的程度,汉人政权才在边疆地区推行与内地同样的政治制度。因此,在汉人政权脉络下,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主要不是由军事、政治层面自上而下地推动,而是由经济、文化层面自下而上地推动。“华夷之辨”是制约中国古代汉人政权边疆开拓与经营的思想瓶颈,是中国古代“有限扩张主义”疆域模式与“差序疆域”形成并长期延续的思想根源。
与之不同,崛起于东北草原—森林交界之地的东北政权,由于居于生态、经济多样之地,因此对不同形态的边疆地区都充满兴趣,积极开拓;而且由于崛起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地区,在族群观念上,能够在保持自身族群本位的前提下,以相对平等的姿态对待其他族群。为了统治经济、文化远高于自身的汉人地带,东北政权强调“华夷一体”,以消除汉人的敌视态度。东北政权由于是由人口较少的族群所建立之政权,为便于控制与管理庞大的帝国疆域,倾向于利用政治方式,将内地制度推广于边疆地区,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广阔疆域的整齐化管理。因此,在北族政权脉络下,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主要是由军事、政治层面自上而下地推动。
总之,相对而言,汉人秉持“华夷之辨”观念,虽在军事、政治层面对边疆开拓与经营有所不足,却利用经济、文化优势长期而缓慢地推动了边疆开拓与族群整合;而北族政权秉持“华夷一体”观念,倾向于利用军事、政治手段,在短时间内以疾风骤雨的节奏,大力推动了边疆开拓与族群整合的历史进程。两种性质的政权虽在边疆政策上呈现历史分途,却从不同角度,利用不同方式,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过程中,扮演着同等重要的历史角色,共同推动着中国边疆“内地化”的历史进程,使中国古代的“差序疆域”逐渐朝向扁平化的“均质疆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