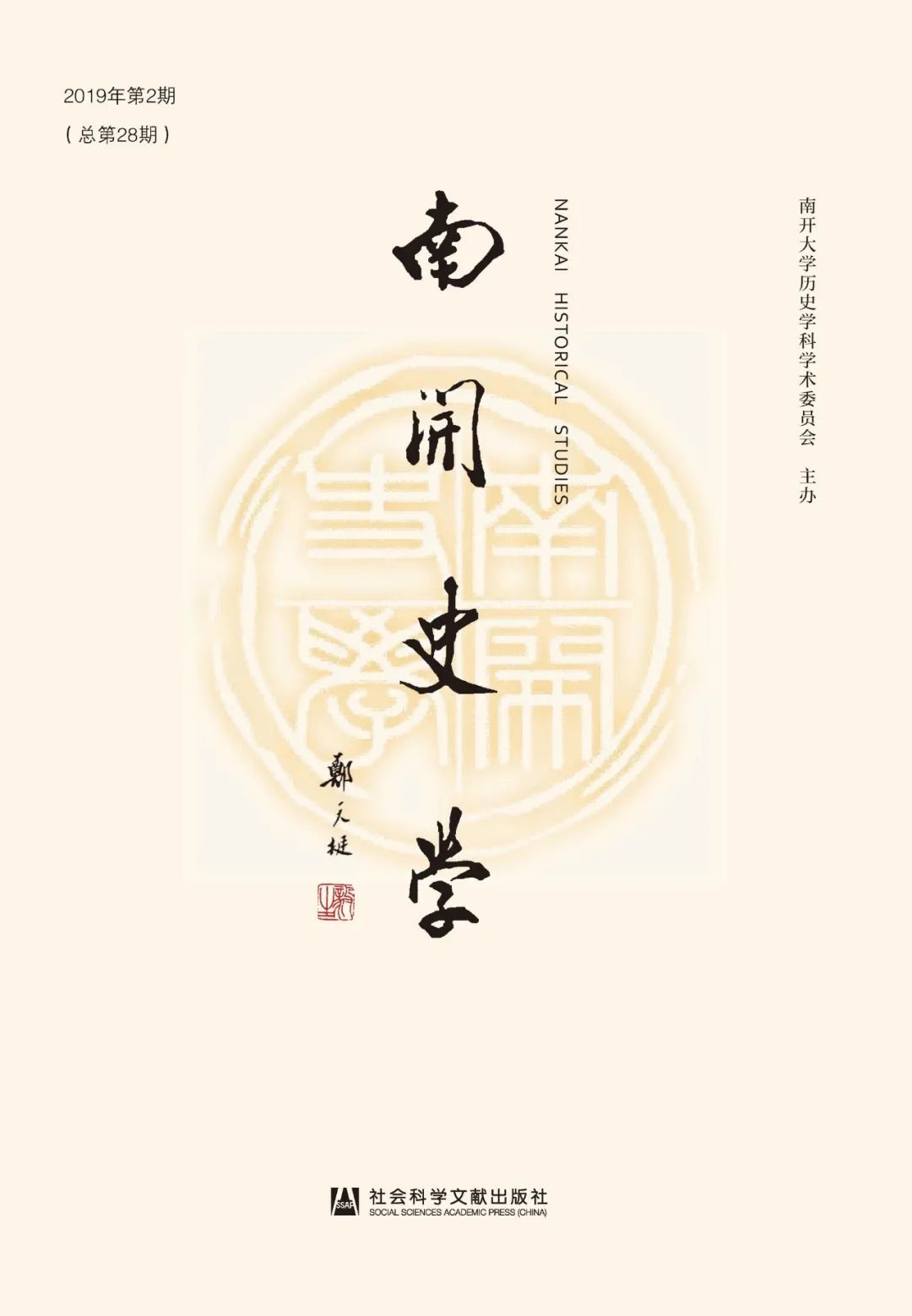
摘要:明代中期以后,商品货币经济关系的发展迫使明政府逐渐放弃对灶户的劳役征收,朝向盐课货币化的道路迈进,促使灶户从官专卖制度下的劳役生产制度中解放出来,逐渐接近小商品生产者的地位。然而,灶户中的贫富分化却因此更加剧烈,使大部分灶户沦于赤贫的境地,留在盐场成为富灶的佣工。于是贫灶与富灶的关系,已变为带有若干劳役性质的雇佣关系。明代后期,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商业资本势力大为膨胀,商业资本因此打入盐场,以提供贷款的方式收购灶户的产品。万历四十五年,改行商专卖制度后,商业资本取代了政府的力量,完全控制了盐的生产,商人不但贷给现款,而且提供原料、生产工具,成为包买主,发展出类似近代西方产业革命前夕产业化初阶(Proto-Industrialization)的散作制(Putting-out System)。
关键词:灶户盐场阶层分化盐业散作制
前言
明代中期以后,商品货币经济关系的发展迫使明政府逐渐放弃对灶户的劳役征收,朝向盐课货币化的道路迈进,促使灶户从劳役生产制度中解放出来,逐渐接近小商品生产者的地位。但这只是变化的一面。在另一方面,灶户中的贫富分化却因此更加剧烈,使大部分灶户沦于赤贫的境地。
明朝自英宗亲政以来,阉宦专政,把明初以来建立的制度都加以破坏,于是边防废弛,土地高度集中,赋役加重,农村濒于破产;同时,人民流亡,变乱四起。在这样腐败的政治下,政府既加强了对灶户的征课,同时由于政治腐败又削弱了统治力量,促成地方豪强对灶户所依赖的生产手段的兼并,使绝大多数的灶户,既丧失生产手段,又增加了负担。
一 灶户生产手段的丧失
灶户生产手段的丧失,表现得最严重的是草荡。明初,每一灶丁拨与草荡一段,虽地广狭、多寡不等,但原则上是挨户均分,各有定界;且草荡地只许自行砍伐煎盐,子孙共守,不许私相侵夺盗卖。当时草荡广阔,灶户得薪易,各安其业,其后,贫难下户因生计艰难而启豪强侵占之弊。早在景泰二年(1451),户部报称:“各处盐场原有山场、滩荡,供采柴薪烧盐,近年多被权豪侵占。”[1]虽有“悉令还官”之命,但腐败的官僚不但不执行,反而促进了地方豪强兼并贫灶的荡地。弘治元年(1488),两淮巡盐御史史简就慨叹说:“近者,草荡有被豪强军民总灶恃强占种者,有纠合人众公然采打货卖者;又有通同逃移灶丁捏称荒闲田土立约盗卖者;其出之价甚少,而递年所得之利甚多,既不纳升合之粮,而灶丁取赎者反被虚词假契,买雇积年刁泼证人,财嘱有私贪婪官吏,以行告害,其有司官吏又不审查,辄差人勾拿淹禁,经年累岁,不得归结,致使草荡日渐侵没。”[2]弘治以后,愈演愈烈,至正德年间,“小灶贫难,而豪强吞噬不已,草荡尽归于富室”。[3]两浙巡盐御史师存智上疏:“近各场滩荡,多为富豪或以近而侵削,或称贷而抵偿,或强夺而树艺,遂使鬻灶无资。”[4]且草荡地因“场司以灶丁屡易,不复拨与”,更给总催豪强占夺之机,或樵割,或开垦,“收利入己”,“仍于各灶户名下征取全丁额盐”,即贫灶不因失去草荡而免除盐课。[5]这种情况随着明朝政治腐败的加深而愈趋严重,如温州“永嘉涂荡,豪右席卷有之,而灶家不沾尺壤”。[6]嘉靖年间,屡有这类的报告。如原本灶户用来种植柴薪的涂荡,也被地方豪强所占有,嘉靖十二年(1533),御史邓直卿奏称:“长卢、山东运司……各场灶滩,所以剐土淋卤,草场所以刈草煎盐;寸土尺地皆属之官,自有界限,例禁不得开耕、变卖。近年以来,界限不明,以致豪强军民越界侵耕,日久相沿任意,或肆行樵收,或占打芦苇;遂使贫灶煎办无资,课额多累,利归豪猾,害及总催,多年展转益甚。”[7]嘉靖二十四年(1545),巡按直隶御史齐宗道也奏称:两淮三十场“各场草荡多被豪民侵占”,“近年以来,侵占益多,甚至妄作民田,诡认税粮,若有业者有之;是豪民种无盐之荡,灶民办无荡之盐”。[8]隆庆元年(1567),御史刘翾也奏称:山东“灶地多被豪右侵夺,宜视旧籍清查”。[9]明末,情况更加严重,不但“灶户之贫者,私将草塘典质债门,富者因得兼并之”,[10]而且由于军队占据盐场,擅改草荡屯田,“以致兵灶杂处,兵强灶弱,莫敢谁何”。[11]
滩荡为制盐所必需的生产手段,豪强侵占后,每将其开垦成田。至嘉靖八年(1529),两淮巡盐御史朱廷立以为荡地除供煎烧之外,颇有余地可以耕种,而灶户“畏私垦之禁,莫敢开耕”,“以有用之产而置之无用,不无可惜”;始建议草荡地除供煎烧外,其余荡地,“有愿自耕种者,即赴分司告报亩数,给帖执照,免其三年之租;以后,每亩肥厚者科米一斗,硗薄者五升”;经题请遵行。[12]嘉靖十三年(1534),两淮巡盐御史陈缟取得吏部尚书许缵的同意,确定草荡地开耕得免税三年的优惠。[13]隆庆四年(1570),朱廷立再上疏,认为灶民草荡地开种三年后,所征税粮虽一斗或五升,“税亦称重”,因此建议:“免其纳租,以助不给。”[14]这一建议采行后,盐场所在之方志不再记载开耕荡地的税额。斥卤之处,多开垦为良田,阡陌相望。万历三十三年(1605),两淮巡盐御史乔应甲巡行各场时,发现范公堤以东的荡田,已为富豪私垦为田,地方官不但不禁止,而且“擅置簿籍,公然给帖”,谓之“升租”,其中“假公济私,报一垦二者,又十场而九也”。[15]据调查结果,仅庙湾一场,即“开至九万九千二百余亩”,“一场如此,其三十场可知;况延袤千有余里,即可比拟三十郡县”。[16]草荡开垦成田,不但使“草荡日促,草无所出,盐将何办”,草价日昂,盐户煮盐成本大增,无以为继,造成灶户逃亡,产量锐减,盐价踊贵。[17]而且由于荡地开耕无税,即使须纳税也不过五升或一斗,比诸州县五六斗以上低得多。因此,地方豪民恃势占垦荡地者多,又造成“豪民种无盐之荡,灶民办无荡之盐”。[18]
灶户不但丧失草荡,有的甚至丧失了盐田。正德元年(1506),国子生沈淮《盐政奏疏》说:“又闻各场灶户,多无灰场,往往入租于人,始得摊晒。”“夫灰场者,产盐根本之地,与草荡者,皆灶丁之命脉也”,本由官家拨给,今得入租于人始得摊晒,则必为他人兼并所致。[19]而四川、云南贫灶也有因“称贷不能偿,至有以面卤准还,全井断与者”。[20]至于本为贴补灶户生活而发给的“灶田”,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万历《兴化县新志》载:灶户之田均为“邻豪侵占”,“膏腴之田尽入彼券,所遗者斥卤污莱,如筵中弃绝”。[21]四川同样有“田土被大户占种不还”的情形。[22]天启《海盐县图经》也载:“富灶田连阡陌”,“贫灶无田”。当政府优恤灶户,减灶粮耗时,富灶得利,贫灶升斗不沾,毫无实惠。[23]因此,万历《上海县志》说:“富家占地万亩,不纳粒米,而莫能究诘,贫弱不取寸草,岁输重课,而无所控诉。”于是更加深了灶户的贫富分化。[24]
至于政府发给灶户制盐“工事资本”的工本钞,因为钞价暴跌,钞法不行,已如同虚设。[25]成化四年(1468)更停止发给。[26]于是灶户不但失去草荡、盐田、灶田等生产手段,甚至连购置工具与供给口食的费用也没有了。
二 灶户盐课负担的加重
灶户一方面逐渐失去生产手段与工本钞,另一方面又因政府的加强搜刮,负担加重。
天下各产区的盐课,按规定是“各有定额”,不得任意增减。[27]其主要目的,在于保证财政有一定的收入。然而,明廷却用其他名目或方法来增加灶户的负担。例如四川盐产区,在明初有“盐井二百七十八,额课一千六百零五万九千九百三十斤”;后来有些官吏悉图陛进,渐增前额。永乐十八年(1420),于永通等九井榷出盐七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斤,列之正额,称为“新增盐”;上流、通海榷出盐五十万八千九百九十一斤,补入额数,称为“埋没盐”。永乐二十二年(1424),福兴等井户因课税难完,“别寻小井煎贴”,榷出盐七万四千六十六斤,称为“添办盐”。宣德年间,富义等井户亦寻井开煎,榷出盐一万五千三百八十八斤,称为“增羡盐”。景泰年间,户部主事汪回显又榷新旧盐井,得井一千二百八十,灶一万五千三百八十八,每丁岁办八引,盐课至二千一百三十五万三千七百四十三余斤,较原额增加五百三十万余斤,约增加三分之一的盐课。其实这些新增的盐课,“数多虚设”,是以“井虽增,人无余利”。成化初年,佥都御史江弘曾建议豁除,未被采纳。[28]自盐课改为折色后,由原额二万七千余两增至七万余两,将近原额的三倍,于是“井塌丁逃”,“灶户日日告累,课银年年称逋,虚额虽存,实征未有,公私两竭,官民俱困”。[29]
宁夏小盐池,宁夏巡抚梁问孟上疏:“额课增至二十六万有奇,第从来捞采未能足数,报部半系虚捏。”于是请定额二十万,其余减去。然而户部回复:仍然原额征课。[30]
两淮额盐银原为六十一万两,自嘉靖三十二年设工本盐后,增至九十万余两。嘉靖三十九年,鄢懋卿总理盐法时,再增至百万两。这些加增盐课,自然加重了灶户的负担。
三 灶户徭役负担的加重
除盐课以外,灶户的徭役负担也不断加重。按规定,盐场是独立于州县行政以外,“灶产、民产各有界限”,互不干涉;即使灶有民田,其钱粮也“总归运司”征纳,不属州县征科。[31]一般民户所负担的杂泛差役,灶户也可优免。然而日久之后,盐场的独立性渐失,灶户既受运司管辖,又受州县管辖。于是灶户的负担加重,既服盐场之役,输盐课,又得服州县之役,输民粮。
灶户的来源主要是附近州县的民户,民户本有田土,佥为灶户之后,田土依然属于州县。而且按规定,灶户所免的是杂役,里甲正役并不能免。于是田粮与差役的科征,成为州县与盐场两个不同系统行政组织间的最大矛盾。如国子生沈淮所说:“有司与盐司分为两家。盐司:‘吾之灶也,知督盐课而已。’有司曰:‘吾之民也,知征赋税而已。’其督盐课者,虽百方棰楚,有司不问也。其征赋税者,虽百端取索,盐司不知也。”[32]彼此尊重对方的权限,还算好的;事实上双方不但在全县之内苛敛诛求,还有许多互相干涉之事。两浙巡盐御史师存智说:“运司官秩不为不尊,所司不为不重”;然而,“灶卤滩统于运司,而钱粮办输于州县”,以致“事无统摄,掣肘难行”。因此请求朝廷下令州县,对于“事干运司者,俱听取问,无得阻挠”。请求虽然批准,但互相干涉之事并未因此而停止。[33]由这个矛盾产生两种相反的情况:有钱有势的灶户勾结官吏,利用优免的法令,逃脱赋役的负担;穷苦无依的灶户不但得不到优免的好处,反而“一身两役,赋外加赋”。
灶户优免差役,本无限制,凡灶户皆得优免。成化十二年(1476)始规定:“丁少者蠲免,丁多者亦量(加)减除。”[34]从此灶户之优免差役,因每户灶丁多少而异。其后杂役多依田粮起科。如弘治二年(1489)行“计丁免田法”,凡灶户应办全课“二十、三十丁以上者,通户优免”,其余“每丁贴与私丁三丁,除田二十五亩,免其差徭、夫马”。[35]弘治十八年(1505),又以“盐课办纳之难易,视人丁之多寡”,而改灶户三丁以下,每丁免田七十亩;四丁至六丁,每丁免田六十亩;七丁至十丁,每丁免田五十亩;十丁至十五丁,每丁免田四十亩;十六丁至十九丁,每丁免田三十亩;二十丁至三十丁以上者全户优免,共分六等。[36]其后淮浙改为四等,一丁至三丁,每丁免田五十亩;四丁至十丁,每丁免田三十亩;十一丁至二十丁,每丁免田二十五亩;二十一丁至三十丁以上,全户优免。[37]嘉靖二十八年(1549),改行“计课免田法”。时盐课多已改折,遂以灶户所纳银数为准,纳银多者,免田役多。例如六钱至七钱者,每一小丁免田三十三亩三分,四钱至五钱者,每丁免田二十五亩,二钱至三钱,每丁免田二十亩,一钱者每丁免田十亩。[38]此外又有“验田免田法”,验明灶户田产的性质,民田当差,灶田优免。如嘉靖十三年(1534),直隶巡盐御史邓直卿奏准:长卢、山东灶户,“置买民田六十亩以上者,乃听有司编差”。[39]嘉靖二十四年(1545),两淮巡盐御史齐宗道奏准:灶户之田系祖遗或买自灶户者,方许优免;其近年置买民田者,与州县人民“一体办纳正办粮差,止免佥头”。[40]嘉靖四十一年(1562),更详细规定,灶户田产以二十年黄册为准,除祖产外,视其置买田产之性质分为四类:(1)灶户买灶田,止令办粮如旧例;(2)已有灶田又买民田者,灶田优免,民田三百亩以内止编银差,三百亩以上另议;(3)绝无灶田新买民田者,如灶田例优免。(4)既有灶田及本县民田又买隔县民田者,许隔县编为力差。其免差以各户头为主,止免户长一人。[41]“验田免田法”遂趋完备。
按规定,免剩之田不得优免。然而无论任何优免之法,皆不免发生诡寄之弊。在未定免田法之初,灶户皆可优免;于是民户多诡寄灶户名下,以免杂差。弘治以后,优免虽有限定,但免剩之田粮,“止量派轻省银差”,与民户比较,“灶户完课有终岁之乐,百姓杂差无息肩之时”。因此“人民作弊”,“或借义难名色,或假冒赘婿”,用尽办法,暗将田粮诡寄于灶户名下,以图滥免。“又有豪强灶户田亩千余,人丁百拾,止当灶丁数名者”,遇州县差役及驿递、夫马,“俱各推拖不行”。[42]两淮巡盐御史陈蕙的报告称:“近年以来,诡寄之弊,不在二三十丁以上富灶之家,反在数丁以下穷户之内。或小灶明受亲戚嘱托而容寄在户者有之,或里书受人私贿及将自己田亩暗寄而灶户不知者有之,或附场卫所豪富官军承买灶田不行过割者有之,或灶买灶田仍存原户以够优免之数者有之,或田多富民因其灶户办盐人丁一丁免田二十五亩,而每户诡寄田一二十亩或三四十亩者有之”,一遇州县编佥均徭、水马等差,“有司验其丁田俱免”;致使“小灶徒负有田之虚名,富豪反受免田之实惠”。[43]这种情形很普遍。两淮富灶“恃盐课不任徭役,俱各占买膏腴田地,不止万顷;兼以逼迫穷民,捏造文契,多以重粮为轻粮,以有站为无站,甚至作为无粮、无站”。[44]于是有田仅“二三十顷而受一役者,有田积二三百顷而不受一役者”。[45]两浙灶户,“其应免姓名,强半入于富人之籍。富人与奸胥为搆假灶丁若干名”,为诡免差役之计。[46]造成“富家占地至万亩,不纳粒米,而莫能究诘;贫弱不取寸草,岁输重课,而无所控诉”。[47]浙江温州英桥王氏等盐场权势利用明廷对盐场灶户赋役的优免政策,趁机兼并田土,宗族势力不断增长。据万历五年(1577)编修的《东嘉英桥王氏族谱》,“嘉靖末年,田积逾万”,至万历初年更是急剧增加到四万亩左右。[48]福建“盐场灶丁有田粮者,照丁优免;往往奸顽富户私通贫灶,嘱托飞诡田亩在户,幸求优免,俾小灶徒负有田之虚名,富家反受免田之实惠”。[49]优免之法本以田粮为准,“贫灶无力置田,无田可免”,已对贫灶无利;加以诡寄影射,“至有一户诡报二十丁,少亦不下十丁者”,遂使“田连阡陌者概得冒免”。政府唯知恤灶,“不知所恤者皆豪灶,非贫灶也”。因此,“贫灶不沾毫末之恩,而豪灶才蒙优免之利”。[50]
由于“灶户置买民田,不复应当科差”优免的漏洞,“灶丁登册者日众,灶户之买民产者日多”,造成“编审之优免日增,而百姓徭差日重”的现象。[51]如万历年间,十年一次普查人口时,福州府各州县有司“所增才数百”,而灶户增至“四倍”。[52]于是版籍之内,“军匠日绝,灶丁日增,灶户田多,民户田少”。[53]这种情形不但“无益于贫灶”,而且“徒损于民”。[54]因为富豪大量的诡寄优免,严重影响州县人民徭役征科的公平,加重人民的负担,引起州县有司强烈的不满。嘉靖三十六年(1557),兴化县知县胡顺华说:该县“土瘠民贫,差繁赋重,兼以灶户置买民田,不复应当科差;以致小民独累,其害有不可胜言者”。[55]泉州府也因“盐户丁米尽数奏免”,发生“诡寄日多,编差不足”的现象。[56]州县官吏为平均徭役,经常与盐场官吏争夺管辖权,破坏灶户优免之利。早在正统二年(1437)刑部右侍郎何文渊已说有司对灶户优免之利,“奉行不力”。[57]其后类似的报告,层出不穷。如景泰五年(1454),兵科给事中王铉说:对优免之事,“有司妄执不从”。[58]两浙运司同知王彪也说:“有司视为泛常,不容优免。”[59]其后这类事例更多。如成化七年(1471),巡盐御史李镕说:“近年以来,有司不准旧例,将灶(户)田粮与民(户)一般加耗起运,又编水夫马夫粮及杂泛差役。”[60]弘治元年(1488),两淮巡盐御史史简说:“近年以来,有司多不遵守,将各场灶丁或佥点解、军等役或小事一概勾扰。”[61]工部尚书康太和说:正德年间,兴化府有司“将盐户不受盐官租”,也就是盐户拥有的滨海斥卤田地,也要“与民间一体编排均徭”。[62]御史赵镗也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说:长芦、山东的州县有司,妄将灶户加科派民壮、夫皂等杂役。[63]于是盐场的独立性遭到破坏,变成受到双重管辖的复杂区域。
在盐场行政与州县行政的双重管辖下,贫灶的负担也是双重的。弘治年间的两浙清泉、长山、穿山三盐场灶户,即“身膺二役,县有里长、场有总催;县有甲首,场有头目;县有收头,场有解户;县有支应,场有直日;县有递年,场亦有递年。则灶之与民,其苦乐已倍矣。为有司者,又以灶得盐利而每困苦之,凡征输杂办,咸欲与民相埒”。[64]山东各场灶户,“既纳灶课,复征民粮”。[65]福建各场盐户,“既与军民诸户轮当本县十年一次之里长、甲首,十年之内又轮当盐场之总催、团首、秤子、埕长”。总催与秤子相当于里长,团首和埕长相当于甲首。盐册与民册,“每十年一次攒造”,“民册编审里役,只赴本县清审,朝往夕归”。盐册编审则须“往省赴运司候审,来往旬日,动费甚艰”。灶户于正役之外,“凡盐司过往公差牌票下场,及该场官吏、在官人役等费,轮月接替支应,赔贩需索之苦,过于民中矣”。且军民诸户递年均徭、驿传之编,“凡民正米一石,只派银二钱上下”,而盐户“每年每丁既纳银二钱五分,每粮一石纳银五钱五分”,“尚有私贴脚费,见年在场答应直月银两及雇募盐丁等役,复照丁产另贴”。比较军民诸户之负担,可谓“轻重悬绝”。[66]
四 天灾人祸的袭击
天灾的袭击,常使灶户破产。沿海灶户因住在海滨之地,随时有遭受天灾的危险。例如淮南盐场在洪武二十二年(1389),海潮坏捍海堰,就漂没灶丁三万余口。正德元年七月七日,飓风溺死灶丁三千余人,十二月又有大水,场民死者万计。嘉靖元年(1522)七月二十五日,暴风雨,海潮涌,“灶舍、灶丁俱漂没,不知其所在”。[67]万历二年(1574),两淮三十场大旱之后,加以暴风雨,“江海骤涨,人畜渰没,廪盐漂没,庐舍倾圮,流离饥馑”。[68]广东潮州府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八月的一次水灾中,“渰死男妇一万二千五百三十名口”,“漂没田亩、盐埕五千余顷”。[69]加以沿海地区常遭倭寇焚掠,如嘉靖年间,倭寇劫掠两淮盐场,使“盐丁罢灶”。浙东盐场遭倭患,“焚荡杀掳,伤残已极”。[70]在天灾人祸的袭击下,富灶降为贫灶,贫灶更是一无所有,而政府常不加救恤。王舜耕说:山东、长芦各场,“近年来各该有司,视为秦越,每遇赈济之时,往往有民灶之分,不肯加赈”,“今年三月内,据长芦运司开报极贫应赈灶丁四千余人到臣,及至行查在仓粟谷,止有一百余石”。[71]有的盐场非但不加救恤,甚至仍然苛征盐课,正如兴化府《莆田县志》所说:“民粮等科,遇灾伤恩典,得以赦除,盐引课银得沾分毫乎?”松江司青浦场,“因海潮内侵,墩荡坍洗,水不成盐”,“而岁办银课如前,加以(嘉靖)三十二、三年兵燹,死徙灶丁,亡者过半”。[72]即使赈济,也是按引给赈,“贫而无力,止办盐二三引者”,得不到多少赈米,“岂能足用?”逃移复业之人与老疾无依之辈,“虽免办课,悉不为赈”。无怪乎人云:灶户之“贫者必逃,而逃者忘归,复业之人转于沟壑,理势必矣”。[73]
五 商业资本的盘剥
明代中期之后,商品经济发达,赋役逐渐纳银化,使人民由劳役制中解放出来。然而乡里小民得银困难,“不免临时辗转易换,以免逋责;有司收纳,既重其权衡”,“及其交官,又杂铜铅以为伪”。[74]在盐场上也有类似情形。盐课折银与盐准许私卖之后,虽为灶户提供了摆脱劳役制的条件,但也使灶户掉进商业资本盘剥的陷阱。因为改折对灶户来说是“舍其所产,征其所无”。[75]嘉靖十三年(1534),温州永嘉场士绅王钲上疏朝廷:“今尽征折色,责非所有,称贷应急,十室九空,往往穷迫逃徙,莫能为生。”[76]灶户为获得银两纳课,必须把生产品变卖,也就是必须依赖市场,依赖商人。商人便趁他们急需银两之际,压低价钱,乘机讹诈。“每盐一引,视常价仅得半之,用是日苦窘急,逃亡数多,而额不可减。”因此,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对灶户的剥削相当严重。嘉靖二十六年(1547),鄢懋卿说:“有奸商恋场,先将低银放与各灶,倍息以充买补者。”[77]嘉靖《定海县志》载:“商人到场买盐,其弊又不可胜言者。盖灶之贫者,无盐可货,必先贷其银,而商人乘之以牟利。数月中,必取倍称之息,倘迟之一年,其息奚啻十倍。”[78]万历《温州府志》也载:“商人到场买盐,贫灶率先贷其银,而商人乘之以射利;数月之间,必取倍息,每盐一引,视常价仅得其半。”[79]彭韶也说:沿海灶户,“自来粮食不充,安息无所,未免豫借他人。凡是煎课余利,尽还债主,而本身之贫,有加无减”。[80]不能偿债时,商人“必讼之运司,发场督责,过于官负”,遂使“强者破产,而弱者鬻子女”。[81]
六 灶户的贫富分化
在生产手段丧失,盐课、徭役加重,天灾人祸与商业高利贷资本的盘剥下,许多灶户在明代中期以后,降为贫灶。同时,在日趋成为小商品生产者的趋势下,本来生产条件较好、人丁较多、草荡较广的灶户,已经有了剥削别人的可能,而成为富灶。
富灶利用钱财“交结本场官,以营己私。贪官易利其馈送,乐与之处,凡所指使,无敢不从”。[82]他们运用种种方法,把盐课或徭役等负担转嫁于贫灶身上。如福建盐场,即因“大户多隐丁不报,却将小户丁口尽数开报,以凑原额”,遂使“各户人丁,有一户数丁而田仅数亩者,而一户一二丁而田至数顷者,相差悬甚”。[83]在这种情形下,贫灶的工本既不能得,差役又不能免,灶田优免田粮之例复为富灶所夺,不但要自身煎办盐课,而且要替富灶承担转嫁的盐课与徭役,前者未足,后者又来。举凡明初优恤灶户之利,贫灶均不能得到实惠。只有多煎余盐,得些米麦以求活命。但又常为官府无偿没收,或为总催富灶敛为己有。因此贫灶生活困苦,“粮食不充,安息无所”,[84]不得已,只有贩卖私盐一途。可是贫灶“卖私盐,人即捕获”。[85]富灶则勾结场官作弊营私,[86]所以富灶“卖私盐,公亦容隐”。贫灶私煮得余盐,也只好借富室私卖,受其中间剥削。[87]每当生活无资之时,只得“先从富室称贷米麦,然后加倍偿盐以出息”,[88]甚者“因欠私债,将弟男并卤池场,准折与人”。[89]总之,贫灶无论如何都逃不过富灶的剥削。盐场上的贫富阶层分化现象日益显著。贫灶的产业因之荡然,全遭富灶借其财势兼并,或为其“恃强占种”,或为其“纠合人众公然采打”,或为其欺骗“立约盗卖”,[90]或因“贫丁已故”,为其干没。[91]故景泰以后,“各处盐场原有山场滩荡,供采柴薪烧盐”者,“多被权豪侵占”,[92]致“富灶荡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93]其后虽有“补丁办盐,或贫难逃移灶丁复业”,又皆不复给荡。[94]因此,贫灶的“分业荡然”,成为无产者。[95]
这种贫富分化的情形,在弘治初年已极显著。工部侍郎彭韶上疏:“海盐煎熬,全资人力,灶户饶给之家,丁多力盛,因山海自然之利,无门户不足之忧,诚与乐土之民等也。贫薄之人,虽有分业涂荡,然自来粮食不充,安息无所,未免豫借他人。凡有煎课余利,尽还债主,而本身之贫,有加无减,故其艰苦,难以言尽。”[96]可见弘治年间,沿海灶户中已有“饶给之家”与“贫薄之人”的分化了。至正德年间,情形更为严重。据南京国子监祭酒章懋的报告:“海滨之民,以煎盐为业者,谓之灶户。其采办薪刍,朝夕烹炼,不胜劳苦,固皆在所当恤。而单丁老弱,家计贫难者,煎办不前,课入不敷,屡遭鞭挞之苦,而盐入于官,或被雨水销镕,又有追赔之患,此穷户尤可哀矜者也……其有丁力众多,家道殷富,为总催大户者,煎盐既多,私卖尤广。”[97]这种分化的情形继续发展,至万历初年,两淮三十场极贫的灶丁已达七万六千七十三丁,次贫丁六千三百三丁。[98]灶中贫户已占了绝大多数。
明代后期,不仅灶户中贫富分化加剧,连原来皆出于殷实上户的总催也有了分化。万历《上海县志》记载:两浙运司荡地、滩场,本来是“计丁分拨,以办课额”的,实际上则“挂册灶丁,十无二三见在,而见在者亦不至场已百余年”。因此滩场、荡地俱为总催所占,由其“办课免均徭”,“本户未闻也”。各场岁办的盐课,“俱是总催各以所管田地、滩荡,召附近贫民耕樵、晒煎,收其租银,纳场解送运司”。“但各催纳银略同,所分土地,不惟美恶悬殊,而顷亩多少亦异”,结果“分地多而又美者,完课犹余百金;分地少而又恶者,卖男鬻女以填足”。“或地虽同而有民田多者,冒免徭银,浮于盐课;穷无田者,岁输二十金,不获免毫厘”。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以致“贫催多逃,每五年一编补,凡承役者澌灭无遗,当补役者闻风先去”。[99]陈与相《报功祠碑记》也说:两浙西路场灶丁课重,不但人人办课,且“责及黄口雏”,甚至“责及腹孕”,是以虚丁供重课,灶丁负担更重,终于逃亡,逃亡则“累催者偿,偿又不胜逋,而催亦贫,贫则不能终偿,亦逋”。[100]这种贫催逃亡的情形,很是普遍。万历《嘉定县志》载:“隆万以来,排催岁受赔累,无不破家。”[101]万历《温州府志》也载:“总催往往破产以偿,困累不胜。”[102]显露出灶户贫富分化情况的严重性。
灶户分化的结果,使绝大部分沦为贫灶或无产者。弘治二年(1489)彭韶巡视沿海灶户后,看见“庶民之中,灶户尤苦”,特上《进呈盐场图疏》,对贫灶的苦处有深刻的描写。其疏云:
贫薄之人,虽有分业涂荡,然自来粮食不充,安息无所,未免豫借他人。凡是煎课余利,尽还债主,而本身之贫,有加无减,故其艰苦难以言尽。小屋数椽,不蔽风雨,粗粟粝饭,不能饱餐,此居食之苦也。山荡渺漫,人偷物践,欲守则无人,不守则无入,此蓄薪之苦也。晒淋之时,举家登场,刮泥汲海,午汗如雨,虽至隆寒砭骨,亦必为之,此淋卤之苦也。煎煮之时,烧灼熏蒸,蓬头垢面,不似人形,虽至酷暑如汤,亦不能离,此煎办之苦也。不分寒暑,无问阴晴,日日有课,月月有程,前者未足,后者复来,此征盐之苦也。客商到场,咆哮如虎,既无现盐,又无抵价,百般逼辱,举家忧惶,此赔盐之苦也。如有疾病死丧等事,尤不能堪!逃出别处,则身口飘零;复业归来,则家计荡尽。诚为去住两难,安生无计!孟轲谓穷民无所归,此等是矣。[103]
七 贫灶的逃亡
在贫苦的煎熬下,灶户为求活命,只有去留两条路:去者逃离盐场,另求生活;留者受雇于富灶或商人,成为靠工资过活的无产佣工。
贫灶大量逃亡,始于正统、景泰年间。如正统二年(1437),两淮、两浙即有灶丁因受差徭追逼而“挈家四散求食”的奏疏。[104]正统八年(1443)与正统十二年(1447),山东也疏奏说:永利、石河、高家港、信阳等灶户,“因蝗旱灾伤,赋役烦重,挈家逃移”,石河场逃去三百八十三户,高家港逃去三百七十九户,信阳场逃去八百一十余户。[105]景泰三年(1452),有疏奏说:江南各府州县有许多逃亡的灶丁与文职官员在任所及邻近州县报作民籍,脱免原役;因此要求各处府州县“从今审核差有此等,俱发原籍当差”。[106]然而一纸命令并不能禁止灶丁的逃亡。景泰四年(1453),四川疏奏说:“盐井灶丁多在深山绝涧之中,无府官里邻临芘。客商到井者,率横索下程,多支引盐。甚至盐数不敷支给,抑令退悔已聘幼女而娶为妾者。又有田土被大户占种不还者。以此贫弱逃亡。”[107]景泰五年(1454),兵科给事中王铉也奏称:“近者灶户与民一体当差,又煎办盐额”,“虽经奏准优免,有司妄执不从”,因此灶户“逃半”。[108]在政府为确保盐课收入的政策下,灶户“逃亡数多而额不可减”,逃亡者遗下课银均由见在灶丁代纳包赔,遂使见在灶丁不胜赔累而逃亡。如山东运司官台等十场远近逃灶遗下丁盐银三千零四两九钱余,即“俱累见在人包赔”。“一户而逃一丁,则一丁之课加于一户,而一户困矣。一镬而逃一户,则一户之课加于一镬,而一镬困矣。一场而逃一镬,则一镬之课加于一场,而一场困矣。”[109]今“以数千家之逃亡而则赔于见户,虽月逼日催,势莫能办,而典男鬻女”又不能,只有逃亡一途。因此“年复一年,愈逃愈累,愈累愈逃”。[110]据万历《山东盐法志》:“大抵海滨贫灶,十室九空,土著业户潜纵逃窜,则以见在人丁包赔办纳,不胜偏累之苦。”[111]万历年间山东盐运使甘一骥说:西由场灶户原额六百户,出办课银九百两,“今见存户不过二百,包赔六百户之差”。其丁课之重可知,因此“逃亡赔累,年甚一年”。整个山东登莱地区灶户,遂由明朝初年的一万三千五百七十一户,四万五千二百二十丁,减为二千七百户,二万丁。[112]长芦地区也有类似情形。正德十六年(1521),郑光琬上疏:“各场见在者数少,逃亡逃绝者数多,虽有招抚复业者,十无二三;其死亡逃绝,俱是见在人户包赔。”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更是“灶地多数被侵占,灶丁日致逋逃”。[113]四川灶丁也“往往有追赔逃窜之患”。[114]河东盐丁“多逃绝”;[115]且富丁可纳银免役,贫丁无银可纳,只得应役,遂致“偏累”“逃亡”。[116]广东以香山场为例,明初“灶排、灶甲约六七百”,正统年间,“仅凑盐排二十户,灶甲数十户”,其后盐田多被邻邑豪宦“高筑基壆,障隔海潮,内引溪水灌田,以致盐漏无收;岁徒赔课,又多逃亡故绝者”,终于在天启五年(1625)不得不把场官裁汰,盐场废除。[117]福建上里场贫灶,“贫无卓(立)锥”,场官又“每百斤勒银一钱,次亦不下八九分,而又有保汤水钱之索,每引亦不下一二分”,贫灶“皆目不识一丁,闻官语则又若爰居之骇钟鼓”,于是皆“俛首听命”,鬻子卖房以偿之,不足则“劝借亲戚以益之”,再不足只有逃亡了。嘉靖年间,据报:“见在人丁只计七千八百有零,比之原额已少三千九百余丁。”嘉靖四十三年(1564),在盐场实际参加生产的滨海灶丁,已“死亡殆尽”。[118]两浙自正统二年(1437)已有灶丁逃亡的事。成化年间,巡盐御史李镕称:灶户的田粮与差役,不能优免,且“灶户例不分户”,因此一般人只见灶户“田亩数多”,其实灶户之地“多瘠卤”,“人力单贫”,每至征课,“不免鬻产卖子,流窜他乡,贻累里长、总催赔纳”。[119]于是在海滨办课的人丁,“仅余三分之一”。[120]崔富《盐政一览序》称:松江分司灶丁额虽有三万人,其实“在灶亲煎者才三千一百七十五人”。[121]其他各场如芦沥场,“自明万历年,灶户逃亡殆尽,丁课已归荡地征输”。[122]明代后期,两浙有些场分,灶丁额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增加的现象。万历《杭州府志》记载:仁和场在洪武初年实在办盐人丁为三千二百一十八丁,嘉靖年间增至一万一千七百四十一丁,万历年间增至一万三千九百零五丁。[123]似乎与一般趋势相反。其实这中间有许多是“富户因避重役,俱附远场充为灶户”,他们并不办盐课,而是“专一结构官利,那移出纳”。[124]隆庆初年,庞尚鹏也发现,虽然“迩来灶丁日增,民丁日减”,但是这些增加的丁口,“要皆诡寄之明验也”。[125]如台州府临海等县灶户,有的明明是绝灶不办盐,灶丁已“死亡殆尽”,但册籍上仍载有灶丁五千三百七十三丁。[126]至于全国最大的两淮盐场,灶丁逃亡的情形也相当严重。正统初年,即有灶丁逃亡的报告,虽然政府不断地佥补,但逃亡的事不断地发生。弘治十二年(1499),监察御史史载德称:“两淮运司灶丁多逃往邻县豪家”,此等逃窜灶丁,“以三十场大约计之,不下万数”。[127]至嘉靖九年(1530),两淮巡盐御史朱廷立说:“各场煎盐灶丁,顷年以来,节遭灾伤,逃亡过半。”[128]户部尚书秦金对此有更详尽的报告,其言曰:“两淮运司三十场……近年以来,生齿日耗,重以嘉靖二年大灾,附海偏场逃大半。遗下盐课,总催包赔不前……加于见在灶丁代办,未及一年,而贫难下灶各可安生者亦以代办而逃……角斜、丁溪、白驹三场原额灶丁二千七百三十丁,已逃灶丁五百九十九丁……余东、马塘、掘港、石港、西亭、余中、吕四七场原额灶丁八千四十三丁……正德三年……逃亡一千八百六十八丁……今新逃亡灶丁二千七百九十四丁……莞渎、天赐、临洪、板浦、徐渎浦五场原额灶丁八千八百八丁……正德三年……逃亡灶丁四千一百一十三丁……今新逃亡灶丁一千五百四十二丁。”则角斜等十五场共逃亡一万九百八丁,比较原额,仅剩四千九百七十八丁。[129]嘉靖二十年(1541)前后,据运使郑漳的调查:“今各灶始以三万五千丁有零,自洪武至今百七十余年,仅得余丁一万。”郑漳认为这太不合人口增长之理,他说:“今凡人家始于一丁,不数辈,生齿盈门,即成巨族。”两淮灶户历经一百七十多年,户口不但未增长,反而降至原来的三分之一,难道两淮灶户“化育与人殊哉!”实际上,他们“畏避正课,逃移相继,或雇直为人佣工,或乞养为人男仆,或往产盐场分为人煎办”。[130]
逃移的灶户,有的“雇直为人佣工”,有的“乞养为人男仆”,有的投入豪强富家为其义子赘婿,有的往其他“产盐场分为人煎办”。据两淮运使郑漳,“如高邮、通、泰等州,如兴化、如皋、海门、盐城等县,如富安、安丰、东台、梁垛、何垛等场”,固为两淮“逃灶之渊薮窟宅也”。[131]此外,有的灶丁还私自剃度为僧徒,有的“窜名军伍”,以求“偷身苟免”办盐劳役。[132]大量灶丁的逃亡,使政府不得不改变方式,将原有征收食物的灶户劳役制度改为征收货币。而盐课征收货币后,也使灶户脱离灶籍更为容易。有的贿赂官吏里书,窜改户口册籍,以求脱离灶籍,或假冒民籍;有的将新生灶丁全不造报;[133]有的利用科举或学术成就改变社会地位,而脱离灶籍。如著名的理学家王艮即出身灶籍,曾治商往来齐鲁,又曾学医,后立志学为圣人,取《孝经》《论语》《大学》置袖中,逢人质疑,日夜讲求,终得阳明先生赏识,得列门墙而脱离煮盐之苦役。[134]又据何炳棣先生的统计,有明一代的进士,出身灶籍的就有三百八十八名。[135]
总之,明代初期,在官专卖的制度中建立的世袭劳役灶户制度,在商品货币经济的冲击下,盐课货币化,灶户中发生贫富分化,灶户大量逃亡,用一切方法脱离制盐苦役,遂使灶户制度崩溃。
八 灶户组织的崩溃
灶户的大量逃亡,不但使灶户制度失去意义,而且使原有的灶户组织发生动摇。
首先在形式上,灶户的团里组织的标准制为一团一百一十户,十户为总催,余百户分为十甲,每岁由一总催领十甲首应役。灶户大量逃亡,不但使组织的结构发生变化,而且破坏了十年一次编审应役的规定。万历《扬州府志》载:两淮灶户已改为“每五年一次,编审灶户,定上中下三户则。各场总催,俱照原额,选其殷实佥充,亦五年一换。各总下灶户,多寡不一,或编二十名,或编三十名,务使灶舍相近,草荡接连”。[136]万历《上海县志》也载,“今盐课出于总催,催有逃缺,课即亏失”,因此改为“每五年一为佥补,而灶丁渐尽”。[137]即总催五年一换,每团总催户由十户减为五户,且每团人户也减至二十户或三十户,比之明初一百一十户要少得多。
其次,由于灶户贫富分化的发展,一般富灶常利用总催的职权,兼并灶丁的场荡,干没灶丁的盐课,[138]甚至“敛穷灶之余盐,入为己有,以罔厚利”。[139]因此,贫灶的“场荡悉为总催所并,而盐课又为总催所欺”,[140]只得“借贷于官豪之家,为其占据役使,或避重就轻,投倚总催人等,隐射额课”,[141]成为“总催家一佣工而已”。[142]于是,总催以所管田地滩荡招附近贫民,耕樵晒煎。煎盐既多,私卖尤广,“通同大伙盐徒,撑驾船只,出境兴贩”。[143]团制防止私盐贩卖的功能因此丧失。
而且豪灶任总催,“交通上下官攒,扶同虚出奏缴”,“逐年所办盐课,止纳十之七八,余皆玩愒不完”,年复一年,不为追赔,遂使团制的催征盐课功能大打折扣。[144]甚至催征盐偿时,“私索辄倍之”,及得纳盐上坨,又“未必及数”。[145]例如福建七场,原收盐课亏折“百一十二万余引”,即“俱系各场总催人等侵盗并包收银钱”。[146]则其催征盐课的功能亦失。
组织结构已变,防止私盐贩卖与催征盐课的功能既失,灶户组织也随灶户制度而崩溃。
九 生产形态的变迁
由于贫富分化的发展,留在场上的贫灶或无产者一般都变成富灶的“家佣”,或成为商人在盐的生产中的直接生产者,因而改变了生产形态。
明初的生产形态是官有的劳役生产,灶户皆领有官给的生产手段与工本,“日率老幼妻子”,[147]“举家登场刮泥汲海”,[148]淋卤候煎,是一种属于官手工业的家庭手工业。自灶户发生贫富分化后,绝大部分灶户降为贫灶,极少部分的灶户则上升为富灶。此般富灶利用种种方法兼并贫灶的生产手段,并榨取贫灶的劳力,因此变得越来越富。弘治初年,彭韶说:两浙“豪强灶户,田亩千余,人丁百十”。[149]福建泉州府同安县的灶户,在嘉靖年间,经查其盐册与黄册田亩,“有自弘治年间原额不上百亩,到今(嘉靖时)逐年新收条,有增至三千亩者”。[150]
富灶经营盐业的生产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拥有较多灰场(盐田)滩荡的。他们把灰场滩荡租给贫灶,以括取私租。正德初年,国子生沈淮说:各场灶户“既无工本,又无柴薪,又无灰场,往往入租于人,始得摊晒”。因此建议“灶户无灰场者,官为取置给与,无使重纳私租”。[151]这个建议虽被载入盐书、府志之中,但实际上并未实行。[152]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形更加严重,万历《上海县志》记载:“各场岁办盐课,俱是总催各以所管田地荡滩,召附近贫民耕樵晒煎,收其租银,纳场解送运司。”[153]显然,这类富灶是依靠占有的生产手段向贫灶进行剥削的。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其剥削的形式已由实物改为货币,他们收的是“租银”,而不再是实物的盐了。
另一类是拥有广大盐场和草荡的。他们直接经营盐业生产,以获得的生产手段榨取贫灶的劳力。正德年间,南京国子监祭酒章懋称:“其殷实灶户为总催者,场荡归其兼并,盐课为其干没。煎者既多,私卖尤广。凡诸灶丁尽其家佣。”[154]隆庆初年,总理盐屯大臣庞尚鹏也说:“各场富灶,家置三五锅者有之,家置十锅者有之,贫灶为之佣工。”[155]陆深也说:“灶丁不过总催一家佣工而已。”[156]霍韬也说:“富室豪民,挟海负险,多招贫民,广占卤地,煎盐私卖,富敌王侯。”[157]此类富灶在榨取贫灶的劳力中变得更富,经营规模扩大。如长芦运司海丰、海盈二场之间有片六十余里的海滩,被富灶高某等买占,共立滩池四百二十七处,每年所得盐利达十万余引。[158]而一般豪灶,“私立十数灶者,七八灶者”,更是普遍。[159]每灶所用佣工当在三四人或五六人,则富灶所经营的盐场规模不小,少者亦有二三十人,已具有手工工场的生产形态,而盐场所有形态中的官有成分,实际上已因此而消退。富灶与贫灶佣工间的生产关系,据《赣榆县志》的解释:“灶户以盐池为恒产,贫者受直为佣。”[160]则已是带有若干劳役性质的雇佣劳动。
明代末期,盐的生产中又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前文说过,自嘉靖以后,随着商品货币经济关系剧烈的发展,盐课折银在全国各产区大规模展开,政府对盐的生产和流通的控制已经松懈,因此商人和灶户有一定的自由可以直接买卖盐斤,于是商业资本趁机打进盐的生产中。正德年间,已有盐商“招集灶徒,私煎私贩”,达数百引者,甚至“交通吏徒,欺侮恣肆,莫之敢膺”。[161]至嘉靖年间,御史鄢懋卿称:“两浙盐额,俱征折色,则各灶既非聚团煎烧,又不由场官督率。”在这种控制松弛的情况下,“是以有私煮私鬻者”,而盐商也趁机进入盐场,以买补为名,“先将低银放与各灶,倍息以充买补”。[162]嘉靖末年,《定海县志》记载,“商人到场买盐”,“灶之贫者,无盐可货,必先贷其银,而商人乘之以牟利。数月中,必取倍称之息,倘迟之一年,其息奚啻十倍,或不能偿,则必讼之运司,发场督责,过于官负,强者破产,而弱者鬻子女”。[163]其剥削程度又远超过国家。尤其是,盐商在场官的支持下更肆无忌惮。万历年间,《温州府志》载:浙东地区也有同样事情,“商人到场买盐,贫灶率先贷其银,而商人乘之以射利;数月之间,必取倍息”。因此贫灶所卖的盐,“每盐一引,视常价仅得其半”。[164]则灶户所受商业资本剥削之苦可想而知。而且自商屯崩溃后,大部分山陕、徽州盐商移住淮、浙,其中有不少住在盐场附近,买补余盐。如歙县人吴荣祖自明天启初年,便在东台场买补,[165]因此得以以高利贷控制灶户。明末灶户诗人吴嘉纪对这种情形有深刻的描写,在他《逋盐钱逃至六灶河》的诗中有云:“称贷盐贾(山西人)钱,三月五倍利,伤此饥馑年,追呼杂胥吏;其奴吃灶户,爪牙虎不异。腐儒骨稜稜,随俗受骂詈;秋清发茱萸,偿钱期已至;空手我何之,乡庐聊弃寘。”[166]说明在山西盐商高利贷剥削的压迫下,灶户只有弃家而逃。此外,张潮的《灶户谣》对此情形也有描写,其言曰:“今之灶户……有时无衣或无食,有时儿女需婚姻,有时煎盐或无草,有时抵价逋官银,有时死丧及疾病,有时庆吊修明堙。诸如此类遭缓急,称贷无门辄悲悒,含情泣诉商人前,少贷数金多数十,刻期愿以盐相偿……旧债未完新债始,若能盐债相适当,祷祀而求歌乐之。”[167]由此可见盐商已成为以低价预购小生产者成品为条件,贷给他们现金的“包买主”,进而产生同一个盐商包买若干小生产者的灶户,这种生产形态与近代西方“产业化的初阶”(Proto-Industrialization)的“散作制”(Putting-out System)相似。[168]灶户在经济上就这样依附了商业资本。明朝后期,随着官专卖盐法遭到破坏,这种情形越来越明显。王珍锡在万历末年说:两淮盐场,“商人纳引,官取其税,如榷关然。迨执引买盐,与灶丁相市,聊别于私贩而已”。[169]则商人只要缴引税,便可与灶户自由买卖,灶户完全超脱原有强制劳役式的盐业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生产盐斤的自由,这就使商人和灶户在盐的生产上发生了更直接的关系。
万历四十五年(1617)实行商专卖之后,“盐引改征折价,盐不复入官仓,皆商人自行买补”,“官铸盘铁锅之制遂止”,盘铁工大费重,灶户无力添设,仰给于商人,甚至锅也由“众商自出资本鼓铸”。[170]从此,商人不但贷给灶户现款,收购其产品,而且提供了必要的生产手段。显然,两淮灶户处于急剧破产中。生产上虽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但其生产手段多由商人供给,商人与灶户间的关系已是雇主与佣工的关系了。
结语
总之,明代盐的生产,前期是在“劳役经济制度”下进行的。其主要目的在于保证财政的收入,具有浓厚的自然经济色彩。明代中叶以后,在商品货币经济关系的冲击下,政府改变盐课征收的方式,由征收实物改为征收货币。明政府对盐的流通控制也逐渐放松,促使盐的生产逐渐具有商品经济的性质。同时也促使灶户从劳役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日益接近小生产者的地位。而且由于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灶户之中发生贫富阶层分化,尤其在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这种变化更为明显。绝大多数灶户变成贫灶,有的逃出盐区另谋出路,有的留在盐场成为富灶的佣工。于是贫灶与富灶的关系,已是带有若干劳役性质的雇佣关系。明代后期,商品经济有了高度的发展,商业资本势力大为膨胀,相比之下,政府对盐的生产与流通降低了控制力,商业资本因此打入盐场,以提供贷款的方式收购灶户的产品。万历四十五年改行商专卖制度后,商业资本取代了政府力量,完全控制了盐的生产,商人不但贷给现款,而且提供原料、生产工具,成为包买主,从而垄断了商业利润,并进而攫取了生产利润,最终发展成类似近代西方产业革命发生前夕“产业化的初阶”的“散作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