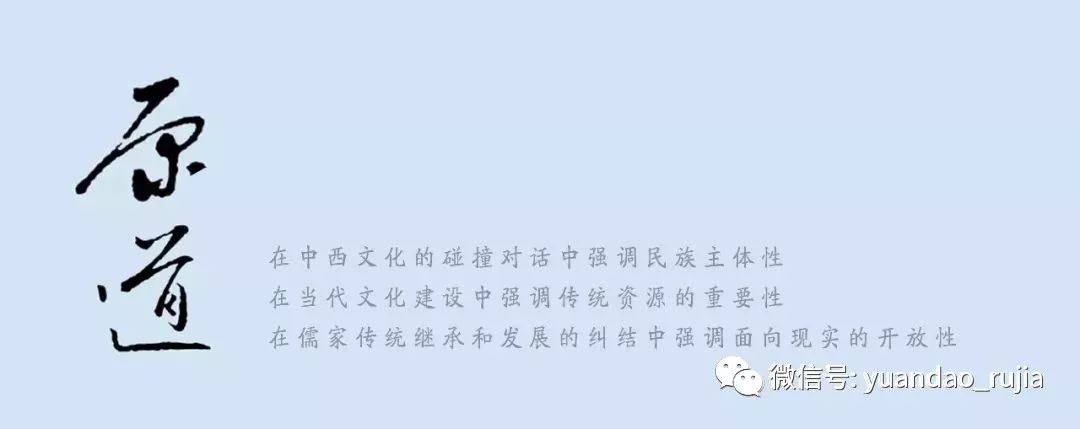
苏轼正统论及其思想价值
毛 钦
(《苏轼文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
内容提要:“正统论”是中国史学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自宋代欧阳修首作《正统论》之后,宋代学者们便对“正统论”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而其中苏轼的正统论在诸多正统理论中别具特色,其首次将“正统论”与“名实论”相融合,成为正统思潮中的突出代表。
苏轼吸收了先秦名家“名实之辩”的逻辑思维与儒家“正名”的政治文化意蕴,将“名实论”融入到“正统论”之中,创立了别树一帜的正统学说。
苏轼的名实论吸收了先秦名家的逻辑思辨精华又融合了儒家“正名”的道德色彩,他的正统论弱化了道德因素对评判正统名位的影响,却在历史观和史学批评中重视道德因素。苏轼的正统论具有重大的史学思想价值,其正统论体现出的史实与道德评价相分离的史学思想和对正统标准的讨论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苏轼;正统论;名实论;思想价值;
一、引 言
正统论是中国史学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谢贵安指出,所谓正统论,“既是中国古人的一种历史观,又是史学活动的修史依据,是对政权丛生、错综复杂的王朝兴衰的一种判断和看法,也是修史时对纷乱如麻的历史线索的一种梳理和描述。”[1]
正统论又以宋代最为发达,梁启超先生指出“正统之辨,昉于晋而盛于宋”。[2]宋儒重视尊王攘夷的春秋学,从而兴起讨论正统的风气。
(北宋形势图)
宋人对正统的探讨主要是对历史上中国历代王朝前后承继的正当性问题的论争。近年来,学界对宋代正统论的研究不断深入,相关成果不断涌现。[3]
然而学界对苏轼正统论的研究仍相对薄弱,[4]李哲的《苏轼正统论中的名实观》就苏轼正统论中的“名实观”因素作出讨论,对苏轼正统论的其它方面则较少涉及。因此,本文拟探讨苏轼融合“名实论”而形成的“正统论”的理论特色及其历史观,进而揭示苏轼正统论的思想价值与影响。
二、苏轼正统论与名实论的融合
苏轼为阐述其正统观而作正统论三首,包括《总论一》《辩论二》《辩论三》,在《总论一》开篇即言:“正统者,何耶?名耶,实耶?正统之说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5]据此将“名实论”融入到“正统论”之中。
苏轼将“名实论”融入到“正统论”中的做法,自有其思想渊源。对“名”“实”问题的探讨起源于先秦诸子,老子与孔子分别提出了“无名”与“正名”的观点,《道德经》开篇即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6]
按照通行的解释就是“可以言说的道不是永恒不变的道,可以称谓的名不是永恒不变的名。”[7]老子认为形而上的“道”是不可“名”的,因而“道”独立于“名”。庄子进一步发展了老子的学说,提出:“名者,实之宾也。”[8]
孔子明确提出了正名思想:“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9]
孔子的“正名”思想诞生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其时君臣关系与社会秩序混乱,故而孔子认为当务之急是“正名”,名位定了,那么礼乐刑罚皆可兴,社会秩序也将得以重新建立。
最早对“名”“实”关系作出系统性的论述的则是公孙龙。公孙龙细致的考察了“名”与“实”的关系,其关系可概括为:“‘实’在于对某类事物的实质或共相的体现,以某名称谓的某物体现了由此‘名’指称的这一类物的共相或实质,并且这被‘名’指称的共相或实质尽其完满地趋于其极致状态。”[10]
(公孙龙)
后期墨家在名家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逻辑理论,从而创建了中国古典逻辑学,他们提出了辩的目的和作用为:明是非、别同异、察名实、处利害、决嫌疑、审治乱六种。[11]苏轼对正统中“名”“实”关系的考察就带有一种古典逻辑学的思辨色彩。
其实,名实问题并非是一个抽象的哲学或逻辑学问题,从先秦名实问题的诞生与发展来看,名实问题与政治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孔子的“正名”思想形成与乱世,与“礼”“道德”等问题是分不开的。
丁亮考察了先秦秦汉经典对名实问题的论述,认为名实问题的发展始终在文德问题的笼罩与伴随下,名实问题其实是文德问题的核心,也就是说,名实问题的发生有一具体的政治文化背景,在此背景下,名实问题有着许多相关、同步或平行的文化议题,如言意、礼乐刑罚、文质与象等等。[12]
那么苏轼正统论中的“名”“实”指的是什么呢?苏轼在《总论一》说:“不幸有天子之实,而无其位,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德,是二人者立于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统之论决矣。”[13]
苏轼实际在此已将“名”与“实”作出对应,“名”即“位”,“实”即“德”。
苏轼在《辩论三》又通过对历代王朝的得位来论述“实”:“尧、舜以德,三代以德与功,汉、唐以功,秦、隋、后唐、晋、汉、周以力,晋、梁以弑。不言魏者,因章子之说而与之辨。以实言之,则德与功不如德,功不如德与功,力不如功,弑不如力。”[14]
由此可以看出,苏轼所谓的“名”是正统这一名位,是对取得中央政权的王朝的指称,这是一种基于史实的认识;而“实”则是其得位之本质,是通过道德对其得位手段作出的评价,具体来讲,苏轼所谓的“实”就是指“德”“功”“力”“弑”。可见,苏轼的名实论吸收了孔子“正名”思想的道德因素。
苏轼对正统之“名”与“实”关系的论点是:“天下固有无其实而得其名者,圣人于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实伤名。而名卒不能伤实,故名轻而实重。不以实伤名,故天下不争。名轻而实重,故天下趋于实。”[15]
“不以实伤名”“名轻而实重”已经鲜明的表达了苏轼的观点,即认为实比名更重要,名只是一个符号和象征,而实才是更为本质的内涵,在逻辑上延续了先秦名家“实”高于“名”的传统。
在此苏轼还用“贤”“不肖”与“贵”“贱”来论述名实关系,“贵”“贱”是“名”,“贤”“不肖”是“实”。历史上“贵”“贱”名位有高有低,这一点我们必须如实地承认,然而“贵”者不全是贤人,也可能不肖,但我们不能以道德上的“贤”“不肖”来否认其“贵”者的地位,“贱”也同样如此。
那么“正统”又是什么呢?苏轼认为:“正统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后名轻。名轻而后实重。吾欲重天下之实,于是乎始轻。”[16]
在苏轼看来,“正统”只是一个名号,而苏轼是轻名重实的,故苏轼作正统之论是“欲重天下之实”。
苏轼的“名实论”在逻辑上吸收了先秦名家“名实之辩”的逻辑精华,同时又吸取了孔子“正名”思想,其“名实之辩”又蕴含道德因素,因而兼具政治文化色彩。而苏轼作为将“名实论”融入到“正统论”之中的第一人,其正统理论在宋代诸多正统论中也可谓别树一帜。
三、苏轼正统论的内容及其历史观
在宋代,欧阳修首倡正统论,作《原正统论》《明正统论》《秦论》《魏论》《东晋论》《后魏论》《梁论》,晚年又删改为三篇,即《正统论序》《正统论上》《正统论下》,晚年改定之论与前论略有不同,而在当时产生广泛影响并引起宋人争论的应为前论。
欧阳修在《明正统论》中承认的正统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包括尧、舜、三代、秦、汉、晋、唐;第二类是“天下虽不一,而居得其正,犹曰天下当正于吾而一,斯谓之正统可矣”,包括东周、魏、五代;第三类是“始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夫一天下而居其上,则是天下之君矣,斯谓之正统可矣”,这一类是隋。[17]
(欧阳修)
欧阳修的正统论提出后遭到章望之的反驳,据《宋史·章望之传》记载:“欧阳修论魏、梁为正统,望之以为非,著《明统》三篇。”[18]章望之的三篇《明统论》今不存,但郎晔在为苏轼文集所作的注中却有多处引用,故从《经进东坡文集事略》中可以窥见一斑。
章望之认为:“予今分统为二名,曰‘正统’、‘覇统’。以功德而得天下者,其得者正统也,尧、舜、夏、啇、周、汉、唐我宋其君也;得天下而无功德者,强而已矣,其得者覇统也,秦、晋、隋其君也。”[19]
章望之不同意欧阳修的观点,而将“统”分为“正统”与“霸统”,这引起了苏轼的不满,苏轼说:“正统之论,起于欧阳子,而霸统之说,起于章子。二子之论,吾与欧阳子,故不得不与章子辨,以全欧阳子之说。欧阳子之说全,而吾之说又因以明。”[20]
可见苏轼是赞同欧阳修的观点的,其创作《正统论三首》的直接原因在于批判章望之的观点而维护欧阳修的观点。
苏轼所承认的正统王朝有十六个,具体如下:“正统听其自得者十,曰:尧、舜、夏、商、周、秦、汉、晋、隋、唐。予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后唐、晋、汉、周。”[21]
这与欧阳修所承认的正统王朝大致上是一致的。苏轼为了阐明自己的正统观点,因而对章望之的论点进行了批判,首先,苏轼讨论了曹魏是否可称为正统的问题。
苏轼首先指出:“夫所谓正统者,犹曰有天下云尔,名耳。”[22]正统只是一个“名”而已。
章望之认为:“魏不有吴、蜀犹吴蜀之不能有魏,蜀虽见灭,吴最后亡,岂能合天下于一哉?”[23]而苏轼则认为,魏虽然未统一天下,但其势力最为强大,就像五代一样。
章望之“不绝五代也,亦徒以为天下无有与之敌者而已”,五代也未统一天下,章望之因五代之强大而不绝五代,魏与之类似,却唯独将魏排除在外,这是没有道理的,因而苏轼感叹“今也绝魏,魏安得无辞哉!”
那么对于未统一天下的王朝,苏轼正统论的态度又是如何呢?苏轼认为,尽管天下不合于一,但倘若有一个强大的中原王朝,而其他分裂势力不足以与之抗衡,也可以称为正统。
“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于一,德既无以相过,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强,于是焉而不与之统,亦见其重天下之不幸, 而助夫不臣者也。”[24]倘若如章望之所言的不予强者以正统,那就是“助夫不臣者”,所以苏轼认为魏在名义上仍是中央政权,应当给予其正统地位。
其次,苏轼讨论了晋、梁是否可称为正统的问题。为了讨论这一问题,苏轼对此批判了章望之“霸统”的理论。
苏轼提出:“始终得其正,天下合于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耶?亦或不以其道得之耶?”[25]接着苏轼分析了得天下之“道”,认为章望之的“霸统”是从“实”的角度来论述,但却“以实言而不尽乎实”,“以霸统重其实,而不知实之轻自霸统始。”[26]
苏轼认为,从“实”的角度看,晋、梁得天下是“以弑”,即通过篡位的手段谋得天下,如果按照章望之的观点将其归类为“霸统”,那么“故虽晋、梁弑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恶,而其实反不过乎霸。彼其初得正统之虚名,而不测其实罪之所至也。”[27]
在苏轼看来,章望之没有处理好“名”“实”的关系,“霸统”的归类实在是不恰当。其实,“霸道”“王道”在中国古代一直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王道崇尚仁义和礼治,而霸道则以武力而统一天下。
苏轼就认为“霸道”“王道”都是“统”的一种,并认为:“夫王者没而霸者有功于天下,吾以为在汉、唐为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后唐、晋、汉、周得之,吾犹有憾焉,奈何其举而加之弑君之人乎。”[28]
最后,苏轼的正统论是一种内部有等次差异的正统论。苏轼认为:“尧、舜以德,三代以德与功,汉、唐以功,秦、隋、后唐、晋、汉、周以力,晋、梁以弑。不言魏者,因章子之说而与之辨。以实言之,则德与功不如德,功不如德与功,力不如功,弑不如力。”[29]
在此,苏轼实际上将他所承认的正统依照“德”“功”“力”“弑”分成了四个等级,第一等的是尧、舜,其取得正统是通过德;第二等的是三代,其取得正统是通过功和德;第三等的是汉、唐,其取得正统是通过功;第四等的是秦、隋、后唐、晋、汉、周,其取得正统是通过力;第五等的是晋、梁,其取得正统是通过弑。
(朱温篡唐)
苏轼的这种有等次差异的正统论分类,是基于其对“实”的看法,也就是基于道德批评色彩的正统论。
前文已经讨论过,苏轼是轻“名”重“实”的,那么对于历史上“固有无其实而得其名者”,苏轼认为只要它们名义上是中央政权,那么就不妨给他们以正统之“名”,而道德评价是可以另作的,道德评价并不妨碍“名”的获得。
苏轼对“正统”的态度也影响到他的历史观。苏轼轻“名”重“实”,也就是重视“道德”因素在王朝兴衰更替中的作用,这种思想贯穿于他的史论之中,因此苏轼常常以“道德”的观念阐释历史。
例如,苏轼在《礼义信足以成德论》中指出世俗的“三忧”:“是非以谷食不足,而民有苟且之心以慢其上为忧乎?是非以人君独享其安荣而使民劳若独贤为忧乎?是非以人君不身亲之则空言不足劝课百姓为忧乎?是三忧者,皆世俗之私忧过计也。”[30]
为了驳斥“三忧”,苏轼提出“君子以礼治天下之分”“君子以义处天下之宜”“君子以信一天下之惑”的主张,而最终的落脚点则是“此三者足以成德矣。”[31]即苏轼认为治理天下,使百姓各安其职的最终手段是德,而成德的手段则是礼义信。
在《形势不如德论》中,苏轼又提出:“凡形势之说有二,有以人为形势者,三代之封诸侯是也”“以地为形势者,秦、汉之建都是也”,接着通过史实分析而指出“德衰而人之形势不足以救也”,“德衰而地之形势不能救也”,因而感叹“此岂形势不如德之明效欤”,最后得出结论“人存则德存,德存则无诸侯而安、无障塞而固矣。”[32]
即无论是三代分封诸侯,以人为形势,还是秦、汉以要塞建都,以地势为形势,都不如德,如果德衰微了,那形势也就不足恃了。
四、苏轼正统论的思想价值与影响
苏轼融合“名实论”而形成的“正统论”在宋代别树一帜,其正统“名”“实”分离的论述不仅对苏轼自身历史观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故应对苏轼正统论在史学思想史上的价值作一评析。
首先,苏轼将正统“名”“实”分离的做法是对史书“书法”问题的一个回应。苏轼将正统“名”“实”分离实际上就是将史实与道德评价分离,无论中央王朝是以“德”或“不德”的手段取得政权,都不能否定其取得正统名位的史实,这体现了苏轼在史书编纂上主张叙事与评价相分离的原则。
中国古代史书就“书法”而言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春秋》为代表的“春秋笔法”,即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另一种是以《史记》为代表的“实录”,将历史叙事与道德评价分离,一般只在卷末以论赞的形势发表评论,故班固评论司马迁“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33]
苏洵曾作《史论》三篇,探讨了史书的“书法”问题,他认为后世学者著史不当效法《春秋》,“后之人其务希迁、固实录可也,慎无若王通、陆长源辈,嚣嚣然冗且僭,则善矣!”[34]
苏轼受到其父亲的影响,他曾提出一个研读史书的“八面受敌”之法:“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35]
所谓“每次作一意求之”即是将史料分门别类的方法,体现在史书编纂上则是纪传体的“志”或者典章制度体如“会要”“通典”一类的史书。这一方法体现了苏轼对史料也即史实的重视。
古人既把《春秋》视为史书,也将其视为经书,其书在叙事上过于简要,而更强调的是一种“书法”,即“春秋笔法”。孔子因春秋之纷乱而作《春秋》,意在恢复社会秩序,因而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其叙事的全面性和完整性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伤。
(曾亦、郭晓东:《春秋公羊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而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史书,在“书法”上则将叙事与评价分离,在篇中先据史料叙述史实,后在篇末以论赞的形式发表评论,表达作者或赞或贬的态度,故而被视为“实录”。
很明显,苏轼将史实与道德评价分离的做法表明他是赞同司马迁的“书法”的,这是苏轼正统论对史书“书法”问题的一个回应。
其次,苏轼对正统标准的讨论,对历史编纂学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苏轼认为“故天下虽不合于一,而未至乎两立者,则君子不忍绝之于无君。”[36]即不赞成以“得天下”为“统”的标准,即使天下“不合于一”也不妨将中央政权称为正统,例如魏和五代都是如此。
这一标准对于解决史书编纂上的正统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作用,比如对分裂割据时代的撰述,纪传体史书以谁为“纪”的问题,编年体史书以谁的年号系年的问题都可以此为鉴。
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时就曾遇到过系年的困惑,这实际上就关乎正统问题:“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37]
司马光“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的做法很可能是受到了苏轼正统论的影响。
苏轼创作《正统论三首》在至和二年,即公元1055年。[38]以上所引司马光的这段论述出自《资治通鉴·魏纪一》,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始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终于神宗元丰七年(1084),共十九年时间,其中后汉纪三十卷、魏纪十卷成书时间在熙宁三年(1070)九月司马光离开开封前。[39]
因此从时间上看,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是在苏轼创作《正统论三首》之后。苏轼乃是一代文宗,其文章在士大夫之间广为流传,以苏轼在文坛的地位和知名度,司马光应当是读过苏轼的《正统论三首》的。
从另一方面讲,宋人对正统论的论争十分激烈,乃至在士大夫之间形成了一场“论战”,例如欧阳修的《正统论》完成之后就引起了章望之的不满,章氏因而作《明正统论》以非之,继而苏轼又作《正统论三首》反驳章望之而维护欧阳修,在这样一股正统论争的思潮之下,司马光对此必定有所关注。
按照苏轼将正统“名”“实”分离的理论,司马光以其系年的做法实际上是在修史实践中承认其正统之“名”。
五、结 语
正统论在宋代可谓蔚为大观,欧阳修、章望之、苏轼等一大批文人士大夫都对这一问题各自作出过论述。宋代讨论正统问题的风气之盛,与宋代春秋学的繁荣是分不开的。
欧阳修将正统观追溯到《春秋》,其在《正统论上》云:“《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40]《春秋》开篇系年曰:“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北宋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以“尊王”作为春秋大义的主旨,其学术影响尤为深远。“尊王”本就是春秋的大义之一,汉唐注疏中对此也多有阐发,但孙复将其尊为《春秋》大义之首,突出了对中央政权的强调与维护。
孙复的春秋学思想受到宋人广泛的好评,其后的刘敞、欧阳修等人都倡导春秋尊王大义,“尊王”也成为北宋治“春秋”学的一大主流。
“尊王”思想迎合了北宋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可见宋代春秋学与政治的密切联系,体现出了经世的用意。这种治春秋学的盛况对当时的学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春秋尊王的大义势必影响到宋代士大夫的思想,而正统论的形成也就与春秋学息息相关。
恰如邓锐所言:“宋代史家普遍以《春秋》大义为思想指导,不同程度上效仿《春秋》义例作史,使得宋代史学的正名观、尊王观、夷夏观以及正统观等诸多历史观念都与《春秋》学关系密切。”[41]
宋以前的正统论多以道德作为评判某一朝代是否为正统的标准,比较典型的是唐代皇甫湜的《东晋元魏正闰论》,皇甫湜认为“拓跋氏种实匈奴,来自幽代,袭有先王之桑梓,自为中国之位号。谓之灭耶,晋实未改;谓之禅耶,己无所传。而往之著书者有帝元,今之为录者皆闰晋,可谓失之远矣。”[42]
(黄甫湜)
皇甫湜从夷夏之防的道德论出发,认为东晋为正统,而元魏为僭伪。至宋代,欧阳修首次将正统观念发展成为一种系统性的理论,他提出正统的两大标准为“居正”和“一统”,其在《正统论上》云:“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43]
形成了以道德和功业两个标准来评判某一朝代是否为正统。汪高鑫指出,宋代正统论的突出特点是:“否定了传统意义上立定正统标准重视纯道德因素的做法,而突出了大一统功业的重要地位。”[44]
我们再来看苏轼的正统论,苏轼认为“正统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即认为“正统”只是一个名号,只要是历史上取得过中央政权的王朝都不妨给予其正统之“名”,即重视史实而不必论其得位之手段是否合乎“道德”。
这就进一步弱化了道德因素在评判某一朝代是否为正统中的作用。那么苏轼是否不重视道德呢?显然不是。前文已讨论过,苏轼是轻“名”重“实”的,苏轼所谓的“实”是得位之本质,是通过道德对其得位手段作出的评价,苏轼在历史观中尤为重视道德。
由此可以看出苏轼对正统问题的态度,第一是对正统标准的认识,苏轼主张以史实为依据,以取得过中央政权的王朝为正统,弱化道德因素对评判正统名位的影响;
第二是在历史观和史学批评中重视道德因素,苏轼将正统“名”、“实”分离实际上就是将史实与道德评价相分离,因此尽管苏轼承认某些王朝为正统,但并不妨碍对其进行道德批评,故而苏轼的正统论是一种在正统内部依据道德评价而有等次差异的正统论。
综上,苏轼吸收了先秦名家“名实之辩”的逻辑思维与儒家“正名”的政治文化意蕴,将“名实论”融入到“正统论”之中,创立了别树一帜的正统理论。
苏轼的正统论弱化了道德因素对评判正统名位的影响,却在历史观和史学批评中重视道德因素。苏轼的正统论具有重大的史学思想价值,其正统论体现出的史实与道德评价相分离的史学思想和对正统标准的讨论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1] 谢贵安:《饶宗颐对史学正统论研究的学术贡献——<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发微》,《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
[2] 梁启超:《新史学·论正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0页。
[3] 对正统论的系统研究,首推饶宗颐的《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其书于1977年由香港龙门书店出版,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再版,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又版。专门讨论宋代正统论的则有陈芳明:《宋代正统论形成背景及其内容》,《食货月刊》复刊1971年1卷8期,后收入陈弱水、王汎森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思想与学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123页;范立舟:《宋儒正统论之内容与特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2期;张伟:《两宋正统史观的历史考察》,《宁波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江湄:《从“大一统”到“正统论”——论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观嬗变》,《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6期等。
[4] 学界对苏轼正统论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第三章,以及李哲:《苏轼正统论中的名实观》,《重庆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
[5] 《苏轼文集》卷4《正统论三首·总论一》,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0页。
[6] 《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王弼注、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2页。
[7]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页。
[8] 《庄子集解》,王先谦集解,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页。
[9]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2页。
[10] 黄克剑:《名家琦辞疏解——惠施公孙龙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6-37页。
[11] 参看李俊主编:《中国古代哲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年版,第52页。
[12] 丁亮:《“无名”与“正名”:论中国上中古名实问题的文化作用与发展》,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13] 《苏轼文集》卷4《正统论三首·总论一》,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0页。
[14] 《苏轼文集》卷4《正统论三首·辩论三》,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4页。
[15] 《苏轼文集》卷4《正统论三首·总论一》,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0页。
[16] 《苏轼文集》卷4《正统论三首·总论一》,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0页。
[17] 《欧阳修全集》卷16《明正统论》,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78页。
[18] 脱脱等:《宋史·章望之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098页。
[19] 苏轼:《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11《正统辩论中》,郎晔注,四部丛刊本。
[20] 《苏轼文集》卷4《正统论三首·辩论二》,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1页。
[21] 《苏轼文集》卷4《正统论三首·总论一》,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0页。
[22] 《苏轼文集》卷4《正统论三首·辩论二》,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1页。
[23] 《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11《正统辩论中》,郎晔注,四部丛刊本。
[24] 《苏轼文集》卷4《正统论三首·辩论二》,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1页。
[25] 《苏轼文集》卷4《正统论三首·辩论三》,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3页。
[26] 《苏轼文集》卷4《正统论三首·辩论三》,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3页。
[27] 《苏轼文集》卷4《正统论三首·辩论三》,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4页。
[28] 《苏轼文集》卷4《正统论三首·辩论三》,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4页。
[29] 《苏轼文集》卷4《正统论三首·辩论三》,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4页。
[30] 《苏轼文集》卷2《礼义信足以成德论》,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47页。
[31] 《苏轼文集》卷2《礼义信足以成德论》,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47页。
[32] 《苏轼文集》卷2《形势不如德论》,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7-48页。
[33] 班固:《汉书》卷62《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8页。
[34] 《苏洵集》卷9《史论上》,邱少华点校,中国书店2000年版,第76页。
[35] 《苏轼文集》卷60《与王庠五首之五》,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23页。
[36] 《苏轼文集》卷4《正统论三首·辩论二》,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1页。
[37]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69《魏纪一》,魏文帝黄初二年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187-2188页。
[38] 《苏轼文集》卷4《正统论三首·总论一》,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0页。
[39] 参见王曾瑜:《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77年第3期。
[40] 《欧阳修全集》卷16《正统论上》,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67页。
[41] 邓锐:《宋代的<春秋>学与史学》,《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8期。
[42] 皇甫湜:《东晋元魏正闰论》,《全唐文》卷686,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031页。
[43] 《欧阳修全集》卷16《正统论上》,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67页。
[44] 汪高鑫:《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经史关系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页。
毛钦,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本文载《原道》第37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