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第一句就写到,“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这给了整本书一个明确的开始,以及追寻的目标。
《纯粹理性批判》是一本关于知识的书,是探讨人的知识是如何成为可能的以及如何获取知识,前者被康德称为先验要素论,后者被称为先验方法论。整本书也是分作这两大部分来展开的。
正如康德所说,一切知识的开始都是经验,所以在先验要素论的第一大部分讲的就是先验感性论,主要是讨论人在“经验”过程中感性认识的特点,这是知识的起点,但并不是知识成为可能的关键点。
知识成为可能的关键,就在于人不仅仅有感性,而且还有知性和理性。所以在先验感性论之后,康德进入了先验逻辑部分,也就是对知性和理性的探讨。在这里,康德详细分析了经由感性获得的那些经验如何变成知识,以及人如何对这些知识进行扩展。
康德从两个角度来进行的分析,一方面可以说是“积极的”,也就是知性如何把感性素材统一成知识,被称为先验分析论,这部分为人类认知总结了方法,划定了疆界。另一方面是“消极的”,也就是如何对那些疆界之外的东西进行判断,或辨别它们的问题,被称之为先验辩证论。前者是关于知性的论述,而后者则是有关理性的分析。
所以,在整个先验要素论里面,康德实际上是将人类的认知过程进行了一个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的这样一个分类:感性用来获得现象的杂多,知性通过其规则将这些杂多联系起来统一为现象,而理性则是在众多现象中去发现普遍原则。
接下来,我们就会正式进入先验辩证论部分,也就是先验要素论的最后一部分,也是关系到人类“纯粹理性”的内容。当然,这里的“纯粹理性”是狭义的,指的就是康德所说的理性功能,而《纯粹理性批判》这个书名中的纯粹理性是广义概念,指的是人类获得知识能力的那种理性的总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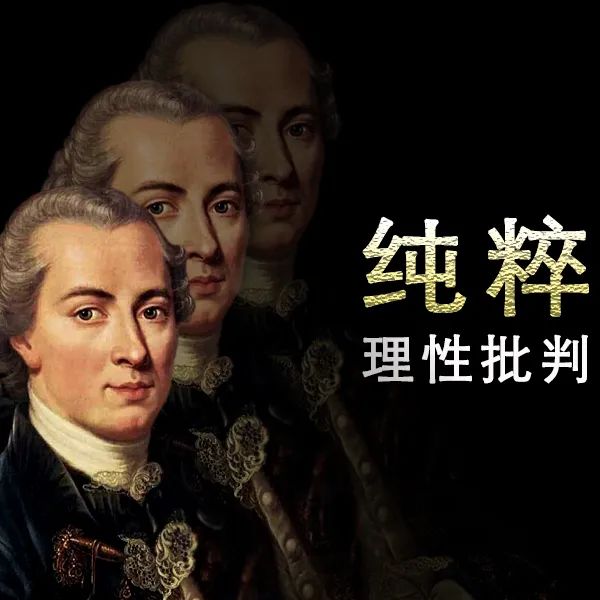
Day 109-118/2020年8月29日-9月7日
先验辩证论
我们首先总体的看一下先验辩证论的导言部分,在导言中,康德提出了这部分内容的必要性以及整体的目标。
在之前的内容中,康德提出辩证论不过是幻相的逻辑,在古典哲学当中,辩证这个词包含着诡辩的含义,引申出幻相、谬误的意思。而在康德这里,一方面沿用了辩证的这个内涵,同时又将辩证发展称为看清幻相,辨别谬误的意思。
这也就跟前面的先验分析论形成了一个补充。先验分析论是积极的,是在知识的范围内获得确定的内容的一种理论;而先验辩证论是消极的,是对幻相进行分辨的一种方法。
那么既然是要分辨幻相,就需要搞清楚幻相到底从何而来。首先康德明确幻相的本质——“真理或幻相并不在被直觉的对象中,而是在关于被思维的那个对象的判断中”。这实际上为我们指明了寻找真理和幻相的方向,或者说是具体的位置。
真理也好,谬误也好,都是产生于人在认识世界,获取知识时所进行的判断中。亚里士多德曾经说,真理就是概念与对象相符合。也就是说真理是一种关系的体现,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真理并不在认知对象本身上,而是人们认知的概念与对象相符合才是真理。所以幻相也就是概念与对象不符合的一种表现了。
康德认为主要有三类幻相:
1、经验的幻相;
2、逻辑的幻相;
3、先验的幻相;
先来看一下关于经验的幻相。所谓经验幻相,也就是人们从经验中获取的概念,与实际的对象不符合的情况。那么人们是如何从经验中获取概念呢,前面章节已经说的很透彻了,从感性开始,经由知性的规则,形成了经验的概念。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怎么会出现错误呢?
可以看到,在经验知识获取过程中,主要是两个步骤,一个是感性一个知性。康德引用当时一个著名的论断说,“感官不犯错误”,为什么呢?前面我们提到了,真理和幻相在关于被思维的那个对象的判断中,这里的关键词是判断,也就是做判断的时候才会出现对和错。但感官是不做判断的,我们知道感性知识获得直观杂多,但并不对它们进行判断。
那么再看知性,康德认为知性是有其规则的,所以在知性的判断中,如果严格按照其规则来进行,也是不会出错的。这个虽然不太好理解,但形象化的来说,知性有点像一个程序,程序是早已编好给定的,输入什么就会按照其规则给出输出,这是不会出错的。
那么经验的幻相出现在哪里?
康德认为,“错误只是由于感性对知性的不被察觉的影响而导致的,它使判断的主观根据和客观根据发生了混合,并使它们从自己的使命那里偏离开来。”
也就是说,感性本身是不会犯错的,其实这个意思是感性没有对错可言,因为它不做判断,而知性本身的机制也是没问题的,出现问题是在于感性向知性提供素材这个传输过程中,人们把主观根据和客观根据搞混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把筷子插入水中,我们会看到筷子弯曲了。感官可以说,我看到筷子弯曲或我感觉筷子弯曲了,这并没有问题。但如果把这个信息传递给知性,同时认为筷子就是弯曲的,就产生了“幻相”。
这里还能引出一个有趣的概念,也就是“知觉命题”。很多时候,当我们说“我觉得”怎样怎样的时候,就是一种主观判断,也就是知觉命题,这种命题,没有办法给一个非常客观的判断。比如在同样温度下,有人就觉得热,有人觉得冷,但没有办法统一的去说哪个人是对是错。很多时候,人的认知谬误就是来自于将知觉命题认作是客观命题。
回到幻相的类别讨论中,康德明确了经验的幻相的产生原理。然后进入先验幻相和逻辑幻相。其中逻辑幻相比较简单,逻辑是有其一套完整的规则的,根据规则是不可能犯错的,但有时候会有一些含混的运用,也就是在推论中对逻辑的错用,比如我们说,“人是分男女的,亚里士多德是人,所以亚里士多德分男女”,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逻辑谬误。
康德认为逻辑谬误是可以通过仔细考察逻辑推论过程本身就能发现问题并清除掉的,但先验幻相就很难被发现,以及无法一劳永逸的清除掉。
那么先验幻相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康德的描述:“这种幻相影响着那些根本不是着眼于经验来运用的原理,如果它们用于经验,我们至少还会有一种衡量这些原则的正确性的标准。然而先验幻相甚至不顾批判的一切警告,把我们引向完全超出范畴的经验性运用之外,并用对纯粹知性的某种扩展的错觉来搪塞我们。我们可以把那些完全限定在可能经验范围之内来应用的原理称为内在的原理,而把想要超出这一界限的原理称为超验的原理。”
先验幻相,也就是那些无法用经验来去检验的,超出知性范畴的经验运用之外的推理。在这里康德还提出了一对概念,他把可能经验范围之内的原理称为内在的原理,与之相对的是超验的原理,也就是超出经验范围之外的原理。
要注意的是,康德也明确说了,先验和超验是不一样的。先验是先于经验,但是有可能运用于经验的,但超验完全是在经验之外,在经验中是找不到对应物的。实际上,先验幻相的本身就是那些超验的原理所带来的,但为什么叫先验幻相而不叫超验幻相呢?我理解是先验本身是一种运用方法,在这个运用方法中产生的幻相,超验是一种结果,是超出经验范围之外的那些东西。如果说超验幻相,本身就已经超验了,就不用再做判断了。所以康德在此称为先验幻相,也就是要在先验运用过程中,识别幻相。
在导言的第一部分“先验幻相”的最后,康德将先验幻相的原因导向了“理性”,是人理性中的一些追求,导致先验幻相的发生,所以接下来,康德就要进入导言第二部分,“作为先验幻相之驻地的纯粹理性”。
那么理性到底是什么呢?
在康德的论述体系中,基本都是按照一个规律,考察一样东西先考察一般情况,再进入纯粹的情况。所以在考察纯粹理性之前,康德首先对一般理性进行了一个总体的论述。
康德认为人的知识产生于感官,前进到知性,而终止于理性。理性是人类认知能力的最高形式。对此我们做一个不是特别恰当的举例:比如我们看到一个苹果,这是最初的感性直观,但我们在感性中并不能得出苹果的概念,而是满眼的各种苹果刺激我们感官的那些杂多。这时,知性参与进来,用它的范畴将这些感官获得的素材进行统一,这样我们脑海里有了一个苹果的概念,我们知道红色的外皮是属于这个苹果的一种属性。但这样还不够,通过对苹果的研究,我们可以用理性进行一种更加广泛和普遍的推论,比如所有的苹果都是有外皮的,这在我们不用看遍所有的苹果的时候,就能够确定属于所有苹果的一个共同的、普遍的属性。
那么康德是如何定义理性这种能力呢,他是这样说的,“我们在先验逻辑的第一部分曾以规则的能力来理解知性;在这里我们把理性与知性相区别,把理性称为原则的能力。”
如果说,知性是一种给定规则的能力的话,那么理性就是在规则之上的原则能力。康德认为理性有两种运用,一个是逻辑运用,一个是纯粹的运用,那么既然有这两种分类,就需要在其上有一个统一,也就是“原则”的运用。什么又是原则?
康德说“原则这个术语是含混不清的,它通常意味着一种能被作为一条原则来运用的知识”。也就是说原则就是一种知识,在康德的分析中,他例举三种当时公认的原则:
1、后天经验的知识(大多数后天经验知识)
2、先天直观的知识(如数学原则)
3、知性的知识(通过概念在普遍中认识特殊的知识)
但康德认为,这些原则都还不是那种彻底的、纯粹的原则,也就是说这些原则只能对归于其下的那些概念进行指导,但并不具备真正的普遍性。对此他还以法律做了个举例,“有这样一个不知哪一天也许会实现出来的古老的愿望,即:我们总有一天可以不去寻求民法的无穷无尽的杂多条款,而去寻求它们的原则;因为只有在这里面,才包含着人们所说的立法简化的秘密。”
法律中的条例和原则之间的关系,就有点像知性和理性的关系。在法律中,针对不同的情况,会给出不同的条款、会有不同的判例,这个都是可以参考的依据,知性实际上就是在认知中起的这样的作用。但人们也会有个愿望,希望在法律中有一些总的原则,比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借此来指导所有的条例,这样就能省掉很多麻烦,这就是理性所追求的普遍性。
在关于一般理性的论述中,康德总结到,“知性尽管可以是借助于规则使诸现象统一的能力,而理性则是使知性规则统一于原则之下的能力”。接下来,就要探讨一下在原则之下,理性的两种运用——逻辑运用和纯粹运用。
关于理性的逻辑运用,比较容易理解,我们每天都在用,所以康德也作出了提醒,他认为我们在现实中有两类知识,一类是直接认识,一类是推论,我们有时候会理所当然的忘记推论知识是通过推论而来,而把它们当作一种直接认识,这是谬误的一个来源。
既然理性的逻辑运用就是推论,那么什么是推论?康德认为,推论有三个核心要素:基础命题、结论命题和推论程序。也就是基础命题在推论程序的作用下得出结论命题。
在推论中,也可以分为直接推论或者叫知性推论和理性推论,“如果推论出来的判断已经包含于前一判断中,以至于不必借助于第三个表象就可以从中推导出来,则这种推论就叫做直接推论;我更愿意把它称为知性推论。但如果除了那作为基础的知性外,还需要另一个判断才能产生结论,那么这一推论就叫做理性推论。”
知性推论比较简单,康德又对理性推论进行了深入讨论,“在每一个理性推论中我首先通过知性想到一条规则(大前提)。其次我借助于判断力把一个知识归摄到该规则的条件之下(小前提)。最后,我通过该规则的谓词、因而先天地通过理性来规定我的知识(结论)。”
举个简单例子,比如“所有人都是会死的”,这是一个大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可以得到男人会死、女人会死,这就是直接推论,也就是知性推论。但我们得不出亚里士多德会死,直到我们有一个小前提“亚里士多德是人”,这样就能得出亚里士多德会死这个理性推论了。
在理性的逻辑运用的最后,康德总结到,“理性在推论中力图将知性知识的大量杂多性归结为最少数的原则(普遍性条件),并以此来实现它们的最高统一。”实际上,这就是理性逻辑运用的最终目标。
那么既然规则的杂多性和原则的统一性是理性的要求,那么如果抽掉了知性,理性能否单独存在,或者说,理性本身是否先天包含有综合原理和规则,如果有的话这些原理和规则又在何处呢?康德紧接着就发出这样的疑问,这也是接下来要探讨的主要内容。
之前说过,知性是针对直观的判断,而理性则不是针对直观,而是针对概念和判断的。理性就是针对概念和判断不断地进行推论,去向前寻找条件的一个过程。如果理性有一个自身的原则,就是寻找条件的话,那么理性就会要求自身不断寻找,直到找到一个无条件者为止。
这里可能有一些难懂,举个例子,如果说一个数列(0,1,2,3……),前一个数字是后一个数字存在的条件的话,当我们给出一个数字比如99,按照理性寻找条件的要求,我们就找到了98,但这个98本身也要符合理性的这个要求,于是我们就继续向前找到了97,直到找到这个序列的那个最开始的“无条件者”——0。
由此康德得出了一个理性原则的描述——“如果有条件者被给予,则整个相互从属的本身是无条件的条件序列也被给予(即包含在对象及其连结之中)。”通俗的来说,理性就是让人可以对一个给定的对象进行推论并得到一个初始的无条件者以及整个推论链条的能力。
那么理性的这种能力,是否有其现实性?康德在接下来的章节将会分为两个部分去讨论,“前一部分要探讨纯粹理性的超验概念,后一部分要探讨纯粹理性的超验的和辩证的三段论推理。”
以下为原文
导言
I.先验幻相
我们在前面曾把一般的辩证论称为幻相的逻辑。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种或然性的学说;因为后者是真理,只是通过不充分的根据被认识罢了,因而它的知识虽然是有缺陷的,但并不因此就是骗人的,因而不必与逻辑的分析部分划分开来。更不能把现象和幻相看作一回事。因为真理或幻相并不在被直觉的对象中,而是在关于被思维的那个对象的判断中。所以人们虽然正确地说:感官不犯错误,但这并不是由于他们任何时候都正确地作出判断,而是由于它们根本不作判断。因此真理也好,谬误也好,诱导出谬误的幻相也好,都只是在判断中、即只有在对象与我们知性的关系中才能发现。在一个与知性的规律彻底符合的知识中是没有错误的。在一个感官表象中也没有错误(因为它根本不包含判断)。但没有任何自然力会自发地从它们自己的规律偏离开。所以不仅知性独自(没有其他原因的影响)不会犯错误,感官段子也不会犯错误;因此,知性不会犯错误是由于,当它只按照自己的规律行事时,其结果(即判断)必然会与该规律一致。但与知性的规律处于一致中的是一切真理的形式的东西。在感官中根本没有判断,既无真判断也无假判断。既然我们除了这两种知识来源之外没有别的来源,所以结论是:错误只是由于感性对知性的不被察觉的影响而导致的,它使判断的主观根据和客观根据发生了混合,并使它们从自己的使命那里偏离开来。例如一个运动的物体虽然总是会在同一方向上保持着直线,但如果有另一个力按照另一个方向同时影响它,它就会转入曲线运动。因此,为了把知性所特有的活动与混在其中的力区别开来,有必要把错误的判断看作两个力之间的对角线,这两种力按照两个不同的方向来规定这个判断,好像夹有一个角度,并把那个复杂的作用分解为知性和感性这两个简单的作用。这件事在纯粹先天判断中必须由先验的反思来做,这就使每个表象(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在与之相适合的认知能力中被指定了自己的位置,因而感性作用对知性作用的影响也就被区分开来了。
我们在这里的任务不是要讨论经验性的幻相(例如视觉的幻相),这种幻相是在对那些本来是正确的知性规则的经验性运用中出现的,通过它判断力就受到了想象的影响的诱惑。相反,我们所要谈的只是先验的幻相,这种幻相影响着那些根本不是着眼于经验来运用的原理,如果它们用于经验,我们至少还会有一种衡量这些原则的正确性的标准。然而先验幻相甚至不顾批判的一切警告,把我们引向完全超出范畴的经验性运用之外,并用对纯粹知性的某种扩展的错觉来搪塞我们。我们可以把那些完全限定在可能经验范围之内来应用的原理称为内在的原理,而把想要超出这一界限的原理称为超验的原理。但我并不把这些超验的原理理解为范畴的先验的运用或误用,后这只不过是未受到本应由批判而来的束缚的判断力的一个错误,这个判断力没有充分注意到纯粹知性唯一允许它起作用的那个基地的界限;相反,我把它们理解为一些现实的原理,它们鼓励我们拆除所有那些界标,而自以为拥有一个在任何地方都不承认有人什么边界的全新的基地。所以先验和超验并不是等同的。我们在前面所阐述的纯粹知性原理之应当具有经验性地运用,而不能具有先验的、即超出经验范围之外的运用。但一条要求取消这些限制甚至要求人们跨越这些限制的原理,就叫做超验的。如果我们的批判能够做到揭示这些僭越的原理的幻相,则前一类只有经验性运用的原理就与后一类原理相反,可以称为纯粹知性的内在原理。
逻辑的幻相(误推的幻相)在于对理性形式上的单纯模仿,它只是产生于对逻辑规则的缺乏重视。所以一旦加强了对当前具体情况的重视,这种幻相就会完全消失。相反,先验幻相不论我们是否已经把它揭示出来,是否已经通过先验批判清楚地看出了它的无效性,它仍然不会停止。(例如这一命题中的幻相:世界在时间上必定有一个开端)。其原因就在于,在我们的理性(它被主观地看作人的认知能力)中,包含着理性运用的一些基本规则和准则,它们完全是具有客观原理的外表,并导致把我们的概念为了知性作某种连结的主观必要性,看作了对自在之物本身进行规定的客观必然性。这是一种幻觉,它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正如我们不能避免海面在中央比在岸边对我们显得更高,因为我们是通过比岸边更高的光线看到海中央的;或者更有甚者,正如哪怕一个天文学家也不能阻止月亮在升起来时对他显得更大些,尽管他并不受这种幻相的欺骗。
所以先验辩证论将满足于揭示先验判断的幻相,同时防止我们被它所欺骗;但它永远也做不到使这种幻相(如同逻辑的幻相一样)也完全消失并不再是幻相。因为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是一种自然的和不可避免地幻觉,它本身基于主观的原理,却把这些主观原理偷换成了客观原理;反之,逻辑的辩证论在解决谬误推理时却只是在处理遵守这些原理时的错误、或在模仿这些原理时的某种人为的幻相。所以纯粹理性有一种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辩证论,它不是某个生手由于缺乏知识而陷入进去的,或者是某个诡辩者为了迷惑有理性的人而故意编造出来的,而是不可阻挡地依附于人类理性身上的,甚至在我们揭穿了它的假象之后,它仍然不断地迷乱人类理性,使之不停地碰上随时需要消除掉的一时糊涂。
II.作为先验幻相之驻地的纯粹理性
A.一般理性
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开始于感官,因此前进到知性,而终止于理性,在理性之上我们在没有更高的能力来加工直观材料并将之纳入思维的最高统一性之下了。现在,当我要对这一最高认知能力作出一种解释时,我感到有某种尴尬。在理性这里,正如在知性那里一样,当它抽掉了一切知识内容时,有一种单纯形式的、以及逻辑的运用,但它也有一种实在的运用,因为它本身包含有既非借自感官、亦非借自知性的某些概念和原理的起源。前一种能力固然早已由逻辑学家们以间接推理的能力(不同于直接推理)而做了解释;但后面这种自身产生概念的能力却还没有借此得到理解。既然在这里出现了理性的逻辑能力和先验能力的划分,那么就必须去寻求有关这一知识来源的一个更高的概念,它把那两个概念都包括在自身之下,我们在这里可以指望通过与知性概念的类比而使逻辑概念成为先验概念的钥匙,同时前者的机能表则提供出理性概念的谱系。
我们在先验逻辑的第一部分曾以规则的能力来理解知性;在这里我们把理性与知性相区别,把理性称为原则的能力。
原则这个术语是含混不清的,它通常意味着一种能被作为一条原则来运用的知识,哪怕它自己本身及根据自身来源并不是什么原则。任何一个全称命题,即使它是从经验中(通过归纳)得出来的,都可以在一个理性推论中用作大前提;但它并不因此而本身成为一条原则。数学公理(例如两点之间只能有一条直线)甚至是先天的普遍知识,因此它相对于能归摄于其下的哪些情况而言有权叫做原则。但我仍然不能因此而说我是从原则而认识直线的一般和自身的属性的,而只是在纯粹直观中认识它的。
所以我将把出自原则的知识叫做这样一种知识,即我通过概念在普遍中认识特殊的知识。这样以来,每一个理性推论都是从一个原则中推出一个知识来的形式。因为大前提总是提供一个概念,它使得所有被归摄于该概念条件下的东西都按照一条原则而从这概念中得到认知。既然任何普遍知识都可以在理性推论中被用作大前提,而知性则为这种知识提供普遍的先天原理,那么这些原理就其可能的运用而言,也可以叫做原则。
但如果我们按照其来源考察这些纯粹知性原理本身,那么它们就根本不是来自概念的知识了。因为假如我们不是援引纯粹直观(在数学中),或援引可能经验的诸条件,这些知识甚至都不会是先天可能的。“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有原因”完全不能从“一般发生的事”这个概念中推出来;毋宁说,这一原理表明我们如何才能对于发生的事得到一个确定的经验概念。
所以,知性根本不可能获得来自概念的综合知识,而这些知识才真正是我不折不扣地称作原则的知识;当然,所有一般全称命题在比较上都可以称作原则。
有这样一个不知哪一天也许会实现出来的古老的愿望,即:我们总有一天可以不去寻求民法的无穷无尽的杂多条款,而去寻求它们的原则;因为只有在这里面,才包含着人们所说的立法简化的秘密。但这些法律在这里也只是把我们的自由限制在它们得以与自身彻底一致的那些条件之上;因而法律所针对的是完全由我们自己所造成的、并且我们能通过那些概念本身而成为其原因的那种东西。但正如自在的对象本身那样,事物的本性因如何从属于原则之下以及应如何根据单纯概念来对它作出规定,这一点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事,至少在其要求中总归是几位荒唐的。但不论这里的情况将会如何(因为这是我们目前还要探讨的),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来自原则的知识(就其自身来说)完全不同于单纯的知性知识,后者虽然也能以某种原则的形式而先行于其他知识,但就其自身来说(如果它是综合性的)却不是基于单纯思维之上的,更不包含依照概念的普遍性。
知性尽管可以是借助于规则使诸现象统一的能力,而理性则是使知性规则统一于原则之下的能力。所以理性从来都不是直接针对着经验或任何一个对象,而是针对着知性,为的是通过概念赋予杂多的知性知识以先天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可以叫做理性的统一性,它具有与知性所能达到的那种统一性完全不同的种类。
这就是在完全缺乏(如我们想在下面才提供出来的)实例的情况下,我们已经理解到的关于理性能力的普遍概念。
B.理性的逻辑运用
人们在直接认识到的东西和只是推论出来的东西之间做出了区别。在由三条直线所界定的一个图形中由三个角,这是直接认识到的;但这三个角的和等于两个直角,这只是推论出来的。由于我们总是需要推论并因此终于完全习惯于它,我们最终就不再注意这一区别了,且常常像在所谓感官的欺骗的场合那样,把我们只是推论出来的某种东西当作直接知觉到的东西。在每个推论中都有一个作为基础的命题,以及另外一个、也就是从前一个中印出来的结论命题,最后还有推论程序,按照这一程序,结论的真实性就不可避免地与前提的真实性连结起来。如果推论出来的判断已经包含于前一判断中,以至于不必借助于第三个表象就可以从中推导出来,则这种推论就叫做直接推论;我更愿意把它称为知性推论。但如果除了那作为基础的知性外,还需要另一个判断才能产生结论,那么这一推论就叫做理性推论。在一切人都是会死的这个命题中已经包含着这几个命题:有些人是会死的,有些会死的是人,没有任何不会死的东西是人。因而这些命题都是直接从第一个命题中得出来的结论。反之,“一切有学问者都是会死的”这一命题则不包含在那个基础判断中(因为“有学问”这一概念在其中根本没有出现),它只有借助于一个中间判断才能从中推出来。
在每一个理性推论中我首先通过知性想到一条规则(大前提)。其次我借助于判断力把一个知识归摄到该规则的条件之下(小前提)。最后,我通过该规则的谓词、因而先天地通过理性来规定我的知识(结论)。所以,作为规则的大前提在一个知识与其条件之间所设的关系就构成了理性推论的各种不同的类型。因而这些类型正如一切判断一般地被按照如同在知性中表达知识关系的那种方式来划分那样,恰好有三个:定言的,或假言的,或选言的理性推论。
如果像多数情况下那样,结论作为一个判断被当作一项任务,为的是看它是否是从已经给出的、也就是使一个完全不同的对象被思维的判断中推出来的:那么我就是在知性中寻求这个结论命题的实然性,看它是否在该命题中按照一条普遍规则而处于某些条件之下。如果现在我发现了这样一个条件,而该结论命题的客体又能归摄到这个被给予的条件之下,那么该命题就是从这条对其他知识对象也有效的规则种推断出来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理性在推论中力图将知性知识的大量杂多性归结为最少数的原则(普遍性条件),并以此来实现它们的最高统一。
C.理性的纯粹运用
我们能否孤立理性?如果能,理性是否还是概念和判断的一个特有的来源,它们唯有从理性里面才能产生出来,而理性借它们与对象发生关系?还是说理性只是向自己给予的只是提供某种形式的丛书能力,这种形式是逻辑上的,它只是使知性知识相互从属,并使低级规则从属于高级规则(后者的条件在其范围内包含着前者的条件),只要通过它们的比较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我们现在马上要讨论的问题。实际上,规则的杂多性和原则的统一性是理性的要求,为的是把知性带进和自己的彻底关联之中,正如知性把直观杂多纳入概念之下并由此将它们连结起来一样。但这样一条原理并未给客体预先规定任何规律,也未包含把客体作为一般客体来认识和规定的可能性根据,而只是一条日常处理我们知性的储备的主观规律,即通过比较知性的诸概念而把它们的普遍运用归结为尽可能最小的数目,而并不因此就有权要求对象本身有这样一种一致性,来助长我们的知性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扩充,同时也无权赋予那条准则以客观有效性。总之一句话,问题是:理性本身、也就是纯粹理性,是否先天地包含有综合原理和规则,以及这些原则有可能存在于何处?
在理性推论中,对理性的形式和逻辑的处理方式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充分的指示,指出在由纯粹理性而来的综合知识中理性的先验原则将基于何种根据之上。
首先,理性推论并不是针对直观、以便将其纳入到规则之下(如知性以其范畴所作的那样),而是针对概念和判断的。所以纯粹理性即使针对对象,它也没有与这些对象及其直观的直接的关系,而只有与知性及其判断的直接关系,这些判断是最先指向感官及其直观以便为它们规定自己的对象的。所以理性的统一不是可能经验的统一,而是与这种知性统一本质上不同的。“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有原因”绝不是通过理性而认识和预先规定的原理。这原理使经验的统一性成为可能,而没有从理性那里借来任何东西,理性没有这种与可能经验的关系单从概念中是不可能提供出这一综合统一性来的。
其次,理性在其逻辑运用中寻求的是它的判断(结论命题)的普遍条件,而理性推论本身也无非通过将其条件归摄到一条普遍规则之下而来的判断(大前提)。既然这条规则又要接受理性的同一个检验,因而只要行得通,就必须(通过前溯推论法)再去寻求条件的条件,那么我们就看到,一般理性(在逻辑的运用中)所特有的原理就是为知性的有条件的知识找到无条件者,借此来完成知性的统一。
但这条逻辑准则不能以别的方式成为纯粹理性的一条原则,而只能这样来假定:如果有条件者被给予,则整个相互从属的本身是无条件的条件序列也被给予(即包含在对象及其连结之中)。
而纯粹理性的这样一条原理显然是综合的;因为有条件者虽然与某一个条件分析地相关,但并不与无条件者分析地相关。这就必须从这条原理中再产生出纯粹知性在只和可能经验的对象打交道时根本不知道的各种综合原理,对这种可能经验的知识和综合总是有条件的。但无条件者如果却是存在,就会被按照将它与那个有条件者区别开来的一切规定性来加以特殊的思量,并由此而给某些先天综合命题提供材料。
然而,由这种纯粹理性最高原则中产生出来的原理将对于一切现象都是超验的,也就是说,将永远不能有任何与者原则相适合的对它的经验性运用。所以它是与一切知性原理完全不同的(后者的运用完全是内在的,因为它们只把经验的可能性作为自己的主题)。现在,条件序列将(在现象的综合中,乃至在对一般物的思维的综合中)一致延伸到无条件者,这条原理是否有其客观正确性?它将对知性的经验性的运用产生什么结果?或者,是否任何地方其实都没有这样一类客观有效性的理性原理,而只有一种逻辑上的规范,即向越来越高的诸条件逐步上升而逼近它们的完成,并借此把理性最高可能的统一性带入到我们的知识中来?或者,是否理性的这一需要由于误解曾被看作了纯粹理性的某种先验原理,这个原理太急于把诸条件序列的这样一种无限制的完备性设定在对象本身之中?但即使是这种情况,又是什么样的误解和蒙蔽会嵌入这些从纯粹理性中取得的大前提(它与其说是公设,不如说是公则)并从经验上升到经验提条件的理性推论中来呢?这些就是我们在先验辩证论中要探讨的,我们现在要将这种辩证论从它深深埋藏于人类理性中的根源处阐发出来。我们将把这个辩证论分为两个主要部分,前一部分要探讨纯粹理性的超验概念,后一部分要探讨纯粹理性的超验的和辩证的三段论推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