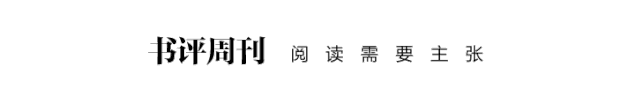
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的前世今生。一砖一瓦的垒砌,孕育了它的血肉;辛劳和汗水,赋予了它生命。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它就成为人类的挚爱,人们生于斯、长于斯、居于斯、死于斯,将自己的命运刻进城市的年轮之中。北京,现代中国的首都,帝国时代的京师,享受着万众敬仰的荣光,自然也有着独一无二的创建史。它是先秦古国燕国的都城,号为燕都,春秋时代的金戈铁马,战国的北地雄风,至今仍是响彻耳畔的传奇,也是这座城市的创建之始与辉煌的起点。千年后,历经数代沧桑,作为蒙元帝国这一世界帝国的大都,它屹立在辉煌的顶巅。来自世界各地的能工巧匠将它打造成举世瞩目的世界之都,接受那些跨山越海的慕名访客们由衷的赞叹。明清两代则延续了它傲视万方的辉煌,通过持续不断地建设和扩张,将这份辉煌一直传递到今天。
《创城记:北京 一座都城的诞生》特刊将借四篇主文和一份书单,分别从周代燕国都城、汉代到晚唐五代的幽州、元大都和明清帝都四个维度展现北京的城市创建史。
这是其中的第三篇,在梦幻与现实的交错中一窥元大都这座世界之都。
撰文 | 何安安、李夏恩
忽必烈伟岸的塑像静穆地注视着前方,这里曾是他用骏马丈量的土地,是野心勃勃擘画的世界之都的中心。如今,这里是一座遗址公园,精心修剪的草坪掩埋着昔日的巍峨城垣。在现代化高楼大厦的环绕下,这座公园就像是辽远的蒙古大草原的一片飞地,散发着阵阵往古幽情的气息。
因此,即使在这里偶遇穿越时空的元代访客也不奇怪——当然,这四个站在忽必烈像前,身穿典型蒙元服饰的汉子并非穿越八百年时空而来,而是一个名为“夜不收”的重演历史爱好者小团体。其成员周渝为了拍这张照片,特意蓄了胡须,以便显得更有当年蒙古铁蹄的粗犷气象。
“我们拍照穿的衣服叫做质孙服,是蒙古勋戚大臣和近侍穿着的一种官服”,周渝解释说。“质孙”即是蒙古语“华丽”的音译。
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将此服饰称为“金锦衣”:“衣其最美之金锦衣。同日至少有男爵骑尉一万二千人,衣同色之衣,与大汗同。所同者盖为颜色,非言其所衣之金锦与大汗衣价相等也。各人并系一金带,此种衣服皆出汗赐,上缀珍珠宝石甚多,价值金别桑确有万数……足见其事之盛,世界之君主殆无有能及之者也。”
在昔日大汗擘画的荣耀之都内,在创建者忽必烈汗的雕像前,身着质孙服,确实恰如其分。尽管蒙元的统治仅维持八十余年,但它给北京这座城市,乃至整个中国留下的文化遗产却余韵犹在,甚至不知不觉地渗透在日常生活之中,习焉不察。质孙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种蒙元达官贵人身着的特色服饰,即使在朱元璋将蒙元统治者驱逐漠北,建立明朝之后,仍被沿用下来,被称为“曳撒”,在与汉式服装结合后,创造出了新的样式。今天,在古装影视剧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明朝锦衣卫们,身上华丽得惹人眼热的飞鱼服,正是蒙元时代质孙服的绚烂遗风。
这群身着质孙服的古装爱好者们,自然对这段历史心知肚明。那天晚些时候,他们齐聚在一家烧烤摊前,大快朵颐一串串烤羊肉。这种用串扦烤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汉代。但撒在上面的各种佐料,则来自遥远的西域,转扦烧烤的方法,则可以追溯到中亚阿拉伯帝国的传统。蒙古征服者的铁蹄在草原和荒漠中奔驰,他们用强悍的武力降服了世界,又被世界各地的文明所折服。当他们翻身下马,在渤海之滨,华北平原之上缔造这座世界之都时,他们内心中激荡的不只有征服世界的欲望,也有一种强烈的热忱:在这里创造一个世界之都。
1
世界帝国之都的诞生
至元九年二月二十七日(1272年3月28日),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下诏,改中都为大都,至此,这座被旅行家马可·波罗赞誉为“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的繁华都市,就此诞生。
与其他朝代不同,蒙元王朝共有四座都城(哈喇和林、元上都、元中都、元大都)。忽必烈继汗位以后,定国号为元,他并建两都,以大都为正都,上都作为夏都的巡幸举措,既满足了忽必烈在生活、习惯上的需要,更是兼控中原汉地与蒙古宗亲的政治需求。四座都城中,大都城的规模最大,建筑最全,规划最为合理,功能最为完备,且地理方位处于最南,从大一统和控制南北地区和联系农耕与游牧区域,以及经营整个封建国家的角度来讲,毫无疑问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都城。从世界范围来看,元大都是当时首屈一指的都城。
大都的前身是辽南京(又称燕京)和金中都,在突厥语中,大都被称为“汗八里”,也就是“大汗之居处”,在《马可·波罗行纪》一书中,也使用了“汗八里”的说法。1280年,马可·波罗跟随忽必烈巡幸的队伍,来到了闻名已久的大都城,对于这座世界城邦“汗八里”,他这样记录:“此城之广袤,周围有二十四哩(一哩约相当于1.6公里),其形方正,由是每方各有六哩。环以土墙,墙根厚十步,然愈高愈削,墙头仅厚三步,遍筑女墙,女墙色白。墙高十步,全城有十二门(此处有误,大都城仅有十一门)……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道远望彼门也。各大街两旁,皆有种种商店屋舍。全城中划地为方形,划线整齐,建筑房舍。每方足以建筑大屋,连同庭院园囿而有余……方地周围皆是美丽道路,行人由斯往来。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
如果从今天的北京区域地图上画出大都的范围,那大都城址正好位于北京的城区之内,北至元大都土城遗址,南至长安街,东西至二环路,三面环山,东南一带为大片沼泽,西南角接近太行山。
要讲北京城的创建,忽必烈是绕不开的人物——中国大一统政权建都北京,始于忽必烈,而作为大元王朝的缔造者,忽必烈同样是大都城营建的最高决策者。周良霄在其所著的《元史》中引用《元典章》的记载,“中统四年(1263年)五月,忽必烈陞开平府为上都,翌年八月,复诏:‘开平府阙廷所在,加号上都,外燕京修营宫室’。”这里的燕京,后改称中都,最终被定名为大都。元代文人黄文仲在《大都赋》中说:“维昔之燕,城南废郛;维今之燕,天下大都。”
忽必烈
1266年,忽必烈任命安肃公张柔与行工部尚书段天佑等开始修建两都,为迁都燕京做准备。这时,忽必烈遇到了一个问题:是否要在已遭到严重破坏的金中都城池、宫阙上复建新宫?最终,在刘秉忠的建议下,忽必烈选择抛弃旧址,在原址东北方旷野上重建新城,仍称中都。整座城市以金代万宁宫(今北海琼华岛)——这是当时保存尚好的金代行宫——为中心,形制为三套方城:包括外郭城、皇城和宫城。无论是新城城址的择定,还是城池、宫阙的规划等,都由刘秉忠统领负责。
刘秉忠为何人?有“聪书记”之誉的刘秉忠有多个名字,他起先名叫刘侃,出家为僧后起名子聪,为官后又改名为刘秉忠。布衣出仕的刘秉忠堪称忽必烈座下开国定都的第一功臣,就连大蒙古国更名为大元,也是刘秉忠对忽必烈的奏议,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
在奉忽必烈之命修建了上都城之后,刘秉忠在赵秉温、赵铉的协助下,对大都进行了全盘设计,奠定了北京市最初的城市雏形。《元史·刘秉忠传》中曾提到,“四年(1267年),又命秉忠筑中都城,始建宗庙宫室。八年(1271年),奏建国号曰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传说中,刘秉忠“通晓音律,精算数,善推步,仰观占候,六壬遁甲,《易经》象数,邵氏《皇极》之书,靡不周知。”这些才干悉数被他运用于大都城的规划和营建之中。至元十一年(1274年)正月,大都宫阙建成。遗憾的是,同年八月,刘秉忠无疾而终,时年五十九岁,没能等到这座他担纲总设计师的都城最终筑成。
元大都布局复原图。
在刘秉忠的规划设计之下,大都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平地创建的街巷制都城。作为元代的都城,大都只有短短九十几年的历史,但时至今日,北京城依然可以在一些街巷间看到当年大都的城市格局和风貌。尽管这座始建于1267年(至元四年)的都城,迄今为止已相隔我们七百五十三年。
大都的设计者当然不只有刘秉忠。除他以外,张柔、张弘略父子,段天佑,王庆瑞,刘思敬,郭守敬,杨琼,以及也速不花,也黑迭儿丁,阿尼哥等也参与到了都城设计之中。
从至元四年大都城正式开工筑城,到至元二十四年,筑城工程全部告成,再到至元三十年完成连通大都和通州的通惠河(标志着元大都城的最终建成),全部工程历时26年。这座亘古空前的都城,以积水潭东岸的中心阁为中心点,城周总计28600米。
大都城的街道是南北东西走向的干道,被划成方整的棋盘形状,各条街道宽阔繁华。黄文仲在《大都赋》中说,“华区锦市,聚万国之珍异”,“天生地产,鬼宝神爱,人造物化,山奇海怪,不求而自至,不集而自萃。”而据《析津志》记载,元大都有米市、面市、菜市、果市、铁器市、穷汉市等30多种市场,集中买卖各种货物,城市规模之宏大自不待言。
2
大都的中心
位于北京西北二环的积水潭,旧称海子、玄武池,是元大都皇城外北面的一大片水面的总称(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元代的积水潭和现在的积水潭并不相同,包括了北京西城什刹海的前海、后海、西海三块水面),它是自元以来流传至今仍在沿用的名字。对于大都城来说,积水潭的地位非同一般。大都城最具特色之处,就是以积水潭(海子)为中心布置城市和环太液池布置宫殿。显然,这是一个大胆的创新,从而也使它在中国都城建设史上独具一格而富有魅力。对此,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勐认为,以水的位置和形态决定大都的城市格局和布置,很可能反映了游牧民族传统的“逐水草而居”的深层意识和生活上的实际需要。《元史·地理志》中记载:“海子在皇城之北、万寿山之阴,旧名积水潭,聚西北诸泉之水,流入都城而汇于此,汪洋如海,都人因名焉”。
大都有两个供水系统:一是由高梁河、海子、通惠河构成的漕运水系;一是由金水河、太液池构成的宫苑用水系统。漕运对于大都城的重要意义无需多言,《元史·食货志》记载:“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江南……而江南之粮分为春夏二运,盖至于京师者一岁三百万余石。”
由丁超所著的《元代京畿地理》一书中提到,元代北京地区的区域与城市人口达到前所未有的数量。至元七年(1270年)大都(中都)地区户口共计18.4万余户,63.5万余人,其中城市人口41.8万人。泰定四年(1327年)大都地区人口发展到极致,高达43.7万余户,208.2万余人,其中城市人口95万余人。也有研究认为,后至元六年(1340年)大都城人口接近百万。
《元代京畿地理》
作者:丁超 主编:尹钧科
版本:北京出版社
2016年12月
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城,对粮食以及各类物资的需求无疑非常巨大。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大都城一方面需要提高本区域粮食产量,另一方面则需要依托远途运输。但隋唐时期所修建的大运河,并不能满足元朝所需,以通州为终点,也为运输带来了许多不便和浪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作为刘秉忠的副手及弟子,郭守敬在这其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孙勐认为,郭守敬在大都营建中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主持兴修水利和制造天文仪器。孙勐提到,郭守敬使用金朝废弃的金口河,解决了修建大都所需西山建筑材料的运输问题,同时还可以在河水流经之地灌溉农田。另外,郭守敬引玉泉之水入城,注入太液池,是为金水河,解决了宫苑的用水。更为重要的是,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在郭守敬主持下,从白浮村开凿渠道,经瓮山泊(今昆明湖),至城内积水潭,向东南直达通州,与大运河相连接,即为通惠河,保证了漕运用水的供给。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基建考古室副主任张中华,曾在2007年4月中旬至2008年5月上旬参与了对万宁桥和地安门东大街之间的北京玉河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据张中华介绍,在这次考古发掘中,清理出了元代通惠河堤岸遗址,这一遗址就压于明代南岸之下,不可谓不令人慨叹。
《大元三都》
编者:首都博物馆
版本:科学出版社
2016年7月
通惠河于至元二十九年八月开凿,于至元三十年八月竣工,历时一年。史书中记载,郭守敬于至元三十年(1293年)修建通惠河完毕后,元世祖忽必烈自上都归,“过积水潭,见舳舻蔽水,大悦,(即赐)名曰通惠河。”自此以后,从杭州出发的运粮船,就可以深入京城腹地,直接驶入积水潭港。而因为水量大大增加,由海路而来的漕船经天津沿北运河也可到达积水潭,使得积水潭成为维系京城“两运”的重要码头。
黄文仲在《大都赋》中写道:“扬波之橹,多于东溟之鱼。驰风之樯,繁于南山之荀。”当时的繁盛可见一斑。首都博物馆国内合作与民族考古研究部主任谭晓玲也是一位资深元史研究者,她认为,作为大运河的中点,积水潭一带是当时大都城中最为发达和重要的商贸区,不知道是否可以将之理解为今天的CBD。
当然,对帝王而言,积水潭的功用不止如此。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罗新在其所著的《从大都到上都》一书中提到,元代皇帝座驾迥异古今,乃东南亚所产的大象,也就是史料中的象舆或者象撵。而《元史·舆服志》记载,这些大象“育于析津坊海子之阳”。这些来自异域他方的庞然巨兽,一如这个庞大的世界帝国的缩影,张扬着它的雄奇与辉煌。
3
幻影之都
那么,这座崛起于13世纪的世界帝国,在今天的北京城留下了哪些印迹呢?或者,对于今天的北京城来说,哪里可以寻觅到昔日的大都风貌呢?
于2003年进行整体改造修建的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自然是其中之一。这个西起学院南路明光村附近,东到芍药居附近的狭长公园里,有着七百多年前的大都城墙遗迹。和平门外闻名遐迩的琉璃厂,得名也可追溯到元朝。这里在辽代被称为海王村,直到元代因海王村位于元大都南侧,距离都城较近,成为烧制琉璃瓦的官窑。孙殿起《琉璃厂小志》记载:“元代建都北京,名大都城,设窑四座,琉璃厂窑为其中之一。分厂在三家店,派工到西山采取制琉璃瓦器之原料,由水路运至海王村之琉璃窑,以备烧制。缘元代由此地至西山,水道畅通,可以用船只启运也。”琉璃厂由此得名。此外,海淀区与西城区交界处的高梁桥,西城区的白纸坊,王府井大街附近的鹁鸽市等地名,也始自元大都时代。
“地安门内的后门桥,其实就是元代的万宁桥。至元七年(1270年),刘秉忠、忽都于思、赵秉温言,“大都城既成,宜有明神主之,请立城隍神庙。上然之,命择地建庙,如其言。得吉兆于城西南隅,建城隍之庙”。这座城隍庙,位于大都城西南隅顺承门里,也就是今天西城区的成方街33号。北京都城隍庙的历史亦由此开始。
除都城隍庙外,北京还有一些寺观也起自大都时代或者更早一些时期。比如阜成门内大街北部的白塔寺(大圣寿万安寺),位于朝阳门外神路街的东岳庙(东岳仁圣宫)等。被尊为全真龙门祖庭的白云观,由尹志平在掌教之后修建于长春宫东侧,丘处机的遗蜕葬于其内的处顺堂。“丘处机还燕以后,成吉思汗下旨将他所居之太极宫改名长春宫。”孙勐介绍说:“元成宗时,张九思的夫人出资在处顺堂右修建了刘仲禄的祠堂。白云观也就成为全真龙门祖庭,号称道教全真第一丛林。”
元代道士瓷像,北京市西城区旧鼓楼大街出土,首都博物馆藏。
但这些建筑遗存和地名,并非是元大都留在人间的唯一遗产——真正的遗产是无形的,就像是质孙服、元杂剧和元曲,以及那些萦绕着这座世界之都所创生的梦幻奇想。那是一个宏大雄奇的幻影,是世界的缩影,是令人向往的俗世天堂。就像桂冠诗人柯勒律治在读完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描述的元大都所产生的幻象一般,那是“内心荒漠中的一块魔地,一眼清泉,一片鲜花碧树的绿洲”。
(特别致谢: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首都博物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孙勐、张中华,首都博物馆国内合作与民族考古研究部谭晓玲,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郭爽对本文均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