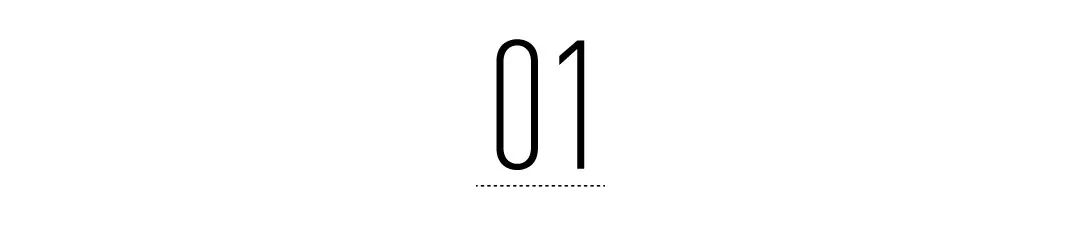讨论《乐队的夏天》第二季时,很多人把五条人和重塑互相对立,给他们贴的标签分别是“接地气”和“文化精英”。
但我认为,五条人的对立面从来都不是重塑,而是那些喊着“不应该描述那些人”的人。
十年前,《海上传奇》在温哥华上映时,导演贾樟柯遭遇了一次意外争论。
电影放完,一个20多岁的女学生抛给贾樟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你有没有考虑,你的电影被外国人看到,会影响他们对上海、对中国的印象,甚至会影响外国人对中国投资的信心?”
《海上传奇》
这番觉悟甚高的质问,惹火了贾樟柯:
“想那么多外国人干吗?就为了那些投资,为了外国人怎么看中国,我们就忽视一种真实的存在吗?中国十三亿人口中有很多人依旧生活在贫穷的环境中,难道我们可以无视吗?”
短暂沉默后,女生轻蔑一笑:
“是啊!为了祖国的尊严,我们当然不应该描述那些人的情况。”
如今,二人的那次争论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但在社交媒体里,你依然可以看到相似的争论。
尽管与那位女生持相同想法的人,理解贾樟柯的人,两边谁也没有说服谁,然而时代的风似乎把那位女生对贾樟柯的质问,鼓动成为最主流的呐喊,占据舆论高地。
不过,只要你把目光从网络移开,投回现实,并不难找到那些所谓脏兮兮的地方。
而且从人员流动来看,这些脏兮兮的地方,与那些“高大上”之地并不隔离对立,而是互通的,并不割裂,无法折叠。
比如在大城市里,那些见不到太阳的地下室,简陋的城中村公寓,相对于大厦林立,彻夜通明的CBD区域、是脏兮兮的。
但这些地方,却让无数刚毕业的外地年轻人,做小本生意的商贩,送快递外卖的打工者,有了不需要花费太多房租的容身之地。他们在这里得以在大城市里实现自力更生,积累进一步向上攀爬的资本。
又如无数个土不土洋不洋的县城,相对于一派现代化景象的大城市,也显得脏兮兮的。
但这些连接城市与乡村的中间地带,却又是无数农村少年接受教育,开阔视野,不再重复父辈命运的起点。
如果将时间放长到从80年代到现在,那么每一个来自县城,乡镇的“小镇青年”,几乎都曾在“脏兮兮”的地方生活过。
以人数而不是话语权来衡量,这些“小镇青年”必然会是这个国家的主流人群之一。
一位网易云用户对《县城》的评论
所以,小镇青年不应是面目模糊的存在。
无视小镇青年的话,那么无论是记录这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还是想展现当下社会,不仅不完整,还会失真。
更何况,小镇青年这个群体,总是会上演充满个体生命力与时代感的故事。
那些从这个群体走出,又能把这个群体的故事讲好的人,自然也就成了“人民艺术家”。
这其中,电影界有贾樟柯,音乐界则有五条人。
B站上有一则名为《县城》的混剪视频,播放量34.6万。其中有几组镜头,来自贾樟柯的《天注定》《山河故人》《江湖儿女》。
视频的背景音乐,是华北浪革的《县城》。他们在歌里反复吟唱着八个字:没有县城,万万不能。
虽然这不是五条人的作品,但对于“没有县城,万万不能”这八个字,想必他们有着真切的感受。
《乐队的夏天》第二季第一期里,仁科和阿茂的出场画面,有一股穿越感。
墨镜,花衬衫,皮夹克,富城头——在上世纪90年代,这些装扮深受潮流青年的喜爱。
而这些青年,往往被保守的人视为流氓。
显然,五条人散发的“流氓”气息,引起了超级乐迷的好奇心。周迅问仁科:你们会打架吗?
仁科愣了一下,然后脱口而出:我知识分子,不打架的。
话音一落,全场哗然。节目播出后,网上也有不少人,把这话当成仁科的玩笑。
实际上,五条人在十一年前就和知识分子、文化人打成一片了。 “文化精英”对他们的关注与热捧,比大众要早得多。
阿茂与仁科都在广东海丰县长大,2004年到了广州后,在石牌村做起了“走鬼”,摆了四年地摊。
不过尽管是流动小贩,俩人也算是文娱行业的下游从业者——仁科卖盗版书,阿茂卖打口碟。
和他们住一栋楼的,有刚毕业的大学生,有在公司上班的白领。和他们一起摆摊的,有算命的、卖水果、卖烧烤的。城管没事儿的时候会和他们聊天,发廊妹们时不时地从摊前走过,留下浓烈的香水味。
2007年,广州要准备举办亚运会,俩人结束了走鬼生涯,盘了一个店面开始卖唱片;2009年,俩人正式组建五条人乐队,并录制了首张专辑《县城记》。
凭借《县城记》,他们拿下华语传媒音乐大奖“最佳民谣艺人”,南方周末文化原创榜2009年度致敬音乐大奖等奖项。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平称五条人“可以算是中国最好的现实主义文学乐队”。
如果从作品的创作倾向来看,他们也早就是知识分子,是文化人了。
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有为普通人进行创作的传统。
唐代白居易为卖炭翁写下千古名句“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老舍在民国时期以人力车夫为主角写出了《骆驼祥子》;先锋派作家余华在1995年以丝厂送茧工为主角写出了《许三观卖血记》。
而在五条人的专辑里,人们同样可以听到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
乐迷们曾这样概括他们的前三张专辑:《县城记》写的是他们在县城的故事,《一些风景》则是讲城乡结合部的故事,而《广东姑娘》则放眼到了广州、东莞这些大城市。
《一些风景》的封面,隐约可见乌坎天后戏台
始终不变的,则是小人物的故事与情怀。
2016年的《梦幻丽莎发廊》,2019年的《故事会》,也同样如此。
那里,有穿着旧拖鞋、骑着旧单车,平时一贯“佬势势”却总是进派出所的道山靓仔;
有兜里没了钱,只能找会计部阿妹提前要工资的酒鬼猪哥伯;有在家里踩着拖鞋跳舞,然后带着小狗出门散步的小情侣;
还有梳着“周润发头”的社会青年阿虎,本来要和兄弟们去打架,却跑到一座大楼面前大喊“阿娇!你爱跟我走吗?我就等你一句话!”
讲述这些故事时,五条人从来不对这些普通人做道德审判,也不为他们打逆天改命的鸡血。
对好色的老光棍阿炳耀,他们哀叹“真是可怜呦”;对失去初恋的打工仔,他们安慰说“明天的太阳依然为你而升起来”。
此外,五条人也时不时地展现内心的柔情与浪漫。
他们吟唱“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他们感叹“风吹过石牌桥,我的忧伤该跟谁讲?”
他们将石碑村里那些粉红色的回忆也写进歌里。他们把梦幻丽莎发廊做成了专辑封面。
那首忧伤的《晚上好,春天小姐》,堪称是他们为风尘中人写的一首情诗:
请你不要害怕这一切
亲爱的春天小姐
那些最香艳的吻
最美丽的笑声
市长先生把你
给遗忘了吗
他曾对你说
亲爱的春天姑娘
这儿永远爱你
春天的风
香艳了吗
美丽了吗
不见了吧
《晚上好,春天小姐》的MV
拍摄于石牌村
而在时代大潮的起落之中,被拍打到角落,然后被人遗忘的,又何止春天小姐。
就连那春天的故事,也渐行渐远,恍如隔世。
创作《梦幻丽莎发廊》时,五条人还将自己看到的一些与小人物有关的新闻报道写成了歌,他们称其为“新闻民谣”。
比如《初恋》就来自一条社会新闻:一个男青年在赚到钱后,开着卡车回到老家寻找他的初恋。结果发现初恋因为家里拆了迁,早就搬走了,家乡也变了模样。男青年失望离去,却在路上遭遇车祸,他忍不住抱头痛哭。
又如《热带》,主角是个杀人惯犯——“有了经验之后他开始杀人不眨眼,再捅死一个去银行取钱的人,抢了钱之后买了一辆摩托,现在的刘德龙不再是个正常人”。
这首歌灵感来源于贾樟柯的《天注定》,
电影里演这个杀手的是王宝强
如果说贾樟柯电影中的山西县城青年,是在灰蒙蒙天空下,混沌且世俗地生存。
那么五条人歌里的南方小人物,则是在湿漉漉的空气里,莽撞而鲜活地活着。
不过混沌也好,莽撞也罢,能够改写命运的小人物终究是少数,大多数的结局,都是早已被写好的,无处可逃的宿命。
为此,他们引用《恋恋风尘》的台词,感叹“人生就像种荔枝,有雨也累,无雨又累 。”
为此,他们把小人物的愿望放到时代中吟唱:“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流晚几年行得不啊.....亲像国家的经济,楼价四散飞。”
他们在《阿琳娜》中写“那些贪食的鸽子,乌鸦麻雀还有天鹅,它们日复一日地等待着那些善良的人们,他们会给它们带来充足的粮食”。
我想起张楚“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这些歌词,是对生灵,对众生最诚挚的祝福。
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仁科与阿茂,能够因为音乐认识,继而走出海丰,搞起摇滚,也是有时代原因的。
这个原因之一,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全球化浪潮。
《县城记》封面写着:“立足世界,放眼海丰”。
全球化浪潮滚滚,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电影、文学,让两个县城青年拥有相同爱好,继而让他们结缘,一起践行这八个字。
除了讲述身边人故事之外,五条人的一些作品,有着浓烈的“县城文艺青年”与“城乡结合部知识分子”情结,闪现着他们自己的身影。
体现这些情结的符号,在他们的专辑里虽然不多见,但一旦出现,就有一种理想与现实相错位的冲突感,颇有自嘲意味。
仁科在《耍猴的人在月台上看苹果》 中唱:“在鸡鸣之前,我和拉面馆的女服务员聊起了理想。黄昏的时候,我和发廊小姐聊着一些哲学问题。”
阿茂在《梦想化工厂》中,讲一个县城青年去拔牙之前,要先看梁文道的《开卷八分钟》。
到了《世情》中,他们则讲述了一个梦想从诞生到破碎的过程:
目睹老三叔婆去世的阿良仔,决心要走出去看看世面,要去纽约,去巴黎,去欧洲看戏,去澳洲钓鱼。结果“风咧在吹,雨咧在落,时间十多二十年过去了”,阿良仔在工厂从早做到暗,哪儿都不曾去过。屋里存着的“十几张CD和几本摇滚杂志”,封存了他那些破碎的梦想。
他们直接触及严肃问题的作品虽然不多,但却颇具力道。
他们通过歌唱两位知名老乡——彭湃与陈炯明,重访了海丰的革命史。
《彭啊湃》,一个啊字让一个教科书中的烈士形象瞬间鲜活,除了彭湃,他们还刻画了革命看客的形象:农民说要回家饲猪,而市民说正在看戏。
《陈先生》只有三句歌词,却用了三种方言:用海丰话唱“1878伊生于海丰”,用粤语唱“1933年讵死于香港”,又用客家话唱“1934年他葬于惠州”,然后发出一声呼唤:陈先生。
他们用《最寒冷的一天》,讲述2008年春节中国南方遭遇的大面积的雪灾;《烂尾楼》则切中民生话题。
而《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中那一句:“今天啦全球化啊,明日就自己过”,如今听来更是应景。
恐怕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在11年前也做不出如此准确的预言。
十年前,《海上传奇》上映,五条人拿到了华语金曲奖的最佳新乐队奖。
同样是县城青年的我,在那一年成了800万北漂的一员。第一份工作,试用期月薪只有2800块。
好在那时在三环内找个地下室还不算什么难事,月租只需要三四百块,剩下的钱足够用来吃饭、交通。
在地下室里,我住了整整一年。那里人员密集,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即便不用说话,住个两三个月也能了解各自的日常习惯,对干啥的都能了解个大概。加上隔音很差,对隔壁的了解就更深刻了。
我的一个隔壁,是个离了婚的中年女人,独自带着儿子。儿子正在读高中,总是被训,想来应该是学习不太好。
另一个隔壁,是一对打工情侣。几平米的小房间,并不妨碍他们把日子过得充满欢声笑语。每周都会上演固定节目,节目的声音在地下室里回荡,撩拨单身汉们的春心。
不过要说最难忘的声音,要数每晚7点半到8点之间,地下室走廊传来的高跟鞋碰撞地砖的咔哒声。
那是几个小妹的上班时间。
其中一个小妹和男朋友住在一起,男朋友看上去没啥正经工作,经常在地下室躺一天。但这并不妨碍小妹很爱他。隔三差五她就会在公共水房里给男朋友刷鞋,让他的运动鞋总是保持通透白亮,比主人活得体面。
还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北京大爷。我不知道他为何也“沦落”到了地下室。他在房间的墙壁上,贴了一张巨幅彩票分析图,上面绘制着五色球的走势。每次从他房间路过,最常见的画面就是他死死盯着那张分析图。
也不知后来他有没有中个大奖。
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没有和他们好好聊过天。但这些片段,就这样永远停驻在我的记忆里。
尽管从住进地下室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在期待搬出去,住进楼房里。但我并不觉得那段日子有多么难捱。反而在觉得自己惨的时候,会及时告诉自己不要顾影自怜。
如果五条人也在那个地下室里生活,这些人也许会被他们写进歌里吧。
写这篇文章时,我总会追问一个问题,贾樟柯的电影也好,五条人的歌谣也好,到底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它们记录着小人物,关怀着小人物,但无法改变小人物们的命运,不是吗?
然而人这种高级动物,除了解决吃喝拉撒,生老病死这些生理需求和问题,还得找到许多东西,填充自己的生命,好让它看上去有意义,让它可以消解无聊、驱赶痛苦,让它以有涯对抗无涯,让它终将尘归尘土归土时,可以坦然一点。
这些填充物,就包括电影,小说,音乐。
它们不需要花太多钱,甚至不需要花钱。这已然是人类文明最美妙的创造。
更美妙的是,还有五条人这样的民间艺术家,为你我这般小人物写一首歌,谱一段旋律,搞得还不赖。
那些歌,就像我曾经的地下室邻居一样,让你知道这世界有很多很多人,虽然不知道前方是否阳光灿烂,但一样在活着。
这就够了。
至于别的,老天自有安排。
不论是五条人,还是我们每一个人,人人都有讲故事的权力。
而那些喊着“不应该描述那些人”的人,才是真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