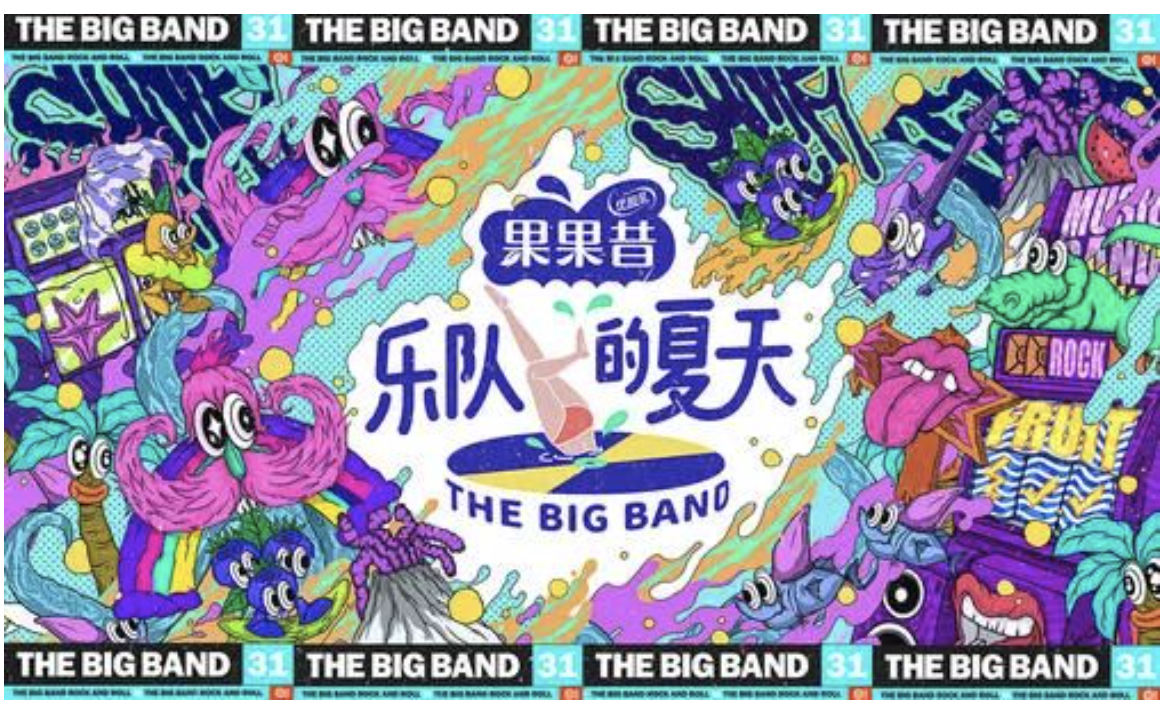
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把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拉在一起做一件事,但人与人连接的可贵之处也正在于此,乐团中性格各异的人可以因为音乐而被粘合为一个整体,并在演出现场呈现出一个有灵魂、有性情的乐队,这本身就是一种对人性的挑战。
——孟庆延
两季《乐队的夏天》感染和触动了很多人,从直击人心的歌词旋律,到和乐队有关的幕后故事等等,每个人对乐队的夏天都有不同的关注点。
社会学学者孟庆延,也是乐夏的老乐迷,开车时不经意的一个瞬间,刺猬乐队改编的《只要平凡》以他意想不到的方式顺着他的耳廓,溜进了他的心房;
据他回忆“这首歌当时听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眼泪情不自禁地往下流,事后百思不得其解,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当天真的没发生什么伤心事,但我的情绪还是毫无来由地被这首歌激荡起来了。从那以后,我对《乐夏》的热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在他看来,马东点评邦邦乐团的一句话“乐队是人与人的连接”有着十分强烈的社会学意味。
“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把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拉在一起做一件事,但人与人连接的可贵之处也正在于此,乐团中性格各异的人可以因为音乐而被粘合为一个整体,并在演出现场呈现出一个有灵魂、有性情的乐队,这本身就是一种对人性的挑战。”
越是用心去做的音乐,越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
我们为什么会被音乐打动?怎样理解音乐背后的力量?作为本期播客的当期主编,孟庆延还想和大家聊一下,怎样用社会学的视角看乐队的夏天,乐队中人与人的关系。
大观天下志 × 孟庆延 × 何必
孟庆延: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何必:北京大学史学博士
01 .
爱一首歌、一支乐队
往往不需要理由
何必:大家好,我是何必,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的教师孟庆延老师,来听他聊一聊他的学术私货。孟老师其实是我的师兄。
庆延:我们认识好多年了,何必以前叫荷包蛋。
何必:你不要透露我的小名,言归正传,师兄最近有看什么综艺吗?
庆延:最近有在看《乐队的夏天第二季》。
何必:想不到您一个学院里的老师还能这么潮。
庆延:一个人潮不潮跟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没什么关系,我个人觉得音乐这个东西更多是跟代际有关,跟年代有关。
80后的很多朋友都是听着窦唯、张楚、何勇、面孔,看着红磡长大的,到现在我手机里都有他们的歌。
《第一季乐队的夏天》公布其阵容的时候,我当时预设了自己会喜欢面孔乐队,因为他能勾起我们80后这一代人的怀旧感,依稀记得,我中学时期就开始听面孔乐队的歌了。
面孔乐队的《梦》在舞台上响起的时候,熟悉的旋律更是让我和身边的很多朋友感慨万千,但后续追乐夏的时候,却发生了一间令我最初意想不到的事,就是我越来越喜欢刺猬乐队啦。
为什么会被一首歌、一个人打动这类问题,确实蛮难回答的;
这就跟你爱一个人一样,让你分析你为什么爱他,分析不出来还好,如果你能分析出来个所以然,那你就是不爱他,因为爱是没有理由的。很多时候,我们喜欢一个人、一首歌或者一个乐队,真的就是一瞬间的事。
我是在开车的时候,偶然间听到了刺猬乐队改编的《只要平凡》,当时听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眼泪情不自禁地往下流,事后百思不得其解,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当天真的没发生什么伤心事,但这首歌就是激荡起了我的情绪。
从那以后,我对《乐夏》的热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久而久之,感受最强烈的一点就是,真正触动人心的不只是好听的旋律、耐听的歌词、现场的气氛和感染力,更是音乐背后的力量和灵魂。
02 .
音乐把乐队中性格各异的人
粘合在一起
何必:怎么理解摇滚乐背后的力量?
庆延:这个力量就是你能够从他们的音乐里找到共鸣,通过他们的音乐,你能感受到这是一群很有力量的人,一群情愿为自己喜欢的事坚持到底的人。
我后来还看过一些关于他们的报道、采访和纪实,令我感触最深的是石璐和子健的故事,他们在一起7年,后来虽然又分开了7年,但始终还在刺猬乐队里面。
抛去炒作的因素不谈,单看这个故事本身的话,我们会感觉到,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这就好比你跟你办公室的人谈了7年恋爱,分手7年,这种情况下,你觉得你还能坦然地跟他坐在同一间办公室吗?
此刻的你们或许对彼此早就没什么感觉了,爱和恨在此刻都是可以避免的,但有一种感觉真的是无处可避,这种感觉就是尴尬,一种熟悉的陌生人才会有的尴尬,双方早就没什么感觉了,但还会对彼此的微表情保持异常的敏感。
视线切换回石璐和子健的故事中,我们会注意到一个场景,改编《只要平凡》的时候,俩人经常意见不合就开吵,互不相让,但这却并不妨碍他们去做一件两人共同喜欢的事,而且更难得的是他们没有离开乐队;在我看来,他们真的有一种超越个人于感情之上的更高的追求和喜爱,就是音乐。
这让我想起了马东在点评邦邦乐团时说的一句话,乐队是人与人的连接,这句话说的特别社会学。
03.
人与人的连接
尤为难能可贵
庆延:有些人生阅历的人都明白,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把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拉在一起做同一件事,正因如此,所以我们才会有团建。
团建这件事,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反人性的,因为这相当于要逼着你和自己不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各种尴尬的事情。
但反过来看,人与人连接的可贵之处也正在于此,乐队能把性格各异的人融为一体,还能在演出现场的时空里向大家呈现出一个统一的作品、一个有性情有灵魂的整体。
刺猬乐队的故事之所以能打动我,也是上述原因,他们的融合本质上是一种对人性的挑战,经历了那么多冲突之后,大家依然可以选择在同一个时空里,呈现一个作为整体的乐队,这是特别难能可贵的。
04 .
合成器不过是一种声音的艺术
它不是人的艺术
何必:听了您对刺猬乐队的讨论和对于音乐的理解,让我感觉您对音乐的理解跟我听到的其他人对音乐的讨论不太一样。
我有一专门做合成器的朋友,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要做昂贵且小众的合成器?
他的回答是,流行音乐(包括重金属摇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靠乐手主观操作能达到的视听效果就已经走到尽头了,此时还想取得视听效果层面的突破的话,就只能从听觉效果入手了,合成器就适应了这样一个未来的潮流。
其实大多数人对于摇滚乐的理解,都是首先诉诸于感官刺激的,音乐和绘画技术也只有持续地取得对感官刺激的突破,才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比如去年比较火的野狼disco,舞曲中营造的蒸汽波的感觉就是靠合成器来传达的。
庆延:合成器的出现改变了音乐的呈现方式,其背后的动因是每代人欣赏音乐的方式不一样。
比如我觉得《乐队的夏天第二季》里面,有一支叫“不速之客”的乐队就比较可惜,他们是玩纯金属的,无论装扮还是技术,他们玩的范儿都特正,有一次,他们上来就说我们才是应该继承大统的,乐队“重塑雕像的权利”的华东听了这句话后,还特别逗地反问了一句,“你经过父皇的同意了?”
他们之所以会发生上述对话,是因为对于80后一代的摇滚乐迷来说金属就意味着正统,玩过摇滚的人都有体会,金属乐对人的身体和器乐结合的程度要求特别高。
熟悉《乐队的夏天》的朋友,多半会记得“面孔乐队不插电弹唱《幻觉》”的那个场景,新裤子乐队的彭磊当时就惊叹道“箱琴能弹成这样太了不起了”,也就是说,其实不是每个乐器都可以直接用身体演奏出相应的现场效果的,金属乐能达到的视听效果是有极限的。
以前玩金属乐的人,经常爱搞大段的solo,在现场搞大段solo的用意是展现我作为吉他手的技术,但现在时代变了,当一个乐器的演奏技术达到极限时,人们要再想取得视听效果的进一步突破,就会去主动探索一些更先进的方式,于是合成乐器就应运而生了。
90后、00后可能特别喜欢听合成乐器,但对于我来说,我会觉得合成器有它的好听之处,但他击中不了我,野孩子张佺在采访时说过一句话,这句话直接解释了合成器无法直击我心的原因,他说“合成器不过是一种声音艺术,它不是人的艺术。”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通过合成器,你虽然能感受到技术的结果,但这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技术和人的紧密结合被隐秘掉了。
吉他手、贝斯手、鼓手、主唱一群不一样的人齐聚现场,用不一样的技术演奏同一首曲子,给我们带来感官刺激的同时,还能发出同样有力量且带有灵魂的声音,这种感觉可能是合成器所无法取代的。
何必:师兄欣赏音乐的风格让我觉得,可能感官刺激对你不重要,相比体会音乐的视听效果本身,师兄更热衷于关注音乐背后的人本身,这是什么原因?
05 .
透过窦唯的音乐
了解窦唯这个人活生生的样子
庆延:我对于乐手的喜爱,往往会超过对音乐本身的喜爱,拿窦唯举例,窦唯是我最喜欢的乐手,我个人觉得窦唯实现了中国人最理想的人生境界,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他在不断尝试按照自己的心意、而非每个人希望他成为的那个样子,去度过自己的一生,你看窦唯早期在黑豹乐队时唱的《无地自容》,《don’t break my heart》,这两首传唱至今。
你注意到没有,这种歌是不能翻唱的,谁翻唱谁翻车,因为这类歌太深入人心了,以至于任何一个人翻唱这类歌,我都觉得跟窦唯没法比。
熟悉窦唯的人也都知道,窦唯早期做的是流行摇滚(或者叫流行金属),但窦唯后期的音乐(比如《噢乖》和《高级动物》)就没有那么多受众喜欢了,到今天窦唯的唱法已经发展到没有人声了,没有词的声音他也不唱,直接就上去器乐演奏一番,一首音乐就结束了,这看似很莫名其妙。
这也是我为什么觉得窦唯做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原因,做流行音乐,让大众普遍接受是打开市场的第一步,但问题是,窦唯本人未必觉得音乐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之前的一些网友,曝光过窦唯在面馆里独自吃面的照片,也曝光过一些窦唯上台演出后被观众哄下去的视频,当时窦唯也没理会大家,唱完就走了。
他常说一句话叫最难不过熬清静,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相比活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人最难的是独处,一门心思做自己想做的事儿,窦唯某种程度上其实做到了这一点。窦唯其实是在通过音乐给世界展现出他自己的生命状态。
对于有些人来说,活得成功、光鲜、热闹才是他的自在,但对于窦唯来说,可能活得清净才是他的自在。在这个意义上,我真心觉得每个人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自在尤为重要。
包括窦唯最近出的很多专辑我也都有买,虽然大多数歌我都很难像哼唱《无地自容》一样下意识地哼唱出来了,但是每每听到他的音乐,我都觉得自己仿佛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窦唯一样。
很多时候,击中我心的音乐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愿意通过他们的音乐去了解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体会人的这种活生生的样子。
听音乐、读论文也好、看小说也罢,其实都是在透过内容本身品内容背后的这层人的意味,举个例子,你读王朔和莫言的文字,一定是两个感觉,贯穿王朔字里行间的是他痞痞的样子,这和我们读莫言时候的感觉就很不一样。
06 .
一句话形容五条人的歌: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何必:师兄很在意人的种种活生生的样子,这种活生生的状态,是不也构成了大家喜欢五条人的原因?
庆延:站在观众的角度看,我很难深入到他们的音乐里面去,因为他们的音乐有着很强的地域性,没在歌词中的海丰陆丰所描述的南方城市生活过的人,很难体会到歌词和旋律中的深层滋味。
他们的音乐我不见得会反复听,但是这个乐队的人我非常喜欢,因为我觉得他们特别自然,抛去剧本设计的因素不谈,我真的能感觉到他们在舞台上的样子,就是他们日常唱歌时的本来样子。
我觉得五条人是比较有烟火气的乐队,他能够传递给人日常那些琐碎的东西,用他们的话描述,就是塑料感,我真心觉得塑料感这个词概括得特别精道。
我们都知道塑料不是什么好东西,里面含有致癌物质,还污染环境,但问题是它就遍布和弥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根本就离不开它。
五条人的音乐传递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他们的音乐看似没有特别高的技术含量、也没有特别高的艺术造诣,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的音乐中特别疗愈人心那部分的市井气和烟火气。
我有一句特别鸡汤的话来形容五条人的歌,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07 .
大家都在追求特立独行的时候
也就不存在什么特立独行了
何必:从刺猬到五条人再到前一阵子比较火的野孩子,给我的一个共同的感觉是,他们在节目里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跟社会和解的姿态,我们知道摇滚一直很强调叛逆、特立独行甚至是桀骜不驯……那么问题来了,师兄是后来听摇滚乐的时候,才开始欣赏这种脱离了叛逆感的市井气吗?
庆延:理论上,我觉得叛逆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叛逆永远跟潮流结合在一起,通常情况下,没有潮流就没有叛逆,没有主流就没有支流。
换句话说,当大家都在追求特立独行的时候,也就不存在什么所谓的特立独行了,因为大家又变得都一样了。
这也是现代社会给大家的一个死命题,每个人可选择的不一样本来就不多,人人都还要追求极为有限的不一样,于是追求特立独行反倒成了一种潮流。
这也想我想起了我之前跟朋友的一组对话,我朋友是单身主义者,但也饱受家里催婚的困扰,家里催他结婚的理由就是说,没结婚没生孩子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是有遗憾的。
然后他就问我,怎样才能破解这句话?我说你不放让你妈妈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如果一个人的一生没有任何遗憾,那岂不是最大的遗憾?
姑且把我的这个反问当成一个诡辩吧,我的核心意思就是说如果人人都追求一样的东西(包括叛逆),那叛逆也就不存在其独特的意义了。
编辑:大豹哥 丨 配图: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