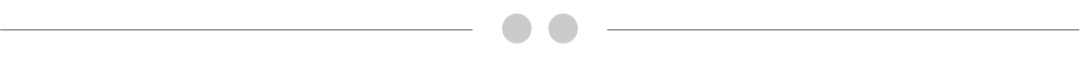《真探》第一季
过去的2024年,社会情绪是躁动的。
数起暴力事件搅动着大众的心神:苏州、深圳、珠海等地都发生过恶性伤人事件。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仿佛照进现实。同时,“NPD”(自恋型人格障碍)、“PUA”、“XX型依恋”等泛心理学词汇频繁出现在流行文化中,成为大众的语言工具包。
恐惧、愤怒、仇恨在不同的社会事件中被滋养,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前不久,我们和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王芳对话,从2024年的恶性事件与大众反应聊起。
悲剧发生后,我们该如何看待暴力,并预防暴力?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该如何疗伤?心理学在大众文化中的崛起,可能带来什么影响?我们如何识别无用的话术,借助心理学形成真正有效的防御和思考?
来源 | 播客《看理想时刻》
1.
善恶从来不是毫无杂质的存在
看理想:今年发生了一些恶性事件后,大众有很强烈的愤怒。有人会认为,去分析嫌犯的背景、犯罪成因,某种程度上是为他“洗地”。因为大部分人无论遭受了多大的委屈,都不会伤害跟自己无冤无仇的人。有一类人就是比较容易犯罪,可能是反社会人格。
王芳:你的后半句我是同意的,就是极端犯罪的人是极少数。但是这个事实不能作为“不要分析杀人成因”的原因。二者没有因果关系,甚至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这些人是极少数,但同时他们造成的伤害又极大,我们反而更要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这些人到底是怎样的人?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在哪个方面或者环节是存在规律的、值得注意的细节,以防范未来可能发生的犯罪?
我特别不同意分析犯罪成因是“洗地”。“洗地”这个词本身就令人不适,这是在恶意揣测动机,而你是没办法自证的。
实际上,很多的努力只是在还原事实、澄清真相,甚至只是在去呈现已知的信息,而这些东西都很重要。比如说在司法上,除了犯罪事实和伤害程度,一个特别重要的量刑标准就是犯罪动机,是加害者的主观意愿,他是筹谋已久的还是临时起意等等。
多数犯罪一定跟这个人是个怎样的人,他的各种前史、成长经历、人生遭遇、所处的生活状态都有关。
在学术研究的层面,像犯罪学、犯罪心理学、遗传学有大量的研究,早就证明了没有什么天生杀人狂,所以去寻找规律是为了防范犯罪,比如为我们的家庭教养、学校教育、社区治理、社会政策、司法干预等等方面提供参考和指导。甚至对于被害人家属,他们也会想知道为什么。
《我们与恶的距离》
恶性事件演变成社会事件,大众是有知情权的,这部分其实是媒体的责任。当然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媒体愿意深入报道了,吃力不讨好。这很悲哀。事情发生了就等通告,然后对前因后果一无所知。
看理想:现在对于嫌犯有标签化的倾向,比如认为他是反社会人格,但如果简单地把恶性事件归结为偶发事件或个人“基因”,普通人会有一种无从防范的感觉。
早年的马加爵杀人案、复旦投毒案,还有详尽的报道分析犯人为何会做出这样的行为。虽然报道发布后可能依旧令人费解,但是否比一无所知更好一些?
王芳:我们面对一些超出自己的认知,第一反应难以理解的事情时,下意识就是恐惧的。我们不愿意想象这些事情有可能发生。
如果罪犯并非纯粹的坏人,而是跟“我”一样的普通人,而他们会在某些因素的复杂助推下走向极致的罪恶,这也就意味着“我”可能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安全的环境里。有一天“我”也会成为被害者,甚至加害者。这种想法是非常令人不安和不适的。
于是我们倾向先确认自己是个好人,永远不会作恶,然后与所谓的“坏人”决绝对立,这样就可以把杀人恶魔和守法公民区分开。
有一位美国哲学家叫詹姆斯·道斯,他写了一本书叫《恶人》。他在书中讨论了一种现象——恶的他者化。
人们会习惯性地把邪恶想象成完全有别于自己的,甚至非同寻常的、很罕见又难以理解的存在,而这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人们可能因此忽略或没办法辨识出那些在频繁制造邪恶的、看似稀松平常的环境性特征。
另外,恶的他者化还可能带来一个反向的作用,就是他者的邪恶化。
我们会害怕他者,把他们视为邪恶,我们就只在他者身上看见我们所害怕的东西,那么到头来,所有被我们认作是他者的东西,所有陌生的事物对我们来说就是邪恶的。
我们刻意去拉远自己和恶的距离,是一种心理上的防御,为了说服自己邪恶是很遥远的存在,所以“我”是安全的。
但如果始终处于这种无意识的、拒绝了解的状态里,那么恶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可理喻,我们就有可能在未来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地、猝不及防地撞上恶的随机发生。
《暴裂无声》
如果我们承认我们与恶的距离没有那么大,甚至是触手可及的,那反而会让我们时刻对潜在的恶保持警惕,进而也有可能预判和防范。
我还在思考,这套防御背后是否还有一个更本质的认知,即我们不太接受人的复杂性。
我们好像特别信仰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恶,希望看到完美无缺的圣人,一无是处的魔鬼。但人就是有很多面,善和恶从来都不是毫无杂质的存在,而是以某种配比共存的混沌体。
如果我们能理解所有人都有灰度,是否就不会那么抗拒去了解恶以及背后的人了。
2.
恶性事件可能预防吗?
看理想:这一类行为可以定性为报复社会吗?有人不同意“无差别杀人”的说法,因为这些恶性事件嫌犯的攻击的对象,往往是没有反抗能力的人群,比如开车撞向行人。这些人是想报复抽象的社会吗?还是想通过犯罪制造存在感,追求更大的社会认知度?
王芳:我们通俗讲“报复社会”,心理学上会讲替代性攻击或替代性复仇。一般而言,如果这些嫌犯有机会给自己的暴行解释,他们会认为自己的行为在道德上是正当且必要的。
从我们的角度出发,会觉得他们在伤害无辜的人,但他们会认为攻击对象是自己所仇恨的外群体的一员,或者是让自己遭遇不公对待的群体中的一份子。哪怕这个连接非常牵强,伤害行为也能被合理化。
换个角度,你会发现那些大规模行凶的犯罪者,他们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长期的酝酿和谋划。他们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也知道这些行为不被法律允许,因此他们会想办法美化自己的恶行。
当暴力行为击中某种社会情绪时,真的会有人为极端暴力拍手叫好,我觉得这是真正需要警惕的部分。
《小丑》
看理想:前面我们讨论了偏个人的原因,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会如何看待这些恶性事件呢?
王芳:之前国外有相关研究,发现有42%的杀手经历过童年创伤,多数是暴力、性虐待或目睹过父母自杀。
有超过80%的人在事件发生前几周或几个月,会达到所谓的危机点。比如他们被停职、被解雇、亲密关系破裂、被社会排斥、陷入经济危机等等。
这些危机会引发他们后续行为的明显变化,比如强烈的焦虑、孤立,然后绝望,他们会感到自己被抛弃、被羞辱,被边缘化了,甚至产生自我厌恶。但是这种自我厌恶最后都外化成别人的错,进而心怀不满,充满愤怒,接着开始策划这种大规模的杀戮,比如购买武器、踩点。
但是我在看资料的时候,也发现一个点。我们国家好像稍稍有一点不同,比如说近期的这几起事件,除了一个行凶者是刚毕业的学生,其他都是50岁上下的中年男子。
曾经有国内的媒体对2004年到2013年公开披露的38起个人极端暴力事件进行过统计。他们发现 30岁到50岁是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比较高发的一个年龄段,大约占到案件总数的73.68%。
一般暴力犯罪的年龄段很年轻,在18岁到25岁这个年龄段。有一些国内的研究总结,这些人的共同点是社会地位较低,社会资源匮乏,上升渠道受阻,社会适应性较差,人际关系不协调,情绪易冲动,并且在近期受过一定的社会挫折。
但是跟年轻人相比,中年人可能更难再通过学习知识技能去改变现状,所以会觉得“反正我这辈子就这样了,那一起完蛋”。
如果综合这些研究结果,你会发现影响因素非常繁杂。
有可能来自先天遗传的高攻击性和冲动性;来自早年生活创伤带来的不适应的人格发展;来自当下劣势的社会处境和经济状况,还有来自因为社会挫败激起的敌意和愤懑,以及通过暴力来展示权力、恢复尊严的这种错误的文化建构。
也正因为因素繁杂,我们不应该把大规模暴力的实施者视为“独狼”一样的个体,好像他们就蜷缩在阴暗的角落里,每天密谋着作恶。不是这样的,而是必须要把这种破坏性的动机置于更大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脚本中去看待和理解。
同时,我们不能因为一件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给一个人定罪。因此这类研究,或是我们去做背后的分析工作,目的不是要去筛查出所谓的“高风险人群”,而是要去找到共性的因素,更广泛地去预防。
那些“高风险人群”,总是在社会上占一定比例的,任何时期、任何时候都有,而且你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更不可能把他们一一找出来。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了一些规律,比如说触发因素包括家庭暴力、校园霸凌、贫富差距、仇恨教育等等,在这些方面整体性地有所改善,就会让那些人不那么容易被引爆。这个是有效预防,可以降低极端犯罪发生的可能性。
《小丑》
看理想:也有很多人在谈及恶性犯罪时,会提到变态、反社会人格、暗黑人格等等心理或精神问题,你认为这和犯罪行为有多大关联?
王芳:首先澄清一下,我们讲暗黑人格,其实还是在一个社会功能正常范围内的。每个人身上都有,只不过有人明显一点,有人弱一点,它都不是一个临床意义上的术语,只是一种人格特征的描述。
至于是否有一些精神疾病会跟暴力有关联,确实有一些,比如反社会人格障碍,或是某些严重的精神疾病,它本身就带有冲动、攻击、难以自控等特征。但是这并不能反过来说那些暴力犯罪的人,多数患有精神疾病。
这种说法事实上已经被证伪了,有研究系统地分析过176个大规模杀手的心理健康史,结果就发现精神疾病因素只关联了其中11%的事件,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行凶者,并没有显著可见或者确证存在的精神疾病。
另一个已经被证实的事实是,大多数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并不暴力,他们甚至更有可能成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而不是肇事者。
每当有类似事件发生的时候,就会听到“凶手是个疯子”、“凶手肯定有精神病”的说法。这是很多人的自动反应,可能是因为这种说法提供了我们对于一件出乎意料、不合逻辑、难以理解的事情,一个看似合理、逻辑简单、好理解的解释。
3.
修建自己的安全系统
看理想:关于无差别杀人事件的成因,AI给出了两个答案。一个是心理危机干预的缺乏,另外一个是社会支持系统的不足。在这两个方面,个人或者社会能够做些什么?
王芳:AI的回答挺切中要害,人们最基本的心理需求就是安全感。向外攻击和向内攻击的人,整体的心理状态都非常不稳定,否则不会自我毁灭或者毁灭他人。
安全感很大程度上是从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来。有个概念叫社会安全系统,由两个世界构成。一个是个人关系世界,包括我们的伴侣、家人、朋友、同事等,他们可以给我们提供情感连接以及重要的社会支持。
另一个就是社会关系世界,包括我们所在的公司、学校、社区,再广泛一点,各种社会机构、社会制度乃至整体的社会经济状况、社会稳定程度等。给我们提供经济来源、社会身份、社会保障、社会秩序,以及道德和价值的依托。
《我们与恶的距离》
这两个世界相互代偿,任何一个系统失灵,人们就会转去另一个获取必要的安全感。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二者都运转良好,但是如果一个人对二者的信任都断裂了,就很可能进入极度的愤世嫉俗的情绪中,进而寻求极端报复和自我毁灭。
也许我们可以建设、巩固和夯实这两个安全系统,只要其中一个值得信任就可以支撑起一个人。比如在家庭里,普及科学养育和情感教育;在学校里,反对校园霸凌,培养情绪调节能力、同理心和心理韧性;在组织层面,倡导人性化的社会和组织文化。
另外在更广大的社会层面,重视基层的社会工作和心理健康工作,在更大意义上减少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在为减少极端犯罪做努力,更本质上,是让人们整体的心理状态变得更好。
说得再小一点,我们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变成他人个人关系世界中的一部分,提供安全感和支持。我看过一个演讲,演讲人艾伦·斯塔克是典型的社会边缘人。
成长过程中,他被包括父母在内的所有人贬低为“一无是处”,他很痛苦,也想过自杀。有一天他的情绪积累到了一个点,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准备做点什么来表达愤怒。他的同学察觉到了不对劲,邀请他来自己家里吃饭。
正是这个微小的善意举动,阻止了一场大规模枪击案的发生。在演讲里, 斯塔克说,当你自己都不觉得自己像人的时候,有人却把你当人对待,这会改变你的整个世界。
人与人之间这种连接的力量让人感动,我们常说,现在社会的戾气越来越大,出门在外要对陌生人好一点,千万不要不小心招惹到了谁,变成了那个出气筒。
这话背后的动机是自保和防御,而斯塔克的故事告诉我们,主动表达善意也许微不足道,但格外有力量。因为你不知道它对于某个人来说,会不会就是那个把Ta重新拉回人间的时刻。
我们确实一时改变不了世界和大环境,但是当有人要滑落恶的悬崖、在最后的一念之差中挣扎的时候,可以去做那个上前拉一把的人。至少,我们可以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互助就是最小的安全系统,我们有时候把系统想得太大了。可能两个人之间微小的善意的释放,就是改变我们所处社会环境的一种方式。
《我们与恶的距离》
4.
心理学渐成显学,让人不安
看理想:这些年心理学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原生家庭、MBTI、PUA、NPD(自恋型人格障碍)等词汇非常流行。记得你说过,自己的心理学节目受欢迎,会有一点不安。
王芳:我上大学的时候,心理系是个很小的系,老师给我们鼓劲说心理学是朝阳产业。它背后的逻辑是随着经济越来越好,人们对于心理学的需求势必越来越大。
这几年心理学好像确实有流行的趋势,我原来以为经济好了,人们就有余力去关心和追求自己的心理健康和精神生活。
但现在看来,恰恰是在追求经济进步的过程中,因为彻底忽视乃至挤压了精神世界,导致人们普遍陷入了一种心灵危机,才来求助于心理学。
所以我有一点不安,很多听众说被我的节目治愈了,可是被治愈的前提就是有创痛,说明大家伤痕累累,让我觉得很心疼。如果心理学的流行只是意味着,社会层面上那些引而不发的伤口以个体痛苦的形式裂开了,我会对这种流行心怀警惕。
一方面,可能会有人单纯地利用这一点来获利。另一方面要小心,心理学的疗愈不要被用来掩蔽我们对于其他更复杂、更深刻的社会性痛苦的来源因素的辨识和改变。
我特别期待心理学可以变成我们关照自己内心世界的工具,去追求更加充实、舒展、美好的生活状态。心理学所倡导的对于个体的关怀、善意和爱,可以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观念和实践,而不只是用来包扎伤口、缓解疼痛。
当然现阶段这个工具也很重要,有总比没有强。
看理想:心理学概念的流行是双刃剑,普通人怎么才能更好地运用心理学来获得帮助,而不是加强贴标签和对立的状况?
王芳:我能理解大家为什么会用这些概念贴标签,因为标签看起来简洁而且精准,可以把之前一些模模糊糊的感受犀利地总结和表达出来。
但是它经常不可考,特别是当我们用一些非常片段的信息下结论,是很有问题的。被贴上标签的人可能很无辜,但是百口莫辩。
扣帽子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事实上,真正的NPD才是扣帽子的高手,Ta完全可以先发制人把帽子扣在你身上,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游戏,谁先成功把帽子扣在对方身上谁就赢。
赢的意思是我拥有了指责、控诉、审判你的道德正当性,就像通过真人秀节目里精心剪辑的碎片做“赛博诊断”,看起来是对某个人的所做所为进行解释,最后却演变成了一场全民审判。
《再见爱人》第四季
这个非常可怕,有“他者化”的意味。用病理性的标签来区隔自我和他者,获得某种幽微的道德优越感乃至快感,这些标签可能会变成合理化自身攻击的工具。
任何的概念和理论,都需要被放到具体的上下文语境里理解,而不是生搬硬套、对号入座。虽然它们有解释性的功能,可以帮我们理解、领悟 、接纳、释然或者改变,但它们不是包学包会的秘籍宝典,更不是真理。
我们需要永远记得,人是具体的,也是复杂的。就算某个理论完美解释了你所经历的一切,也很难告诉你下一个选择应该怎么做。
就算是典型到符合一切NPD症状的NPD,也是一个人,也有无法用这个简单标签来描述的方面。而且即便都是NPD,也可能在很多其他方面千差万别。
所以不要把任何理论和概念奉为圭臬,也不要反过来用任何具体的人证明抽象的理论和概念的正确性。我们可以把它们作为了解自己、反省自身、健康生活的工具,而不是困住自己、攻击他人、释放恶意的工具。
研究者发现,当整个社会复杂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的认知反而可能会走向简化,来保护内心的秩序感。
近些年这样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可能也跟整个社会的流变有关。我们好像在做某种程度的自我保护,代价是丧失了原本应该捍卫的人的复杂性。
当我们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理解所有的一切,最终带来的可能就是人与人的对立、群体跟群体的撕裂。世界没有变得更好,反而分崩离析。
看理想:2024年热门韩综《思想验证区域》,最开始把嘉宾按四个维度进行分类,但观众会慢慢发现,人的复杂性没有办法通过这些维度来判断。看完这个综艺,你的感受如何?
王芳:我觉得这个综艺最精彩的地方,是打破了所有人的预设。导演的目的是观察那些躲在标签后面的人,在遇到具体的个体的时候到底会怎么样。
《思想验证区域》
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这种差异性,人们即便在某些地方看似是一样的,但具体的行为选择和思考逻辑依然不一样。这个综艺呈现了这种差异性,也呈现了这种差异性从何而来。人们在互联网上举着标签互相攻击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看理想: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的英文名是"The World Between Us",我们仍然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共同拥有的也只有这个世界。“愿你的身边有光,愿你就是那道光。”
*本文整理自看理想播客《看理想时刻》第14期,有编辑删减,完整内容可在看理想App或小宇宙等播客平台收听。
采访:dy
微信内容编辑:林蓝、布里
策划:看理想新媒体部
封面图:《小丑2:双重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