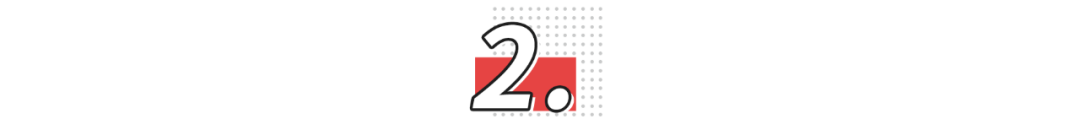编者按
如何看待本次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主题?中美欧关系的互动有什么特点?当下应该如何应对特朗普冲击?当地时间2月16日中午,我们带着以上问题,在慕尼黑对话了香港大学政治学教授及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CCCW)的创始主任李成。
核心提要
1.关于本次慕安会的主题“多极化”,李成认为中美欧各自有不同的理解。美国特朗普政府执行的是单极化方针,欧洲长期秉持的是专制民主非黑即白的两极化世界观,中国是真正践行多极化的国家。在慕安会上王毅外长谈到了过去十几年中国做的尝试,也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2. 关于美欧之间的分歧,李成认为,尽管万斯副总统讲到了欧洲跟美国的价值观的冲突,但实际上他们很多的思路是吻合的。无论是欧洲还是北美,都存在着非常激烈的两派:两个党或者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这并不能简单理解为欧洲与美国的冲突。
3. 关于中欧互动和俄乌和平进程,李成认为欧洲对于中国的角色认知存在悖论:希望中国起积极作用,但又不希望中国取代美国。中国一方面可以积极解释自身立场,另一方面也可以积极发挥自身作用,比如针对欧洲政要呼吁中国参与俄乌和谈。李成认为中国一定会起积极的作用,但并不是领头羊,这是理性的策略。
4. 关于美国是否会撤离欧洲集中精力遏制中国,李成认为当下美国的政界、学界的担忧到了新的高度,所以产生这样的认知。但特朗普意识到中国的强大和与中国合作的必要性,而且他本人更多倾向于解决国内问题,因此特朗普上来以后将有个窗口期。中美关系会受到各种事件影响,所以无法预测这个窗口期能维持多长时间。中方意识到,中美关系很多是结构性问题,但没有放弃从领导人这里把握机会。
对话丨侯逸超
编辑丨侯逸超 庄雯蔚 王诗韵

中美欧对“多极化”认知不同
侯逸超:李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邀请。首先我很好奇您参加本次慕安会的最大的感受。这次慕安会报告主题是“多极化”,但中国、美国和欧洲对此理解可能都不一样,我印象中欧洲似乎也在逐渐的回归基辛格先生所说的“权力政治”,您对这方面有什么感受?
李成:首先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多极化,但实际上各国各地区对多极化的认识是不一样的。你如果问世界的下一个趋势,美国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做单极化,是美国优先,(是保持)美国霸主地位,回到了像19世纪帝国主义的状态,而且是保护主义。尽管他的有些官员也说起过多极化,但是特朗普本人很明显更多(在意)美国自身的利益。
欧洲是主张多极化的。但是大家也注意到了,在拜登政府时期,欧洲跟美国走的很近,而且它看世界还是两极化,也就是所谓的专制跟民主之间的的抗衡对立。从一定程度上讲,他们突出了中美的博弈,但实际上这是错误的。中美的当然是两个大国,当然(世界上)还有其他大国、其他群体。中国领导人实际上从来没有接受过G2的概念,同时也不认为中国是超级大国,认为现在唯一的超级大国是美国。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更符合多极化。
▎2025年2月14日,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克里斯托夫·霍伊斯根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第61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开幕式上致辞。图源:新华社
多极化的原因有很多方面,例如世界如今面临的挑战与传统的挑战并不相同。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核扩散,还有很多问题都需要各个国家的共同努力,所以这次(慕安会)多极化的主题是对的,虽然对此很多认知,尤其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认知是有矛盾的。
我对这方面最大的印象是北约现在出现了很大的矛盾,它内部自身的观念是分裂的。其中非常有意思是万斯的讲到了价值观念的问题,过去这价值观念是所谓的民主和专制,当然现在依旧如此。但这个价值观念把美国放在哪里?把欧洲放在哪里?这就很值得探讨了。
目前(有关价值观念问题)可能还是在试探性的一个阶段。世界未来的趋向很多是跟事件交织在一起的。我们还是要谨慎地判断世界未来趋势,它是有可能改变,但是会往哪个方向改变呢?在未来一段时间,包括俄乌战争的进展、中东的和平、亚太地区稳定,都是非常重要的关注点。所以现在来讨论世界趋势还是为时过早,但是关注多极化的主题是对的,但是很少有人真正的认识到这一点。
以多极化世界观这个概念来观察正在变化当中的世界,我觉得在这方面中国是走的比较好的,而且身体力行。王毅外长并不是在讲中国有很多新的东西,而是更多的说中国在过去几年、十几年当中推出了很多的观点,实际上被现实证明是正确的。
▎王毅外长在慕安会上发表讲话。图源:AP News
西方对华认知的改变需要一个过渡时期
侯逸超:从您参会的体感来看,大家对于中国的方案认可度怎么样?我看到慕安会报告中,对于中国方案的一个评价是pole positioning(起始领先),但是报告里面大多数还是比较负面的评价。
李成:西方现在还没有真正重新检视他们的对华政策,这需要一个过程。目前中国的声音已经得到包括南方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认可,但西方的对华认识需要一个过渡时期。
目前俄乌战争还在进行,他们对中国的立场实际上并不是特别明确。因此王毅外长也解释了中国对俄乌战争的态度,讲到中国比较早就参与了和平的建设,且提到了谈判的重要性。所以,这都需要一个认识转变的过程。西方世界现在更多对万斯副总统抱着极大的反感和恐惧,要重新检验对华认知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我觉得中国身体力行,更多地表达了中国对全球治理所起的积极作用。就像王毅外长所说,这当中认知和观念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尽管万斯副总统讲到了欧洲跟美国价值观的冲突,但实际上欧美很多思路依旧有吻合的地方。
▎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泽连斯基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面。图源:Getty Image
无论是欧洲还是北美,都存在着两个派系非常激烈的冲突,即两个党或者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我们不能简单地讲这概括为“欧洲和美国的冲突”。但很遗憾现在这种非黑即白的概念(更为流行),而非中国所推崇的中庸和价值观的多元化。这实际上是各自文化背景导致的不同,而这个不同需要时间来消化和改变。
欧洲对中国存在认知悖论
侯逸超:俄乌的和平方案也是这次慕安会的一个重点,很多嘉宾对于中国所要扮演的角色非常的好奇。比方说之前的慕安会主席伊辛格先生,他说中国和印度应该参与到这样的安全机制里面,提供安全保证。您是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
李成:欧洲实际上对“中国在当今变化的世界中应该起怎样的作用”一直有个自相矛盾的悖论。一方面,欧洲跟美国站在一起,认为中国可能在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当然要取代美国这种观点本身是错的。而且据我的观察和分析,长期以来我觉得中国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民间,除了极个别,大多数人是并不想改变这个秩序。前天王毅外长的讲话已经非常清楚,但西方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一方面是不希望中国取代美国,但同时又希望中国扮演更多的积极的作用。这本身就是有很多的矛盾的。
中国(对全球治理)提出了很多倡议,但西方并没有跟上。当然有些欧洲国家,例如匈牙利、希腊、部分西方国家的有识之士是有跟进的,但是大多数欧洲国家政府并没有。所以这个悖论还可以延续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目前的情况下面,这种矛盾将如何进一步的发展值得观察。
一方面,我认为中国需要更频繁地解释立场,同时在欧洲发挥更多积极的作用。
俄乌战争其实是个试探点。西方尤其是美国,曾经有这样一个叙事(narrative):俄乌战争前,我美国会告诉你们(欧洲),俄罗斯会攻打乌克兰,你们不相信,(但事实确实发生了)。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中国(大陆)会打台湾,你们信不信?当然乌克兰跟台湾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中国始终在俄乌战争当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已经锁定了中国作为头号敌人(并试图通过俄乌战争的叙事来强化对中国的警惕)。从历史渊源上来讲,正如王毅所说,中国跟乌克兰有很多良好的关系。如果你看中国新闻联播有关俄乌战争(的报道),往往都是一条消息是俄罗斯方面的视角,另一条消息是乌克兰视角,西方人对这方面是不了解的。
在这种情况下,目前中国一定会(在俄乌战争中)起积极的作用,但并不是去起领头羊的作用。这就与西方对中国的很多担忧、恐惧相互呼应,因此都在批评。我觉得(中国目前对待俄乌冲突采取的)这种外交策略,应该说是比较理性的。
侯逸超:关于乌克兰问题和亚太问题,慕安会有意地进行一些联系。比如我昨天参加了一场名为“小世界:欧洲和亚洲的安全链接”的讨论会,日韩外长出席。会上就会讨论特朗普是不是会从欧洲撤出,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亚洲去制衡或压制中国;反过来欧洲嘉宾也说欧洲会去印太采购更多的军备,来加强自己的国防自主,您认为现在这个欧洲的这个安全话题和亚洲的安全话题有多么相关?是不是足以构成地区联动?
李成:这让我想起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也存在着刚才你说的这种不同的解读。
▎2010年,奥巴马总统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图源:维基百科
那时奥巴马曾说过,他是美国的第一位太平洋的总统,同时他采取了一个政策,叫Pivotal to Asia Pacific(重返亚太)。实际上,奥巴马当时的想法并不是要遏制中国,是更多的意识到世界地缘政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亚太地区崛起,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的事实。我不认为他本人就是要遏制中国。中国正在变得强大,也可以起很大的积极作用。但这种叙事最后并没有成为(如今)最主流的(观点),而更多的(演变为)要针对中国、遏制中国,但它本意不是这样。
十几年时间过去了,我觉得(美国)他们本身并不一定是要遏制中国。实际上特朗普也是这样,他意识到中国的强大,跟中国合作的必要性,从他目前的演讲当中确实这样。但同时美国的政界或者学界都对中国的担忧和恐惧又达到了新的一个level(程度)。
你可以说他们的战略重点发生了变化,因为这(国际局势)跟二十多年前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9·11事件”的时候小布什总统突然意识到美国树立的敌人是错的。一开始他认为中国、俄罗斯和伊拉克是(美国)最主要的敌人,但最后(发现)是恐怖分子。他意识到这个错误,于是就在后来改变了他的对华政策。2008年他到中国为奥运会鼓气,这(可以被视为)是很大的一个变化。
▎小布什夫妇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图源:新华社
但问题现在地缘政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的政界、学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人一直有对霸主地位的担忧,对中国的担忧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人们会认为俄乌战争结束、中东和平之后,(美国)会针对中国的,但实际上有时候美国领导人讲这些是为了(美国)国内的听众,或者这是本身就被错误地解读了。这其中有很多复杂因素,它并不是就像我们所说的这么简单,(美国)就是要把重点放到中国去。
那么,美国是不是有能力或者是有意愿去这样做?是很主动地要去做,还是更多地像特朗普的inward looking(内向而不关心外界), 更倾向于把自己国内的情况搞好?这些都是在变化当中的。
地缘政治或者国际关系最难以把握的就是事件。因为事件会改变很多领导人的视野和决策。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避免这种突发事件、怎么更好地沟通、怎么抓住机会,对各个国家来讲都是极其重要的。
中国需要抓住与特朗普交易的窗口期
侯逸超:我觉得特朗普他是一个交易型的总统,他提供了很多窗口,或者提供了很多这种可能性。但是就是从慕安会报告去年的提到双输(lose-lose)到现在的安全化,我的感觉这个大的趋势实际上是不断在收紧的,特朗普个人(在国际社会上)可以做交易的空间有多大,或者说我们怎样去应对这个趋势?
▎2024年慕安会报告将“双输”定为主轴。图源:MSC官网
李成:因为很明显,特朗普是希望跟中国达成交易、达成协议的,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在(特朗普)竞选期间,(他)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中国领导人都有很多赞美的言语,这不一定是假的,而且是一贯而为之的。当然,新冠疫情期间也向我们展示一个特殊情况,他有时候会甩锅中国。
特朗普他不是意识形态很强的人,但他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人,这点也是一个悖论。特朗普当然更多地为了他本人或者美国的利益,他不会为中国(的利益)去做事,这一点要搞清楚。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特朗普总统可能并不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可能我(的评价)对他不太公正,他是个善变的人,我觉得国际事件的变化会让他改变。
特朗普确实是想走孤立主义(道路),更多的是把自己国内事情做好。但是在当今的世界上,国际事务跟国内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在海外有几百个军事基地。当美国突然之间意识到他在某些方面面临了新的威胁的时候,他不会一直往孤立主义走,这种变化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这也是对中国的外交当中一些新的一些挑战。我想中国领导人应该比较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变化。无论如何,特朗普上来以后(中国)有个(能与其交易的)窗口期,虽然我们不知道这窗口期能维持多长时间。
▎特朗普就职后,再度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图源:AP News
即使是在拜登总统执政的最后时期,中国在跟美国打交道的过程中知道美国政治环境并不是那么友好,也意识到中美关系的很多问题是结构性问题,但是中国还是要抓机会。中国是不同意全面脱钩的。尽管中国无论是“双循环”还是“一带一路”,更主要是“双循环”,都是在做为中美全面脱钩做最坏的打算。即使中国不愿意全部脱钩,这种战略和策略也是极其理性的。
侯逸超:您刚才提到特朗普交易的逻辑,这样一个基本逻辑是纯粹为了经济利益,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加征关税也好、政府裁员也好,他其实都是为了谋取更多利益去减缓美债的压力,或者说去应对这种经济挑战。您觉得他这个逻辑是纯经济性的,还是说也包含其他方面的考虑?
李成:我觉得特朗普很明显,他是一个商人,他所有的东西都是交易。但是有两个方面他是不变的,一个就是要增加关税,第二个是保守移民政策。但问题是,在经济政策的过程当中,他要用通过他政治手腕去贯彻执行,要通过美国的实力地位来执行。如果没有美国的实力,他怎么能做到让其他国家来认服?所以这是不能够切割的。
确实,他跟其他总统相比更关注经济议题,这与他的商人背景有关。但这个过程当中,他应该很清楚的认识到这些议题的执行需要其他的资源,因为在政治学的研究当中,我们都知道经济是叫low politics(低级政治),而安全是high politics(高级政治),任何国家都是这样。
中美之间需要更多交流
侯逸超:本次慕安会上很多人都期望中美外交团队能够会面,但是现在没有相关的消息,那么您认为接下来中美会进行什么样的沟通?
李成:(中美领导人)他们已经通过电话了。目前美国最关注的问题还是俄乌战争的进展。中国(对美国虽然)极其重要,但是现在不一定是最主要的议题。而且由于欧洲现在这种激烈的反应,中国也不一定希望高调的来推进中美之间的互动。不过,特朗普说他上任100天左右的时候要访问中国,届时应该会有更多信息的跟进。
▎2017年特朗普访华时,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起参加了欢迎仪式。图源:路透社
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的民间交往(还在继续)。我们跟兰德公司安排了,包括洪博培大使、格雷厄姆·艾利森,还有美国的参议员、新泽西的参议员安迪·金(Andy Kim)都参加了这次圆桌会议。各方都非常理性,我想这些声音也会传达给各国的高层。此时此刻,民间的交往、学界的交往可能会做一些比较好的准备工作。
很遗憾在过去几年当中,由于脱钩断链,由于对对方的很多的(制裁),尤其是对中国的很多的打压,所以(中美交流)这方面实际上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种交流接触来看到双方共同的利益的所在。在目前的情况下面,我觉得这种意识形态急剧的这种支配(dominat慕安会官方的圆桌会议,邀请中美双方的有识之士,像傅莹女士、薛澜、姚洋代表中国e)是不正常的。西方夸大了意识形态的冲突,却没有更多强调了价值观念多元化和互相的包容性,而这方面的中国文化可能会使中国处在比较好的立场上。
侯逸超:谢谢李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