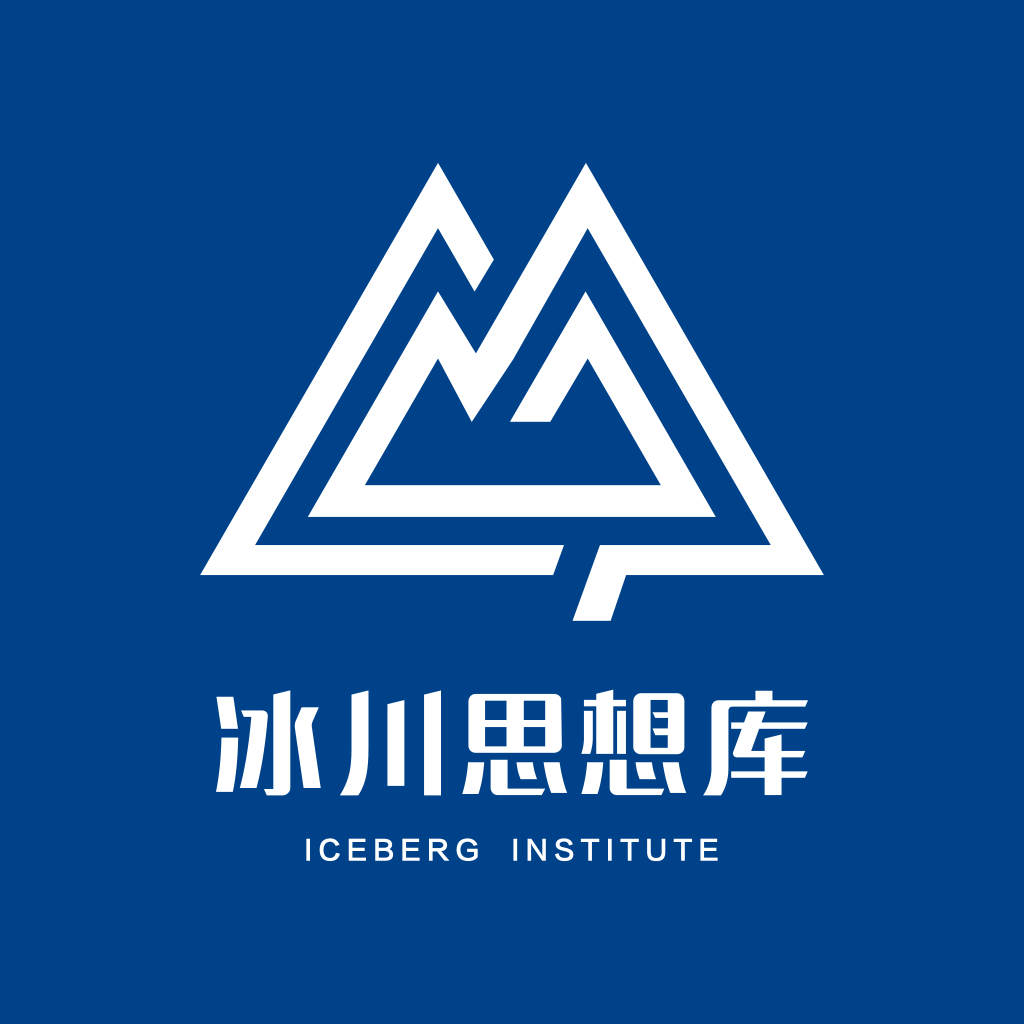企业在推动经济增长和践行社会责任中的力量,很多时候并不在于捐赠多少资金,而在于能否以市场逻辑激活内生动力,让农民从“抱着金饭碗要饭”变为“掌握点石成金的手”。
撰文丨艾川
“这里的农民,是在捧着金饭碗要饭。”
2025年4月13日晚,央视镜头前的钟睒睒站在云南高山的茶园田间,连续几次都忍不住向主持人陈伟鸿发出类似的感叹。
实际上,早在去年8月第一次的访谈中,钟睒睒就已经提前剧透了下一个目标:“这个(茶)产业当中,我认为我们在后端,因为我们依靠了中国的茶的产量,就是种植面积,我们掐了它的尖,但是我们农民的收益率仍然是非常低的。”
仅仅是几个月后,这个目标就有了可见的成果。
不到一年时间里,钟睒睒三次登上央视。看起来每次讲的内容似乎都并不相同,但仔细看这三次访谈会发现其中都有一个共通的关键词——“农业”。
钟睒睒为何如此聚焦农业?到底又是因为什么让钟睒睒下定决心,让农夫山泉的新目标是扎根云南?
01
找方向、垂直型、往上卷
在央视的访谈中,钟睒睒就像是一位普通的茶农,他对茶饼的制作、发酵的温度、水分的控制等制茶过程如数家珍。
不过,他对茶的理解显然不止于技艺本身。
在钟睒睒看来,云南拥有良好的农业资源禀赋,却因为未能够实现足够的产业化,而使得产业的真正价值没有发挥出来。而他为农夫山泉设定的下一个目标,就正在于改造云南的这片想象空间巨大的广袤茶园。
而改造的思路,钟睒睒也已经基本想清楚了:
农业的出路在于工业,我们不向下卷,我们一定是往上卷,我们向下管理质量,向上去卷市场,我们还是要把茶价卖上来的。
在最早的那次央视访谈中,钟睒睒就提及了“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跨越”,而在赣州的对话更是触及了他的“农业梦”以及对农业品牌的理解。
这一次在云南,能够很明显看出,钟睒睒的思考已经不止于当下的商业本身,当他开始谈及产业化的逻辑时可以清晰看到,作为企业家,他正在探触更多关于农业的底层思考——“很多时候农业是一定要根据产业来做,产业不发展,农业是发展不了的,反正农夫(山泉)是准备下决心在这个地方了。”
确实,传统农业中,农户分散经营导致产品品质参差不齐,难以满足现代市场对标准化、安全性的需求,这也意味着茶农在面对市场时的议价权过低。而改变这种现状,出路正在于工业化。工业化通过统一技术标准(如精准施肥、温控仓储)和严格流程管理,确保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可控。
也就是说,工业化能够通过技术、管理和产业链重构,系统性解决传统农业的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市场脱节等问题,同时推动农业向高附加值、可持续方向发展。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钟睒睒的“往上卷”战略会发现,其本质想说的,还是以工业化重塑农业基因,以市场化激活资源价值、重构产业话语权。
▲钟睒睒(图/视频截图)
可以看到,在云南,农夫山泉在提升和扩大茶叶收购的同时还捐赠初制加工厂,以工业化和标准化,改变整个产业的生产观念和方式。通过供应链的逆向整合,突破茶产业的分散化困境,并以溢价收购激发茶农的生产积极性。
这不仅是授人以鱼,更是长期性的“授人以渔”。
因为这样的“往上卷”并不是内卷,而是跳出零和博弈的竞争框架、打开新的增量,其意义远超商业范畴:它证明了中国农业完全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设计,跳出“低价竞争-低质循环”的困境,走向高附加值、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回过头看,在赣南、新疆、广西和云南这些地区,农夫山泉助农和产业改造模式都选择在农业产业链上的垂直深耕。
这其实也符合农夫山泉的战略长期主义。按照钟睒睒不久前公开分享的经营哲学,在“方向选择”上,农夫山泉选择了农业型垂直企业的方向,并在这个领域通过农夫的路径,积累和创造农业知识,提升系统性能力。
02
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
从工业的视角回过头看农业,会发现有待补足的空间是巨大的,这也会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巨大增量所在。
传统农业以出售原料为主,利润空间有限。而工业化能够通过深加工和品牌化,显著提升附加值。最直接的例子就是云南古树茶原料收购价仅几元/斤,但制成标准化茶饮后,售价可翻数十倍。
而且,产业化的好处不仅仅是利润的增加,一旦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就意味着能够进一步增强抗风险能力。工业化整合种植、加工、物流、销售等环节,形成闭环产业链。例如,农夫山泉在云南建厂后,既能稳定收购茶农原料,又通过自有品牌“东方树叶”直接对接消费市场,减少中间环节的利润流失和市场波动风险。
现代农业的竞争已从“产量比拼”转向“价值争夺”,而工业化是连接农业生产与消费市场的核心纽带。当消费需求从“量”转向“质”,从单一转向多元时,工业化赋予农业的不仅是生产方式的变革,更是一种主动适应市场、创造价值的能力。
正如钟睒睒在访谈中所提到的,不可能所有茶叶都能够成为“劳力士”,同样重要的是如何占领“斯沃琪”的市场。单一的“劳力士”钳制生产端的产业格局,必定是不健康的。
图/视频截图
今天的消费者对茶饮的需求早已超越解渴功能,转向健康、便捷与品牌认同,农夫山泉这套以价提质,并引进先进生产线的改造思路,不仅解决了茶叶品质波动的问题,更通过标准化生产将云南茶原料转化为符合当代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这种转变背后,恰恰就是工业化对市场需求精准把控并进而推动农业产业化的结果。
从更大的视野来看,全球化竞争进一步凸显了工业化的重要性。中国农业长期面临“优质原料、低价出口”的尴尬局面,比如日本绿茶凭借工业化生产的稳定性与品牌溢价,国际均价高达中国茶的十倍。
这种差距并非资源禀赋的差异,本质上其实是工业化水平的直接体现。日本茶园通过等高线种植、机械化采摘和全流程温控,确保每一批茶叶品质高度一致,从而支撑起“静冈茶”“宇治茶”等高端品牌;反观中国茶产业,尽管拥有千年历史与多样品类,却因标准化缺失、产业链割裂,难以在国际市场建立统一认知。
▲农夫山泉捐赠茶厂里的现代化制茶设备(图/网络)
农夫山泉在云南推动的工业化改造,正是试图破解这一困局——通过建设现代化茶厂、统一初制工艺,将分散的农户生产纳入标准化体系,将云南茶原料转化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商品。这种模式不仅提升了农民收入,更重新定义了中国茶的价值链:从“原料供应者”转向“品牌主导者”。
03
重新认知农业
说到底,农业工业化的本质是“进化”而非“替代”。工业化不是消灭传统,而是升级其内核将农业从“生存经济”升级为“效率经济”和“价值经济”。
但工业化并非简单复制工厂模式,而是结合地域特色与文化基因,打造“有根的现代化”。日本保留茶道文化,但制茶环节全面机械化;云南古法制茶可转型为高端手工品牌,与工业化量产产品形成差异化互补。
工业化是工具,目的是让农业焕发新生——既留住土地的馈赠,又拥抱现代文明的红利。就像钟睒睒在第一次访谈中说到的:
中国农业为什么有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这是它在全世界国家当中,非常非常稀少的。但真的是需要长期有人,包括我们现在的高等院校,要把论文变成产品,要在中国的大地上扎扎实实到地头去、到田头去、到山里去,这样中国才能真正地把这个地基打扎实。
图/视频截图
过去30年中,钟睒睒无疑是与农民走得最近的企业家之一。
钟睒睒的三次央视访谈之所以聚焦农业,与他的人生经历也有关系。在去年8月的《对话》访谈中,他提到,“对农业我是有情怀的,因为我本身就是个农民。”从他在《浙江日报》时曾专门跑农业线,到他开启第一个创业项目种蘑菇,再到新疆种苹果,到东北种大米,以及花近20年时间在江西赣州种脐橙,钟睒睒的大半辈子几乎都在研究农业问题。
在农民与企业的关系重构上,钟睒睒推行“契约农业”模式,通过长期稳定的收购协议,保障农民收入,打破“靠天吃饭”的困境。例如,在赣南脐橙项目中,他与农户签订高于市场价的收购合同,即使在2013年脐橙黄龙病危机中,仍以高于市场价收购滞销果品,并投入资源帮助农民消灭病害、研发无毒苗种。
对于钟睒睒而言,这些投入是不设限的。在去年12月《对话》节目中,钟睒睒指出,这些产业投入上的账,“是对农民、工人、工厂、社会,这四个方面都有价值的账”。
图/视频截图
现在钟睒睒的新目标是云南的广袤茶园。
面对中国茶叶的产业困境,他开始尝试推动云南茶产业对标国际标准,重塑“中国农产品”的全球形象。
这无疑是需要勇气和决心的,因为这一目标,意味着要重新定义的农业图景,为行业提供了兼具经济价值与社会意义的转型范式,将农业从传统“弱势产业”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现代产业。
不过,对话中钟睒睒也认为,这件事也不是农夫山泉自己能够完成,“我希望跟当地的企业家一起参与进来,重新认识云南的茶产业的天然禀赋与它的可以发展的前景的广阔性。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工厂能给大家带来一个示范的作用。”
从赣南脐橙到云南茶叶,钟睒睒也已经明晰了农夫山泉的发展目标,即“垂直型企业”。在这次节目中,钟睒睒也提到,“我们捐赠这个工厂,希望这个工厂能够起到培训、帮助、提升产业化水平——让农夫山泉有一个根在这里。”
企业在推动经济增长和践行社会责任中的力量,很多时候并不在于捐赠多少资金,而在于能否以市场逻辑激活内生动力,让农民从“抱着金饭碗要饭”变为“掌握点石成金的手”。
对于商业来说,这也是一条共赢之路,正如钟睒睒所言:“唯有跟土地产生链接,这个产业才是稳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