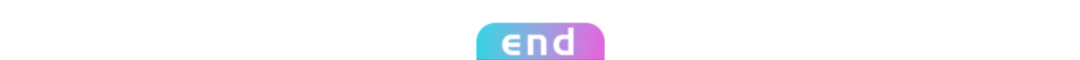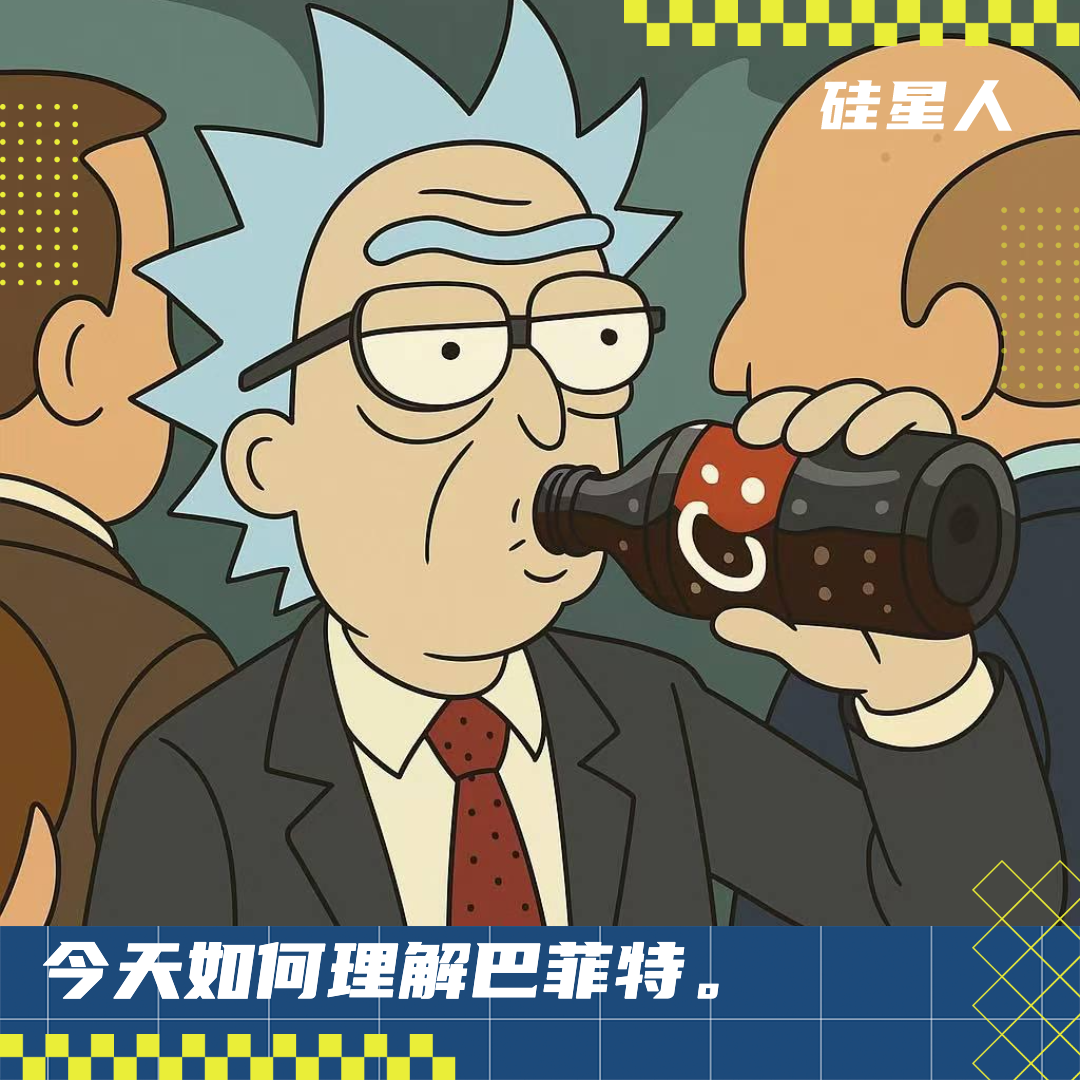
图 / ChatGPT
Prompt / 王兆洋
美国中部时间周六(5月3日),被誉为“投资界春晚”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年度股东大会上,聚光灯一如既往投向了主席台中央那位94岁的传奇人物——沃伦·巴菲特。然而,在这个看似寻常的周六,空气中除了对智慧的惯常渴求,还弥漫着某种告别的预兆与现实的寒意。
会议的高潮并非出现在对某个投资案例的复盘,而是在长达五小时问答环节行将结束之际。
巴菲特以其特有的平静语气,投下了一枚真正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消息:
“我现在想借这个机会,提前和大家谈一件事……现在是格雷格·阿贝尔(Greg Abel)应该在年底正式接任伯克希尔首席执行官的时候了。”周日的董事会上他将正式提议,并“相信董事会会全票支持”。
这位执掌伯克希尔近六十载、将其从濒危纺织厂塑造成商业巨擘的老人,终于明确了交棒时间表。他还以一种极致的信任姿态承诺,自己不会出售任何一股伯克希尔股票,甚至断言,在阿贝尔的领导下,“伯克希尔的前景会比我自己领导时更好”。当然,他也为自己保留了一丝回响:
“将来有可能出现一个可以大量投资的机会。如果那一刻到来,我仍可能会出来出点主意。”
这个宣告并非凭空出现,而是伴随着令人警惕的现实注脚。就在同一天,伯克希尔公布了其2025年第一季度财报:
运营利润同比大幅下滑14%,从去年同期的112.2亿美元降至96.4亿美元,核心的保险承保业务利润更是近乎腰斩(暴跌48.6%)。财报还将美元贬值列为不利因素,并罕见地在风险提示中点名了美国现行关税政策及地缘政治风险带来的显著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公司账上的现金及短期国债储备已飙升至惊人的3477亿美元,再次刷新历史记录,占总资产比例高达27%,远超约13%的历史均值。这笔巨额现金,既是实力的象征,也无疑是对当前投资环境的一种无声的、极度谨慎的判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巴菲特周六当天对具体政策的评论显得尤为突出。当被问及关税问题时,他给出了迄今为止最直接的批评:
“美国不应该‘将贸易当作武器’”。这位通常对具体政治纷争保持微妙距离的“奥马哈先知”,似乎也无法完全忽视贸易壁垒对其遍布铁路、能源、零售等实体经济帝国的潜在侵蚀。
因此,当巴菲特的名字最终将不再与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日常运营紧密相连——通过这场股东大会上精心铺陈的宣告——一个时代如同内布拉斯加平原上空的积云,缓慢而确定地改变了形状。
这位投资家,其漫长得近乎覆盖了战后美国大部分商业史的职业生涯,本身就是一部关于资本主义的、充满复利奇迹却又略显单调乏味的史诗。他的“退休”(即便只是卸任CEO日常职责),标志着一个重要象征的淡出,迫使我们重新审视这位几乎从未犯错的偶像,以及他所代表的一切——尤其是在他选择离场的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
故事的起点,早已是精致打磨到极致光滑的传奇素材:大萧条阴影下出生,痴迷数字与概率的男孩;挨家挨户送报,从自动贩卖机生意中悟出资本积累本能的少年;师从本杰明·格雷厄姆,将“价值投资”奉为圭臬,并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奥马哈,远离华尔街喧嚣的青年。他收购了一家濒临破产的纺织厂——伯克希尔·哈撒韦,作为自己帝国的起点,这本身就充满了某种逆向而行的象征意味。人们津津乐道于他数十年如一日住在1958年购买的老房子里,开着普通的车,早餐可能是麦当劳,以及对樱桃可乐的终身热爱——这些细节被反复提及,勾勒出一个与天文数字财富形成鲜明反差的、近乎苦行僧式的“普通人”形象。他用最朴素的方式,讲述着最复杂的资本故事。
他的伟大,首先镌刻在那张令人敬畏的、穿越数个经济周期的投资成绩单上。当同辈的基金经理们在市场的狂热与恐慌中几经沉浮,巴菲特和伯克希尔却以一种近乎节拍器般的稳定节奏,实现了财富的指数级增长。从美国运通“色拉油丑闻”危机中的果断买入,到对可口可乐品牌护城河的深刻洞察,再到对吉列、富国银行,乃至后来对苹果的重仓——每一次重大出手,都根植于对企业内在价值的冷静评估,而非对市场情绪的追逐。
他的成功并非源于预测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而是识别那些拥有强大竞争优势(他称之为“护城河”)、管理层值得信赖、且价格合理的“好生意”。在信息爆炸、交易频繁成为常态的时代,他坚持“少即是多”,用极低的换手率和极长的持股期,对抗着人性的贪婪与恐惧。与标普500指数的长期对比图,足以让任何试图“战胜市场”的人感到谦卑。他的年度股东大会,在他的老搭档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离世后,更像是信徒们缅怀与聆听的最后阵地,尽管巴菲特本人也即将在日常管理的第一线隐退。
他与芒格这段长达半个多世纪、堪称商业史上最伟大的伙伴关系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如果说巴菲特是那个最终拍板的人,芒格则是那个不断拓宽巴菲特认知边界、提供“多元思维模型”的智识引擎。巴菲特曾坦言,是芒格让他突破了格雷厄姆“捡烟蒂”(买入极其廉价但质地平庸的公司)的局限,转向了“以合理的价格买入伟大的公司”。他们之间的对话,充满了机智、坦诚和深刻洞见,是巴菲特投资哲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芒格的先行离去,让巴菲特如今的交棒更添了几分时代的落寞。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那张耀眼的成绩单和充满智慧的语录上移开,投向更广阔的现实世界,一种评价上的犹疑便开始浮现。巴菲特的智慧,似乎主要且几乎完全地,倾注在了资本的配置与增值上。即便是他此次罕见地直接批评关税政策,其出发点似乎仍是基于对商业环境和利润影响的担忧,而非更广泛的政治伦理或社会公正层面的疾呼。
这与他一贯的风格相符:尽管他承诺捐出绝大部分财富并发起了“The Giving Pledge”(与比尔·盖茨夫妇共同发起),但在推动社会变革、解决气候变化、贫富差距等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方面,他的直接影响力似乎与其财富规模并不完全匹配。与那些利用自身平台和资源直接介入政治辩论、推动科技创新、甚至挑战现有权力结构的企业家或活动家相比,巴菲特显得更为超然和保守。他似乎满足于做一个极其成功的“系统内优化者”,而非“系统变革的推动者”。在一个日益撕裂、危机频发的时代,这种置身事外的姿态,或可被视为一种审慎,但也可能被解读为一种责任的缺席。
更深层次的审视,则触及巴菲特成功模式的本质及其隐喻。他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理性化身:极度自律、耐心、诚实,一生中几乎没有留下重大的道德或商业污点。这种“无趣”的正确性,本身就构成了他魅力的一部分。但他的财富,并非来自亨利·福特式的工厂流水线,也不是史蒂夫·乔布斯式的颠覆性创造,而是主要通过“动脑子”——精准地识别和投资于他人“弄脏双手”建立起来的企业价值。这并非否定其智慧和努力,但这种成功路径,天然带有一种“旁观者”和“裁判者”的意味,而非“建设者”的筚路蓝缕。
它微妙地迎合了一种心理:普通人或许难以成为下一个爱迪生或马斯克,但似乎可以通过学习巴菲特的智慧,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资本的游戏中分一杯羹,从那些实体经济的建设者身上“获利”,而无需亲历建厂、研发、销售的艰辛。
当这种“聪明人的游戏”被巴菲特演绎到极致,并且被证明可以积累起富可敌国的财富时,他那些原本可能因“无趣”而被忽视的、关于耐心和理性的语句,就升华为人人传颂的格言。
他的成功,让“投资”这件事本身,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光环和智力上的优越感。而那高达3477亿美元的现金储备,仿佛是他当前对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最直白的注脚:在一个风险加剧、价值难觅的环境里,即使是“先知”,也选择了手持现金的极致审慎,而非大规模地“弄脏自己的手”去建设什么。
这不禁让人想起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评价爱因斯坦时提出的那个深刻问题:
“伽利略的方法和自然主义,在17世纪思想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牛顿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启蒙运动的整个进程是建立在牛顿原理和方法之上的……达尔文亦如此——他的进化概念影响了生物学之外的很多思想领域。但,爱因斯坦呢?撇开那种人类善良同社会公正和非凡智力相结合所展现的东西……在一个很多人似乎按照全然不同的价值而生活的社会中,爱因斯坦有什么影响呢?”
借用到巴菲特身上,我们可以问:撇开他那无可匹敌的投资成就、个人品格的纯粹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榜样力量,在一个迫切需要行动、创新和承担风险以应对气候变化、社会不公、地缘政治冲突(正如伯克希尔财报中坦承的风险)等严峻挑战的时代,巴菲特的“遗产”是什么?
世界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按照巴菲特所理解的方式运行:周期波动,人性不变,优质资产最终胜出。
他教导我们在周期中保全自身、获取利益,这无疑是宝贵的生存智慧。然而,在今天这个连伯克希尔自身利润都显著下滑、贸易壁垒高筑、地缘政治阴云密布的“糟糕的时代”,我们或许更需要那些敢于“改变世界”的弄潮儿,那些愿意承担巨大风险去解决根本性问题的“建设者”。巴菲特显然不是后者。甚至,当巴菲特式的成功被过度推崇时,那些“弄脏双手”的、充满不确定性的、试图从根本上改变游戏规则的努力,反而可能显得更加不合时宜、更加“愚蠢”。
这并非要否定巴菲特的伟大,他无疑是二十世纪后半叶至今最杰出的资本配置者,一个将理性与耐心发挥到极致的典范。但在一个迫切呼唤变革的时刻,一个只专注于在现有框架内做到极致完美的偶像,其“好”,或许真的“不够”。
他的告别在股东大会的热烈掌声与对格雷格·阿贝尔领导下未来的期许中到来,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财富传奇,也留下了一个关于智慧、财富与时代责任的、在3477亿美元现金映衬下显得更为沉重和迫切的问号。
世界需要更多的巴菲特来保持理性和稳健吗?还是说,世界因为有了太多的“巴菲特信徒”,而缺少了那些真正推动历史车轮对现状的不合理敢于改变的“疯子”和“傻瓜”?这恐怕是这位即将淡出日常管理的奥马哈先知,留给我们的、最复杂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