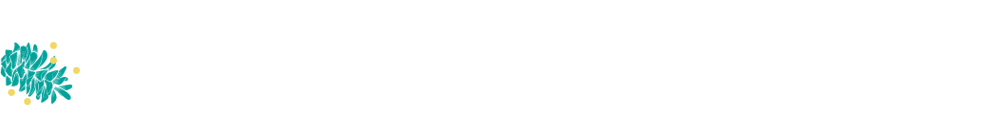文丨高敏
编辑丨雪梨王
这是一起发生在家族内部的性侵害:2022年4月,22岁的宋辰报警,说自己从2007年到2014年,一直遭受宋金宇的猥亵。宋金宇是他的亲叔叔。案子在2024年5月9日一审开庭,6月24日,深圳市宝安区法院判宋金宇犯猥亵儿童罪,刑期4年6个月。宋金宇不服,提出上诉,2025年2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我在深圳见到宋辰时,案子还没开庭。那段时间,他待在家里,日夜颠倒地打游戏,只有不得已要见律师和心理咨询师的时候,才勉强出门——他患有焦虑、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接受过药物和物理治疗,并因此中止了高中学业。他说自己没法过正常的生活,能活到现在,“不过是死命撑着而已”。
这条自救之路漫长且艰难。宋辰第一次把被猥亵的事告诉家人是在2016年3月,他16岁那年,却在2022年4月才报警。心理咨询师、律师、医生、警察、法官都问过他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晚才报警?”而亲戚们问得最多的则是,“为什么不拒绝,还继续去给他搞?”
答案是复杂的。发生家里的性侵害,就像房间里的大象——所有人都看得见,却集体选择沉默。宋辰告诉我,比起叔叔,他更恨自己的父亲宋海江。16岁那年,当他终于鼓起勇气把儿时被猥亵的事讲出来时,父亲的不理解和不作为,让他几近崩溃。他把“想死”挂在嘴边,也“想杀了我爸”。姐姐宋欣告诉我,“弟弟随时都有可能从自己面前消失”——在这个家中,比宋辰大四岁的宋欣是唯一坚定支持他的人。
原本,我试图搞清楚这起发生在少年时期的性侵害会给受害者带来怎样漫长的伤害。接触宋辰一家后,我意识到,他的经历或许折射出一个更普遍的困境:当伤害发生在家里,受害者往往要对抗的不仅是施害者,还有整个系统的沉默与失能。
而它造成的阴影,往往比伤害本身持续得更久。
被忽视的与被厌弃的
宋辰拿到二审判决书,是在今年4月16日。其实更早一些的时候,姐姐就告诉他,二审的事情了结了,但他没怎么在意。他甚至记不清宋金宇被判了几年,“就算他进去了,关我什么事?已经过去这么久了,这个惩罚对我来说有任何意义吗?”当初之所以站上法庭,宋辰说,是想“给那件事一个了结“,让自己“在某种层面上得到解脱”。
提起宋金宇,宋辰总会用“那个人”代称,因为内心深处觉得“恶心”。这些年,他努力让自己切换到第三方视角,“把它当作一件事情而已,可以不在乎”地去讲述出来。
3月初,宋辰搬去了贵阳,和朋友住在一起。他试着过上正常的生活,在晚上好好睡觉,等哪天想工作了就先随便找份工。他告诉我,最近“状态比之前好一些”,并把这归因为“不用再见到我老爹了”——这是他又一次逃离“那个环境”的尝试。
我们上一次见面是在2024年。宋辰身形单薄,一米七的个子,体重不到100斤,眼睛里总透出一股介于质问和愤怒的神色。他说自己上学时基本没交到过朋友,似乎永远无法融入某个群体。过去某次在饭桌上,爷爷用嫌弃的语气说他“很凶”,他才意识到自己面部表情通常很糟糕,“让任何人都不想接近”。
2024年5月9日的庭审现场,他用这双“很凶”的眼睛镇定地瞪着宋金宇——那是他时隔7年后再次见到后者。起诉前,检察官建议宋辰本人出庭,在案发时隔多年、证据较弱的情况下,这样“更有说服力”。
“他连正眼都不敢看我。”宋辰向我描述法庭陈述时的场景,“他哪儿敢看我?”
从出生那年到11岁,宋辰一直住在爷爷家的老房子里。那是位于城中村的一栋6层自建楼,宋辰一家住4楼,长他17岁的叔叔宋金宇跟爷爷奶奶住在2楼。
宋辰从小居住的城中村的入口
对于学龄前的时光,宋辰觉得“挺幸福”,他记得骑在爸爸宋海江肩头的画面。他那时的理想是当“科学家”或“老板”——因为爸爸就是老板,是这个家族中唯一出去创业的人。
但几年后,宋海江变了。他开了几间餐馆,每天半夜回家,说是去应酬,回家后也不讲话。他只关注孩子的成绩,如果宋辰没背好乘法口诀表或课文,就用拖鞋、衣架打他。再后来,宋海江出轨了。这件事让宋辰的母亲黄丽茹变得冷漠而易怒。宋辰打碎一只碗,或者下楼去爷爷家玩,都会引发她“发了疯似的”打骂,甚至罚他下跪。
在学校,宋辰也被当作“异类”,他不懂怎么和人交流,“不敢去接近别人”。
只有二楼的爷爷家让他感到舒适,客厅里的台式电脑,是宋辰彼时唯一的“玩伴”。
姐弟俩告诉我,打从他们记事起,就从未见到宋金宇工作过。他几乎不与外界交往,至今单身。大多时间,都“蹲”在家里打游戏,偶尔会出去打桌球,或者在通宵游戏后的早上出门吃麦当劳。家族里的人觉得他“自闭”,日子久了,也就放任了他这种状态。他的房间里有两张床,只留下一条窄窄的过道。宋金宇睡在较高的床上,下方柜子里装着动漫卡牌。
常年在家的宋金宇,成了最容易接近宋辰的人。
他教宋辰玩游戏;在家庭聚餐时提前带他离开去桌球厅;偶尔会做东西给他吃。宋辰13岁生日时,宋金宇亲自做了蛋糕,还送了他最爱的英雄联盟角色玩偶。宋辰缺失的那部分关注和陪伴,似乎在宋金宇这里得到了部分满足——“这是最可怕的。”若干年后,宋辰说。
根据判决书,2007年到2011年,宋金宇多次趁和宋辰独处的机会,用手伸入后者的衣服、裤子进行抚摸。2011年,宋金宇随父母搬离了老楼。但宋辰去爷爷家玩电脑时,又多次被摸下体。猥亵一直持续到他14岁。
宋辰说,最严重的一次是2008年春节期间,整个过程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少年隐约觉得“事情不对劲”,至于这是什么,为什么不对劲,他不懂。无论家里还是学校,没人教过他。但从心理和生理上,他无法控制自己去想“那件事”。他开始在课堂上走神、打瞌睡,成绩越来越差。眼看应试教育的路可能走不通,宋辰初中毕业后,宋海江决定送他去国际学校,为出国做准备。
与此同时,他们发现了宋辰的异常。他会在学校频繁用手机,在家和父母吵架,原本乖巧听话的孩子,变成了“叛逆的问题少年”。
2016年春天,一次未经允许的手机检查撕裂了这个家庭平静的表象——家人发现了宋辰手机里与同性的暧昧聊天记录。面对突如其来的质问,16岁的少年在慌乱中吐露了更沉重的秘密:他说自己小时候“被叔叔弄过”,并用“少食多餐”隐晦描述了那段经历。
见面时,宋辰告诉我,当时他依然不理解那段经历是对自己的伤害,也并非向家人发出某种控诉或求助信号,他只知道“这个事情不对劲,而且影响了我”。之所以讲出来,更多是为自己的性取向找一个开脱的借口。
终于说出口的秘密
围坐在饭桌前的一家三口愣住了。
“紧接着,大家都哭了,大哭”,宋辰记得,他当时觉得有些奇怪。再后来,从父母的转述中,他得知,父亲找了宋金宇沟通,对方的答复是,“男生之间玩一下,没什么。如果觉得不行或者实在不舒服,可以安排道歉,双方握手言和。”
此后,事情好像不了了之了,宋海江的反应也像是“这事过去了”,没有再提。
黄丽茹的反应更剧烈一些。宋欣记得,母亲去潮汕老家求了个符,烧了泡水让宋辰喝,说是用来“驱邪”。很多年后,黄丽茹告诉我,宋金宇当时的说法让她觉得是在“找借口”,她很生气,“梦到自己拿把刀去插他”,这样的梦来来回回持续了一两个月。
黄丽茹是潮汕人,十一二岁就没了父亲,很早到深圳打工,谈过一次恋爱就结了婚,之后做起了家庭主妇。婚前,她对性一无所知,电影里的人接吻,她不敢看,把脸别过去;十几岁的时候,她还坚信“跟男人坐在一起会有宝宝”,从陆丰坐车去广州,会把旅行包卡在座位外面死死抓住,害怕自己被男人碰到,“碰到就会有宝宝”;生宋欣前,她以为“小孩是从屁股生出来的”——因为小时候,母亲是这么告诉她的。
直到现在,除了自己的丈夫、弟弟和医生,她几乎没和男性有过任何身体上的接触。
也因此,黄丽茹跟儿子的关系并不亲密。儿子小时候,她因为得过传染性疾病,担心传染给儿子,所以即便抱他,也不会用正脸去贴。很多年后她反思,觉得自己“笨得要死,很无知”,“宋辰觉得为什么人家的妈妈会抱抱亲亲,我妈妈却不会。因为我思想就是这样的啊,这让他觉得一点儿亲切感都没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孩子很晚熟,而且受到伤害了我们也不知道,也不懂。”
“我们小时候想亲近妈妈,但她有时候状态很奇怪,不知道怎么和她相处。”宋欣回忆。她分析,可能由于父亲出轨以及夫妻日常沟通中的傲慢与打压,导致母亲长期处于不安和压抑之中,从而无意识地将孩子当作了情绪发泄的对象。
宋辰当然也不明白自己遭遇了什么。
初中以前,他没从学校和家庭中接受过任何性教育,“连大人都羞于启齿,你还指望一个小孩子从哪里得到这些教育呢?”直到初三,有了自我意识,他才隐约觉得“不对劲儿”。但他总记得,宋金宇当时说,“不要告诉别人”。儿时的经历告诉他,必须听话,不听话就会被大人打骂,于是他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
即使在饭桌上讲出来后,宋辰也没有过多考虑自己的状况——他当时的念头是,“不要告诉爷爷”,他担心爷爷身体承受不了;他也在乎别人的看法,怕影响到家族的颜面。
45次心理咨询
不同于父亲的回避和母亲无济于事的“驱邪”,彼时的宋欣陷入了自责。她愧疚于自己的失职,“没有做好姐姐的角色”,以及开始想要为弟弟做些什么。
家族里向来重男轻女,作为长姐,宋欣很早就习惯了父母把关注和资源倾向弟弟,也默认了这种“男孩优先”的家庭秩序。两人小时候虽然睡上下铺,但关系并不亲近。回想起来,宋欣总觉得自己应该更早一些发现弟弟处在“缺乏安全感”的状态中——比如他总担心单车被偷,坚持要上两个锁;出门会随身带一把开了刃的蝴蝶刀防身;有一晚一起睡觉时,弟弟突然来抓她的手,宋欣觉得男孩子这样有点儿“娘”,于是松开了。
得知宋辰的遭遇后,宋海江不是没有变化。他第一次主动参加了儿子学校的家长会,有空也会接送他上下学。但宋欣觉得这些不够,她开始在大学里留意性科普相关讲座,带宋辰一起去听。她还辅修了心理学,学习有关心理创伤相关的知识。看到有关性侵的文章,比如韩国电影《熔炉》的影评,房思琪相关新闻,林肯公园主唱(儿时候曾遭遇过来自成年男性的性侵)自杀的消息,她都会转发给父母,希望他们意识到宋辰的遭遇并不是简单的“玩玩而已”。她试图说服父母,要让宋辰接受专业的心理咨询。
可父母觉得一次 2000块的心理咨询太贵,在宋海江看来,心理咨询就是坐在咨询师面前哭诉抱怨,没什么用。
宋欣花了几个月沟通后,一家人终于在2016年10月在深圳市春风应激干预服务中心尝试了家庭形式的心理咨询。在咨询师的观察下,他们聊开了宋辰的遭遇,那之后,宋辰的状态似乎有些好转,不像之前那般抑郁和易怒了,于是他开始接受长期咨询。父母有时会陪着一起,但这总使得咨询过程变成相互埋怨。场景通常是这样:聊到宋辰的状况后,咨询师请父母发言,宋海江开始讲自己在外打拼都是为了这个家,却得不到家人的理解;黄丽茹会在这时哭起来,说自己也很不容易。咨询焦点因此变得模糊。
最差的情况是,诉苦变成指责,再升级为吵架。之后,父母开车离开,姐弟俩坐地铁回家,几天内彼此不再讲话,冷脸相对。
宋欣跟父亲的对话
2017年之后,宋辰开始频繁离家出走——有时直接坐车去外地见网友,有时半夜走出家门去网吧或者见朋友,彻夜不归,也不回复家人的信息。
父母觉得儿子叛逆、需要被管教,把他从国际高中送去惠州的寄宿学校。在惠州,他的状态变得更差,更经常、直白地提到“想死”。等到2019年,他又转回深圳,父母坚持让他寄宿。那段时间,他上课完全无法集中精力,精神几近崩溃,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确诊为重度抑郁加重度焦虑,以及创伤性应激障碍。医生建议去精神专科医院,之后,他转去了深圳康宁医院,接受了近两年的治疗。
治疗包括药物治疗和物理治疗,医生会将磁极贴片贴到他的太阳穴上,以一种微弱的电流刺激大脑的某一部分,以达到调节情绪的效果。黄丽茹记得,宋辰那几年精神状态很差,吃药时过敏反应也很大,手掌都裂开来。
宋辰在康宁医院看病时,宋海江终于愿意陪他去一趟。他还向医生求助,说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问对方别人的爸爸都是怎么做的。医生说,别人都是先报警,然后带孩子看病,你是我20多年来遇到的第一位这样处理的父亲。
宋海江听后,觉得医生是在挑拨他们父子的关系,自此再也没有陪宋辰去过医院。
从2016年到2021年9月,宋辰一共进行了45次心理咨询。宋辰告诉我,也就是在这一次次讲述和分析中,他逐渐认识到过去的遭遇对自己是一种伤害,以及这种伤害是由他人造成的,不是自己的错。
但伤害远比他认为的更持久和严重——他时而想去死,时而想要杀人,去报复,又时常处于抑郁中,对所有事都丧失了兴趣,觉得前途一片灰暗,一切都没有价值。
“我做的每一件事,需要长时间有反馈的事,到最后总是负反馈,而且经常在中途,我就已经被自己的负面情绪压垮了。”宋辰告诉我,游戏算是例外,属于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反馈的事,“哪怕反馈是负面的,也可以迅速开始下一步。”
想要报警的人
自从知道宋辰的遭遇后,在这个四口之家,“那件事”成了他们口中的特指。父母不会主动谈起,但只要姐弟俩说出这三个字,大家都知道它指的是什么。
事实上,回避、不沟通几乎是这个家庭一直以来的相处模式。宋欣拿弟弟打游戏的事举例,“(父母)不直接说,也不引导不教育,小时候是打骂,现在是直接回避。”这个说法在黄丽茹这里得到了证实。她告诉我,有一次,通常下午起床的宋辰到晚上都没出房间,第二天早上也没开门,她害怕儿子出事,但也不敢敲门,“喊了,他会不爽”。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留意儿子房间里的动静和声响,看他走出房门的时候,松一口气。
这种回避被宋辰解读为“漠不关心”。除了姐姐,他从家人那里得不到任何安慰和支持。 那段时间,宋辰一边在姐姐的督促下接受心理咨询,一边在想死和报复之间横跳。他从未想过向家族公开这件事,或为自己讨回公道。整个家里,只有宋欣想到了报警这个选项。
除了宋欣,没有人赞成报警——宋辰没有心力去做,他觉得没证据,自己没能力证明那曾经的伤害。更何况,这种发生在男性之间的性侵害会被法律认定吗,他不确定。宋海江的态度暧昧且游离,“你们要我怎么办”,他总是这样说。姐弟俩明白,这表明他不支持报警。黄丽茹则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我管不了”——这其实是一种“不知道该怎么办”和回避的状态。她从没想过报警,也不敢想,她能做的就是做好一个家庭主妇应该做的事。
宋欣希望得到母亲的支持
关于报警这件事,黄丽茹向我描述了一个场景:在客厅里,宋欣坚定地提出应该立即报警。话音未落,宋海江拍桌暴怒。站在沙发旁的黄丽茹和宋辰被突如其来的爆发震住。看到父亲激烈的反应,宋辰转身就要往外走,“都是我的错,我消失就行了。”
“如果家庭内部成员不把它当回事,是不是能从法律上寻求一些帮助呢?”宋欣告诉我,之所以坚定地想要报警,是因为宋辰觉得反复吃药复查影响工作状态,停止了去康宁医院的治疗。于是走法律程序成了宋欣唯一的办法,“我一直以来的动力,就是不要让弟弟死掉。”
寄希望于监护人去报警没有希望。2018年11月,宋辰成年了,宋欣打电话给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值班律师咨询。电话里,律师吕孝权告知她,案子可能涉嫌猥亵儿童罪,但证据和追诉时效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手物证已经不存在了,且案发至今从未报过警,已经超过了10年。一般猥亵儿童罪的犯罪追诉时效为10年,只有符合聚众、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等加重处罚情节的,其犯罪追诉期最长可达15年。
追诉时效的问题不难解决——由于受侵害时间持续了7年,犯罪行为的追诉可以从最后一次行为结束算起。最关键的是证据上的缺失。律师提醒宋欣,可以找宋金宇当面沟通,录音取证。即将挂掉电话时,律师询问了宋欣的身份。得知是姐姐后,对方有些震惊,“这事应该你父母出面,不是你去做。孩子被亲叔叔性侵长达几年,作为监护人的父母干吗去了?这是他们的失职。”
2019年清明节家庭聚会后,宋欣亲自找宋金宇对峙取证。
那次对话持续了1小时左右,宋金宇始终不承认自己对宋辰进行过性侵害。他说自己摸过他的生殖器,教过他自慰,为了看是否有包茎而翻过他的包皮,他把这些称为“男生之间的交流”。
宋金宇说,只有性交才算侵犯。
宋欣反驳,“你碰过他的生殖器,他不愿意的话,那也算(性侵)。”
“他没有不愿意啊,你问过他不愿意吗?”宋金宇反问宋欣。
“他还那么小,你怎么知道他愿不愿意?他都不懂啊。”
宋金宇表示,“我也不懂,老师没有教过。”
阻力和支持
拿不到更多有力证据,加上宋辰的消极和父母的不作为,报警的事一直搁置着,直到2021年9月,全家再次一起进行了心理咨询。那一次,咨询师提到,走法律程序是可以帮助宋辰走出创伤的选项。
宋海江当场说没有证据,没办法走程序;黄丽茹则提到了宋欣之前录音取证的事。
咨询结束后第二天,姑姑和爷爷便知道了消息,找上门来。他们的要求很简单:别报警,可以让宋金宇来道歉。
他们劝宋辰算了,因为“阿宇本身有病”;他“很内向”,成天在家里打游戏,不出门也不吃饭,“应该是有忧郁症”;“假如处理得严重要坐牢,就是伤害了他,又伤害了整个家族”,“这件事传出去,我们在村子里问题很大,别人肯定会对我们指指点点。”爷爷和姑姑说出了自己最真实的顾虑,他们还劝宋辰体谅一下宋海江,说他夹在中间,“是最难做的”。
“如果你有抗拒,知道自己不应该继续被搞,为什么一直会去他那里被他搞呢?”——这是最刺痛宋辰的问题。
“你知不知道我小时候是怎样的一个小孩?”宋辰情绪激动起来,“我小时候很听话,直到初三我才有自我意识,才明白这件事。”
爷爷和姑姑见说服未果,悻悻离去。
《熔炉》剧照
彼时,宋辰在宋海江朋友的装修设计公司做学徒。日常帮忙做一点儿设计,更多的是跑腿送文件、跑装修现场,以及跟老板一起应酬饭局。关于报警,他其实也犹豫,这种迟疑主要来自现实考量——担心报警会失去父亲这边的人脉和资源,以及在村里被人议论。宋欣为此求助了深圳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的律师,并劝宋辰跟律师沟通后再做决定。一个月后,宋辰找律师咨询后得知,即使报了警,也可以保护他的隐私。最终,他和律师喻志蕴签了委托协议,决定报警,开始走司法程序。
“可以把这件事情的处理,当成是做一场不可避免的手术。”喻志蕴对他说,但这个手术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后来,喻志蕴告诉我,之所以想要陪宋辰走这么一段,是想陪他经历这个疗愈的过程。她当时跟宋辰说,想让他在过程中感受到,不是所有人都对他的遭遇无动于衷或置之不理,是有人愿意跟他一起走的。施害者也不会如他担心的那样,毫发无损地逍遥法外。
2022年4月18日,宋辰正式报了警,5月18日警方立案。2022年12月23日,宋金宇被刑事拘留,24天后被取保候审。
爷爷和姑姑在2023年底再一次上门来谈判。“想着年轻人受伤了,伤痛可以随着时间慢慢被冲淡。”爷爷说。宋辰立刻否定了,他觉得可能一辈子都放不下,说自己“到现在依然很想死,想自杀”。
爷爷最后亮了底牌,说自己的宗旨是家和万事兴,如果非要打官司,搞得两败俱伤,“就会没有了经济来源,村里所有人看不起我们家族。如果你们官司打赢了,我会把你们爸爸的物业全部都收回来”,“那就没有亲情可言了,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想不想要钱呢?”宋辰不懂这是求和还是威胁,但他还是决定走下去。
“是姐姐代替了父母的责任。”宋辰告诉我,报警一直是宋欣在推着他往前走的,“你不能指望所有受害者都是坚强的或者有信心的。社会对受害者的支持是很微小的,几乎没有,至少我看不见啊。是我姐去学习了很多东西,才走到这一步。其他和我有同样经历的人呢,会有这样的姐姐吗?”
走上法庭,算是宋辰主动为自己迈出的一大步。但彼时他告诉我,自己对结果没抱什么期待,“如果结果不好,好像(日子)也不会过得更差了。就算是一个好结果,他受到了惩罚,又能怎么样呢?他付出的代价有我付出的代价大吗?迟到的正义还能叫正义吗?”
开庭时,宋金宇的律师为他做了无罪辩护,他自己也一直否认犯罪。喻志蕴告诉我,由于报案时间太晚,这个案子无论是证据还是追溯时效上,都有些“先天体弱”,但宋欣提供的录音是很关键的证据。宋金宇自称“只是触碰了下体”,虽然他主观上认为这不属于性侵,但客观上证实了其确实对受害人实施了猥亵。
宋辰本人的出庭也增加了可信度。虽然他的自述属于间接证据,但结合其他证人的证言,以及过去几年的心理咨询和就诊记录,法院一审认为他的陈述“真实性高,具有明显亲历性”,“足以认定被告对被害人实施了猥亵事实”,适用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第三款和第八十七条,判其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唯一的正反馈
那么当施害者被判刑,案子看上去有了不错的结局,受害的一方能就此走出来吗?
“走出来”似乎是大家的普遍期待,陪宋辰一路走来的宋欣、律师喻志蕴和心理咨询督导师隋双戈博士都跟我提到过这个词。但宋辰自己也不确定。
实际上,对宋辰来说,相比宋金宇,父亲的不作为给他造成的伤害更大,也更深远。“我想杀了他”,宋辰不止一次说过,他原本不高兴的脸变得更愤怒了。
其实在事情最早被捅破的两三年,宋辰对宋海江是抱有期待的。如果他能“尽一个父亲的责任”,比如报警或者提供经济层面的帮助,那大家可以继续“好好做父子”。但宋海江非但没有,他甚至在子女报警前,去为宋金宇找律师——他内心的天平,似乎还是倾向了亲弟弟这方。
“他不知道,他自己才是一直刺激我的人。”宋辰说。
说过无数次想杀掉父亲后,2024年2月23日,宋辰真的行动了。当晚,他打电话给宋海江,说要去餐馆楼上的办公室找他。宋海江以为儿子要来谈判,其实宋辰“就是打算去弄他,办公室里什么工具都有”。他先是骂宋海江:“你还是个人吗?你儿子变成这样,你却什么都不做!”宋海江不以为然,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宋辰冲上去动手,但他太瘦弱了,很快就被父亲死死摁住。最终宋海江离开了办公室,留下宋辰将能砸的杯子、电器砸了一地。
2024年10月,宋辰在电话里告诉我,他觉得什么都没变。彼时,该案一审已宣判。
“我已经输了,说难听点,等于‘净身出户’了。本来我可以成为一个正常(好好读书考大学)的孩子,现在我没有前途,没有学历,被耽误了10多年,它(法律结果)能让我的生活带来什么美好转变吗?家里人都把它当所谓的家事。一个小孩被人猥亵了,大家会质疑为什么你当时不说,可问题不是出在施害者身上吗?整体环境不会因为一个个体承受了巨大的伤害,而发生改变的。”
他现在停止了心理咨询,认为那只能起到暂时稳定情绪的作用,“这件事情对我造成的伤害,判他4年半是根本弥补不了的。我没有心力了,我现在仅存的力量只能支撑我这样苟活下去,如果再让我去触碰什么可能性,我怕我的心死了,人就真的死了。”
《神秘肌肤》剧照
隋双戈接触过不少类似个案,他把这种难以走出来的状态称作“卡住”或“僵住”——坏人得到了惩罚,并不等于创伤就没有了,因为创伤带来的影响实实在在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他可能还会像之前一样,处于无助、抑郁的状态。
他打了个比方,就像受惊状态下的青虫,会僵着不动。因为它不能逃跑,也没有办法战斗,“僵住”是保全自己最本能的方式。只有周遭环境安全了,它才能慢慢舒展身体,一点点恢复。如果没有安全的环境,它很可能一直卡在那个状态,有的人一辈子都是这样。
“案子了结,宋金宇被判刑,算得上有正反馈的事吗?”4月下旬,我在电话里问宋辰。他已经“逃”到了贵阳,试着让自己好起来。
“有,但不是现在。”宋辰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他说比起法律给他一个公正的裁决,他更希望这样的事能被关注,被看到——这是我当时用来说服他接受采访的话,但现在他认同了这种说法。“如果能引起社会对儿童保护的重视,特别是让更多人意识到,男孩子同样可能遭遇这种伤害,或许就能减少像我这样的受害者。这大概是整件事唯一带来的正反馈了。”
在贵阳的这段时间,宋辰和父亲再没说过话,偶尔给母亲发下消息,但每天都会在QQ上和宋欣聊几句。一般都是宋欣主动,问他吃了什么,过得怎么样,或者发点梗图和表情包,“总之他有回复,我就确认应该没太大问题”。她在日记本里,清楚记录着这些年和弟弟相处的点滴,其中一段是:“2023年11月21日,弟弟说有件事情不太好意思说,我以为是性相关或者是钱的话题,没想到他是希望抱抱。我便给了一个被他说有些重的抱抱。”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宋辰、宋欣、宋金宇、宋海江、黄丽茹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