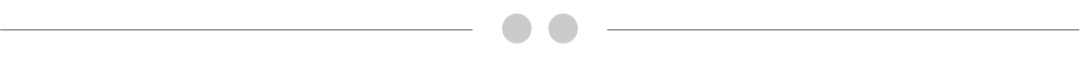《歌手2019》
前段时间,苏打绿在巡演中度过了自己的21岁生日。这是他们拿回姓名的第三年,与粗砺的世界交手的阵痛冷却下来,肉眼可见的改变却在随时发生。
主唱吴青峰前年频频失声,为了不让观众失望,努力调整声音的状态。他曾经在一场演出中,为没能完美演唱道歉:
“失声对歌手来说是一件非常折磨的事情,但是今天有这么多喜欢音乐的人聚在一起,我想,不管是你们还是我,接下来多多少少都会有很多很挣扎、很无奈的时刻,但我希望不管在什么时刻我们都能有在生命中值得歌颂的东西。”
今天我们想聊聊吴青峰,在这篇文章之前,我们已经在音乐中和他轻轻碰过了肩膀。我们是歌颂者与聆听者,一种世界上很美丽的关系。
01.
漂浮
对吴青峰进行定位是毫无必要的事情。音乐圈素有“独立”与“流行”的分庭抗礼,而吴青峰更乐于做一个逃逸者,逃逸于所有限定词的牵引,在空气中漂浮,自由自在。
他从小就身处边缘地带,也早早地放弃了对归属的执迷。小时候被老师选入合唱团,他的声音和其他人格格不入,只能演唱独唱的段落。他发现跟别人不一样也没关系,还是有自己的位置,有可以做的事情。
他在苏打绿时期就已经频繁跨界,拿“韦瓦第计划”的四季主题专辑来说,从《春·日光》到《冬 未了》,分别融合了清新民谣、英伦摇滚、古典诗歌和管弦交响。
个人专辑《马拉美的星期二》更是各类音乐人的沙龙盛会,巴萨诺瓦乐界的小野丽莎、津轻三味线演奏家蜷川红、法国圣马可童声合唱团……与他冲撞出和谐悦耳的乐音。
他的作曲方式与众不同,不靠乐器,而是哼唱,有时候干脆从猫无意间在钢琴上踩过的几个音符开始。他并不熟练掌握任何一门乐器,却也由此摆脱了乐器和弦的局限。乐评人王硕说,他能用一种接近什么都不会的方式,创作出很多什么都会的音乐人写不出来的音乐。
他也作词,很多是那种叠满了嵌字、藏头、典故的文字游戏,无论是文字密度还是晦涩程度,都和经文有得一拼。在第33届金曲奖颁奖典礼上,他的《小情歌》收获了歌手余佩真的感谢与调侃:
“我高中重考的时候非常喜欢你,太喜欢你的词了,可是我又不知道你在写什么,所以我就去问老师到底什么是‘度秒如年难捱的离骚’?”
有趣的是,他作词的另一首《迟到千年》,真的被选入台湾国中二年级的国文教科书。甚至还有好几篇硕士论文因他诞生,诸如《华语流行歌曲融入华语文教学——以苏打绿四首歌为例》和《吴青峰歌词修辞现象学研究》。
他对此的回应是“江湖郎中装神弄鬼”,往往还会附带一个受之有愧的表情。罪魁祸首或许是字典,小时候他没有耐心看课外书,就去翻字典研究字形与字义,也奠定了他后来对现代诗的喜爱。
《联合文学》杂志尝试将他的词作纳入某种诗歌的范畴,被他全然拒绝。“我觉得自己根本是在圈外,收不到讯号的地方。我没有资格加入任何光谱,可是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自成光谱,你们都会在我的怀抱之中。”
《太空人》MV
02.
薄膜
参与见证华语音乐几度转型的陈珊妮曾说,“努力迎合时代与潮流的人很多,最难的是像自己。”自成一派的吴青峰,从不认为忠于自我是了不起的事情。音乐于他,根本是一种自我疗愈的本能。
成年之前,他会在家人争吵或者不想见生人的时候躲起来,把音乐开到最大声。音乐像一层薄膜包裹着他,然后四周开始上色,变成不一样的风景。他也会趁家里无人,照着二姐弹奏的钢琴旋律有样学样,或者假装为郑板桥的词作钢伴,完全享受其中。
18岁他高三,在比赛的截稿日期前挤出了一首词曲创作,从此找到了灵魂的出口。他不习惯向别人诉说心事,觉得太刻意,写歌就顺畅许多。从旋律和想象开始,在不需要多大的房间里乱弹,心里的画面得以被描摹。他也重新被薄膜包裹,感到安全。
正因如此,他的音乐总是给人一种强烈的画面感,而旋律和文字在背景中携手共舞。就像他为苏打绿创作的第一首歌的歌名,那是“空气中的视听与幻觉”。
好友安溥说他的创作力像李白,既是直觉式的,更是爆发式的。灵感常常在睡着之前到来,他要起起睡睡三四次,才能落个清净,否则就会被梦追着跑,有时候是朋友给他放歌听,有时候是直接对他说话,有时候又是一团灰色的烟雾。他说自己这辈子都没有过睡饱觉的感觉。
也有时候,同一首歌的词曲创作延宕出不短的时差。专辑《马拉美的星期二》的全部作曲早于作词两年,两年前的曲子底色明亮,可需要作词的当下他的心境却是灰暗的。他担心辜负这些歌,在梦中一拖再拖,直到再也无法拖下去。写完之后,他再也没有做过类似的梦,立刻松弛下来。
他大多数快乐的歌,都写于不开心的时候。好比早期的《飞鱼》,是他在饱受忧郁症困扰的时候,被朋友拖出去看海的灵光一现。他生性敏感而容易受伤,但音乐创作赋予他强大的复原能力。
“写完的当下,我就觉得已经跟世界沟通完毕了,就算我诉诸的对象不必定能听到这首歌,我也不用等待任何回应,就已经跟自己达成一个协议。”
《译梦机》MV
03.
蝉鸣
吴青峰说自己像蝉,大鸣大放的生物。
这不只关乎他蓬勃的创作力,也关乎一种天然的正义感。《掌声落下》是对隐藏在电脑屏幕后的“键盘侠”的抨击,《巴别塔庆典》是对无共识的现代人自说自话的嘲讽,《他举起右手点名》是对极权主义引诱普通人作恶的愤慨。
边缘者的身份,让他敏锐地察觉弱势及少数群体的处境。在《沙文》中控诉性别暴力,在《彼得与狼》中为“玫瑰少年”叶永志应援,在《墙外的风景》中呼唤婚姻平权。
他常常在音乐中触碰社会议题,初心却不是为了议题而议题。实际上他比谁都害怕“议题”二字会导向非黑即白的表态,进而在群体内部制造分裂。“光只讨论议题,而忽略中间有血有肉的部分,直接跳过迷雾,是很可惜的。”
他不期待受到“勇于表达社会议题”的赞许,从始至终,他只是单纯地捍卫自己想要的世界。所以在涉及自身时,他捍卫的动作也不会变形。
表达者难逃被误解的宿命,他的《小情歌》就曾被误认为迎合市场需求的作品。他因此较上了劲,有一年的时间不唱《小情歌》。等情绪过去,他幡然醒悟这同样在欺负自己的作品,仿佛它做了错事才见不得人。
多年后他在《……海妖沙龙》中把自己比作一艘摇摇摆摆的破船,无可避免受到周围噪音的影响,依然忠于自我。他不改少年心气地写:“谁的叽叽喳喳甩也不甩,怎么样,咬我啊,我才不在乎”。
吴青峰难得的一点是自我而不自溺,他的音乐即便基底是酸涩、愤怒、灰暗的,总有一抹亮色点缀,那是他也许与生俱来的幽默感。
每当经历不好的事情,他会将自己抽离出来,想象用未来的眼光回溯,就能把经历变成笑话。从前他被爸爸拿苍蝇拍抽打,在皮肤上烙下格纹。每次被同学问起,他都开玩笑说是烤肉被烫到。有一天同学忍不住告诉他:“你们家好爽,怎么一天到晚在烤肉。”
他迄今最灰暗的经历,是与前经纪人林暐哲近三年的著作权纠纷。曾经最信任的伯乐扯下面具,露出人性的狰狞面目。《……催眠大师》算是他对这段经历的反刍,歌词中的“伯乐已殁”和“把我还我”字字泣血,却也不乏黑色幽默的段落。
他坦承,在创作完成的当下就已经开始放下。直到现在,他不介意把它当作警世寓言来演唱。
《巴别塔庆典》MV
04.
废墟
蝉在大鸣大放之前生活在土壤里,就像人无法一直与世界沟通,应该允许失语。吴青峰曾经在房间的灯上布置树枝型的装饰,“关了灯,我觉得自己就像土里的蝉一样,在自己的世界和外面的世界之间纠结”。
如果吴青峰只是孑然一身,或许有可能不知疲倦地和世界大战三百回合,可他早已经习惯了肩负他人的命运。他动过一次退圈的念头,起因是媒体侵扰到了他在乎的亲友。如果他热爱的唱歌让他身边的人受伤害,他将无法自私地唱下去。
那段时间他去看了齐豫的演唱会,在听完《橄榄树》后痛哭流涕。齐豫说,在成为别人的橄榄树之前,还是得先成为自己的橄榄树。
第一张个人专辑《太空人》制作期间,他刚开始与林暐哲打官司,妈妈陪他出庭时情绪激动,他觉得自己有点不孝,又哭了一场。《太空人》整张专辑的概念,是一个瘫痪在床的病人的脑内活动,也是当时吴青峰的内心写照。他正处在无法信任世界的阶段,周身散发着低气压。
他的朋友们用迂回的方式默默关心他,比如在他难得提出专辑制作的想法时,拼命帮他达成。对他来说,这些伸出的援手像黑暗中的光亮。而他得以在光亮出现的瞬间,一点点捡拾自身的碎片。
“在经历的当下,没有人能替我们分担痛苦。但很多人意外的一句话,或许会让我们放在心中很久很久,成为我们的浮木,不知不觉就救了我们。”
“在感谢这些人之外,我觉得我一向是少了一点体悟,就是我应该回头感谢我自己。除了很爱写很热情,我觉得我其实真的算蛮努力的。”
吴青峰形容《太空人》是一座废墟,一如涅槃重生的他自己。他饱尝了暌违已久的泥土的滋味,又把不好的事情化为泥土的养分。在这样的意义上,废墟并不沧桑,反倒是生命力最旺盛的空间,能够自由地融入每一个需要被拥抱的存在。
这其中当然也包括自己。在随后疫情严重无法出门的日子里,他有好好与自己相处。坐在书桌前一动不动地进行脑部活动,远远的,猫在注视着他,舒适而又自在。
他喜欢的美国歌手多莉·艾莫丝有句歌词,“I would cry 1000 more oceans if thats what it takes to sail you home”。回头追索,他惊诧地想起《太空人》专辑的最后一句正好是“谢谢你等我,我回家了”。
“你”和“我”都是他自己,他用眼泪牵引自己回家。
《一点点》MV
尾声.
37岁是吴青峰真正的成年礼。这一年他发布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第一次脱离乐团的羽翼重新出发,第一次发现自己最适合的身份是歌颂者。
他的音乐与歌声,有一股巨大的温柔的力量。他遭受过世界的恶意,所以懂得痛苦的感觉。但当他理解了恶意同样来源于痛苦,就选择用温柔来作反射。
他点进过骂他“娘”的人的微博,发现大部分的他们比他懦弱。“如果他们有一天接受到像他们骂我一样的谩骂的话,绝对会比我易碎。”
他的创作是他疗愈自己的方式,让他受尽挫折却毫发无伤。而对他的创作产生共鸣的人,是额外的礼物。他不介意这些共鸣是美丽的错误,歌颂者与聆听者隔着灵魂的薄膜互相对话,没有谁比谁知道更多关于世界的真相。
第二次成年之后,他对身为歌颂者的自己也变得温柔,允许声音偶尔的旁逸斜出。曾经他为了配得上别人的夸奖,逼自己每首歌从头唱到尾零失误。如今他要接受声带的退化,用过去好几倍的力气,来维持及格的状态。
也许做不了常青树,但观众教会了他现场的意义——不管声音是否完美,每一次共度的时光都独一无二。最重要的是他喜欢唱歌,喜欢的事情要开心做,因为“笑着流泪是比真心难过幸福很多的事情”。
资料来源:
《联合文学》、Vogue Taiwan、天下杂志、耳朵借我、点灯 人生好风景、美丽佳人、今晚9点见、人物、爱思不Si
撰文:布里
策划:看理想新媒体部
封面图:《马拉美的沙龙》live@衛武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