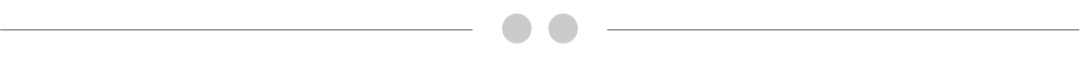《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2025年7月8日,大连工业大学发布公告,以“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有损国格、校誉”为由,开除一名女生的学籍。
多名法学界人士指出,公告本身存在侵犯隐私权、法律适用错误等问题,高校无权因学生与外国人发生性关系而开除其学籍。饶是如此,仍有大量声音支持大连工业大学的决定。
为什么女生的性行为会被定义为“有损国格”?支持开除该女生的男性,有着怎样的价值观,如何看待女性身体?
今天,性别研究者Alexwood将剖析当性别和国族身份、民族主义交叉时,女性身体如何被符号化,“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定义了父权社会”。
讲述|Alexwood,《别任性》主播、性别研究者
来源|看理想音频节目《性别不麻烦》
01.
女性身体作为民族国家的代言
战争往往会突出女性身体作为民族国家代言的角色。战争中的女性身体是保家卫国的武装力量,也是侵略势力的性暴力凌辱对象。
在中国妇女解放事业的发展进程中,上世纪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占有重要位置。民间自发的妇女解放运动进行的同时,官方也从上至下地推进“禁缠足,兴女学”等一系列纲领。
早在晚清时期,慈禧就颁布了劝戒缠足的懿旨上谕,并从北京开启女学兴办之风,到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将反缠足运动推向法制化,颁布《禁止妇女缠足条例草案》,规定条例颁布之后的六个月内,需要对缠足女性完成放足,30岁以下妇女在六个月后仍未放足则要缴纳罚金。
这一系列举措是推进妇女解放的正向力量,但是对于缠足妇女产生的强制规范性,也导致了一些负面后果,比如一些妇女因为传统文化的影响,觉得放足是一种屈辱,甚至有人因此自杀。另外一个重要批评是:解放妇女并不是这系列动作的目标,而是附带产物。
在国家主权受到外强威胁的危机时刻,“强国保种”会变成优先任务,而19世纪末的维新知识分子,比如梁启超,开始意识到“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因为“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
为了“强国保种”,要先对中国女子进行身体和头脑上的“改良”,于是去缠足和促女学被纳入当时社会维新图强的议程。女性身体其实是被赋予“母亲”的符号和优生优育的功能才得到解放的。
根据历史学家夏晓虹的研究,妇女解放在宏大议程上还有别的价值,那就是让女性为男性,尤其是精英男性减负,共同承担富国强民的责任。所以,救国才是提倡女学的最高宗旨,男女平等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很多男性知识精英看来,男女平等的确是一个目的,因为这是思想进步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指标。
1902年马君武翻译的《斯宾塞女权篇》提到:“欲知一国人民之文明程度如何,必以其国待遇女人之情形如何为断”。对于许多马武君这样的进步人士而言,女权被赋予了超出女权的更大意义。
《黄金时代》
其他国家的情况也与此呼应,上野千鹤子在《为了活下去的思想》中写到,在二战中,日本女性的参战不是通过“女性也承担兵役”这种平权话语实现的,而是通过成为“军国的母亲”、“军神的母亲”这种让女性足以比肩烈士的自我牺牲话语。战后,母性成为和平的象征;但在战争中,母性则是“被动员、被当作执行战争任务的象征符号”。
除了母亲这个身份,民国时期女性还有一个与国家振兴紧密相关的身份:新时代伴侣。相对于作为母亲的种族延续功能,伴侣这个角色需要提供的价值更复杂,但同样是被安排,被赋予的。
上世纪20年代起,随着高校兼收女生,女青年学生群体出现。她们从诞生以来就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凝视的对象,曾经有女学的毕业礼吸引了五百多人围观。女学生形象还出现在戏剧里,扮演追求自由爱情但遇人不淑的爱情悲剧主角,也出现广告里,代言各类女性商品。
在当时,女学生作为一种新品种的女人被观看、被消费、被想象,她的性价值不同于传统原始的性价值,而是与国家进步、思想解放等等宏大叙事挂钩。因为,她有思想,有知识,追求“自由恋爱”,她能够实现“封建女性”不能满足的“新青年”男性们的需要。
但似乎没有人关心,那些被新时代抛弃的旧女性,被新青年抛弃的旧妻子,过着什么样的人生。
在《五四婚姻》里,作者孔慧怡描绘了几组看似站在新文化运动两端的女性的生涯,她们分别是鲁迅的妻子朱安、同居妻子许广平,胡适的妻子江冬秀、恋人曹珮生,徐志摩的第一任妻子张幼仪、第二任妻子陆小曼,以及林徽因。
这几位男性都在原有的婚姻外,被五四“新女性”吸引,结成新的伴侣关系。他们以妻子的小脚为耻,因为那是家国落后的历史标记,他们又替女性规定了,中国女子需独立自由,就像胡适到美国留学后见到的女人一样。
但是在他们和“新女性”的关系中,除去所谓的“自由恋爱”,“男女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从观念和符号转化为实践。无论是小脚的“旧女性”身体,还是女学生的“新女性”身体,都从未摆脱代言民族国家时代形象的符号化。不再能迎合民族情感和时代标准的女性身体,无论是在宏观的历史叙事中,还是微观的亲密关系中,都被理所当然地淘汰。
以上批评不是在否定那个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正面影响,而是想指出覆盖在女性身体上的国家话语。当时很多男性知识精英的确在积极和真诚争取男女平等,也相信男女同权是自然真理,但是在这种男性主导的“女性解放”运动中,“妇女”是一个社会改革议程中有待解决的问题,女性本身不是主体,也没有主动性。
“自由独立”成为一种对新女性的规范性要求,因为这是国家和时代的需要。女性被要求独立自强,但何为独立,如何自强,却仍然被男性和国家话语塑造,就如同在此之前的女性被要求依附顺从无才一样。女性“美德”从来不由女性自己设置。
当性别和国族身份以及民族主义发生交叉,女性的身体被符号化,至于是什么样的符号,则取决于当时的意识形态和宣传目标。对侵略者来说,女性身体一样是符号,代表着被占领、控制、裁制的对象。所以女性在战争中往往面临强奸等性别化的暴力,对于占领者就像奖品被认领和瓜分。
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在《战争:人性、社会与被塑造的历史》中记录,仅在1945年,德国就有上万妇女在短时间内被苏联士兵强奸,斯大林为他们辩护:“一个人从斯大林格勒战斗到贝尔格莱德……土地上越过1000千米,跨越他的战友和最爱的人的尸体……经历了那么恐怖的事情后,和一个女人开开玩笑又有什么可怕的?”
战争中,“胜利和失败通常是用性别化的方式来表达的”,对失败一方的强奸和阉割,都是羞辱敌方民族意志的暴力行为。而战争结束后,平民女性也更可能以“通敌者”的罪名被剃发、游街,承受性别化的暴力,成为集体情绪的发泄对象。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马莱娜在战后被民众侮辱。她的身体在战争前被镇上的男性觊觎,在战争中被德国人占有,然后在战后被同胞们以“正当”的爱国主义为由践踏和驱逐。她的身体就是不同权力抢夺控制权的战场。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无论是把女人作为母亲高尚化,还是作为侵犯对象低贱化,都是民族国家的话语对女性自主权益的架空,后者往往被前者吞噬——女性身体自主权总是要让步给更宏大的“家国大义”。
阿富汗在2021年被塔利班占领后,连商店橱窗里的女性假人模特都要遮住面部。这些画面提醒着公众,女人的身体不属于自己。相对于男性身体,女性身体总是被迫承载更多的民族尊严和意识形态规范,并以此为名承受更残酷的道德裁决。
公权力对女性身体的侵略性干预⼀直存在,美国的堕胎权斗争也是典型的例子,但很多强调公共和私人领域分野的男性自由主义者这些时候却选择性失明,只有自己的私人权益受到公权力侵犯的时候才站出来抗议。
男性在民族主义和父权的交叉作用下,同时被塑造为国家主体和性主体,而女性被塑造为这两个话语的共同客体。所以与国家话语下女性身体的符号化相对的,就是性别关系中男性对女性身体的占有和掠夺。相对于战争时期,在和平时期,女性身体的客体符号化同样普遍,她们是社会稳定的关键工具,又是性别暴力的承受者。
02.
女性身体作为男性的所属物
女性身体作为男性的所属物,这种观念是各种形态的性别暴力的基础,也是现有性别秩序中难以撼动的一种观念。
2023年1月,演员张静初发布消息:“在经历了十几年被造黄谣和网暴的伤害之后,我终于打了人生中第一场官司。官司虽然胜诉了,可是维权之路依然艰难,判决书下来半年了,对方依然拒绝执行法院判决,至今未在涉案账号上发表道歉声明。”
张静初从成名起就持续性成为黄谣的对象,这种现象总被视为难以避免也求助无门的职业危害,她也因此一直保持沉默,相信清者自清,但事实上,她经历的是性别暴力。
终于在女性意识大幅提升的2021年,张静初不再沉默,诉诸法律手段,起诉了侵犯她名誉的视频账号。同时她鼓励更多女性不再容忍诽谤者,勇敢维护自己的权益。
2023年7月,短视频平台网红小雪发布视频,讲述自己被造“黄谣”后报警、取证及保全证据的经过。网友造谣她是网上某不雅照片的主人公,大肆宣传并以此牟利,并来她和丈夫的直播间骚扰。小雪通过卧底进群收集证据,并进行“区块链证据保全”,对相关人士提出起诉。她的回应被称为“教科书式”维权,也为女性网友提供了鼓舞人心的榜样。
《倒霉性爱,发狂黄片》
与此同时,2023年3月,重庆大学学生贺某某偷拍女生,并在群聊和其他男生对女生进行色情意味讨论,具体包括“敲晕了带回宿舍给兄弟们围观”,“礼貌问价”等不堪言论。当事人女生的诉求是对群里发言的男生通报批评,要求语言羞辱过她的男生在群聊中发布不少于30秒的正面露脸道歉视频。而学校处理的方式只有全校通报批评,加手写书面道歉信。
还是2023年3月,苏州大学学生赵某某因传播淫秽物品被判拘留十天,后被开除学籍。赵某某从2022年5月开始对女性朋友的照片进行恶意淫秽P图,并附文带有“x狗”“x货”等羞辱性词汇,造谣同学私生活混乱,甚至在评论区泄露受害女生的个人信息,给当事人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精神伤害。女生历时6个月终于找到谣言发布者,赵某某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并毫无愧疚悔改之意。
这几年被曝光的男性偷拍、造黄谣事件屡见不鲜。
从性骚扰、造黄谣,到家庭暴力、性侵犯和妇女拐卖,这些事件是性别暴力的连续体。性别暴力的核心就是基于受害者的女性身份,对其身心的威胁、强迫、伤害,以及剥夺自由。
男性对女性的暴力,不是偶发个体事件,而是一个现象模式。哲学家凯特·曼恩在《应得的权力》中阐释了导致这一套性别化现象的基础概念:男性应得权利感,即男性期待女性为他们提供传统意义上的一系列女性商品,包括性、护理、养育、生育。男性认为这些女性商品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同时认为一些传统意义上的男性商品,例如权力、权威、对知识的掌控等等性别特权,也是男性应得的。
所以有时候男性的厌女行为不是出于对女性的敌意,而只是出于没把女性当做和自己一样的人。对于这部分男性而言,女性的定位不是一个作为人的个体,而是一个作为人的提供者——提供生育、情感劳动、家务劳动、照护劳动、物质支持、性满足,等等,而男性认为自己占有对方的身心和劳动是天然的权利。
带着这样的认知,男性很难看到自己行为的问题。近些年美国发生多起骇人听闻的非自愿独身者枪杀女性事件,这些行为用男性应得权利感来解释就是:他们认为女性的爱、青睐和仰慕是他们应得的权利。他们行为最根本的动因不是性,而是因为天然的权利没有得到满足,所以他们感到被伤害,被剥夺,自己有权利“反击”。
《混沌少年时》
这种思维的普遍和典型性不只“非自愿独身者”才有,曼恩提到:“如果一个人固执认为自己有权得到女人在性、物质、生育和情感方面的付出,那他在进入恋爱关系前可能会产生非自愿独身倾向,而进入恋爱关系后则出现伴侣间的暴力行为,特别是在他感觉挫败、心存怨恨或妒火中烧的时候……迟早会成为施虐者”。
哲学巨匠玛莎·努斯鲍姆在《傲慢的堡垒:性侵犯、问责与和解》系统性论述了“物化”概念,她给出了一份清单,拆解将人看作物品的几种方式,这些方式互相缠绕又彼此独立:
第一,工具化;
第二,否认自主性(把对象看作缺乏自我决定性的存在);
第三,无生气(认为对象缺乏能动和主动性);
第四,可替代(对象可以和其他类型的对象互换);
第五,可侵犯(物化者认为对象缺乏完整性的边界,是某种可以打破、毁坏和侵入的物品);
第六,所有权(对象可以被拥有、买卖或者成为私人财产);
第七,否认主体性(将对象看成是某种不需要考虑其经验和感受的物品);
第八,噤声(将对象看成无法言说的物品)。
这些概念不仅适用于性别关系,而是像男性应得权利感一样,也体现在所有社会关系中。
对一个人的物化,涉及到对其自主性和主体性的否认,导致不将对方当完整的人来对待,而大部分男性无法承认女性具有充分的自主性和主体性。
而且,并不是只有男性这么看。社会一直以来都许可男人去实践和巩固他这些“应得的权利”。
如果一个女人没有给某个男人他认为应得的东西,或者公然蔑视规范和期望,反而会因此面临惩罚和报复,伤害可能来自这个男人,他的支持者,以及她深陷其中的社会结构。如曼恩说:“男性应得权利感会与其他压迫性体制合力产生不公平、不合理,甚至有时候是离奇的后果。”
2015年,19岁的布罗克·特纳在参加完斯坦福兄弟会派对后,性侵了22岁且酒醉失去意识的香奈儿·米勒。可在庭审期间,媒体总是提到特纳高超的游泳技术,和他因此失去的大好前程,却不提米勒的前程。人们把这次性侵称为“不幸的事情”。
特纳母亲长达三页半纸的声明中,没有一次提到米勒,特纳的父亲悲叹自己的儿子对肋骨牛排都没有胃口,失去了“无忧无虑”“开朗随和”的天性。他不但不认为特纳罪有应得,而是认为特纳因为强奸所遭遇的后果不公平,他是个好人,即使后来有来自其他人的证词显示特纳并非那么品行端正。
这种不合理的应得权利感会催生更多厌女行为,因为当事男性认为自己才是权利被剥夺的一方,而女性被剥夺的权利完全不会进入他的视野。在前述国内事件的后续舆论中,出现了和特纳强奸案完全一样的声音。
对于苏州大学和重庆大学对肇事者的处理结果,有男网友发表如下言论:“这让我再一次见识了她们和各路媒体的暴行有多耸人听闻。我不想以后只是开了几句带有黄色属性的玩笑,就被人批判,就被上纲上线,就被霸凌,踏上一万只脚,这太恐怖了。”
重庆大学事件中,发表侮辱性言论的男生之一的家长,对于曝光ta儿子的同学发出公开警告,内容如下:
“杨同学你好,我是名单里一名同学的家人。他最近变得很敏感,大吼大叫。在我们耐心沟通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他正在遭遇网络暴力。我仔细询问了前因后果并且翻阅了聊天记录,发现他并没有说什么出格的话语……希望你看到之后请主动联系我们,与他道歉。否则我们将会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
这些反应中的颠倒黑白,可以从“男性应得权利”的角度解释。有网友做过很精准的分析:不是男性突然开始造黄谣,而是造黄谣的男性终于得到了处理。之前那些没有被处理的黄谣其实是一种性别特权,现在我们只是逐步拿走了这份性别特权。
《道格拉斯被取消了》
博主“维司塔”曾经重新发出某媒体在2017年刊登的一篇文章:《一桌没有姑娘的饭局,还能叫吃饭吗》。博主写道,“2017年,MeToo到来前的时代,这就是大媒体公开发的文章,这就是‘高端圈子’饭局常态。”
文章作者用自以为风月的笔法描绘了所谓的“京圈饭局风情”,对女性的描述现在读来恶臭难忍。但放到五年前,文章代表着绝对的文化主流,在此文引发的网络争议中,批评和反对的声音被轻易盖章为“政治正确”对性自由的围剿,对言论自由的侵犯。
如今,网络氛围似乎的确有些不同。很多男性也因此怀念曾经互联网上的“自由风气”。他们怀念的,其实是能理直气壮地把女性身体当作一块肉的风气。这恰恰证明了这些年女性主义的发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舆论环境。
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过往种种言论对女性的冒犯,因为我们仍然处在关于女性身体的同样现实里,只是更多女性看到并开始拒绝这个现实。
女性身体显然很多时候难以属于我们自己,但或许当我们警惕被固定在一个看似尊贵的国民之母位置上,当我们拒绝被当作物品摆弄、需要和控制,当我们拒绝这是男性应得的权利,我们的身体自主就开始回到自己身上。
参考资料:
《晚清文人妇女观》|夏晓虹
《五四婚姻》|孔慧怡
《战争:人性、社会与被塑造的历史》|玛格丽特·麦克米伦
《为了活下去的思想》|上野千鹤子
《应得的权力》|凯特·曼恩
《傲慢的堡垒:性侵犯、问责与和解》|玛莎·努斯鲍姆
*本文整理自看理想音频节目《性别不麻烦》第9期,有编辑删减,完整内容请移步"看理想"收听。
🗒 🗝
看理想首档
专注性别议题的音频节目
音频编辑:香芋
微信内容编辑:铁柱
策划:看理想新媒体部
封面图:《罗曼蒂克消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