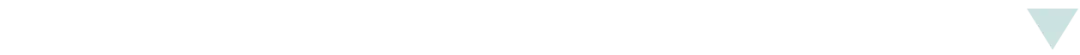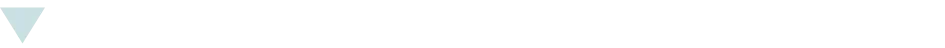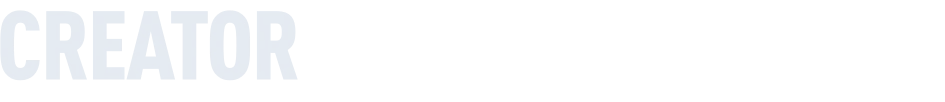初次见面,老哈一开口就抛出一个颇具威力的观点:“高层住宅老化是一颗定时炸弹。”
老哈是国内资深业委会人士、国家注册物业管理师。这是8月中旬的一天,上海的气温逼近40℃,他面前的冷饮杯上沁出层层水珠。
老哈称自己是国内第二代业委会主任,那已经是快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刚搬进新建住宅小区的老哈们未曾料想,这一簇簇高楼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如此深刻的改变。这不仅指房市的腾飞和催生的GDP,更包括房产作为一种私有财产,重新塑造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社会结构,让国人在过去几十年里经历了彻底的居住革命。
然而,时间轴行进到2024年,新的变化来了——过去数十年间诞生的商品房小区相继迎来维修养护的高峰期,从显性的电梯故障、房屋折旧、供水管道老化,再到公共空间的失序,我们安居乐业的一切正在悄然变老。
人们尝试各种方式挽救住房老化:城市更新、老旧改造,直到最近热议的“房屋养老金”制度。2024年8月23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董建国表示:“研究建立房屋体检、房屋养老金、房屋保险制度,构建全生命周期房屋安全管理长效机制。”目前,上海等22个城市正在试点,其重点是政府把公共账户建立起来。
在种种探索中,业委会是不可忽视的存在。作为一种在中国出现了33年的小区业主自治组织,它曾寄托了人们在狭小的社区空间里自治、合作、联结的美好想象。现实却是严峻的,据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德福在调研中的观察,目前中国只有1/3的业委会发挥作用。
在过来人老哈看来,邻里间试图解决房屋老龄化的集体自救终究是徒劳,他建议“弃卒保帅”:
“如果你不想因为物业管理、小区衰败对你的生活产生困扰,你每隔10到15年买一个新小区的房子,搬家。”他的声音轻易地压过了咖啡馆的背景音乐,听得周围人愣了一下。
我在另一篇传播广泛的文章里也看到了类似心路历程。文中自述了一位业委会主任联合几位热心业主,尝试对老旧小区进行自救。他们的探索以失败告终,“最终的结论是——这条路极难走通,成本太高,不如努力攒钱换房”。
文章发表于2019年,当年人们对房价只涨不跌还抱持着热切的笃定。如今,楼市跌宕打破了幻想,这意味着人们无法轻易地复制“每隔10到15年买一个新小区的房子”的英勇决策。买房、换房变得更为谨慎,人们在输入银行密码一掷万金之前,务必思考:
如果你的后半生和所有固定资产将系于某套房产乃至一个日渐衰败的小区,你该如何面对它们慢慢变老?
肖深是最近感受到居住苦恼的业主之一。事实上,最初推动我来上海的原因正是他。
肖深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们居住在位于上海普陀区一座超大型的高层住宅小区,中远两湾城。这是上海二环线内最大的小区,拥有1.1万户、4万多常住人口,分为东西两区,环抱苏州河。小区在2007年左右就组建了业委会,今年换到第四届,共15人。去年,该业委会起诉前物业公司返还全体业主4000万元公共收益和结余,一度被媒体封为中国“最牛业委会”。但今年4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撤销此前判决,发回重审。
肖深于2001年购买了这个小区里一套视野极佳、窗前无遮挡的高层住房。这栋30多层的住宅楼有200余户,配了4台电梯。
今年夏天,肖深退休。一直忙于工作、常年出差的他形容自己像“老社区的全新人”,终于有时间打开沉寂在微信里的楼栋群,并重新打量他的附近。
7月初的一天,一位邻居在群里提起,楼里有台电梯在上行时会发出奇怪的响声。紧接着,五六位邻居相继提到“电梯停在1楼不开门”“很多楼栋都换了新电梯”。肖深也加入了这场他本以为再普通不过的讨论,他想知道,2001年至今一直没有更换的电梯,是否会被“强制更换”。然而这个问题像是投进湖面的石块,瞬间激起波澜。
那天,大约有十几位邻居附议,理由诸如:住宅电梯一般使用15-20年就应该报废了,这是关系住宅所有居民的安全大事;难道一定要等到出事再换吗;其它楼栋如果都换了,为啥不抄作业……
也有数位邻居反对。理由诸如:电梯没有强制报废这一说,只要通过每年特种设备检测即可;若换梯项目有腐败,白白浪费维修资金账户的钱,怎么向业主交待;如果不能从根上解决装修户的野蛮搬运问题,新梯没多久就会折腾坏了……
肖深自嘲“不明深浅莽撞地闯入楼内事务”,并开始研究小区更换电梯的情况。据澎湃新闻2024年8月报道,中远两湾城这个明星小区共计206台电梯,已有188台(91%)开始换梯,其中149台(72%)完成换梯。肖深家所在楼是整个小区最早建成的楼栋之一,至今没有启动换梯流程。
肖深从已换梯楼栋和物业得知,在该小区,换梯要满足三个条件:有牵头者;本楼2/3以上业主参与正式投票,并有1/2以上业主同意;成立电梯工作小组,负责换梯期间的沟通、工程监理等工作。
然而他的楼栋不满足任何一个条件。肖深曾在楼群里发起了一次关于更换电梯的非正式统计:虽然楼内有近60%业主表示“支持换梯”,但有意成为电梯工作小组成员的业主为0位。
支持者名单里,几乎没有一个是肖深心目里的“关键者”,譬如,本楼的第三届业委会代表、第四届业委会候选人、绝大多数的业主小组成员与楼组长,以及日常总为电梯当“义工”的曾为电梯大修出力的几位业主。也就是说,曾经/现在为这栋楼鞍前马后的热心业主,在面对换梯时,都选择沉默。
或许是“关键者”的沉默产生了心理暗示,随着时间推移,肖深关于换梯的倡议在楼栋群里得到愈加沉寂的回应。没有人告诉他,为什么小区多数楼栋都已换梯,而本楼换梯如此之难。他也探不出原委。他想起别人口中一句戏言:你们楼就像“九龙城寨”,一直是老大难。意思是人心不齐。这句话让原本就看不懂的居民,甚至包括肖深自己,抱持不趟浑水的想法。
但面对家里的两位八旬老人,和楼里已使用了23年之久、时有异动的电梯,肖深开始思考:每一个人的需求,怎样才能合理、合规、一步步地、通向多数人的需求落地?
周扬是北京市丰台区某个小区的业委会主任。更确切地说,他是一个被理想主义驱动、在老旧小区颓败的边缘、尝试努力逆势的新一代业委会主任。
2021年,周扬所在的社区干部动员,说市里鼓励由街道社区牵头召开业主大会,组建业委会。周扬是个生意人,“喜欢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提起上海的两个相邻小区,因为业主自治水平不一,每平米房价差了至少5000块钱。
“小区走向衰败的过程里,所有业主的权益都是受损的。”周扬说。他成了这个小区里为数不多的主动报名候选人的业主,竞争对手几乎都是退休人士——这个位于北京南三环、诞生于千禧年的小区有1200余户居民,老业主多已从体制内退休。
社区书记看到候选人里冒出来一位还没退休的,“高兴坏了”。周扬不负众望,顺利当选,于2022年春走马上任。他的决心中有一层朴素的期待:“通过解决一些问题,让小区变得更好一点,哪怕唤起一部分业主的主人翁意识,参与到小区治理工作也好。”
紧跟着,“主人翁”们的家长里短就找上门了:楼上的老太太接到诈骗电话,砰砰敲周扬家门说自己“心脏都难受”;单元门坏了、电梯脏了,甚至租户问题,也在群里@周扬。
——按理,这些都不属于业委会主任职责,而是对口派出所、物业和居委会。
周扬所在的社区组织过几次线下协商会。其中一次是关于电动车充电棚的使用和安全。那天,一位上年纪的业主来势汹汹,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条,逐条历数物业工作的“七宗罪”。工作人员上前阻止,无用。等老业主讲完,周扬起身解释,反映的问题从流程上应该怎么处理。但这位业主不听过程,只是以更大的音量攻击他。
“现场鸡飞狗跳,你可以想象?”周扬的语气里混杂着无奈,“咱不说什么罗伯特议事规则,最起码,大家应该讲理吧?事实是,有的居民觉得谁嗓门大、谁能闹,谁就有理。”
类似的会议开过几次,周扬发现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比这更让他沮丧的是:“大家不知道怎么运用自己的业主权利。”
总之,周扬一开始花了很多精力解决具体的小事。他很快意识到工作思路陷入误区,要抓大放小,解决主要矛盾,比如:老旧改造。
2022年,周扬的小区幸运地赶上一次免费的市政老旧改造。当时,丰台区实施数个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这座小区名列其中。这次改造内容包括更换单元门、上下水管线改造、室外电气安防监控工程等。我在周扬发来的业委会工作简报中看到,自这一届业委会上任以来,一直跟进改造工作,包括监督排查安全隐患,与社区、物业、施工方联合入户沟通,等等。
原本是好事一桩,纷争却随之爆发——2022年下半年的某月,周扬的小区因业主投诉太多,荣登北京市各小区拨打12345电话榜首。
那时候小区已经落成二十年出头,给水管道生锈,有崩裂的风险,但凡某处漏水,至少楼上楼下两家遭殃。这次的施工方案里包括给水管线改造,但若要更换,需要得到从1楼到顶楼全部住户的同意。
结果,某栋楼的8套户型(即8条线路)无一成功。
拒绝理由五花八门:“有的是租户不愿意配合改造;有的业主说,我刚装修的橱柜,用的很贵的材料,你得给我恢复到装修的水平。”从施工方到物业,再到居委会、业委会,做了多轮沟通工作,仍旧失败。“稀里糊涂地把这么好一个(免费)改造机会放走了。”周扬说。
施工方案还包括加固安放空调室外机的平台,并统一更换护栏。当时许多护栏已经锈蚀,有的水泥基座也粉化了。依旧有人跳出来反对,“我们家的护栏挺好的,不能换”。
一次,一位业主因为和施工方无法达成一致,在微信群内辱骂项目负责人,接着发展为对骂。负责人愤而退群。周扬看不下去,在群里提醒,解决问题要有基本的秩序。随后,几位业主转而攻击他。直到周扬打了110、拿到报案回执后发到群里,争论才得以平息。
周扬做过产品经理,他有次在朋友圈里开玩笑说:有的号称治理过亿级用户量级社区产品的同行,可以来试试业委会,你会发现面对小区不到 1 万人的邻居,都得抓瞎。
据光明网,中国已然是世界上既有房屋最多、房屋建成年代最集中的国家。住建部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中国城镇既有房屋中建成年份超过30年的接近20%,意味着这些房屋将集体进入设计使用年限的中后期,而预计到2040年前后,近80%的房屋将进入这一阶段。
——在业主们为悬而未决的“70年产权到期”和“房产税”忧心时,房屋老龄化很可能会更早到来。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德福调研过全国二十多个城市、两百多个小区,他总结了中国式小区衰败的“铁律”:一个小区大概有十年“黄金期”;十年后小区老化,物业管理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们正在进入物业纠纷的爆发式增长期。”
当小区必须直面楼房、设施的维修改造翻新时,业委会的能动性显得格外重要,用肖深的话来解释是“只有需求才会触发职能”。媒体人张丰在一篇关于“房屋养老金”的评论中写道:“比建筑、设备更新更重要的是‘人的更新’……一个类似业主委员会的机构,能够一直运转,而且非常丝滑、高效,决定着大楼的大部分事务,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治’。”
事实上,在20世纪末期第一批中国现代商业房落成后,一代代居民就开始积极探索业主自治了,由此1991年在深圳,一个名为“业主委员会”的新物种诞生。
老哈的业委会生涯开始于2005年夏天。当时他所居住的南京某小区彻底乱套:保安、保洁、物业消失,小区的日常运转停滞;不到一周,人们捂着口鼻进出楼栋——垃圾箱堆满了垃圾,“小区臭了”。
业主们的怨气像炸弹一样接连爆炸。老哈想法摸清了背景:业委会要求物业加强服务,提出了一些苛刻条件;物业公司认为满足不了,以业委会收回合同为由选择了罢工。
老业主委员们顿时慌了,9个人里辞了7个。老哈作为增补委员上位,至此开始了他长达二十年的业委会实践与观察。
“过去业委会的成立往往伴随着业主维权。”老哈敲敲桌子说。他年轻时在机关工作,为人低调,“说话声音很小的”。如今他去大学和街道社区讲基层治理,“100人以下不用话筒”——“业主运动出身的人还需要话筒吗?”老哈笑了笑。
彼时,学界也对业委会这股新生力量抱以期待。“几乎所有研究都告诉我们,业主维权行动标志着中国民间社会力量的成长。”王德福曾写道。
老哈提起业主自治一个转折性事件。南京托乐嘉花园小区,这是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的大型小区,他们曾在六年内更换了八任业委会。2016年10月,小区选聘新物业公司时,甚至网络直播临时业主大会的投票和唱票现场,一共有1.5万余名网友收看。
2016年11月5日,托乐嘉花园新、旧物业交接日,多位业主统一着装,头戴头盔,手持防爆盾牌,组成了一支“业主护卫队”。起因是,原物业公司放话不会撤离小区,他们曾和业委会爆发过冲突。
几天后,在南京一座五星级酒店的豪华大厅里,托乐嘉花园举办了和新物业公司的签约仪式。随后,数条红色条幅从小区居民楼顶气势磅礴地垂下,上面写着:“不要等到国足出线再换物业。”
2015年,时任民政部副部长顾朝曦写文提到,当时全国已经有22%的社区建立了业委会。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研究者们普遍判断,实际正常运行的业委会仅1/10。
而早年活跃于圈子的业委会主任们大多在努力无果之后意志消沉地淡出,也有的在任期间被迫离职。
目前,各地政府没有明确的业委会数量统计。王德福在调研中的观察是,只有1/3的业委会真正发挥了作用,还有1/3存在问题。
为什么业委会的运转如此磕绊?最显著的原因:中国的小区太大了。
为了在有限的土地里尽可能装下更多的人口、实现利益最大化,高密度小区几乎是开发商们的最优选择。这也使得幅员辽阔的中国成为全世界以高层住宅为主的少数国家之一。王德福说:“新型商品房小区的体量基本上都是1000户以上,3000户甚至5000户以上的超大型小区也不在少数。”这意味着普通住宅小区至少有数千名居民,多则上万。
小区越大,动员成本越高,决议的难度也随之增加——光是成立业委会,就要召集一半业主参加业主大会。
肖深推动楼栋老旧电梯更换时,恰好赶上小区第四届业委会选举期。他曾在微信群里喊话本楼的第四届业委会候选人,能否牵头换梯?未获回应。事后,他得到了一个他虽然不太理解,但毕竟保留着些希望的解释:你提出换梯的时机不对,换届前没法表态。
肖深私下得知,这次换届筹备了整整一年。知情人士告诉他,“千万不能选举流产,否则要等半年方可重启,从头来过再折腾一年”。肖深向我解释,若业委会难产长达一年半,非但顶替其部分功能的居委会吃不消,想动用维修资金却找不到人批准的业主们,也不愿意。
面对这次换届,在选票发出的一周后,微信群里出现了各种声音:有人嘲讽等额选举;有人质疑上届留任者比例太高,占6/15;更多的声音,是一篇关于第三届业委会存在问题真伪莫辨的文章,最聚焦的诟病是信息披露、换届审计、账目等“透明”问题。
这是肖深第一次切身经历“感觉杂音混乱,既没人制止也没人回应”的业委会换届过程。他听说,每次换届都会闹腾,那些“透明”问题也是历届的老问题。几周后,小区业委会换届成功,闹腾归闹腾,有一个能运转的业委会,肯定比没有好。
“与其说居民对业委会工作的支持参与,建立于‘对代表个人’的信任,毋宁说是建立于‘对制度’的信任。包括民意传递的通畅、民意统计的规范、做事用钱的透明。若失去‘对制度’的信任,居民的支持参与程度大打折扣,那么自治组织就失去了‘自治’的基础。”肖深说。
这恰好体现了王德福对目前国内业委会困境的总结:“合作难,信任建立难,监督难”。“业委会要主动通过各种制度的设置、规则的建设来获得业主的信任感。”他说。
财务不透明,猜忌四起,信任缺失,这样的恶性循环并不难理解。老哈算了一道数学题,假设一个小区有1000户,每户100平米,按照上海宝山区现在每平5万的均价计算,这个小区的资产至少值50亿。
也就是说,1000户家庭的安居乐业、至少50亿的固定资产,最终维系在5到15个邻居组成的业委会身上,且他们不领工资,要像做公益一般靠情怀和责任心来为社群谋福祉。
这种担心并非无源之水。过去近20年,老哈参与或围观过200多场业主大会投票。据他观察,有时候业主大会选票的水分就像潮湿的夏季。“现在有的人不仅搞自己的小区,还能够联合起来,搞其他小区。”
这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有的人”拥有专属称谓:“职业物闹”。新华社《半月谈》在2023年报道:“职业物闹”会挑选业主多、有维修需求和公共收益的小区;常以维权名义挑起小区矛盾,抹黑业委会和物业公司;最后掌控新业委会,更换物业,逐步掏空小区维修基金和公共收益。
“换物业本身是很大的利益,一个大型小区每年的公共收益也很多。”王德福说。公共收益包括电梯广告、公共用房租金、停车费等,有些小区的公共收益账户积累达上千万,年收入有几百万。维修基金账目同样也是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数字。
“等换了更好的物业,房价可能也会涨一点。”老哈说,这些人谋得好处,高价卖了房子,再寻找下一个猎物。这股风气出现之后,业委会内部清浊难辨。老哈也失了信心,在2019年底卸任了。
对这种“难上加难”的状态,周扬感同身受。他说,小区里最核心的矛盾是争夺资源,小到紧张的车位,大到公共收益、维修基金。
“公共资源就像唐僧肉”——面对它,业主们有两种态度:要么觉得跟自己没关系,漠不关心;要是涉及到自己的利益,像火药一点就着。
王德福调研过北京的一座高档小区,业主非富即贵,“当年都是山西的煤老板,拿麻袋拿着现金去买的房子”。老板们习惯了在商场上零和博弈、发号施令,谁都不服谁,于是玩起了“权力的游戏”——小区换了四个物业公司,业委会没有一届干满了五年,中途全被反对派搞下台。
周扬也进过一个全国业委会主任群,群里翻来覆去聊的都是这些——怎么建立好的业委会制度,怎么提高业主的自治能力。理想主义的新人进群了,心灰意冷的老人退出了,最后总是不了了之。一回,周扬拜访一位年近60岁的老业委会主任,对方态度消极,摆手叹气:“这些事情大家吵了20年了,没什么进步!”
周扬所在的5人业委会成立3年,如今只剩下3人了。按照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如果再辞职一个人,该小区本届业委会自动解散。
“目前的物业模式,还有业委会模式都是有问题的,不管是立法实施,还是政府给的资源和支持,很多事落不了地。”周扬说。
“但是”,周扬清清嗓子——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他的情绪在亢奋和理智之中转换。“虽然你想做什么都做不了,但是你杵在这儿就比没有你强。”
他认为业委会像是某种精神图腾,它意味着至少在表面上,这个小区的业主是“团结一致”的,它能执行业主大会的意见、代表业主的集体利益,监督物业,配合居委会。
如果这是一个有修缮刚需的老社区,那么哪怕选出一个名义上的业委会,也比选不出业委会、导致维修资金用钱受阻要强。
“业委会的作用是你需要让齿轮转起来,你推动了一下,小区事务会运转起来,形成循环。当然它也可能朝差的方向走,只要有人把这个趋势止住,然后给一个反向的力让它转起来。”周扬说。
偶尔有业主转发“取消物业”的文章链接到微信群,周扬并不赞同。“虽然物业公司这种模式也存在问题,但是没有物业公司,修电梯、通下水道、清理垃圾这些事,谁来干?”
现在,为了维系小区里这个“精神图腾共同体”,周扬决定,哪怕少干点活(干得多,矛盾可能也越多),也得让它活下去。
多重思虑之下,他成了一个“无为而治”的业委会主任——从这位理想主义者的思路转变里,我似乎理解了肖深的楼栋群里那个“最牛业委会”沉寂的原因。
北京大学朱晓阳等学者在一篇关于中国基层治理的论文提到,他们曾观察过城市小区业主委员会运作,发现有两种小区的业委会倾向于功能良好,一种是单位型小区,另一种是同一单位人集体买下其中大比例房子的小区。
“这些小区的社区工作者不少是原农村集体领导(如村小组长)或者是单位熟人。也就是说,这些地方的社区工作者是从其服务的社区中长出来的,或者说是扎根在社区的。”
这从侧面呈现了现代小区治理之难的另一重背景:高度陌生化的社会。
四十年前,老哈生活在大院式的老房子,老邻居之间熟络,谁家有什么事招呼一声,其他人都来帮忙。“邻居出远门把钥匙放我们家,他表姐过两天来取钥匙,大家都认识。”
现在,“你看谁认识谁?”“每个人都把自己保护得很好。”老哈说。人们在紧凑的建筑空间里建立起都市气质的边界,只关心自己的生活。
王德福认为,更重要的时代背景是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完全转变了。
老哈所描述的四十年前的生活画面,建立在当时大多数城里人的生产、生活非常有规律,“劳动和生活分得很清楚”。“如今的职场是个强关系,我们都没有自己的空间了,”王德福说,“社会生产压力很大,对于仍在奋斗中的人来说,你回到小区,最想获得的是安静的休息,修复一下被职场反复蹂躏的精神。人们在地缘关系里面的社交欲望是相对下降的。”
原子化的社会也有例外。这些业委会观察和实践者们提及的特殊时间点是新冠疫情防控时期。王德福经历了2020年初疫情之下的武汉。防疫初始,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居委会在哪儿,也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社区。很快,社区成了整个防疫体系的基础环节和末端;甚至在一些特殊时刻,物业和居委会的运营能力,决定了人们居家期间的生活质量。
老哈则在上海度过了2022年的春天。看到社区在微信群里发出招募志愿者的公告后,老哈对妻子说,我是干社会工作出身的,不报名说不过去。等他赶到位于车库的集合地时,现场已经到了几十个人,几乎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我看了以后特别感动。”
这个位于上海浦东的小区在那个春天变得紧密。楼上的邻居在群里借烧菜的大料,老哈说,我家有,你下来拿。邻居下来时塞给他4个土豆。
生活在中远两湾城的一位业主也告诉我,居家办公时他的手机坏了,和外界联络都成了问题,更别说当时要靠手机抢菜来获取生存物资。一位邻居听说后,主动送来一个备用手机,帮他度过了特殊的两个月。
那段经历让王德福确信,即便今天的城市生活是陌生化的,但人们在特殊时刻会主动建立互助的网络。它带来更长远的启发是,“中国人要学会重新过邻里社群生活”。
2022年底,老哈加入的那个社区志愿者群在相关防疫工作结束后,自动解散了。这一度让他耿耿于怀,毕竟“疫情期间能站出来的那都是真正的志愿者”。
当生活回归正轨,周扬觉得,唤起大家的参与意识——主动关心小区的大小事务比什么都有效。退一万步,即便用他擅长的生意法则计算:当建筑的老龄化不可逆转,如果人们再不去参与小区里的公共事务,“房价每平米如果掉两三千,你这一套房就得差多少钱来了?”
一个现代都市小区的顺利运转,不单单基于商业雇佣关系,同样依靠每一位居住于此的市民的关心。正如周扬常跟邻居们说,只要我们走进小区,这小区的事就和你有关系——面对日渐老化的小区,任何人都无法置身其外。
文中肖深、周扬、老哈为化名
作者 王之言 | 编辑 周褶褶
排版 魏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