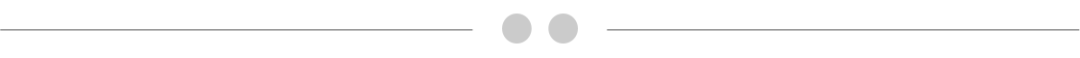近几年,毛姆的名言“阅读,是一所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已经成为了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当我们谈及阅读时,最先想起的好处,就是它能把我们带进一个避世的防空洞。
然而,阅读真的只是一种“消极”消遣吗?其实不然。阅读不仅能让我们逃避世界,也能让我们更理解这个世界。
关于阅读的种种讨论仍在进行。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阅读方式的变迁会对人类产生什么影响?纸质书还是阅读的最佳载体吗?
今年的世界读书日,看理想,邀请了窦文涛、史航、张悦然(按首字母排序),一起谈谈新兴的阅读场景、个人的阅读经验与思考。
在三人的圆桌对谈中,你会发现原来他们和我们共享着相似的阅读困惑。比如窦文涛说,他读书实在是太慢,好像家里的书一辈子都看不完了。
怎么解决?或许这是个假问题。读书呢,可以任性一点。不管你手中拿的是一本书,还是一部手机,开始看就完事了!
📱 💬 📚
读书,可以任性一点
窦文涛 x 史航 x 张悦然
1.
开卷有益
窦文涛: 今天是世界读书日,我先出个题,悦然和史航都是作家了,开卷有益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张悦然: 我爸爸有一个大书柜,小时候我会在那儿不停地翻书。离我最远最高的是《鲁迅全集》,有整整十卷,我觉得好枯燥,所以就把底下什么《乱世佳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全看完了。
有一天实在是没书看了,我就从顶上拿下来一卷《鲁迅全集》,一下子掉下来一个东西,一看,是我们家的存折。
窦文涛: 夹在《鲁迅全集》里呢?
张悦然: 对。因为我父亲是研究鲁迅的,他把存折放在《鲁迅全集》里就很合理。另一方面,他也觉得我肯定不会想读《鲁迅全集》,所以放在那儿是最安全的。
史航: 我觉得他不是防你,他首先想小偷不爱看鲁迅,所以小偷不会过去。再一个就是,他可能觉得这辈子的钱都是从鲁迅身上挣的,所以存折得放那儿。
张悦然: 对。我当时一看还有些钱,就放心地放回去了,但是知道存折放在《鲁迅全集》后我就不太敢拿下来看了,算是耽误了我阅读鲁迅。
窦文涛: 原来鲁迅的《狂人日记》里,看遍了全篇都是“吃人”二字,悦然这儿是看遍全篇都是存折。
张悦然: 这个真的叫“书中自有黄金屋”了,开卷确实有益。
窦文涛: 女作家是书中自有黄金屋,那男作家是不是书中自有......(颜如玉)?
史航: 我是男读者不算作家。不过开卷的话,至少可以看看作者的照片。看书的时间可能很长,但看照片可以很快,下次跟人家聊天就有话题了。开卷不一定读很久,读一点有一点的好处。
窦文涛: 所以开卷有益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史航: 意味着跟人打交道的时候有话题,有社交货币。
2.
碎片化阅读 vs. 沉浸式阅读
窦文涛:我想问问你们,现在纸质阅读和电子阅读的时间比例是多少?我差不多是一半一半了。
张悦然: 我也是。
史航: 如果加上微博肯定是一半一半了,而且我还看网文。
窦文涛: 那你们相不相信有一天,当仿真技术越来越厉害,比如一百年以后,纸质书就会变成一种收藏性的玩意儿了呢?
史航: 可能性一定有,但很可惜我赶不上亲眼见证那一刻,因为我们人的寿命有限。
你见证过竹简被纸取代的那一刻吗?没有,它是用了漫长的时间去完成这个更替的。我觉得未来一定是双轨制、多轨制都有的状态,而正好交接的那一刻,不见得我们都能看得着。
窦文涛: 我觉得数字阅读和纸质阅读对人的思维方式影响会是更大的问题。
前段时间,我看到好像是耶鲁大学的一项研究,说他们研究了几千个50岁以上的人,为时12年,排除了教育、种族、身体等等因素后,得出一个结论,有碎片化阅读习惯的人,会影响寿命,而能读厚书的人就活得越长。
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气一以贯之”对身体有好处。现在科学也证明冥想对人的身体是有好处的,因为当人处于冥想状态时,有利于基因复制。那么再想想读一本书,也是长时间专注在一件事上,这也是一种定,入于一静。你们觉得这事儿是不是对身体有好处?
张悦然: 是有好处。我觉得读那种特别长的小说,比如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读完就像跟着两个女孩过了一辈子,感觉自己活了好几遍,过了一个漫长的人生,然后又回到了一个起点,所以有时候会感觉很沧桑。
史航: 三生三世。
张悦然: 你就感觉重生了,对死亡的感受也不一样了。
史航: 我最近经常跟人交流一年读多少本书。我比别人多一点,因为别人都是一口气读完一本书再读下一本,我基本是六七本书同时在读。
我觉得“沉浸”好像是一个高大上的词,但是跳跃非常有意思。比如斯特兹·特克尔的《美国梦寻》,厚厚的一本讲了上百个美国人的生活自述。你隔两页又看另一个人的生活,这是不是在看更多的三生三世?
所以我也喜欢看微博,在微博能见众生,在纸质书或者长阅读里只能见天地。众生就是这么碎的。
窦文涛: 现在就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现代人缺乏耐力,连续长时间地干一件事才是好的。比如说你摒弃诸缘,你能不能连续三个小时维持做一件事儿?这是有好处的。但是另一种现实就是史航这种,八匹马儿在脑子里奔跑。
张悦然: 跟我俩相反。
窦文涛: 我是你们俩的综合。
史航: 文涛差点儿露馅。
窦文涛: 是这样,我现在很大部分的时间确实是同时看好几本书,今天看到这儿了,明天再看。我每次就把一本书劈叉放在这儿,另一本书又劈叉放那儿,捡起来什么是什么。我的感觉,就像人生。
这么说起来有点酸,一个“自闭”的人他不出门,但是他会接触很多个人、很多个场景。
今天某种心情适合看一个人的传记,上次没看完,抓起来接着看;今天的心情好像适合看点鸡汤,又抓起来这么看。于是看书就成了随缘,随着你心情的缘或当时所需。
这个过程虽然打乱了原作者给你设定的顺序,但是我们横向地在书里穿行,形成了一种读者主宰式的阅读脉络。 就像咱们吃顿饭,你很少说一盘菜全吃完,再吃下一盘。 最后你就形成了自己的一种知识结构。 在教授看来,这是不是可能不大好? 因为不够系统。
张悦然: 你们还是在主宰阅读,想驾驭。
史航: 他没有,他就把自己当成一个保龄球,被咕噜过去,撞到什么算什么。
窦文涛: 悦然把我说得挺美,但是实际上之所以陷入这么一种局面,是因为诱惑太多了,书太多了。
我现在就有一个苦恼,因为我老买书,书堆积如山,可是说实在的,我看的书肯定都比你们少,因为我看得非常慢。八匹马儿跑也是出于一种无奈,因为我永远不可能把所有书看完,但买了总得看一下。悦然看书看得快吗?
张悦然: 我是不太敢把书放下,因为有的放下可能就读不完了。我认为很多好书都是一种重负,读中间到中后段都像在翻越一个山岭。比如我看托马斯·曼的《魔山》,中间有一段时间是很苦的,但翻过去以后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还挺享受那个苦的过程。
史航: 我觉得就像微信加了很多人,但有的人浅尝辄止聊两句就可以。书也一样,废书而走,不是失败,不是背叛,是节省时间去迎接另外一个人。
但文涛刚说的感觉有点焦虑,就像是今天我过生日来了四拨人,我都得招待,有哪个没招待好,心里就不舒服。但书不是人,你把它晾着就晾着,也可以随便捡起来。像你的书都扣着,才像一只只鸟儿在飞翔,合上的话就是块砖头。
窦文涛: 这个意象好,那你家就是鸟窝了。
史航: 我特别爱读一种题材,日记。日记就好在可以随便翻,它随时从零开始,我觉得这是有趣的。其实我们不叫主宰阅读,是给自己的放任找到了越来越彪悍的理由。
3.
读书慢,是我有问题吗?
窦文涛: 我读书读得慢,本来是有点焦虑的,后来读《庄子》焦虑就减轻了。
《庄子》讲“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买那么多书,一辈子也读不了十分之一的焦虑,就是《庄子》这句话给我解了。他说你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你要知道的是无涯的。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就是说你拼命想拿有限的时间去追逐无限的知识,实际上你肯定就会“die”,就死了,不行了。这话宽慰我了,能读多少算多少,无所谓了。
史航: 他老人家都这样,何况我辈?我有一句话就叫给来生留点悬念,别这辈子什么都知道。
窦文涛: 那来生也得有才行。为什么我读得慢?因为我总想实践书里说的东西。比如《庄子》里面讲到人的精神要充塞天地,读到这儿我就停住了,然后思考到底能不能,怎么做,庄子有没有瞎掰?我想试试。
张悦然: 你还是想要一种完全的参与感。这个感觉和史航很不一样。你想钻到书里去,去兑现那本书。但是对史航来说,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游魂,他能够自如地在好多地方待着。
史航: 就是那一团虚光,你不知道它具体在哪一点上。
窦文涛: 你是怎么样的状态?
张悦然: 取决于是虚构还是非虚构。看小说的话我需要沉浸,我很讨厌被打断。但是对于知识类的书,我没有文涛这么严谨,还是一种从对岸去看的感觉,有种距离感,文涛是要把自己推向知识的原子内部。
窦文涛: 但是如果你不想弄明白,为什么要看?
张悦然: 我觉得阅读进去的每个字都会被吸收,像脂肪一样肯定会变成能量。你为什么不等它和其他积淀的知识发生反应,交汇一下?
窦文涛: 所以后来我有一朋友跟我说,他说你这么看书,一行字上定俩钟头,试试精神上能不能达到书里说的境界,这是在修炼,哥们。我一听,说是修炼挺好的。
史航: 看一个字看俩小时,那不就是金庸在《侠客行》的《白首太玄经》里,把一个字看成一套剑法或者拳法,看其中的运动轨迹一样吗?
其实人不用主动安排自己的时间和兴趣,你是被安排的,你一定会遇到某一本书,一页纸耗你两个礼拜,也会遇到一种书,几个钟头就翻了十几本。
窦文涛: 我 还想问问,你们读的书都记得吗?
张悦然: 我不太记得。所以现在电子书有记笔记的功能,对我还挺重要的。做老师有时得强迫自己记下一些东西,要不然记不起一句话是谁说的,怎么说的,出自哪儿。有个足迹还是很重要的。但是史航好像都记得出处。
史航: 你看孔雀开屏很难,但孔雀会说多练练你也可以。如果同一段书的内容你和不同人在不同的场合都讲解过,你就容易记得。
4.
年轻人不读纸质书了吗?
窦文涛: 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读书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问题了,像是一种食物。但我发现有一小部分年轻人很有意思,可能是小时候强制性读书给读伤了,他们一看书就睡着。他们也想改这个毛病,但我觉得实际上是他们没有从书里得到快乐的习惯。
史航: 首先这些朋友应该高兴,睡眠质量比很多人高。读书特别多的人都容易失眠。
窦文涛: 我觉得人性没有太大两样,我们小时候因为贫乏,一本《水浒传》读15遍,如果把今天的年轻人放到我们小时候那个年代,他们也会拼了命地找书,因为没有别的娱乐。
但是今天好玩的东西太多了,我见到有的18、19岁的孩子,几乎没看过印刷的读物。他们吸收信息的方式全是数字化的,比如打游戏或者社交软件。
史航: 我就是半边看书,另外半边打游戏。我打某一个古代战争游戏,攻城有5分钟才能到下个回合轮到你上,所以这5分钟我就在另一边看看《罪与罚》,时间到了再回去点两下游戏。对我来说都是乐趣。
窦文涛: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八匹马儿跑的状态。我们未来的人类是不是要习惯于多屏生活,或者说分心生活?但是好像从心理学的研究上来看,这是不可能的。在一秒钟内,你可以快速切换,但你不可能同时专注在两件事上,所谓的“同时”只是频繁的快速切换。
史航: 对,就是切换。我的两种情绪,两种人格在玩游戏和看书之间轮番登场。
窦文涛: 有时候想起对未来人类的很多思考,我觉得可能性是无限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未来人类的大脑也会接受快速切换的训练。其实现在的人的思维方式就表现出来有所不同了。
我们的脑子之所以这么聪明,其实跟文字和阅读有极大的关系。我那天看一个互联网的调查,原来现在占用网民时间最多的,第一是短视频,游戏好像排第二,然后还有在线阅读。
史航: 游戏还是个需要用脑子判断的事,因为你得用手指戳。但短视频你只需要按一下,它一个视频完了就会切换到下一个短视频,你就可以待着,无论睡着还是醒着。
窦文涛: 所以说这种短和碎片化的内容的特点是,它是事实的集合,而不是逻辑,或者说很少逻辑。这其中往往没有一个推演的过程,你不知道来龙去脉,直接看到结果。事物在短视频里可能被简化了,原本一件事有五个原因可能变成了一个原因。
那天我听一位哲学教授说,很多人一听见概念就头疼,可是,人能像今天这么聪明,完全是因为人类用概念和语言来思考。所以我们不必在谈论一条狗时,真的牵一条狗过来。
正因为有了语言和概念,我们从空无中创造一个世界,可以聊上下五千年。所以他认为不要小看文字这个符号,我们就是用符号来思考的,我们能在脑子里进行像代码一样的复杂运算。
史航: 所以脑子才能装那么多东西。
窦文涛: 从这个意义上,如果人完全不阅读,就需要担心大脑退化的问题,因为你的符号思维被弱化了。
史航: 不爱读书的人,等于没有一个字典或者大百科全书,你得跑遍整个世界,才能说完自己的一句话。
张悦然: 这让我想到阅读和写作之间的关系。原本我教书时是觉得写作是进阶,阅读是初阶,但现在其实反过来了,阅读课上的同学明显比写作课上的同学更资深,更“文学”。
史航: 写作课在今天相当于某种排泄。
张悦然: 对,为什么写作课人多、门槛低,就是因为它实用。这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人们不想读,但是想输出,阅读反而成为一件更高深的事情。
窦文涛: 那能输出什么呢?
张悦然: 输出文案,文案可以变成短视频,输出广告语,广告语可以变成短视频。需要输出的东西都会变成有用的东西。现在的很多写作教学其实和阅读分开了,很多课就是在教大家如何写得天花乱坠。
史航: 因为写作能直接发表,它就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但是阅读从来不是一个人生活中可发表的一部分。
张悦然: 阅读就是因为不实用,你没法量化它的作用。
史航: 读不读书都是一辈子。
窦文涛: 为什么你们那么爱读书呢?
史航: 我们是老天选的。
窦文涛: 看把自个儿说的。
史航: 别人腿脚利索,眉清目秀,不用读书就能活下来,那如果你啥都不行,各方面都残次,你只能靠读书充实自己。
窦文涛: 我觉得悦然说的更有意思,还是因为书能给人最普遍的一种好处,就是忘。你看了也不必记得,你不用管读了它有没有用。
张悦然: 它会来找你的。
窦文涛: 咱要说人有内涵就在这,所谓内涵就是你自己也不知道你肚里有些什么东西,但是别人觉得你肚里有东西,是不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