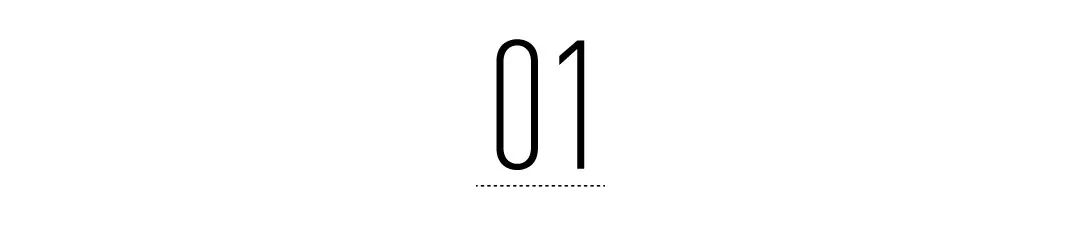《冀西南林路行》专辑封面
12月22日零点,石家庄乐队万能青年旅店发布了他们的新专辑《冀西南林路行》,很多乐迷的朋友圈一片欢腾,像过年一样热闹。毕竟,距离他们发布的首张专辑《万能青年旅店》,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
十年,当年听着“是谁来自山川湖海”的年轻人,已经步入中年,开始过上了“囿于昼夜厨房与爱”的生活。十年前,他们以为“傍晚6点下班”就是无聊中年生活的开始,今天才发现,那已经是打工人最大的福报。
听听吧,也许这张专辑里也有你的十年。
“妻子在澳洲,我去喝几瓶啤酒……”
因为“妻子”在澳洲,所以“我”下班回家无所事事,但又较为闲散自由,还能出门喝喝酒,不用张罗做家务。
啊,这就是中年男人的婚姻生活吗?“升官发财死老婆”,但死老婆太残忍了,老婆在澳洲似乎就是个两全其美的故事……
很好笑对吧?可我第一次听《杀死那个石家庄人》的时候,确实把“熬粥”听成了“澳洲”,再进行这么一番琢磨的。这是一个还在学校念书的十几岁小子,对未来的大人的世界,所能穷尽的一切想象。
《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歌词截图。
“万能青年旅店”乐队(后文简称万青)的歌词向来以经得起琢磨闻名,对他们歌词的解读、过分解读甚至误读,俨然已经成了欣赏万青的固定流程。
新专辑《冀西南林路行》的动机,据说源于乐队经过被大力开采的太行山,目睹被劈得支离破碎的山体、遍地的采石场、水泥厂和矿口的经历。
这么一说,歌词似乎很容易理解?如果仅止于此,那就不是万青了。
万青歌声里依然有雷声隐隐
以《采石》《泥河》《山雀》组曲为代表,万青这次说的就是大山被现代化消耗一空的故事。
这是最容易得到的一种解读。但听多两遍才发现,字句间要表达的并不只是“环保”和“大自然的悲鸣”。
比如《泥河》,前两段交代人类到来之前,“严格而缓慢”的山,一边稳坐水畔,一边担忧着远处的“雷声隐隐”(炸山开坑的声响)。
炸开道路来到这里的人,以困窘的形象出现,“一贫如洗”,“劳动、饮酒、叹息”,夜晚露宿山间河床上。他们为现代化建设挥汗如雨,却不是现代化成果的享受者,在这里,炸山的人并不是反派,而是和山一样承受着被消耗、被掏空的命运。
再到《山雀》,这首歌最触动我的地方,是“爱与疼痛/不觉漫漫道路长/生活历险/并肩茫茫原野荒”——继“是谁来自山川湖海/却囿于昼夜厨房与爱”又一句情话。
厨房与爱固然是世人追求的幸福,但《山雀》笔锋一转,结尾来了句“大雾重重/时代喧哗造物忙/火光汹汹/指引盗寇入太行”,讲述者“我”显然拜服于当代生活的伟力之下,转而背叛了曾经“不觉道路长”的爱侣。
《山雀》歌词截图。
三首组曲的点睛之处,应该是《采石》中的“崭新万物正上升幻灭如明星/我却乌云遮目”。你瞧,新专辑还是在记录人和现代文明的关系——说得更精确一点,这种反思依然是从记录时代的落潮者而不是弄潮儿出发,以一种“失败者叙事”的角度进行的,和首专《万能青年旅店》显然是同源。
首专《万青》的歌词创作背景尽管离我一个广东人很远,涉及北方工业城市衰落、下岗潮、转型期阵痛等等,我在欣赏的时候却并不感到隔阂,因为歌里和时代背景有关的意象并不是主角,仅仅是故事的注脚,而好故事往往和发生在哪里无关。故事打动人,靠的是一些普适而又直指本质的东西,像《杀死那个石家庄人》里描述的那种疏离的家庭关系,你可以在自己和你身边找到无数映射。
可回到《冀西南林路行》,万青似乎放弃了严肃文学式的表达——这里的严肃文学指的是网红“大咕咕咕鸡”提出的概念而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目力所及都是意象,支离破碎的意象、意象再加意象:山、石、水、鸟兽、爆破、雷鸣,但偏偏缺了故事。或许也不是没有故事,只是故事的主角不再是“人”,而是大自然,在客观上确实更难令我们这些“囿于厨房与爱”的凡夫俗子产生共情。
到了终于与“人”相关的《郊眠寺》,意象的堆砌感反而更重了。“电子荒原”之上,又是电缆,又是数字、地产、水泥、宗教、医保,blablabla,像是要把人间一切事物活动都写进歌里——但是!意象和素材的堆叠并不高明,什么都写,想把所有事情都说尽的野心,最大的可能是一件都没能说好。
2013年12月14日,万青在一场演出中。图/yuen yan/wiki
太行山里没有万青
两张专辑虽然都是“失败者叙事”,它们所暗示的结局却极为不同。
《万青》里,渔王用风暴和喉咙换取饮食,醉倒在洗浴中心,失意也诗意。整张专辑讲的也正是“人如何失意地活着”,那些面对黑暗横渡海峡的年轻人,最后都活了下来。
人年轻的时候,做点稍微勇敢的事都会自觉悲壮,总觉得自己难受得要死了,但你通常都会活下来,然后慢慢失去自己曾经认为了不起的那部分特质,成为与其他人的最大公约数,换来某种意义上的和解,并继续活下去。
万青的现场。
在首专《万青》里,最可怕的关键词是“黑暗”,但歌曲里的主角,还是可以在面对黑暗之后,小确丧又小确幸地活着。这就是十年前万青塑造的“石家庄特色蓝调摇滚”气质:以布鲁斯为基底的旋律,吟唱布鲁斯音乐的主题——生活与受苦。
展开来说就是,百多年前黑人奴隶辛勤劳作的田间悲歌,神奇地完成了在中国的本土化,替那些被千禧年高速增长落在后头的小城游民唱出了自己的心声。
也正因缺乏了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高速增长,2010年后我们猛然发现,除了一线城市拆迁户和互联网暴发户以外,绝大多数人都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小城游民。这股社会动力,这种不言自明的宿命感,缓慢地把万青推到了国摇第一把交椅的位置。
万能青年旅店封面。
到了《冀西》,完全反过来了,不再有什么黑暗,“崭新万物正上升幻灭如明星/我却乌云遮目” ,看不清吗?并不是。
人和自然被榨干、丧失活力和尊严的进程,你我看得清清楚楚,云的下面泥沙俱下,看不清的只是云上的生活。万青仍然直指本质,但这背后的基调更无望,人失去讨价还价的能力,嬉皮董二千兜兜转转,发现人类世界到底还是成了“前已无通路后不见归途”。
要是把两张专辑和十年间万青的处境放在一起,我最大的观感则是“矛盾”,而且是愈加矛盾。
2010年以来,社交媒体高速发展,万青的走红也得益于此,先是早期微博网红推荐,再到豆瓣、知乎上引发的广泛讨论,辅以流媒体软件对歌曲的广泛传播……整整十年,如果你去查百度指数,万青虽然谈不上大红大紫,没有什么剧烈波动,但大部分时间段里数值还是可以碾压五条人的。万青的歌虽然处处对现代文明抱以冷眼,但必须承认,他们能达到今天的地位,有现代文明的一份功。
“十年磨一专,青年变中年。”
如今,想在破旧的城中村Livehouse里见到唱破旧生活的万青?难了。
接下来,他们会出入各种巨型音乐节,成为音乐工业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小的一部分),成为现代文明的元素之一,这时再去谈反思?你很难说,这是违和还是难能可贵。
我并不想借用“四五线没有李诞”这样的话,可在太行山缝隙里讨生活的人,显然是没什么机会去音乐节听万青的,最大的可能是到工地继续搬砖,好一点的可以当个保安。这才是最严肃的事实。
与十年前不同,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体,我倒是掌握了很多“置换”“和解”的生活技巧。
感谢时代,我能随时听到十八线小乐队;感谢现代物流,我能跨洋跨洲买十八线小乐队周边。我不再对大型音乐节感兴趣,不再关注名头特响的乐队,这意味着不必抢票,不必人挤人,不必老争论“谁谁谁出专辑了万一这专辑不行中国摇滚乐是不是要完了”,更不必在音乐软件评论区领略成百上千的电子荒原精神垃圾,比如“万青都出新专辑了你还没有对象”。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这些事上,真的很消耗人。
听不懂万青,没所谓,那就去又闷又小又黑的Livehouse看看十八线小乐队吧,他们都带着那种对生活很不甘的热情,像你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