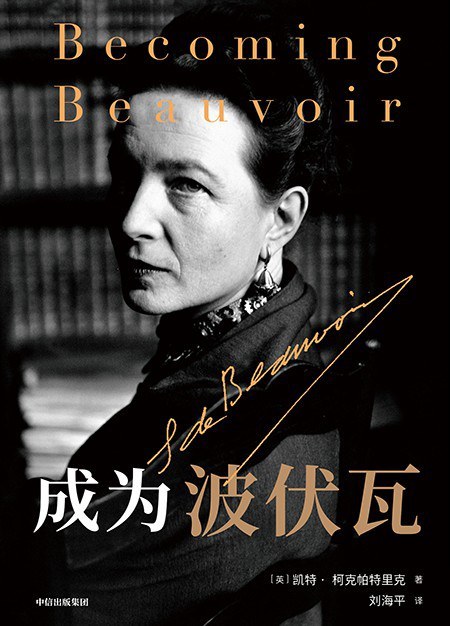
在为⻄蒙娜·德·波伏瓦撰写传记时,凯特·柯可帕特里克提出了关于真相的问题: 我们讲给他人的故事,他人所讲述的关于我们的故事,以及我们讲给自己的故事,这三者孰真孰假呢? 她所指的是,作品中,波伏瓦呼吁女性的独立自由,树立了她与萨特开放平等又不可分离的爱情特例——但在情人口中,波伏瓦利用和背叛了其他女性,后来被公开的日记和信件又表明,萨特既非波伏瓦哲学的全然偶像也非她爱情的中心。波伏瓦并没有许诺供出一切,凯特为她正名道,探讨她没有在作品中完全说真话的原因,要将波伏瓦还原至生活场景中。尽管如此,没有一部传记能以全知视角还原真相,《成为波伏瓦》只试图找到一条新的出路。只要证明波伏瓦自我的力量,以及“成为一个女人并不意味着要掌控你所成为的那个人物的方方面面”。后者使得全书对波伏瓦的认识,更为自由和公正。如果我们追求精神的真相,而非细节的真相,恰恰能够看到一个流动的波伏瓦,一个处在永恒的“成为”中的波伏瓦。
《女宾》是波伏瓦出版的第一部小说,故事蓝本是处在“本质的爱”中的波伏瓦和萨特,以及他们拥有的第一段“偶然的爱”——波伏瓦的学生奥尔加。萨特不仅鼓励波伏瓦从个人生活中汲取题材,还建议她用奥尔加替换⻄蒙娜·薇依作为原型,增强与波伏瓦的人物对比度。尽管现实中,萨特对奥尔加的痴迷,一度使波伏瓦濒临崩溃,她还是认同地采纳了建议。小说写到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为止,结尾弗朗索瓦兹送皮埃尔去集合的情节,与《波伏瓦回忆录:岁月的力量》中波伏瓦送萨特的情节几乎一致:他们赶到集合中心,广场空荡荡的,警察让他去另一个地方报道,“如果你愿意就零点来,我们不能特意为你一个人安排一列火⻋。” 现实中,这部从1938年开始创作的小说,到1941年夏初才写完。“早在它收尾前,你就和它不合拍了。”波伏瓦在回忆录中写道,最后的几章迫使她不断重新审视和修订开头的几章,写下它是为了表达自己正超越过去,但现实中更新的自己,并没有在小说中得到反映。
小说中,不分你我的弗朗索瓦丝和皮埃尔,将格扎维埃尔纳入其中,由此建立一个“任何人都不会牺牲的、真正的三人组合”。格扎维埃尔中途放弃了他们,因为她无法完全占有皮埃尔;皮埃尔一面追求十全十美的爱情,一面为了自我满足不停伤害着两个女人。弗朗索瓦丝则总在挣扎中孜孜不倦地劝说双方再度接纳彼此。皮埃尔对格扎维埃尔产生了对自己从未有过的感情,弗朗索瓦丝为此感到不安,她要重新接近皮埃尔,唯一的方法是重新亲近格扎维埃尔,像他那样观察她。以第三人称写成的小说,波伏瓦被困住被遗弃的痛苦清晰可感,甚至整部小说都像在诉说她不能对身边任何人倾诉的痛苦,而她的痛苦又体现出一种哲学抱负。往常,弗朗索瓦丝所在之处就是巴黎的中心,可一旦皮埃尔和格扎维埃尔单独在咖啡馆相处,这座咖啡馆就成了巴黎的中心,而弗朗索瓦丝则被流放了。和皮埃尔的疏远,动摇了弗朗索瓦丝自我的存在感。“外面没有任何东西吸引她,里面没有任何东西挽留她。”小说中,弗朗索瓦丝哭了几次,最终都平静了下来,“因为必须回复到充实的事物和自我中”。有一次,她边哭边逃,像被一阵龙卷风卷走了一样,因为她在格扎维埃尔身上发现了和自己相同的意识。“每人在体验自己的意识时都把它看作一个绝对的东西,这是确实的。很多个绝对怎么能并存呢?”
皮埃尔惊讶于弗朗索瓦丝能全身心体验到一种思想,现实中,萨特也十分羡慕波伏瓦的这种本领。波伏瓦具备的另一种本领,是对他人遭遇的深切共情,她不能理解对此漠然的人。而萨特总把自己视为超越一切的存在,具体的事件对他而言都微不足道。《岁月的力量》中,她讲述了年仅十九岁的犹太人朋友布尔拉的遇害经过,她再次清醒地认识到世事无常,感到自己偷了这个本该属于这位年轻人的世界。而萨特劝她,十九岁和八十岁死去并没有多大区别。《名士风流》里的安娜,又把这个年轻人的故事讲了一遍,她望着圣诞节上的蜡烛、冬青、槲寄生,暗暗地想,迪埃戈再也看不到了,“这儿给予我的一切,全是我从他们那儿夺来的”。而从哀悼中抽离出来对罗贝尔来说总是更容易,他安慰她,生死之间的距离并没有那么远。
波伏瓦在回忆录中热情地描绘过战时朋友们相聚的“节日”,这些“节日”——战前曾度过多少个这样的夜晚,通宵达旦,尽情交谈——扮演和放大了生活里能享受的快乐,尽管没有什么吃的,但至少有几瓶酒可以喝。热闹令三十多岁的波伏瓦重新感到振奋,相信未来还会和从前一样。《名士风流》就始于这样的节日场景。第一个和平的圣诞节里,安娜看着女儿纳迪娜在朗⻉尔怀里的笑容,想起过去迪埃戈这样抱着她的时候,她也是这样喜笑颜开。一旦得知,一个被自己接纳过的人,就此消失了,日子就无法再在恐惧和希望中折衷。战争使外部世界面目全非,也颠覆了波伏瓦的内在自我。过去,她所学会的“他者存在的意义”只是私人交情,战争中,她感到自己“散落在地球的四面八方,每一根神经都和他人、和所有人维系在一起”。1939年,她还在渴望幸福,1941年,“幸福”一词已经失去了意义。
无论在《名士风流》还是在《女宾》中,波伏瓦都借着生活或情感的危机,重新审视了自己与萨特的关系。萨特曾经能给她庇护,“他的命运给我保证了世界的命运”,但他们真的是同一个人吗?还是他们只是同一个萨特?如果有意识地让自己和萨特拉开距离,这个爱了几十年的人,显得如此陌生。伟大的人物会“把世界看作属于自己的,为了对世界的错误感到负有责任,对它的进步感到光荣”。没有女人会这么做,她不会成为梵高、卡夫卡,不会“企图扮演整个人类命运”,“她不会把人类的苦难看做自己的罪过”。《第二性》中的这段结论,可视为波伏瓦将自己独立出来,对世界承担责任的企图。
1949年,《第二性》出版,成为女性主义经典。1954年,《名士风流》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波伏瓦曾尝试将年少挚友扎扎的生死往事写进《名士风流》,结果还是删去了,在同一年,将之写成一部中篇小说。但她同样感到不满,没有为其命名,生前也未公开手稿。这部未命名的手稿,就是《形影不离》。不同于波伏瓦之前的小说,它平铺直叙,充满了她所追求的“文学的真诚”。鉴于中文版出版的时间,这则两个天才少女的故事、亲密的关系和命运的倒置,很容易让人想起费兰特和《我的天才女友》,但它们有着本质的不同。波伏瓦感到,扎扎去世后,自己继续活着是一种过错,她甚至在笔记中用了“献祭”一词——扎扎是自己获得自由献出的祭品。中年的波伏瓦,几次回忆一段从始于九岁的感情,要用文学还给扎扎自由的生命。
这是希尔维人生经历的第一次感情,转校生安德蕾成了她的同桌,从此,希尔维还能保持第一,仅仅是因为安德蕾对此不屑。学校的老师形容她们“形影不离”,这个词散发着浓烈的童年气息(波伏瓦在信件中一直保留这个称谓,“形影不离的扎扎”。)安德蕾是“独一无二的”,她总能令希尔维震惊,为了逃避毫无自我的社交,她用斧头砍伤了自己的脚。她总在丰富希尔维的词汇,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永远”第一次砸在了希尔维心上,而 “非柏拉图式的爱情” 又是什么?一个深夜,她们在厨房谈心,安德蕾很沮丧,没有人因为她本身而爱她。希尔维终于坦白,自己一直很爱她。那时,她们才真正了解了对方,同时也意识到,过去形影不离的两个人之间,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
《形影不离》中希尔维关于自己的回忆如同隐身,她完全让位于安德蕾,心甘情愿扮演着从仰慕者到控诉者的角色。安德蕾的一生只有二十二岁,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不顾母亲的坚持和男友帕斯卡(梅洛-庞蒂)的劝说,为自己赢得了爱情。她闯进了帕斯卡的家,见到了帕斯卡的父亲,“我不是您的敌人,我也很高兴认识您”。他的父亲对她说,“只是您太疲惫了,还发着烧”。安德蕾回家后陷入了谵妄。葬礼上,希尔维几乎认不出她,“我模糊地意识到安德蕾是因这种白色窒息而亡”,她在坟墓的白色鲜花上放了三朵安德蕾最爱的红玫瑰。
《第二性》第二卷中,波伏瓦分“成长”、“处境”、“辩解”和“走向解放”四个章节,展开叙述了希尔维“模糊的意识”。传统的婚姻,多少要求女性断然地与她的过去决裂,合并到丈夫的天地中。她只有内在性,没有超越性。她不被允许直接控制未来和世界,只能通过丈夫向群体超越。这些婚姻中的女性不完整。扎扎在少女时代,虽然可以求学,也能相对自由地行动,但身处家底丰厚的正统家庭,她的人生仍然受到恪守传统的控制。她与波伏瓦一样有进步的决心和叛逆的勇气,最初是她带领波伏瓦挑战权威,而内心信仰与欲望的矛盾,不被亲人理解的孤独,自我价值被否认的痛苦,这些长期积压的阻力,耗尽了她的生命。
“人生让我发现世界如其所是”,《巴黎评论》的采访中,波伏瓦说,“年轻时我以为探索世界是去发现美好的东西……我先是一点一点,然后是越来越多地发现世界上的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