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公众号置星标 ↓
防止内容走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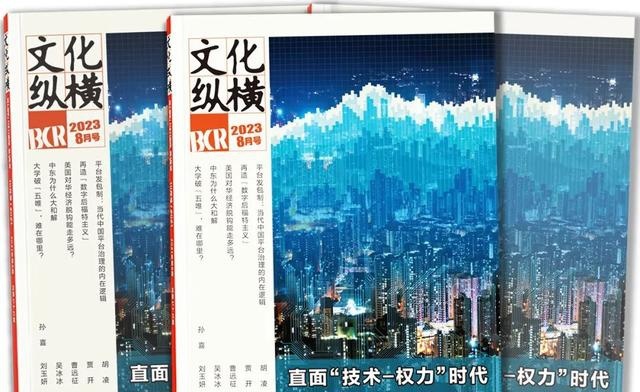
《文化纵横》2023年8月新刊发行
点击上图或文末左下角阅读原文查阅
投稿邮箱:wenhuazongheng@gmail.com
《文化纵横》邮发代号:80-942
✪ 吕德文 |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有为而治:节俭、
高效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第二章
▍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
从历史视角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乡村治理变迁本身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产物。乡村治理处于特定的环境之中,不同区域、不同历史时期,乡村治理的实践也不尽相同。一方面,乡村治理嵌入了国家建设进程中。国家性质、国家能力以及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异,都会塑造出不同的乡村治理实践。另一方面,乡村治理嵌入了特定的乡村社会结构中。乡村社会结构的差异、乡村社会变迁的速度,也会塑造出不同的乡村治理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立了单一制的国家治理体系,实行中央集权是实现国家一统性的前提。因此,维护中央权威,加强中央政府的各项能力是我国特色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根本特征。但在实践中,中央集权在不同领域、不同历史时期,其治理程度并不相同。换言之,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间,二者各自的程度始终处于变动中,这在根本上决定了乡村治理变迁的轨迹。
以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为观察视角,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来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变迁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乡村治理服务于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我国逐步确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中央对地方人权、事权和财权都有较大的支配力。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人民公社体制主导了这一时期的乡村治理实践,其显著特点便是乡村治理服务于国家资源的汲取,用以实现工业化建设。
二是改革开放初期乡村治理“放权”的过程。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源自安徽小岗村大包干的农村改革,其本质自始至终都是一场对基层、对农民的“放权让利”改革。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后,对中央、地方和农民三者关系的经典表述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其落脚点是充分调动地方和农民的积极性。深入其中可见,微观上的“放权让利”改革,是建立在以地方分权为特征的宏观体制变革基础之上的。
三是20世纪90年代后乡村治理逐步“均权”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均权”特征:在某些领域加强集权,在某些领域又进一步分权,集权与分权并行,复杂互动。比如,在财权领域,逐步形成了复杂的“均权”体系。一方面,中央政府在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改革,极大地强化了中央的汲取能力;另一方面,地方并未因此失去积极性,而是通过税费征收、乡镇企业及土地财政等方式,加强了地方财政的自主性。
概言之,从20世纪90年代到党的十八大之前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经过了“复杂且灵活的动态调整”。其明显趋势是,国家在资源汲取、制度调控等方面的能力得到了加强,这使得其在宏观调控及地区均衡之间的统筹能力也得到了提升。但是,地方的自主性并未受到影响。地方政府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方面,还是在社会管理及人事安排方面,都拓展了诸多空间。在乡村治理实践中,也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景象。一方面,乡村治理呈现出鲜明的“积极行政”特征;另一方面,过于积极的乡村治理实践也制造了危机,成为世纪之交“三农”问题的主要症结。
具体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治理变迁的轨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治理主体的变迁轨迹:大致而言,治理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变迁轨迹。在人民公社时期,乡村治理主体比较单一,严重依赖政社合一的政治机构及群众动员机制。在“乡政村治”模式下,乡村治理主体逐渐多元化。一方面,基层政权的形态复杂多样,不仅有乡镇党委政府,还有由七站八所组成的数量庞大的事业单位;另一方面,村级组织也逐步多元化,村干部、党员和村民代表成为村治主体。而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中,不仅乡镇党委政府和村两委是乡村治理的主体,各类社会组织也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
第二,治理内容的变迁轨迹:总体上,乡村治理的重心逐渐从“政务”转向“村务”。乡村治理的内容包括“政务”和“村务”两个方面,前者指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各项行政任务,后者指自主管理村庄公共事务。大体上,人民公社时代的乡村治理内容,主要是服务于对农业剩余的汲取,“政务”主导“村务”;在“乡政村治”模式下,“政务”和“村务”既分而治之,又相互配合;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下,“村务”成为乡村治理的重心,大多数“政务”如民政、社保、计生等都是服务于村庄事务等“村务”的,而从村庄汲取资源的行政任务已经越来越少。
第三,治理方式的变迁轨迹:概言之,乡村治理方式的变迁具有鲜明的制度化特征。制度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乡村治理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二是乡村治理的制度执行能力不断提升。人民公社时代,乡村治理主要依靠国家权力,尤其依赖政治动员和基层干部的工作经验,制度化程度比较低;而在“乡政村治”模式下,虽然行政理性化不断加强,但其制度执行能力较差,很多情况下要依赖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治理现代化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健全党组织领导的“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也意味着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
乡村治理处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最基层,嵌入了乡村社会中,需要与民众进行广泛接触。因此,乡村治理的变迁轨迹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支配下进行的。
一方面,传统国家代表特定的统治阶级利益,国家治理能力不足,国家汲取农业剩余的动力也不强,再加上传统的乡土社会具有较为完整的村落共同体,乡村社会变迁的速度较为缓慢,乡村治理具有鲜明的“无为而治”的特点。现代国家的国家治理能力较强,乡村社会急剧变迁,这使得乡村治理的实践更为复杂。如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乡村治理体制经历过多次变更,这和国家建设的历程是相互匹配的。人民公社制度之所以存续,主要是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服务于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城市建设。而改革开放时期的“乡政村治”模式,主要是农村改革驱动下的产物,此时的国家建设,主要是通过市场转型来实现的,而村民自治是释放农民自主性的具体表现。进入新时代,我国启动了乡村振兴战略,需要进一步强化乡村治理效能,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便应运而生。
另一方面,不同的村庄社会形态,对乡村治理实践会产生明显不同的影响,从而产生不同的乡村治理类型。原生秩序型的乡村治理,村庄具有较强内生秩序生产能力,村干部是村民的“当家人”,基层行政权力难以干预村庄事务。次生秩序型的乡村治理,村庄缺乏内生秩序生产能力,但国家正式制度能够有效落实,村干部按章办事,基层行政权力可以安排村庄事务。乡村合谋型的乡村治理,村庄没有内生秩序生产能力,正式制度也无法有效落实,村干部是谋利型的,乡镇政府通过灰色利益换取村干部合作。无序型的乡村治理,则指的是“村务”无人打理、“政务”也无法落实的乡村治理状况。
总的说来,三种乡村治理模式是由特定的乡村治理环境塑造而成的,它们之间并无优劣之分。可以这样认为,它们都较好地完成了各自的历史任务,却又有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人民公社制度成功地实现了国家和社会制度的重组,真正意义上完成了国家政权建设,并为工业化建设立下汗马功劳,但它无法调整日益紧张的国家与农民关系,最终导致了这一模式的瓦解。“乡政村治”模式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它难以解决分散的小农与国家、市场对接的问题,引发了20世纪末的“三农”危机。某种意义上,党组织领导的“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就是为解决“乡政村治”模式的固有矛盾而来的。
《有为而治:节俭、
高效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作者:吕德文
内容简介
吕德文教授基于“广、泛、深”的田野调研,从节俭、高效两个关键词出发,对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以及当前新的治理举措,展开了深入研究,尝试探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一种可能性:通过激活简约主义传统来优化乡村治理体系。
作者扎根田野,基于实证经验,着重探讨了三大问题:乡村治理的制度空间,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以及乡村社会变迁视阈下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归宿。书中解释了那些成功的乡村治理实践是如何创造性地转化原有的制度空间的,而一些现代的做法产生了怎样的结果,既有对乡村治理中老问题的新阐释,又有对乡村治理中新现象的理性解读,全方位地分析了乡村治理诸问题。
本文为友情合作推广,编选自《有为而治:节俭、高效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第二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打赏不设上限,支持文化重建
订阅服务热线:
010-85597107
13167577398(微信同)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早8点至晚8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