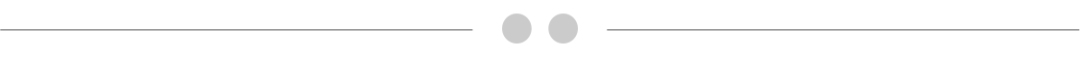他们为了守护国家而入伍,但受到伤害时,国家又为他们做了什么?
韩国人很敢拍,也很擅长用影像关照现实。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无不反映了某种社会现状,触碰了韩国的痛处——《寄生虫》与阶级矛盾,《黑暗荣耀》与校园霸凌,《素媛》与性侵犯......
由Netflix出品的《D.P:逃兵追缉令》(以下简称《D.P.》)是“敢拍”中的一员。2021年播出的第一季豆瓣评分高达9.1,第二季于今年七月底放出,评分稳定在8.5分上下。
虽然评分有所下滑,但《D.P.》仍是韩国难得的作品。它兼具戏剧性与批判性,揭露韩国军队中的霸凌潜规则,用一个个逃兵的故事,拼凑出受害者的面目和系统的腐烂。
有人说鸡蛋碰石头会粉身碎骨,但“即使被砸碎,也会留下痕迹”不是吗。
1.
当一个地方只有男人,会发生什么?
韩国《宪法》和《兵役法》规定,所有身体健康的韩国男性均有服兵役的义务,他们会因此脱离日常社会约两年,在军营里训练和生活,成为国家安全的一环。以此为背景,《D.P.》展开了它触目惊心的故事。
安俊浩(丁海寅饰)是一名新兵,入伍不久就被负责抓捕逃兵的D.P.(全称“deserter pursuit”)组选中,因此获得外出的权力。对于服役中的军人而言,这是莫大的特权,因为可以借职务之便出去吃喝玩乐。抓不到逃兵归队会被痛骂一顿,抓到逃兵归队就是锦上添花。
但安俊浩接受邀约不是为了出去玩,而是为了逃离军队内的霸凌,如同他要抓捕的许许多多名逃兵一样。
韩国是一个讲究等级文化的国家,年纪小的人要服从年纪大的人,辈分低的人要服从辈分高的人,而强调纪律和秩序的部队,自然会将等级文化放大到极致。
《D.P.》开篇就展现了安俊浩被老兵黄章秀霸凌的片段。黄章秀一边拷问安俊浩无关紧要的琐事,一边用手推搡他,而安俊浩的脑袋后方,是一根凸出的钉子。任何肢体或表情上的不悦,都可能让安俊浩一头撞向墙上生锈的铁钉。而这只是部队生活中稀松平常的一部分,它如一个隐喻,暗示着往后的如履薄冰。
新兵要承受言语上的侮辱和肉体上的暴力,是部队里公认的潜规则。老兵通过霸凌辈分比自己小的士兵来确立权力地位,这甚至是他们解压的方式。在霸凌发生的链条里,最上端的军官睁一只闭一只眼,其他士兵则假装不知情,以换得不被欺负的特赦。没有人愿意反抗,因为“向来如此,忍忍就好”。
很多时候,《D.P.》刻画的霸凌场面都让人极度不适,但这不是恐吓性的奇观,而是在还原一个只有男性且非常强调雄性气概的环境里,究竟会发生什么。安俊浩之外,老兵黄章秀的另一个霸凌对象是性格温柔的曹石峰,除了言语及肉体暴力,他会用打火机烫曹石峰下体的毛发。更触目惊心的是,另一位老兵还曾强迫曹石峰在他面前表演自慰。
这些涉及性的霸凌行为严重摧毁了曹石峰的自尊,他的处境其实和被强奸的女性并无区别。当一个地方只有男人,且高度崇拜雄性特质,那些不具有传统雄性气概的男性,就会被划分为“女性”。“女性是一种处境”在曹石峰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著名女权主义者苏珊·布朗米勒在《违背我们的意愿》中提出过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强奸的本质是权力而非性欲。她通过美国男子监狱中发生的男男强奸案件来论述,监狱强奸并非因为施暴者一定是同性恋且要发泄性欲,因为自我解决永远是最方便的选择;实际上,他们要通过压制一名男性,来确立自己的上层地位。强奸一位男性意味着剥夺他的男性性,他因此变成“女性”,而施暴者则变得更男性。
媒体人陈迪分析《违背我们的意愿》一书时写到,“男性气质的文化,期待男人攻击、侵略、夺取、占有;它要求男人有权力,要有能耐让他者屈从,最好是有本事让他人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都要来服从你;而强奸,几乎对上了男性气质要求的每一寸胃口。”
《D.P.》中,曹石峰的遭遇就是布朗米勒揭开的现象的缩影。部队的特殊环境及其滋生的暴力,反映出父权文化最病态的一面,同时是“男性也是父权制的受害者”最有力的佐证。
成为上位者不是出路,因为永远有人比你更强,更有权力。真正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建立一套牵制权力的机制,而不是指望一个人不要成为弱者。这当然是条更难的路,因为它需要众多人共同完成。而大部分弱者等不到这样的拯救,他们只能在自毁和成为下一个加害者之中选择。
2.
枪口抬高一寸
曹石峰选择自毁。第一季的最后,曹石峰殴打了企图霸凌他的老兵,然后他踏出军营,去寻找刚退伍的黄章秀复仇。安俊浩和搭档韩浩烈不得不外出追捕他。
追捕的过程是痛苦的,因为受害者曹石峰在踏出军营的那一刻成了违法的逃兵,而安俊浩深知他什么都没有做错。曹石峰要绑架黄章秀为自己报仇,因为旁观者、权力上位者,没有一个人帮过他,所以他只能用自我毁灭的方式,捡回一丁点被践踏、被碾碎的尊严。
在好几轮的追捕中,曹石峰不断地质问他们:为什么要抓我?为什么受罚的是我?这个问题实际上贯穿了他被霸凌的每一分每一秒,他不顾一切地绑架黄章秀也是为了得到答案:为什么要霸凌我?为什么是我?
黄章秀简短的回答刺破了霸凌的真相:因为以为那么做也可以。
“那么做也可以”的背后是一个慕强的社会。针对个体的暴力会发生,是因为个体周遭的每一个环节都在回避强者的过错,伤害他人成了强者被默许的权力。所以问题的答案最残忍的地方在于,关键不是受害者是谁,而是加害者可以这么做。
曹石峰最终在特勤队的包围下开枪自尽,安俊浩奋力扑向他,将对准下颚的枪口推开一寸,救下曹石峰。这一寸的营救姗姗来迟,如果早一点发生,或许受害者就不会崩溃到这个地步。《D.P.》是一部让人坐立难安的剧,不过也正是在刺痛中,那些枪口抬高一寸的瞬间给观众留下漫长的余味。
马克思·韦伯称现代社会的官僚制为“理性的铁笼”,军队恐怕是最符合这个形象的国家组织之一。为了保证国家安全系统的高效运转,每一个士兵、每一个军官都有自己的位置,服从上级命令格外重要,而脱离秩序的人则会受到严苛的惩罚。追缉组作为部队系统中的一环,具有让脱序者归位的功能,是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中负责兜底的一部分。他们也因此见识到在铁笼下拼命挣扎的个体。
曹石峰之前,有一个逃兵叫许治度。安俊浩和搭档韩浩烈在追捕他的过程中了解到,他唯一的亲人奶奶罹患阿尔茨海默症,所住的房子还在拆迁边缘。许治度逃营的原因是想挣够钱把奶奶送进疗养院,于是他混进了拆迁队,近距离守护奶奶。
成功抓捕许治度后,安俊浩和韩浩烈在归队的路上做了一个决定,释放许治度。他们让他挣够钱再回来自首。那是安俊浩和韩浩烈作为人的决定。
许多研究现代性的学者都观察到,现代官僚制度的一大特征是非人格化,通过不把人看作人来维持某种秩序。政治学者张新刚总结,“它要求在运行中排除个人的因素影响,排除了个人好恶,排除一切非理性的影响。这种非人格化的特征就表现为,无论是在现代经济、政治,还是社会、军事的系统里,个人的性质变得不太重要了,相反,是否拥有专业能力和知识才是更重要的评价标准。”
安俊浩和韩浩烈在追缉的职位上所做的,正是放弃了一小部分专业能力,来成全逃兵的难处。当他们把逃兵当具体的人来看,他们也守住了自己作为人的自主性。这或许就是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所强调的“判断力”。
执行命令是容易的,因为这不需要思考,而在命令之下藏一块救生垫,永远比前者更需要勇气。
3.
旁观者之罪
《D.P.》第一季将叙事重点放在逃兵的故事上,展现了韩国部队如何滋生霸凌,以及个体在纵容霸凌的部队里被一点点撕碎的过程。到了第二季,剧集似乎想将批判对象正式拔高到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上,因此新增了几个军队高官的角色,其中,由池珍熙饰演的具子云是所谓的最大反派。
面对屡屡爆出的霸凌事件,具子云的立场是守护部队的形象,尽可能污名化和打压受害士兵。而安俊浩所代表的追缉组,自然是站在具子云的相反面。其实不难看出,第二季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它对具子云的塑造过于脸谱化,对权力结构如何异化个体没有更深的挖掘,整部剧也往更戏剧性的类型片方向走。
相比于第一季认真讲每个逃兵的故事的叙事策略,第二季花了大篇幅描写安俊浩如何守住意外获得的机密USB,为此不惜一人单挑一支队伍,只为将这些秘密公之于众。这导致《D.P.》最后变成了一个歌颂个人英雄主义的故事,多少有点流于俗套。
但第二季的结尾为它扳回一城。安俊浩顺利保住的USB,虽然不至于让权力瓦解,至少让石头沾上了扔向它的鸡蛋。一切尘埃落定后,归队中的安俊浩却在街头偶然看见黄章秀,他和一群朋友有说有笑,看起来已经开始了新生活。《D.P.》在此延续了第一季留下的批判性。现实不是爽文,现实是霸凌者会重新变回普通人,继续过他平庸的一生。至于霸凌的记忆,只会化作受害者一生的伤害,如同留在曹石峰脸上的那一道疤。
与前段时间爆火的《黑暗荣耀》不同,《D.P.》陈述的霸凌者谈不上是百分百的恶人,甚至,他们也有顺从和善良的一面,而这正是霸凌的真实面目:只要进入特定的环境,谁都可能是霸凌者,谁都可能是受害者。实施霸凌的时候,霸凌者想的仅仅是“这么做也可以”、“这么做没人会阻止我”。这就是权力的荒谬,荒谬在它仅仅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念头。
《D.P.》到最后依然在坚持一个观点:如果一个环境中发生了暴力,那么环境有无法逃避的责任。实际上,从最初的叙事视角就透露出这一价值观。本剧的主角安俊浩和韩浩烈,除了是追缉员,还有一个重要身份是旁观者。他们每抓一个逃兵,都是以旁观者的视角来认识一个逃兵。
当我们讨论一个环境时,讨论的不仅是体系,体系下的旁观者也是环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旁观者没有制定规则的权力,但他们的每一点行动都可能影响权力的实施。因此《D.P.》试图对话的不是霸凌者,而是暴力发生时沉默的大多数。
在第二季大结局的那场法庭戏中,安俊浩的上司林智燮上尉作证词时说,“在这种情况下(指因霸凌发生的枪击案),我们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应对呢?答案很简单,我们等通知。......我想说的是,不能因为像我这样的军人,只为了等待命令,眼睁睁地看着有人死去。”这番话像是对旁观者的审判,一字一句地宣读“旁观者之罪”。
回到本剧主角,安俊浩也不是一开始就懂得“思考”。他从小看着父亲殴打母亲,即便万分唾弃家暴的父亲,但更怨恨母亲从不逃离。他的觉醒来自首次追缉任务的执行失败。当时因为要陪前辈喝酒唱K,本应抓捕的逃兵在这段时间内烧炭身亡,而他恰巧是借火机的人。
此后,那个意外借出去的打火机一直刺痛着安俊浩,他再也没有办法旁观或无视眼前的苦难。
汉娜·阿伦特曾以“恶的平庸”来提醒世人,不要成为一个不假思索的人。安俊浩有打火机警醒他自己,那我们,又有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