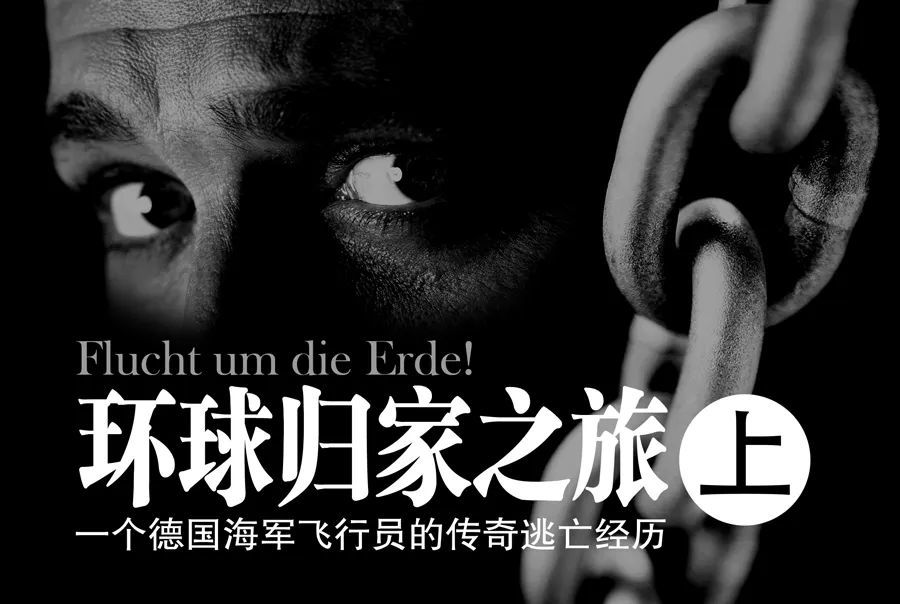
中国有句古老的成语叫南辕北辙,形容前进的方向和目的地背道而驰。发明这句成语的人不一定知道地圆说,因为地球是球形的--理论上说,即使方向不对,也是能到达目的地的,只是需要绕远--甚至环绕地球一周。在战火连天的1915年,一位德国老兄就亲自验证了这个理论,进行了一次环游世界的归家之旅,这次旅程充满了各种戏剧化的情节:纵身一跃,逃离正在穿越西伯利亚的战俘列车;近乎绝望,一次发生在满洲冰冻荒原中的徒步跋涉;暗地里偷偷送上的墨西哥银币和假护照,还有如猎犬般追逐不休的英国特工--这并不是某本间谍小说的片段或好莱坞大片的情节,而是德国海军飞行员埃里克·基林格(Erich Killinger)的亲身经历。
年轻的候补军官
当1914年夏天,战争阴云笼罩欧洲大陆时,基林格还是德国海军米尔维克军官学校的学生,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包括他。基林格出生于1893年3月21日,老家在舍瑙(Schönau),靠近巴登的维森塔尔(Wiesental in Baden),他在1913年4月1日考入了海军军官学校,成为该校1913届第四期军校生。在教官凶神恶煞的咆哮下,基林格像一名普通新兵一样接受了基础步兵训练,摸爬滚打了一个半月后又被送上训练巡洋舰“维尼塔”号(SMS Vineta),前往加勒比海和南美洲进行航海训练,洗甲板、削土豆、没完没了的操练令人筋疲力尽,在结束了10个半月的远航后,基林格已经被海风吹打得结实强健,终于可以作为初级候补军官回到米尔维克,于1914年4月开始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军官必修课程,可惜这种舒坦日子没持续多久。
■ 由红砖构建的德国海军军官学校,1910年落成。基林格就是在这所学校中踏上军旅的。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在犹如堆满柴薪的欧洲撒下一点火星,引起一场席卷世界的冲天战火。伴随着战争警报,米尔维克军校宣布停课闭校,所有学员都中止学习,被提前分配到舰队,为祖国和皇帝陛下尽义务。基林格在1914年8月被派往威廉港(Wilhelmshaven),登上轻巡洋舰“柏林”号(SMS Berlin),该舰是第三港口守备支队的三艘老式巡洋舰之一。他在“柏林”号上只呆了一个月,在9月份报名参加了海军飞行队,前往柏林接受空中观察员的培训,在这里与飞行员卡尔·冯·格里森海军少尉(Karl von Gorrissen)成为搭档。1914年11月,基林格机组加入驻普茨希(Putzig)的海军第1飞行大队(Seefliegerabteilung I),配属于水上飞机母舰“格林杜尔”号(Glyndwr),该舰本来是一艘英国货船,战争爆发后被德国海军俘获,并加以改装。从1914年12月到1915年3月,格里森和基林格随“格林杜尔”号在但泽湾进行训练,主要内容是侦察,并且尝试搜寻潜艇,德国海军并不急于将这种新型战舰派往前线,而是先花时间探索其运用方法。直到1915年3月底,“格林杜尔”号才携带4架无武装的阿维亚蒂克B.1型双翼水上侦察机(Aviatik B.1)前往东普鲁士的梅梅尔(Memel)开始实战部署,基林格机组则在3月28日进行首次战斗侦察飞行。
■ 年轻的基林格,此照摄于他被俘接着又脱逃辗转返回德国后。
■ 1909年的“柏林”号轻巡洋舰。1903年下水,与之后出现的“吕贝克”号都属于“不莱梅”级。这艘老舰在一战后成为德国允许保留的8条巡洋舰之一,经历了整个二战,直到1947年才凿沉。
海上迫降
“你难以想象这一天究竟有多热,直到扇叶停止旋转为止”,这句话是一战时期飞行员们的口头禅,即使坐在四面通风的座舱内,发动机散发的热量还是让人感到酷热难当。在1915年4月6日那天,基林格和他的机长冯·格里森对此是深有体会,他们当时正在俄国海滨城市里堡(Libau,今拉脱维亚的利耶帕亚Liepaja)上空执行侦察任务:从梅梅尔基地起飞,深入俄军防线后方40公里实施侦察,飞行路线先是穿越波罗的海(Baltic Sea),然后转向东飞往目的地,在里堡上空他们将转向南方,飞过里堡与帕拉根(Palagen)之间的空域后掉头返航。据估算这次飞行只需花费三小时左右,谁也没想到会发生什么意外。在德国飞行员眼中,这完全是一次不受任何威胁的例行公事,因为当时战斗机还不是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至于俄国人的防空手段--用老式步枪和机枪组成的零星拦截火网--格里森少尉根本不屑一顾,子弹连皮毛都擦不到。实际上,这次飞行像以往一样非常顺利,至少在他们掉头返航前是这样的。
■ 阿维亚蒂克B.1型双翼机。这种飞机的飞行能力虽不出众,但综合性能较为稳定,衍生出陆地起飞型和水上型,还可以携带鱼雷和炸弹等武器作为攻击机使用。
时至中午,飞机已飞过里堡,任务也圆满完成,现在是往南调头回家的时候了。冯·格里森熟练地调转机头,毕竟基地远比波罗的海上空舒服。但就在此时,他们的座机“基尔-51”出现了可怕的状况,飞快转动的螺旋桨突然发出一阵让人毛骨悚然的响声,紧接着竟然折断了!断裂的叶片向下飞旋而去,还把右侧机翼下方的浮筒打得粉碎。这一切来得极为突然,丧失动力的飞机立即打着旋坠向地面,宛如一只瘫痪的飞鸟。幸好格里森经验老道,在飞机下坠过程中逐渐控制了平衡,改出盘旋,但当务之急是赶紧寻找一处适合迫降的地点,否则小命不保!
很显然,失去一侧浮筒的水上飞机在陆地上迫降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他们只能调整方向向波罗的海滑翔,但即使能在海上成功迫降,在没有及时救援的情况下还是相当危险的:即便他们能够幸存,也很难避免沦落为战俘的命运。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格里森毫不犹豫地压低高度,做好了一切准备。在距离海岸线7000米开外的地方,他们的飞机一头扎在海水里,尽管降落动作非常完美,但失衡的飞机还是翻滚起来,剩下的左侧浮筒也在此时被摔得粉碎,巨大的冲击力将两名飞行员都抛出座舱。在一番挣扎后,正面朝下的飞机残骸开始扭曲并下沉,脱落的左侧机翼漂浮在离沉没点不远的海面上,还算完整,看起来是个不错的临时救生筏,但在两人抓住它之前就慢慢漂远了!
■ 格里森和基林格机组,后座上留着胡子的是基林格。尽管意外坠机,但不可否认的是好运一直眷顾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