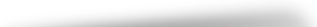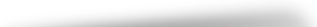
今天我们的评审书目——《蓝夜》,来自美国女作家琼·狄迪恩。她唯一的女儿因病突然离世,悲痛之余,她以文字记录与女儿的点滴回忆,以此与挚爱道别,获得走出悲伤的力量。她说,我们需要学会接受失去,就像接受偶尔的急流旋涡和每日的潮起潮落。
关于婚姻、孩子和记忆,关于人们愿意或不愿面对的一切……透过这些文字,我们终将意识到必须学会接受失去,就像接受偶尔的急流旋涡和每日的潮起潮落。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评审团”,我们将不间断地为大家送上最新鲜的阅读体验。书评君期待,在这个新栏目下,向所有人提供关于阅读的优质评价,也同新的优秀“书评人”共同成长。
The Jury of Books
评审团
本期书目
《蓝夜》
《蓝夜》
作者: [美]琼·狄迪恩
译者: 何雨珈
版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年5月
作者简介:
琼·狄迪恩,美国女作家、记者,生于1934年。她在小说、杂文及剧本写作上都卓有建树,在美国当代文学领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05年,琼·狄迪恩获美国国家图书奖。2013年,美国政府授予琼·狄迪恩美国国家人文奖章。
她的写作风格惯用独特的角度审视人生,以简约细腻的笔法刻画人物,她叙述故事时并不巨细靡遗,而是干净利落、突出关键细节、断裂文句,在字里行间留出一片片空白,留给读者遐想的空间,回味的余地。
主要作品有《蓝夜》《向伯利恒跋涉》《奇想之年》等。
它讲的是什么?
蓝夜将尽,夏日已去。
本书是琼·狄迪恩的代表作,为了纪念逝去的女儿,她写就此书。
狄迪恩在书中探寻生与死、情感与自我之间的关联:是否我们从根本上无法互相了解,甚至对彼此一无所知?是否因为我们的不同,使我对你的痛苦甚至离去的预兆置若罔闻?是否即便没有生死的阻隔,我们也不曾真正亲密?
关于失去,关于悲伤,关于幸与不幸,关于婚姻、孩子和记忆,关于人们愿意或不愿面对的一切……她说,我们需要学会接受失去,就像接受偶尔的急流旋涡和每日的潮起潮落。
它为何吸引人?
为了生存,我们讲述。
——琼·狄迪恩
读来令人心碎。这是对失去的热切追索,跟死亡与时间的悲伤斡旋。
——《纽约时报》
美国版《我们仨》,《奇想之年》的姊妹篇,一本献给挚爱的告别之书。
美国国家图书奖、人文奖章得主,当代现象级女作家琼·狄迪恩,奥巴马为她颁发“国家人文奖章”,称她是“美国政治和文化至为尖锐和值得尊敬的观察家”。她的文字鼓舞了几代女性的思想与精神。
《蓝夜》抢先试读
我不知道多少人会自认是成功的父母。自觉成功的人一般会举出那些象征着(他们自己)社会地位的东西:斯坦福的学位、哈佛的MBA、常春藤联盟大学毕业生聚集的律师事务所的暑期实习。而不怎么愿意自夸做父母的技巧的人(也就是大多数人),会像念经一样重复我们的失败、疏忽、不负责任和各种托词。“成功父母”的定义经历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从前我们认为,成功的父母能够鼓励孩子进入独立的(成人)生活,“提升”他们,放手让孩子去飞。如果孩子想要骑着单车冲下陡坡,父母可能会象征性地提醒一下,冲下这个陡坡就会进入一个四岔路口。但归根结底,最想培养的还是孩子的独立精神,所以父母也就不唠叨,不过多地提醒了。如果孩子想去做一项结局可能很糟糕的活动,父母可能会提醒一句,但只提一次,不会再说第二次。
我在二战期间的孩提时代便是如此。在战争中长大,就意味着我需要比在和平时代更强的独立性。父亲是空军的财政官,战争刚开始那几年,母亲、哥哥和我就跟着他。日子过得并不算艰难,但想想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期间,生活在美国军事设施附近的那种异常拥挤、混乱不堪的状况,我的童年也绝不是安居无忧。在科泉市,我们第一次有了真正的房子,那是精神病医院附近的平房,有四间屋。但我们没有打开包袱收拾行李,妈妈说没有必要,因为随时都可能接到“命令”(“命令”对我来说是个神秘的概念,不容置疑)。
每到一个地方,大人们就希望哥哥和我能适应,能凑合,能在建立生活的同时也接受眼前的事实,那就是无论我们建立怎样的生活,都会因为“命令”的突然到来而终止,被推翻。我从来都不清楚到底是谁下的命令。但就算我觉得不合理,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世界正在大战。战争不可能因为孩子们的愿望有任何缓和或转移。孩子们容忍了这令人不快的事实,得到的回报就是他们可以创建自己的生活。这些孩子的父母面临的最好选择,就是任由孩子们自由野蛮地生长,而这背后隐含的影响,却无人去深究。
战争结束了,我们又回到萨克拉门托的家。但家庭教育的主题依然是放任自流。我还记得十五岁半拿到实习驾照时,就觉得可以吃完晚饭从萨克拉门托开车到太浩湖了。要沿着蜿蜒起伏的山间高速公路开两三个小时,到达之后,我们又立刻转头开回去,因为车里的饮品都带齐了,再沿着来路开两三个小时回家。我开车消失在内华达的高山之中,而且还算是彻夜醉驾,结果爸妈一句都没有说我。我还记得,大概也是十五岁的时候,在萨克拉门托北边的美利坚河漂流,结果被大水冲进一个分水坝,然后拖着漂流艇来到上游,又玩了一次。对于我这样的行为,爸妈仍然一句话也没有说。
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现在实在是无法想象了。
为人父母的行程表上,已经没有时间让你去容忍孩子这样大胆放肆的消遣了。
尽管这种良性的忽略让自己受益,轮到我们当了父母,对成功的判断标准,却是我们能对孩子进行多么严格的监控,恨不得把他们紧紧拴在身边。巴纳德学院院长夏竹丽建议父母多给孩子一点信任,不要对他们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大包大揽。她提到有位父亲,专门休假一年来指导女儿的大学申请准备工作。她提到有位母亲,亲自陪着女儿去见系主任,讨论一个研究项目。她又提到另一位母亲,说因为自己付了学费,要求校方把女儿的成绩单直接寄给她。
几年前,波士顿东北大学的卢因女士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写了大学校园里代沟变小的问题。不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家长们的问题,也指出了学生自己的问题。其中有一个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学生,一个月和家人的手机通话时间远超三千分钟。她似乎把自己家看作一个很有用的学术资料库。“我可能会给爸爸打电话,问他‘土耳其的库尔德人是怎么回事?’这比自己去查找资料容易多了。他什么都知道。我爸爸说什么我基本都会信。”另一个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学生被问,有没有觉得和父母太亲近了,她一脸茫然不解:“那是我们的父母啊,他们本来就应该帮我们。这本来就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啊。”
我们越来越觉得,这样深入参与到孩子的生活中是特别正当的行为,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我们把他们的号码设为快捷拨号,通过聊天软件注视他们,追踪他们的去向。我们认为打过去的每个电话他们都要接,只要他们计划有变就要向我们报告。我们总是胡思乱想,觉得一离开我们的视线,他们就会遇到前所未有的新危险。我们会把“恐怖主义”挂在嘴边,彼此警告“世道不同了”“和以前不一样了”“不能放任他们干我们以前干的事了”。
然而孩子总是要面临危险的。
女儿金塔纳出生之后,我没有一刻不在担惊受怕。
我怕游泳池,怕高压线,怕水槽下面的碱水,怕药橱里的阿司匹林,怕“破碎男”本人。我怕响尾蛇,怕湍急的水流,怕泥石流,怕出现在家门口的陌生人,怕没由来的发烧,怕没有操作员的电梯,怕空荡荡的酒店走廊。恐惧的原因显而易见:这些东西可能会伤害她。问个问题:如果我们和孩子能清楚地了解彼此,这恐惧会消失吗?是我们俩的恐惧都会消失,还是只有我的恐惧会消失?
成年后的我们,便渐渐淡忘了童年时的沉重与恐惧。
如何参与“评审团”?
我们希望你:
| 是一位认真的阅读者,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 期待将自己在阅读中产生的想法用文字表达出来,与更多人交流,甚至引领一种主张。
| 时间观念强,能够遵循我们的约定。
你只需要:
| 点击,在表单中告诉我们你为什么想读《蓝夜》,或者你对相关话题有怎样的了解和兴趣。
| 等待我们的回复。我们会尽快选取5位评审员,然后确认地址与联系方式,于清明节假期后尽快将书寄出。
| 在两周内(从收到书之日起)将书读完,发回500-1000字的评论或读后感。
如果你被选中为当期阅读评审员,我们还将邀你加入“阅读评审团”微信群,让你遇到更多热爱阅读、认真思考的同路人。
也许有的人会觉得——一本免费寄送的书,换来这么多的要求,不值得呀。
但赠阅并不是“阅读评审团”的核心,我们所期待的,是让有意愿有能力表达自己见解的读者,有一个发表和交流的平台;是让那些原本灵光一闪、只有自己知道的思考,在鼓励和督促之下能够被文字所记录、被他人所阅读;是为了通过认真的讨论,让“热点”的潮水中多一些独立的、真诚的声音;甚至,是为了发现和培养新的书评作者,让我们以这种方式相遇,然后看到你从此不断成长。
你,来吗?记得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