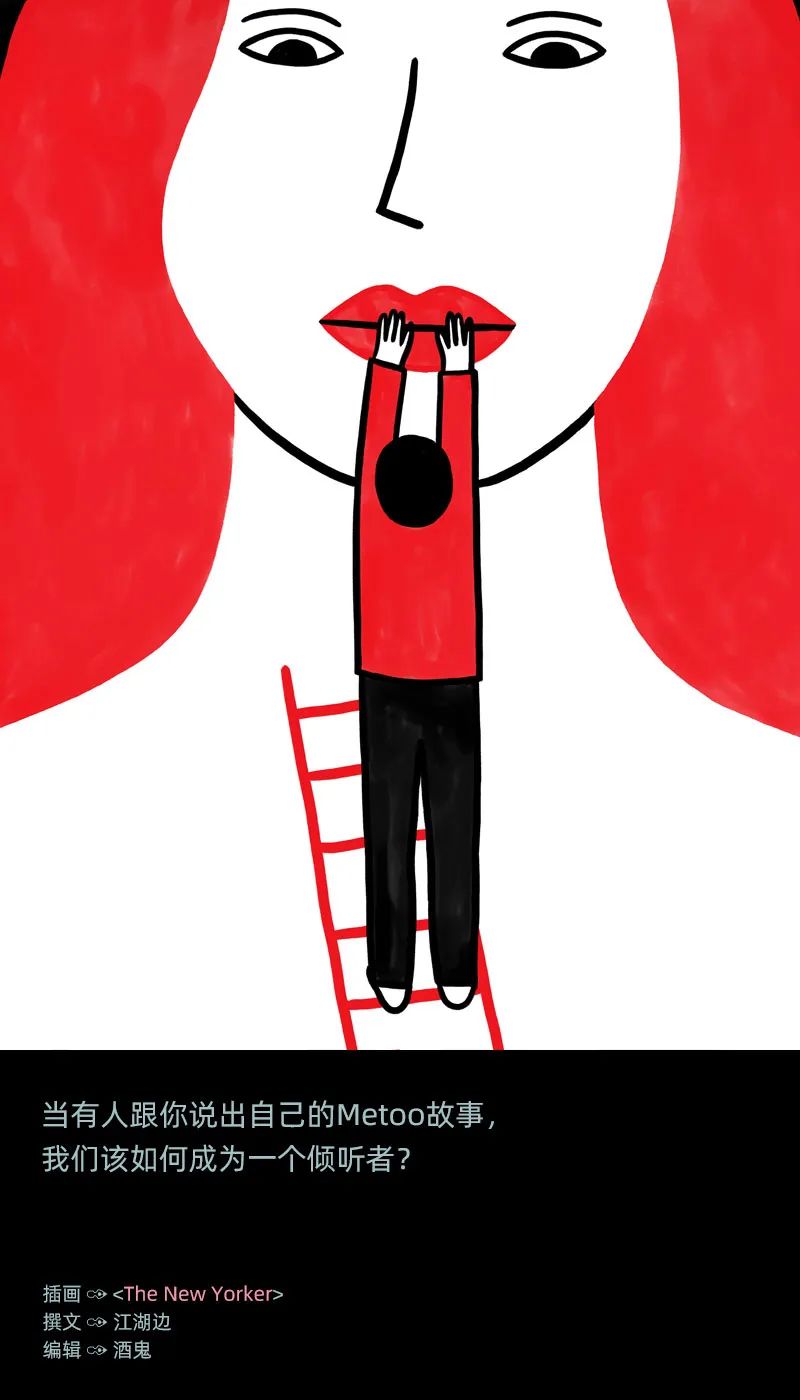
当我还是一个初中生的时候,《校园缤纷》报一个满脸长痘的年轻男记者与我父亲交涉,以拍摄宣传为名,将我带到市里有名的景点内进行性骚扰。
搂抱、摸胸,吮吸我的手指直到沾满唾液。我清楚地记得,与他同行的其他人(摄像、司机、还有一个女同事)对此置若罔闻。
我感觉不舒服,但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最后我安全地回家了,什么也没说。
又过了几年,我在上海坐公交车,人很多。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用一根手指伸进我的紧身牛仔裤,卡到屁股缝里。我看向他,他看向窗外。然后我到站了。
那时候我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回家后告诉了妈妈,但她笑着告诉了其他亲戚。其中一个亲戚说:下次遇到这种事,你就用高跟鞋踩他。
之后的几十年里,我在有关“性暴力”的话题中变得非常愤怒。
我帮委屈的大学同学出头,在微博上发言,与激进女权主义者交朋友,还在简单心理写稿——总觉得必须做点什么,来对付那两个我曾经什么都没做的性骚扰者。
图/The Nation
说起来,起源于“韦恩斯坦案”的全球Metoo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进行了好几年。
虽然它最终需要落到规则的建立、法制的健全和公民意识的觉醒上,但在“性暴力幸存者”个体的疗愈层面,我仍然觉得:
Metoo运动的最大成果,就是Metoo运动本身。
它引发了一场“说出故事”的浪潮。它让无数的幸存者有机会抱团讲出自己的真实经历,不被评判、有人相信、被人支持。
这正是不同形式的心理治疗(精神分析、存在主义和认知行为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在一个被信任的环境中,安全地进行自我表露。
因为“说出来”本身,就是疗愈的开始。
当我们讲出痛苦时,痛苦就变小了。
许多研究表明,自我表露,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形式,都能缓解长期的压抑压力,从而改善健康状况。
简单地谈论我们的问题,与信任的人分享负面情绪,可以深刻地治愈压力,并减少身体和情绪上的痛苦(Pennebaker等,1988)。
这里的重点是:安全、值得信任的、支持性的环境。
当一个性暴力幸存者倾诉ta的故事时,什么样的回应才算“支持性的”?
图/KUNC
如何回应一个性暴力幸存者的倾诉
怕说错话,让ta更难过
不知道该给什么建议
面对一个创伤比我更严重的人,我的脑子好像卡壳了
……
当面对一个“谈论如此隐私的话题”的朋友时,我们常常会冒出上面这些疑惑和紧张:对方这么信任我,我好怕说错话!
在这里我们提供一些谈话的指南。
当你不知道如何开口,可以考虑这3句:
“我相信你。”
“这不是你的错。”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因为相信,承认,就是与ta站在一起的表现。
1)听就好了,多关注对方在说什么。因为“不听”的人比你想象中多,甚至可能没有人真正在听。
在性暴力事件中,幸存者常常难以证明对方所做的事。因此ta们常常是被“不信”和“质疑”的那一方。“你凭一张嘴就是证据?”
或者被开玩笑:“男的即使被性侵,也是占便宜的那方”。
一些性骚扰新闻下的热评,这就是人们对于性暴力幸存者看法的最普遍的真相。
2)承认痛苦,但不要假设他们的感受。可以问问ta真正的感受是什么。
一些有关ta的问题可以让人感觉到,你在听。
许多性暴力幸存者都会经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导致焦虑、抑郁、睡眠困难、干扰性思维,影响日常生活。
但每个幸存者对痛苦的应对方式是不同的。不要把ta们的痛苦夸大,或者想当然地说:“那你现在好了吧”?
3)不要问太多问题,尤其是可能有攻击性的问题。
比如:“你喝酒了吗?”“你拒绝了吗?”“你为什么去他的房间?”“你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才谈?”,这些问题在暗示ta也有错。
4)告诉ta,能讲出来是很勇敢的行为,你有很强大的力量。
但这不意味着不分享的人很懦弱。何时进行自我表露,表露到什么地步,出于什么原因进行表露,都该是幸存者本人全权掌握的。
图/Vox
5)告诉ta,这不是你的错。
在当下,“受害者有罪论”依然十分盛行。
“仙人跳?”、“你确定ta没在勾引吗?”“ta也得到了好处啊”、“ta平时看起来就很不检点”、“ta并没有完全拒绝,甚至在过程中出现了生理反应”——因此受害者常常怀疑是自己的某些方面导致了受害(比如穿得太少)。
6)不要逼ta好起来,因为性暴力的治疗不是线性的,疗愈没有确切时间。
避免说一些暗示ta们需要好起来的话。比如“你已经自暴自弃多久了?”、“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才会好?”
7)表达愤怒或悲伤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也是有感情的人。
8)不要因为帮不上忙而自责。而是进行自我关怀、自我同情。
听朋友诉说自己的创伤,也是一件痛苦的事。
作为倾听者,我们也要练习自我照顾,设定合理的界限。
如果你不能应付ta的情况,可以问ta,是否需要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图/BBC
“你不是一个人”是种强大的感觉。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叙事,当我们自己的故事被另一个相似的人听到,就会产生“联结的力量”。
哈佛大学博士、布朗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周韵认为,Metoo的本质是一种赋权行为。
“这么多人站出来,其实是把重新定义什么是我能接受的性、亲密关系、感情关系、相处模式的定义权和主动权,交给了每个人自己。”
许多陷入痛苦的人,都被一种疯狂的想法所折磨:我是孤独的,没有人站在我这边。
如果你在有生之年不得不遭遇了性暴力,我们希望你知道:我们看到你了。我们听到了。我们相信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