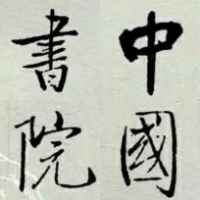书名:岳麓书院史
作者:朱汉民、邓洪波
出版社:湖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01
中日甲午战争,湘军败于辽东半岛的日军枪炮之下,中国败于取法西方的日本,泱泱大国仅存的半点矜持也被东邻小国剥夺殆尽,亡国灭种的危机赤祼祼地摆到了每个中国人面前。这给“中兴将相”之邦的三湘大地震动极大,素有湖湘人才渊源的岳麓书院更是理所当然地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痛定思痛的湘中士绅一改住日保守,而趋于维新,成为戊戌运动的先驱和大本营。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五十三岁的王先谦受湖南巡抚吴大澂之聘,由城南书院山长转任岳麓书院山长,接替八十四岁的徐棻,带领称名最古的岳麓,开启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近代化征程。
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
因宅名葵园,学人称为葵园先生。
应该说,教育改革是湖南新政的先导,也是整个新政中最有成效的部分。新政之前,院长王先谦凭着主管全国(国子监祭酒)及地方(江苏学政)教育练就的职业敏感,以大学者和名乡绅的双重身份,勇于担当,成为新政的首倡者和积极参与者,并带领岳麓书院加入到改革的行列,使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校经书院、时务学堂一起,成为推动改革的三大引擎,实为湖南新政的排头兵。
岳麓书院的改革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开始,二十三年达到高潮,二十四年因陷入与时务学堂的争斗而停滞,谨叙述如下。
订购《时务报》
岳麓书院的第一项改革措施是,王先谦山长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月发布手谕,订购《时务报》令诸生阅读,以“广开见闻,启发意志”,为改革作思想准备。这是将称名最古的书院引向近代的大动作,意义非同小可。
《时务报》
王院长手谕有两点需引起特别注意:
首先是订阅《时务报》的理由,既本于读书致用的通则,源自“强邻逼处,列国纷乘,脧我胎膏”,“国将不国”的严酷现实,《时务报》“议论精审,体裁雅饬”,且随录“谕旨暨奏疏、西报,尤切要者,洵足开广见闻,启发志意,为目前不可不看之书”。更寄希望于忠义之乡的湖南、英贤所萃的书院,祈院中诸生临危而变,“开拓心胸”“开广见闻”,“发愤而作”,以“备国家栋梁之用”。
其次,购《时务极》以解放思想是由岳麓书院牵头,与城南、求忠二书院联合行动的,既彰显省会书院改革的态度、决心,是一种策略,也反映出王院长的影响力与领导力非同一般,鼓动创于宋代的城南、湘军新贵大本营的求忠同时改革,实非易事。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年十二月由王院长领衔呈报创建时务学堂,以培养学通中外体用兼备的人才。次年正月,也即在王院长之后两个多月,湖南巡抚陈宝箴也发布《购〈时务报〉发给全省各书院札》,将关心时务之风由岳麓书院吹向各府州县书院。湖湘学人通过看报,周知本国与西方各国之事,识时务,开风气,解决了认识与思想问题。于是,“恶谈西艺”的风气得以改变,近代化改革的基础得以奠定。
整肃清厘
岳麓书院的第二项改革措施是,以整顿反对德国人来湘,“藉端滋闹”之事为契机,整肃清厘,开除“桀骜喜事”学生十余人,酌定章程五条,预为改革作出制度保证。
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月,“德国谔尔福来湘,岳麓书院多人藉端滋闹”。先是宁乡文姓廪生“倡首鼓众到省城藩署鼓躁”,回到书院后,“犹立讲堂之上,对众宣扬与藩宪抗论情形,自鸣得意”,“举动猖狂”。此所谓借反对外国人来湘,“纠众生事,哄塞藩署”,引起巡抚陈宝箴“盛怒”,严令追查。王院长遂“藉手”“整饬”,除“详革解究”带头闹事的文、曾两生外,“并访得桀骜喜事者十数人,陆续驱逐”,又开除了“吸食洋烟”的学生周莲翁,及冒名顶替者多人,态度强硬。
同时又发布文告,指出“院中风气迥不如前”,大谈“父庇不才之子,其家必出凶人;师容不率之徒,其塾必无良士”的道理,强指“从来遇事生风,最为书院恶习”。实际上是对当年反德国人入湘的学生运动进行坚决镇压。这自然招致学生反对,在三月份的馆课考试时,有居住道乡祠的学生刘安斌借“其为人也孝悌”之题,“解上为庠序师,谓为师者为人果能孝悌,则犯之者自鲜”,“强书就我”,“倒置文法”,“反复申明”,攻击院长,“以快其讥讪之私”。结果以“险诈居心”,“明目张胆,毫无忌惮之徒”而遭到“移学注劣”的严惩。
总之,光绪二十三年二至三月的学潮,以岳麓书院学生反对德国人谔尔福来湘开始,以开除学生十余人,“酌定章程”五条规范诸生行为结束,实际上向“恶谈西艺独烈”的湖南士绅明确宣示,称名最古的岳麓书院要向西方敞开胸怀,迈开近代化步伐了,且“虽身障狂澜,所勿恤也”。严惩生徒、立法清查、酌定章程,意皆为近代化改革扫清障碍,它之强硬推动实与前此购阅《时务报》的柔性宣示形成组合力量,仍属改革的铺垫性工作。
发布《月课改章手谕》
岳麓书院的第三项改革措施是发布《岳麓书院月课改章手谕》,引入西学课程,全面实施涉及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设施,以及有关招生、考试、师资等方面的近代化进程。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一日(1897年7月10日),王先谦的《岳麓书院月课改章手谕》发表于《湘学新报》第九册,是为其全面改革的总方案。
通读该手谕,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是改章源自礼部,侍讲学士秦绶章奏请整顿各省书院一折所提方案是其改革模版,变通书院章程以应社会需要,即扩旧规以收实效是其主要精神。此所谓渊源有自,改章乃遵照朝廷指示进行。
二是岳麓改章依朝廷方案而作变通,月课分为经、史、掌故、算、译五门,前三门,院长亲自督课,算学别立斋长,译学延请教习。算、译二学课额分为别五十名、四十名,学制均为三年。
三是强调屏除意见,启牖灵明,以通时务而归于务实为改章目的,坚决反对“言词章者谓考据害性灵,讲训诂者轻文人为浅陋,理学兴则朱陆争,朴学兴则汉宋争,地球通则中学与西学又争”的不良学风,对“终朝饱食,口舌纷纭”,“逞其簧鼓”的浮嚣、空疏士习深表忧虑。
《湘报》
应该说,岳麓改章是一个“仿西学式”的改革,它涉及到教学内容、组织形式与办学体制等深层次的问题,对岳麓对全省书院的改革皆有重大意义。据《湘报》48号、49号记载,次年闰三月,城南书院官课“以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致、考工六门命题”课士,求忠书院则“改课经学、艺学、译学、律学、杂学、商学、兵学、算学八门,另聘教习,别类讲解,按月出题课试”。
可见,开风气之先的岳麓书院,对省城书院的改革,有着某种引领与启导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在经史一统的旧天下,开辟出算学、译学的新路径,其功甚伟。今日湖南大学的数学学院、外语学院,应该以每年的7月10日为院庆日,并赓续先辈开风气之先的优良传统,自豪自信,为千年学府的走向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发布《岳麓书院新定译学会课程》
岳麓书院的第四项改革措施是发布《岳麓书院新定译学会课程》,时在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1897年7月20日),距改章手谕发表仅十天,可见其改革力度相当大。《课程》由岳麓书院的译学教习制订,共十四条,实为难得一见的百余年前的外语教学原始文献。
《岳麓书院新定译学会课程》全文
这个《课程》是当年的外语教育工作者制订的,可谓出自行家,颇能反映当时外语教学规律的认识水平。这里至少有五点应该引起注意:
一是英语和英文的区别,说明当时已将语言和文字分得很清楚。
二是课程的设置,所谓拼法、写字、杂字、杂语、作句、作论、写信、文法、口述、笔录、翻译,共计有十一门之多,涉及语音、语法、词汇、写作、口语、听说、翻译等差不多现代外语教学的各个方面,其起点程度之高令人惊讶。
三是对语言教学循序渐进规律的认识,这从第一条“书课”所设计的三年课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
四是不论课堂内外,师生问答都要用“英语”,强调语言环境的营造。
五是限额招生,每班只许四十人,这相对算学每班五十人来讲,可以说是小班教学,而且从其“额外不得增加一人”的规定中,我们更加可以认定,百余年以前的外语老师已经意识到了必须让学生在课堂上获得尽量多的练习机会,符合语言教学,尤其是非母语教学的规律。
岳麓书院实施外国语言文字教学的意义,因限于资料还不能作比较全面而审慎的评说,但至少有三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在中国“称名最古”的书院中授受外语,本身就是书院开始近代化的标志,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反过来又为这种交流的深入,尤其是中国人了解世界、走向世界作出了贡献。
第二,引入了诸如分科分班、百分制、按钟点上下课、交费上学、学习限期、毕业文凭等一些西方教育的概念与办法,有功于书院乃至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而这些则从一个侧面再次证明,书院凭着其千余年发展的根基,得以拥有因循时代,融通中外的博大胸怀,可以满足中国士人不断变化发展的文化需求。
第三,作为千年学府湖南大学的第一源头的岳麓书院的外语教育,是她从古代走向近代的坚实轨迹,那种无视书院教育转型,而人为地割断中国教育历史,尤其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的做法,有违客观事实,是不可取的。
岳麓书院《月课改章手谕》的颁发和《新定译学会课程》的制定,为古老的千年书院注入了新鲜空气,标志着中国称名最古的书院已经实实在在地迈上近代化的改革之路。这一年十一月,时务学堂开学,梁启超登坛讲授。其时,岳麓书院已开办译、算教学四个月,并为适应新教学内容而“别造房屋两间”,完成了近代化教学设施的改造。
收藏新学、西书
岳麓书院的第五项改革措施是收藏新学、西书,以满足院中诸生“发皇耳目,开拓心胸”,即更新知识的需求。与改章月课不同,置备西学新书要延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才进行,这与前此订购《时务报》以开广见闻之精神不协,不知原因何在。
《西艺知新卷》
(书名列于《捐助岳麓书院书籍题名》)
因而在南学会遭长沙周启明的质疑,其称:
■
“广储书籍,始足以开风气而拓见闻。岳麓所藏,仅有中书,多不适用,人领数卷,岂足以发皇耳目开拓心胸?宜置书数千金以供文人博览。或谓子言诚是,其如财力支绌何?余谓上台之加意湖南至矣。校经学会、时务学堂之举,动辄逾万,且系常款,尤优为之,何有于是,且岁修局素有盈余,如得抚宪札饬,岂不足办?并劝绅士捐之,数千金书可立致也。此书院之宜整顿者四也。”
这说明,院中“仅有中书”已不能满足因阅《时务报》而洞开的新学需求。面对质疑,当时的回答是:
■
“岳、城、求三书院现无西学书籍,应即置备,以公同好。去岁,原任上海道刘观察麒祥、江苏补用道蒋观察德钧、翰林院庶吉士熊太史希龄三人,集赀购到制造局所译西书,共二十四箱,每箱壹百二十种,每府书院捐置一箱,现在常、衡、□、□均已领去,惟岳、城、求尚无人来取。倘有愿领者,可向王祭酒转询熊庶常给发可也。”
时在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二日。不久,蒋德钧、刘麒祥、熊希龄所捐新学书籍入藏御书楼,从闰三月二十六日开始,《湘报》在第61号、65号、69号、70号,以《捐助岳麓书院书籍题名》为题,连续刊载一百二十种西学书目,让人知晓借阅。此举适时满足了人们开拓心胸、吸收新知的愿望,为改革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与文献保证。
综上所述,岳麓书院一直走在改革的前列,并推动着时务学堂创立,而且其改革在经世致用、通晓时务物理的固有传统导引之下,遵循着轻科举、重实用的逻辑向前推进,也深入到教育深层次问题,可喜可贺。惜乎!时务学堂开学不久,王院长卷入与梁启超的民权平等问题的论争,教育让位于政治,改革差不多停顿。
*本文整理自朱汉民、邓洪波《岳麓书院史》,文章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