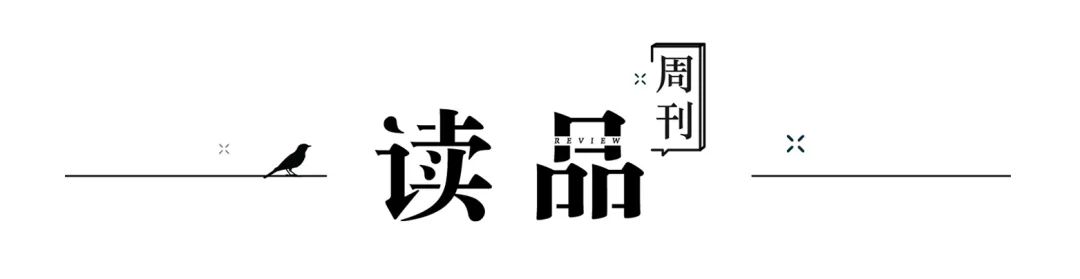
在巨大的社会变迁中,是什么决定着普通人的命运?
最近,豆瓣新书榜上的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张医生与王医生》引发了网友和读者的热议。有人隔空和书中的人物产生了情感联结,有人借此反思时代、环境和家庭对自我的影响,有人趁着“东北文艺复兴”的余温,再次审视这片广阔而神秘的土地……
本书的作者伊险峰和杨樱,是两位独辟蹊径的媒体人。2008年,伊险峰创办了《第一财经周刊》,这也是杨樱记者和编辑职业的生涯起点。在新闻报道之外,他们也寻求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张医生与王医生》是二人进行长篇非虚构文学创作的起点。这本书的写作契机,源于两位作者对中国四十年来社会变化的兴趣,“这变化快且剧烈,总需要一个来龙去脉”。
张医生与王医生是伊险峰的初中同学,他们都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沈阳工人家庭。两位作者认为,这代人是流动性最强、人生积极、机遇完好,并且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完成身份转换的一代人。而他们生活的城市沈阳,在这个过程中处境复杂。
一座失落的城,两个逆势上升的人,这之间会产生怎样的张力?我们究竟能在两位成功的东北医生身上看见什么?
姜斯佳 / 文
沈阳老工业区的变迁
在讲述张医生与王医生的故事之前,必须要先介绍隐藏在本书中的另一个主角——沈阳城。
满清前期,沈阳经历了快速发展,从小城市快步迈入大城市。日占时期沈阳形成了工业基础,新中国建立后又经历了一次大的发展,此前从皇姑区碧潭公园到和平区中山公园之间的大面积荒野变成了繁华市区。三次大发展都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
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为了适应市场经济,沈阳不得不从一个工业城市向去工业化的消费型现代化城市转型。
沈阳的中心市区之一,过去繁荣的老工业区铁西区,到了2002年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为了救活濒临破产的铁西区,沈阳市政府决定将铁西区老工业基地与国家级开发区——张士开发区合并,130多家大中型企业搬迁,大部分厂房被拆除或置换成了符合城市“士绅化”标准的“ABC”(艺术画廊Art Galleries、精品店Boutiques和咖啡馆Cafes),过去沈阳铸造厂的旧厂房被保留下来,改建为中国沈阳工业博物馆,默默诉说着旧时代的辉煌。
相较于废弃的建筑物,被舍弃的人的命运往往掩埋得更深。张医生与王医生的父辈们,在时代的大变迁面前,命运似乎微如尘埃。
2001年,媒体人李海鹏在《经济观察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长日孤独的城市——沈阳人的性格、文化、生活和希望》的文章,用解剖刀一般犀利的语言概述了当时沈阳人的状态:“曾经在生意场上嘲笑广东人抠门的沈阳人一觉醒来,发觉世界已经陌生。他们为脱离时代的价值观,或者更本质地说,为了豪爽、自大、懒散、仗义的性格而付出了代价。”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沈阳被比喻为一杯无法对外界刺激作出“正确反应”的“白开水”:“如果一袋茶投入到一杯开水中,开水必然会渐渐变色,但沈阳的问题是,水已经开了,但还是白的。”身为沈阳人的李海鹏把希望寄托于未来新一代“年轻人”:“年轻人是城市的希望,那袋茶悬在杯子上方,现在他们准备让它落下来。既然他们不能忍受不时髦,需要一点波澜、一点味道、一点变化,既然他们大多数只能坐在沈阳这个板凳上,那么他们就得想想办法,得体地走进已迟到了的21世纪。”
《张医生与王医生》
伊险峰 杨樱 著
文汇出版社
逆势上升的“奖学金男孩”
《张医生与王医生》的主角张晓刚与王平,便是当年李海鹏文中“坐在沈阳这个板凳上”的新一代年轻人。在东北四十年来去工业化的社会震荡中,他们凭借家庭的支持,从小就成为“奖学金男孩”,在超过三十年的奋斗中摆脱了被社会淘汰的命运。
正如书中对张晓刚父母终生成就的概括:“他们用微薄的力量、充沛的精力、智慧和爱,让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跟了上来,不但没有掉队,而且逆势上升。他们带着三个孩子实现了跃迁,进入到富裕且专业的群体之中,与90年代那个迷茫困顿、看不到出路的沈阳截然不同。”但他们从中感受到的幸福、欣慰,还不如庆幸多,又不得不伴随着疲惫和怀疑。
两位主人公的母亲,一位以身段灵活见长,一位以勤奋自律为荣,都具备现实的野心和势利的远见,她们希望通过精心培养,让孩子成为“奖学金男孩”,以避免重复父辈们的不幸命运。张晓刚的母亲杨淑霞为此制订了严格的计划:第一步,“奖学金男孩”的上升之路必须与普通的日常生活分割开来,扑克、麻将在家里是被严格禁止的,学习不好的孩子不被允许进入张晓刚家的家门;第二步,要跟贫困生活做个切割,在家中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全力投资教育需要一点远见,这不只表现在对教育时间的总体投入,也包括对子女尽可能的经济支持,张晓刚想学吉他,杨淑霞毫不犹豫掏了四十二块钱,哥哥想学摄影,一百五十块钱买相机,还有游泳,集邮……这种支持并非以功利性为前提,而是一种出人头地的寄托和希求。
王平医生的母亲曾慕芝,则通过1004张电影票改变了王平的人生轨迹。电视没出现之前,看电影是当时的沈阳人最热衷的娱乐方式,曾慕芝通过卖电影票获得了很多人脉资源。在当时的民间社会中,有关系、会搞关系是一种能耐。王平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曾慕芝通过卖电影票认识的“懂行”的人,获得了儿子报志愿的最优解——医大七年制本硕连读。王平提及母亲时,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相对于家中更有“用处”也更具能量的母亲们,两位父亲的形象则要脆弱和模糊得多,或因循本分,或沉迷阅读,显然没能称职地完成“何为男子气概”的言传身教。父亲权威的缺席,为王医生和张医生这新一代沈阳人后来的命运转折埋下了伏笔。作为当年优秀的“奖学金男孩”,尖子生的求学经历和专业的技术背景并不能保证他们进入社会后如鱼得水;恰恰相反,早年“奖学金男孩”被要求的某些品质,以及成长期间缺乏父亲们足够的影响力,让他们在后来的“社会化”过程中信心、能力和技巧等方面都显得先天不足。
40多岁,还学不会“社会”
“我们的生活变好了,为什么精神却荒芜了?”在社会巨大的变革之下,两个成功的医生也感到相当的疲惫和困惑,东北沈阳这座城市仍在不断塑造、摧折他们。
李海鹏在本书的序言中指出:“本书所写的两位医生的故事,倘若严厉地说,大致就是这样。他们的‘成熟’始于人生发轫时期与社会潜规则碰撞导致的心理创伤,止于一种悲剧性与喜剧性参半的尴尬状态”。
似乎,所谓“社会”对男人的要求更类似于“微型军阀”——成功男人必须在各种社会联盟和资源之间游刃有余;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奖学金男孩”们从小被灌输的那种凭着专业真本事吃硬饭、不喜欢玩弄政治技巧的男性气概,恰恰是一种要不得的累赘,甚至是一种注定会诱发失败的致命性格缺陷。
书中记录,王平医生多次说“要是会来事儿的话,这个东西就解决了”。“会来事儿”在他眼中是表露乖巧和体贴的“妾妇之道”,是一种基本的社会技巧,其要点恰恰在于违背男性气概,因而他拒绝掌握。
最终,两位医生都成了不情不愿的荷花式的人物,有的部分出淤泥而不染,有的部分染,有的部分想染却染不上。他们的社会身份走向专业人才的舞台,精神世界却留在童年小屋里。
在故事的结尾,王医生考虑到女儿的将来,下定决心以后要更“社会”一点,因为女儿大学毕业,他作为父亲需要为下一代走上“社会”之路准备更多的社会资源,开始关注他在“好大夫”网上的各种人脉资源;至于张医生,自从太太去了加拿大独自闯荡,他也已经意识到以后“不能独自进晚餐”,要时刻提醒自己“融入社会”。
“无论是犬儒的、男子气概的、波希米亚的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究其根本,也是尊严、价值和情感的表现,其情可悯。”这是李海鹏对书中所有沈阳人精神世界的概括,又何尝不是当代人正在经历的一种罗网式的人生体验?
延伸阅读
《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个墨西哥家庭的自传》
[美]奥斯卡·刘易斯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本书讲述了墨西哥城一个家庭的故事,目的是向读者们呈现,在经历社会和经济巨变的拉美大城市中心区的贫民窟,住在一居室的出租屋里长大成人到底是怎样一番景象。奥斯卡·刘易斯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方法,让读者对一个普通家庭进行更深层次的查看,每一个家庭成员会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讲述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历。这种多人自传体的方法也易于减少调查者的偏见,并同时为读者带来情感上的满足和理解。因为人类学家在直接和受访对象接触时能够体会到这样的满足和理解,可在充斥了专业术语的人类学专著中却很少传递出来。
《识字的用途》
[英]理查德·霍加特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当一个社会变得更富裕时,它会失去其他价值吗?教育和识字能力使数百万人浪费在消费流行文化上吗?媒体是否强迫我们进入表象和物质的世界,抑或这一切都充盈美好?本书提出这些问题时,英国正在经历20世纪中期巨大的社会变革,然而作者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今天却没有失去其针对性和力量。作者对英格兰北部消失的工人阶级社区的价值观提供了迷人的洞见,并将其与他对带有强烈影响力的美国大众文化的看法一起编织。本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文化研究领域。
视觉中国供图
编辑:张垚仟
© copyright 读品周刊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请给我们留言,获取内容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