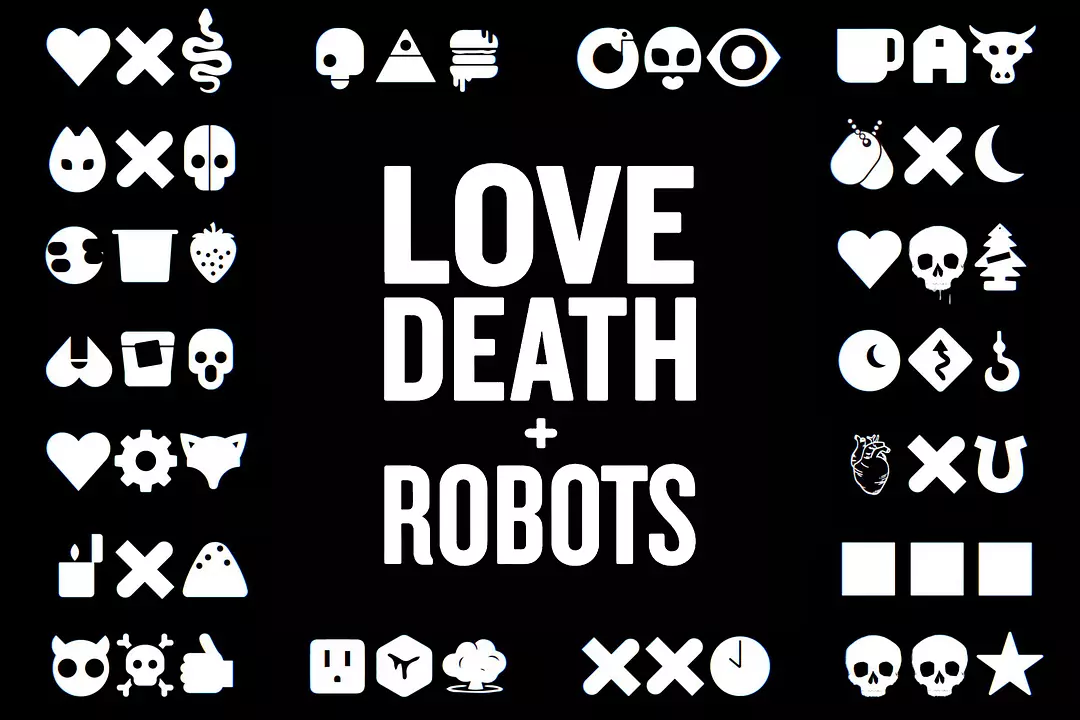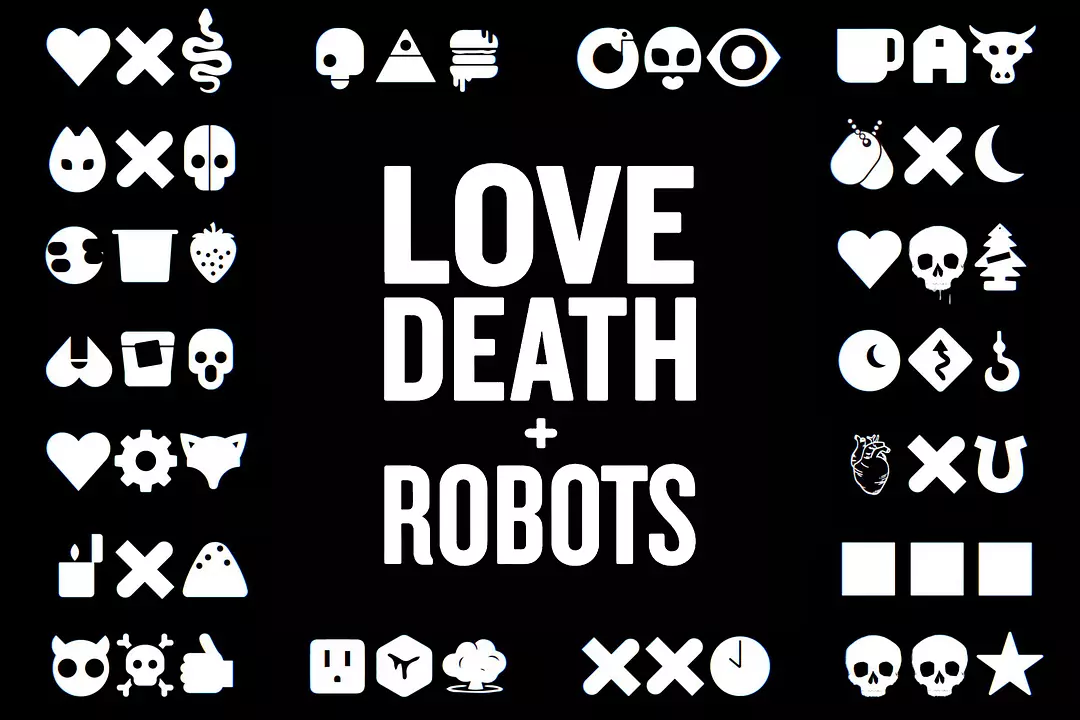
撰文/千江记(此账号为凤凰网校园KOL)
导言:《黑镜》编剧查理·布鲁克曾对“黑镜”这一命名进行了阐释:“‘黑镜’是无处不在的,它出现在墙上、桌子上、每个人的手掌上;冰冷的闪着光的电视上、显示器上、手机上。电子设备关闭之后,屏幕黯淡,就像一面面黑色镜子,你看到的,是自己。”从这个寓意出发,我们身处在一个“黑镜”时代,“黑镜”以电子信息科技为内核,在其光滑如镜的表面上反射出未来社会的影像。《银翼杀手》、《攻壳机动队》、《黑镜》等系列作品都对这一未来图景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描摹,“科幻漫谈系列”栏目便注目于此类现代性科幻寓言进行阐述。
♣ ♣ ♣
那么,我们不妨就从近日大热的《爱,死亡和机器人》(Love,Death and Roberts)聊起。
这部18集动画短剧由Netflix出品,凭借短小精悍的篇幅、高度浓缩的剧情和诡美冷冽的画风,引发一股浪潮,IMDb评分高达9.2,豆瓣评分更是直逼9.3。
其中第一集《桑尼的优势》(Sonnie’s Edge)与第八集《狩猎愉快》(Good hunting)有类似之处,二者都隐含着女性主义内核,并通过科技对自身的改造实现了女性的权利与公平。在对女性主义的张扬中,镶嵌着对“意志”与“身体”关系问题的探讨。
这一探讨其实并不新颖。早在1995年诞生的《攻壳机动队》(Ghost in the shell)便已将这个议题拆解到了极致,而《爱,死亡和机器人》的优点便在于精华的浓缩,只撷取最关键的部分,短小精悍,点到为止,毫无赘余,却引人联想,触发思绪。因而不妨将《攻壳机动队》系列与《狩猎愉快》《桑尼的优势》放在一处,进行对照。
①
20世纪60年代,“赛博格”一词最初由美国航天局科学家曼菲德·克莱恩斯和内森·克莱思提出,他们意图利用科学技术来提高宇航员与太空工作者的身体性能,以适应地球外的严酷环境。赛博格可以被看作是经过自动化手段改造的生物体,是生物和技术结合的产物。
80年代,堂娜·哈拉维扩充了这一概念,将“赛博格”定义为“一个控制有机体,一个机器与生物的杂合体,一个社会现实的创造物,同时也是一个虚构的创造物”,落脚于文化领域,意图借此来跨越一切身份认同的矛盾与障碍。在人与机器的杂糅与交感之下,未来的人类形象将接受全新的定义。
在《桑尼的优势》中,桑尼在被伤害之后,不得已抛弃了人类肉体,灵肉分离,将意识植入怪兽体内,获得了一个更为强健有力的意识载体,但同时她无法离开怪兽的身体。斗兽场上的失败意味着肉身的死去,因而桑尼借助内心关于毁灭的恐惧,一次次获胜。
《狩猎愉快》中的妖狐燕从兽的心理意识过渡为人,后被改装为义体人形态,在机械师梁的帮助下,以机械的形式恢复了兽形,燕重新生出九尾,被科技二度摧毁的燕,最终利用科技完成了复仇。在这部短片中,机械和科技取代了天地灵气,成为一种新的魔法,未来时空的机械造神理念达到了与上古时代的万物有灵论相并举的程度。
二者主动或被迫运用机械和科技维系着自身存在,并在此基础上,以科技为武器,继而谋求权利与公平,以实现一种更好的生存状态,而这正是现代人类运用科技所做的事情。
而她们的共同之处也在于她们都无法抛弃自己的外在形体。
同样作为完全形态的义体人,日本导演押井守的科幻题材动画影片《攻壳机动队》中的女主人公草薙素子通过对形体的毁灭和抛弃,实现了一种精神形态的永在。
这部作品的时空设定为2029年的未来世界,全身“义体化”的主人公草薙素子在追捕科技罪犯的过程中,生发了对“自我“命题的疑惑和思考。除了脑组织外,素子全身上下无不是人工材料制成,如同一段被困在躯壳之中的灵魂,而她的罪犯黑客“傀儡师”则与之相反,是一段自称为生命体的具有自我意识和思维能力的变异程序,没有躯体的束缚。
在《攻壳机动队》的第二部《无罪》中,巴特和同事在追踪黑客的过程中在寺庙的墙上看到了这样一句话:“生死去来,棚头傀儡,一线断时,落落磊磊”。
这句话出自世阿弥的能剧《花鏡》,大致可译为:人活一世,死灭之时,就如同棚车上的木偶线断裂了,维系身体之线(即灵魂)断裂时,肉体也随之飘荡零落,归于虚无。旨在说明灵魂之于身体的重要意义,而用在影片中,却指向了相反的意涵:肉身零落之时,灵魂才可自在飞升。
从古希腊哲学开始,人们便持有将身体与灵魂分隔开来的观点,苏格拉底认为身体是“圈养和囚禁灵魂的地方”,肉体消失之后灵魂依旧可以独立存在。
柏拉图继承了这一观点,认为身体是阻碍灵魂获得真理与知识的障碍,死亡为灵魂打开了身体枷锁。身心二元论显出雏形,在笛卡尔那里正式提出“身心二元论”观点,建立在“我思故我在”的思想基础之上,怀疑思维印证了人的真实存在,具有心灵、能够思维的实体是为人之本,心灵可以不依托肉体而独立存在。
素子在同思想战车的战役中撕裂了双臂,外部肌肉与内嵌的钢筋铁臂绞扭在一起迸溅来开,与那句“一线断时,落落磊磊”遥相呼应,素子打碎了躯体外壳,与傀儡师结合,灵魂得以从身体容器之中解放,获得自由,在毁灭中得以重生。通过抛弃肉体的形式实现了精神意志的永存。
②
若说《桑尼的优势》的主题之一是机械和科技使人类意识得以存续,那么《狩猎愉快》讲述的则是机械科技束缚了人,同时又塑造了人。二者囿于表达时长的限制和创作者的主观思想倾向,未能再前进一步,其探讨仅仅徘徊于科技兴废的层面。而在《攻壳机动队》中,导演完成了一则未来时空下的人类精神困境的寓言,即在AI与人体仿真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精神困境,即对自我的怀疑和界定。
这一思考与古老的“特修斯之船”命题相近:如果一艘船在航行之中渐渐更换了所有的零件,因此得以航行数百年,那它是否还是原来那艘船?如果一个人将身体内的所有器官更换为电子元件和义肢,那该如何界定此人的身份,亦或此人是否还可称之为“人”?既然人的肉体能够机械合成,大脑与电子信息网络相连接,记忆可以植入或移除,灵魂也可从信息海洋之中孕育而生,又该如何划定人与非人的界限?
在萨特看来,物的本质是先天规定、一成不变的,所以物的存在是“本质先于存在”,而人的则是“自为的存在”。
人的本质处于一种波动之中,通过个体的自由选择和实际行动进行着塑造和改变。相较于物,人具有永不止息的超越性,这种超越性产生于人对自由的追逐和个体意识的张扬中。
素子是被人类塑造生成的,是科技的造物,而她奋不顾身追求自由的姿态,是对人类肉体形态的彻底放弃,素子在自毁行为中不仅实现了意识的解放,而且实现了从“完全状态的义体人”向具有精神向度的人的跨越。
③
值得一提的还有这几部作品呈现出的赛博朋克(Cyberpunk)风格,这一风格倾向于一种落魄的颓废美学,此类作品往往将荒凉破败的旧都市与高度发达的科技时代结合在一起,除了符合“赛博朋克”的反乌托邦的先定色彩之外,营造出了一种绮丽的反差,破旧而糜丽,触发了一种复杂而奇异的化学反应,形成了独特的美学。
香港九龙城寨便是承载这一情结的真实场域,逼仄通天的破旧楼宇,狭窄阴暗的街道,潮湿幽深的小巷,四通八达的楼中通路,充满了未来时空的折叠感,同时亦满足了西方世界对于东方神秘的想象与窥看,因而“香港九龙”成为了一个文化符码,在诸多科幻作品或游戏场景中不断粉墨登场。
《爱,死亡与机器人》系列的《见证》、《狩猎愉快》的故事发生地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中国香港:《见证》中高耸齐整的楼宇和破旧荒凉、空无一人的街道,身裹艳丽罩衣的浓妆女孩衣不蔽体地在街道上、楼梯间夺路奔逃;《狩猎愉快》中,香港的通天楼宇之上,几艘飞船来回穿梭,呈现出了风光颓靡的香港夜景,燕变身机械妖狐,伴月而行,末日般的狂欢气息至此终结。
《攻壳机动队》的电影场景同样设在香港九龙,除此之外,片中萦绕徐回着一种哀感意氛,存留着日本传统文化中的“物哀”之美。
叶渭渠将 “物哀”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因男女恋情而产生的哀感,第二层是感于世相,对人情世态的感慨,第三层是感于自然风物。
在片中“物哀”情致主要是感于世相,体现为对苍凉陈旧都市群像的空镜描绘:繁丽的霓虹灯招牌,斑驳破旧的墙体,千篇一律的招贴广告,脏旧街道上行走在雨中的人们。而在《攻壳机动队》中空镜部分的配乐《傀儡谣》将这种哀感体现得淋漓尽致,愈加衬托着落寞都市的苍凉底色:
“若吾起舞时,美人亦迷醉;
若吾起舞时,皎月亦响鸣。
神降婚合夜,破晓虎鸫啼。
远神惠赐。远神惠赐。”
④
在此类影片中,高耸入云、寒光如刃的大厦与城中狭窄破败的街巷几乎形成了一组固定意象。而这不仅是一种风格取向,更是对现实以及未来的一重映射。
两种生活面貌有云泥之差,而显现在同一时代,在这一高一低之中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科技高扬,文明落魄,呈现出一种参差的错落之感。
正如现代性作品对现代化社会的抵抗,科幻作品的内核,实则都是反科学的。
现代文明中,技术与人类之间呈现出了极其复杂的关系,在科技的支撑之下人的生命得到延长和丰富,甚至有人设想可通过克隆、记忆上传等方式实现永生,但另一方面,人逐渐异化了自身,甚至成为技术的附庸。
人们追求理性、科技、真理,渴望对一切事物进行界定与控制,“赛博格”站立在后现代文化视域之中,对现代化提出了质疑和批判。如在《攻壳机动队》中低空飞翔的巨大飞机阴影,便象征着科技对人的压迫和逼视。
科技发展的速度犹如火箭升空,光与电子穿梭于万物之间,上帝已死,人们解除了精神规训,惊喜地发现自己拥有了作为造物主的能力,可以运用手中的工具,成为机器人的始祖,彻底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因而人类的精神层面出现真空,驾驶科技堕入深渊,因而直插云端的建筑群无声耸立在废墟之城。
科技造福着人们,造就着人们,同时又囚禁着人们。
素子虽是现代科技文明的造物,但她对造就自身的文明怀着一种游离和审视,试图从科技铸就的躯体中抽离出来。在人类战胜了死亡、跻身造物主行列的时候,需要有人不断躬身自照,思索人的本质及本源,人何以为人。
戴锦华在一则演讲中说道:“当这些(科幻)故事被想象、被讲述、被构造的时候,它们都是作为预警、梦靥而出现的。”
包括《爱,死亡和机器人》、《攻壳机动队》系列在内的科幻故事,便是这样一块反射未来景象的“黑镜”,不乏想象和迷思,是一则则具有启示性的精妙寓言。
一代又一代人,无不在踮着脚尖,审慎而警惕地眺望未来。
(本文为凤凰网大风号校园KOL作品,未经授权,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