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艺术》(Chinese Art)是西方早期研究中国艺术的重要文献,1958年在纽约出版,上下两卷。作者William Willetts(魏礼泽)(汉学家、西方艺术史家)从中国的地理特色着手,系统梳理了玉器、青铜器、漆器、丝绸、雕塑、陶瓷、绘画、书法、建筑等中国艺术的各个门类。他坚持客观描述作品的方法,“并不对所讨论器物给予美学价值论断,而是让器物自己说话”。
“让器物自己说话”,与观复博物馆“以物证史”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我们选择翻译此书的原因。此次我们邀请到美国CCR(Chinese Cultural Relics《文物》英文版)翻译大奖获得者对此书进行正式专业的翻译,译者也是MLA(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国际索引数据库)和AATA(国际艺术品保护文献摘要)收录的美国出版期刊Chinese CulturalRelics的翻译团队成员。
本着尊重原著的原则,此次翻译将存疑处一一译出,其后附有译者注。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本书,在绚烂璀璨的器物中,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辉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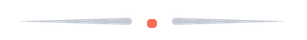
所有这类的山水画中,都使用了平远视角。山峰不再有高悬在我们头上的感觉;也不会从脚底下拔地而起穿过整个画面一直延伸到很远很高的地平线。山峰这时推到了平原的远处。当然,所要表现的自然地貌决定了采取哪种构图方式。Li Cheng和郭熙居住于黄河下游,这里的远山延伸在平原上,所以适合用平远方式表现。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藏的《黄河山谷秋日图》就可以比较肯定的确认为11世纪黄河这一派别的作品。
平远像高远一样,也被纳入了中国山水画的教科书。他在13世纪的山水画家,比如马远和夏圭的作品里面,被突出地应用。
画
我对这幅画的历史一无所知。但可以肯定的说,这幅画重现了郭熙艺术的主要特点。主题内容为冬季;画面表现了萧索的景象,和Toledo艺术博物馆的卷轴的冬季山水相同。后者也应该是郭熙作品。而且,两者的风格特征也类似。枯涩的树枝,中国人叫做蟹爪,我看起来更像是触须或者圣甲虫的腿,这种画法被认为是他的典型手法。其他特征包括短促、密集的笔触,表现的是灌木丛埋在雪里的样子,位于中景。而且远山的处理方式不是通过轮廓线,而是通过留白加上分水墨擦。这种技法可能是从花鸟画的没骨画法而来。
我们不能就此结束《冬林图》的讨论,应该还说一下松树林。因为这之后的山水画里面多有出现松树林,特别是元代画,直至后来变成了一种陈词滥调的存在。郭熙将此作为一种在“图像盒子”里构造相对深度感层次的方式。“如果数里之外的山峦还没有树那么大,则该山并不大”,他说。通过施加一种透视缩短的方法,松树林实际上将视线导向深处;这方面发挥的功能类似Claude Lorraine的风景画中前景中孤立树的作用。后者也是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的欧洲风景画中经常出现的,就像中国山水画常见松树一样。
中国艺术中出现的松树还有特别的一层意义。因为松树是坚韧和长寿的象征。正如Fitzgerald所说,它象征着学者-官员不畏霜雪,永葆正直的精神。所以郭熙认为,松树是自然地领导者,可以支撑藤蔓织物。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引申。发现木瘤植物也在中国山水画的前景中经常出现,这属于Clark所谓的“无意识中的点缀物”第二个例子。同样的想法在欧洲的绘画和诗歌中也有,比如Altdorfer,Grunewald以及梵高的作品中,以及海涅的诗歌《Ein Fichtenbaum steht einsam》中也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