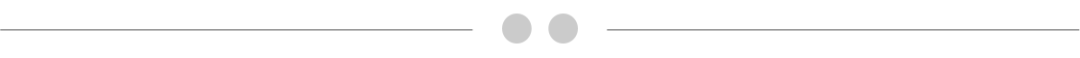2022年第五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初选名单公布在即,在公布之前,五位评委——梁永安、林白、刘铮、罗翔、王德威——和“报幕人”许子东一起在线上聊了聊对今年参选的67部作品的整体感受和对青年作家的期望。
在线上论坛中,有许多有趣的瞬间,我们整理出来放在文字回顾之前与大家分享。
🔈
01 梁永安老师自我介绍之后,许子东老师调侃他是“爱情专家”,梁永安老师一本正经地说:“文学里面有很多爱情主题。”
02 林白老师看到今年参选的作品,用了一句很美妙的话——“一下子冲到海面上,蹦得很高,我在水里看着他们好厉害,喷出很多气泡。”她还提前表达了对一些作品的喜爱,我们不得不做消音处理。
03 在文学一线工作很久的刘铮老师,说到今年的作品时,扮演了红脸的角色,但两个小时之后,他从悲观的批评变成乐观的祝福。
04 罗翔老师一直自称“门外汉”,他总“感觉好像又听到苏格拉底的嘲讽,你这个无知的人又在跨界发言”,许子东老师及时补上:“在座的只有你听到苏格拉底的声音,我们都没有听到(笑)。”
05 王德威老师不仅聊到了大陆的青年文学,还提到了台湾地区文学和马来西亚华语文学,与此同时他还注意到了南方文学的亮眼表现。
06 许子东老师担任过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评委,他以“过来人”的身份,友情提示各位评委,可能在未来评选中会出现争执:我们最后那次评委讨论吵得一塌糊涂,那次碰到像唐诺这样的人真是苦死了,跟他战斗。
01
本届作品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现象?
许子东 :请大家简单说说对本届作品的整体感受,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现象,以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跟海峡两岸、大中华地区其它文学奖比较,有什么不同?
梁永安 :这届作品和我的期待还是有非常大的共振。我们的文学在巨大的历史变化里,在很多方面是失声的、缺席的。发生变化的历史内核部分,有的阶层,比如那些背井离乡的打工者,表达的时候还没到。
所以我会有一个最深切的体验,中国现代文学失去了很多机会,比如乡村的声音并没有很好的呈现,我们的乡村是全世界最大的乡村,我们本来应该是写农民或者乡村小说最好的国家。我看这些作品的时候特别重视乡村这一块,这些失声者。很多写自己的乡愁、纠结,来到城市的种种心路,非常讲个人精神的微体验,用一个外在的逻辑、大的历史来解释自己,发声的这部分很多都在城市里。
我们的青年文学还是力求跟历来的文化或生命价值找到一种衔接,你可以感觉到背后有一种推力想去质问生存的种种问题。但总的来说,它的美学不是悲剧式的、英雄式的、毁灭式的,而是尽量在人伦里、在人的世界里去书写破碎,跟我们的传统还是有一定的勾连。
我总的感觉,代际的紧张感,这方面的书写还需要大大加强,现在90后、95后父母是农业社会最后一代人,新的一代青年是现代社会的第一代人,真正在历史的关口,这时候青年写作,代际关系是特别复杂的,怎么把它更好地写出来,不是表面的问题,而是深度的问题。
许子东 :梁永安教授提到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现代青年人写作当中的乡愁,一个是代际的紧张感。双雪涛的作品里写下岗工人,说离开工厂就是他的乡愁,就像农民离开土地一样,而且他的作品里面,的确像你说的,代际之间紧张,但不是毁灭,而是觉得自己的父辈被人欺负,作为儿子辈看不下去,而这种儿子辈看不下去父辈被人欺负,其实在苏童、贾平凹等很多作家里一直都有体现,而只是他们的作品里面父辈是被革命浪潮冲击。
青年作家跟前一代的关系,不仅是生活当中他们跟父辈的关系,还有他们跟前一辈作家的关系,到底是一种毁灭性的挑战,还是一种貌似挑战实际上还是在传承接受这种苦难的宿命,我只是正好有一个联想。
林白 :我以前没有那么集中地读过青年作家的作品,这一次集中看了个把月,戴着老花镜,觉得很厉害,让人振奋。一下子冲到海面上,蹦得很高,我在水里看着他们好厉害,喷出很多气泡,很激励的。
一包书打开,有的居然有900多页,两个手捧着才行,一个手拿不住,看了好吓人,非常烧脑,我从头到尾每一页都看了,体量庞大,综合性非常强,方志、通俗、族谱、口述史、词典、食谱、传说、巫术、诗歌......什么都有,纵横交错,我觉得是文体实验走到了一个高处,所以我认为它是最有叙事雄心的小说。
我没有学院知识分子这种话语体系,我就是老百姓的,按照烧脑和不烧脑区分。看这批作品也是有点累的,相当于每看一部就翻过一座山。总的来说很棒,肯定是比我年轻的时候写得好多了。
按长短分,这次可能长篇更多。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以前好像都是短篇集拿奖,一个文学奖那么有影响力,应该有长篇出来,结果这次有很多长篇来了,而且很棒。
有的小说用方言写作,我一边看一边用铅笔标注那些词,一看这个词很熟悉,我小时候用过的,但是这三十多年我已经完全忘记了,这些词从茫茫黑暗中冒出来,TA在地,我不在地,语言铿锵有力,有广阔的视野、海洋气息,也有很强烈的诗性,光色、水色都是很好的,讲述的方式、语言想象力。还有一部写未来的事情,又是未来,又是现代,他很有想象力,这个想象力不是漂的,不是玄虚的,它是下沉的,这个作者有很强劲的哲学思考。
当这个评委原来觉得压力很大,是一个有负担的东西,但是阅读到好的作品,自己觉得很有收获。
许子东 :以我的经验告诉你们,我们最后那次评委讨论吵得一塌糊涂,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看法,最后真的完全是靠选票,而且不单是你投一个人,你还要投其他人,哪怕是放到第二、第三,都会影响到TA最后的总分,所以这是这个奖可爱的地方,它真的就是你们五个人最后决定,我那次碰到像唐诺这样的人真是苦死了,跟他战斗。
刘铮 :由于我在一线工作比较久,所以我决定不说很多好话,想从否定的角度上来谈我的一些观察,来讲一些我认为这些作品缺少的东西。
第一,我以前读过夏志清先生一篇文章,印象很深,叫做《现代中国感时忧国的精神》,这篇文章里面举的一些例子不是我们常会想到的现实主义文学,他甚至提到了沈从文写的《阿丽思中国游记》这样带有幻想性质的作品,但是他从文本中获取了作家潜藏在文本下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那种感受。我提这个文章的意图就是想说,今年看过这几十部作品,我感觉这里面基本上没有感时忧国的作品,这是我个人的感触。
第二个观察,刚才林白老师也提到一些作品,有炫学的写作手法、模仿西方现代主义的那种创作,但是我个人而言,现在的年轻人还没有达到知识分子写作的高度。我们回顾一下民国时期,作家不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他们自己的作品中,都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觉,把知识分子的思考融入到文学创作中来。我们这次评奖,参赛者最高年龄可以到45岁,很多作者已经接近中年了,三四十岁,如果是知识分子的话,这些特征应该体现出来了,炫学式的写作和知识分子式的写作中间有很大差别,知识分子所思考的事情不仅仅是作为装饰性出现的学问,而是那种真切的、与社会现实和世界发展的方向有一种共鸣,或者是在方向上有一种趋近。
第三个特点,我认为是没有讽刺调侃的作品,这个很耐人寻味,我们有过《围城》这样很经典的作品,为什么到了今天,在年轻人的作品里没看到讽刺和调侃?这跟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思想以及阅读的趣味有没有关系?
我暂时先提这三点,不是为青年人打气,而是希望从事文学的人,不管是青年,还是中年、老年,都去思考这个问题。
罗翔 :我确实只能发表一些门外汉的看法,非常非常主观。我经常能够感到一种虚无感和幻灭感,在这些作品中贯穿的一个主线,通常都是对一些周边经验的主观式的解读,但很少能够跳出这个经验做一些超验或者客观的追问。有的时候读完一本作品,心情会非常沉重和恍惚,但是又找不到一个出路,他也没有给你一个出路,也不试图给你一个出路,感觉我们这些读者进入到时间的荒原,在无尽中漂泊,就像一块玻璃被打碎了,每一个碎片又折射一些碎片化的影像,很难拼凑一个完整的影像。
这是我个人对大部分作品的一个基本的主观感受,当然不一定对,感觉他试图提出一些问题,但是又不知道提出一些什么样的真正的问题,他似乎又很少能够给出一些有意义的答案。
王德威 :我对于大陆文学不同的写作方式或实验,其实知道的有限,特别感激这个机会,把我逼出了舒适圈,我是真的一头栽进这67部小说里。我约略谈一下我个人的观感,然后我把这个问题稍微扩大一点,也讲讲海外的华文文学和大陆华文有意义的对话。
我要呼应刚才梁永安教授说的,这个问题不仅是农村写作的问题,而是对现实或现实主义如何界定的问题,看得出来,至少这次参赛的作者有意无意都在思考什么是现实,怎么去界定、描写现实,怎么去介入现实。这里面有相当有意思的作品,让我们有兴趣知道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但是我要呼应大家共同的感受,我们似乎在寻找一种有力气的陈述,一种有力气的故事,这次很多作品在技术或者想象层面上操作得非常精彩,但是缺乏我们这些非青年的评论者想向往的一种东西,这是代表我们自己是过时了呢,还是这些青年作家还没有达到我们所标志的理想目标?这是可以辩论的,到底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还是我们把自己这个世代的期望强加于另外一个世代身上?或者我们真的可以说,以我们的阅读量、生活经验而言,也许目前这个世代还有一些可以继续增强写作实力或者创造力的地方。
在实际的阅读经验里面,我觉得有两个方向也许可以提出来作为大家的参考。
第一,还是现实主义小说的问题,我们怎么去界定怎么写实,怎么去看待生活经验。这些小说家企图想要做一些介入的努力,但是似乎还欠了临门一脚,我们赞叹之余,仍然意犹未尽。
第二个方向,这次也看到地方和地域文学写作的一个倾向,前两届东北写作成为大家趋之若鹜的话题,这次南方写作成了一个新的可以注意的方向,有的作者喜欢从山川地物、风土人情进入,有的从聊斋、各种各样的中国传统幻想进入,这些都代表一个新的方向。这次特别巧,有一个南方写作的“祖师奶奶”林白女士担任评委,我想林白应该很高兴看到有很多年轻一辈作家以地域作为出发点,但是他们的操作方式是很不一样,这一点是我有所期待的。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想把话题稍微扩充一点,如果我们今天谈当代中国或华语写作现况,目光应该不止于大陆作家,放眼海外,其实有很多有趣的作品值得参考,我很期待未来的创作者在阅读彼此或者阅读大陆名家作品的同时,也可以参考一下海内外的华文作品,也许会得到不同的灵感,尤其是在文字操作的华丽的、幻象的、玄妙的想象方面,都是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有一点我可以特别明确地指出来,至少我所熟悉的台湾地区文学和马来西亚华语文学,在最近几年对于风土和环境,还有整个大的世代变迁、人跟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逐渐成为一个很严肃的话题。大陆的山川之大,这么多作家如果已经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地域,或是集中在传统的乡土写作,我觉得那个部分可以更近一步深耕细掘。这次参赛的有几本触及到这个方面,但是我仍然不觉得真正触及到大陆以外的读者好奇想知道的部分。
总的来说,这些话题真是方方面面,就像格列佛漫游世界的感觉,有的话题大得不得了,大到让我这样一个微小的读者似乎没有能量去真正想象这样哲学性的问题,另外,还有非常精致细微的描述,但是精彩完了之后,你不禁要问下一步要做什么?所以在过大跟过小之间怎么摆放自己在现实和现实写作的位置,我觉得是未来的挑战。
02
当下,文学意味着什么?
许子东 :各位怎么看文学对于当下这个时代的意义?这个题目当然很大,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回避,文学应不应该记录现实、介入现实?如果需要,怎样书写才是真实深刻的,要怎么把握时代精神,才不会沦落为一种新的庸俗?
罗翔 :作为门外汉,我一直在思考什么叫文学,我个人对文学的理解非常浅薄,我觉得文字还是要文以载道的,但问题是文又如何去载这样一种道?可能有三种立场:“朝闻道”这是一种乐观主义的载道精神;还有一种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悲观主义的载道历程;还有“道可道非常道”的怀疑主义的载道立场。
我希望文学作品能够在这三种立场中进行一种切换,能够让我们产生一种共鸣,让我们不断去追寻这样一种道。但是我感觉,一种精致的、技巧主义的写作可能会回避这样一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作品越来越加深我的一种虚无感。
至于“学”,什么是学问?学问是不是要有一种问题意识,带着一种学生的谦卑心态去寻找答案,去追求真理?作者肯定不是真理的代表,也不是真理的化身,但是作者可以以一颗谦卑的心去寻找问题。
“學”是会意字,两只手中间是一个爻,这个爻卦表明无限的意思,它是表明知识本身就是无穷无尽的;下面是一个“子”。文学,从字面意思来说,作为一种文字的学问,它是不是仍然要探究无穷无尽的、变化无穷的天人之道,在人类的总经验中,以一个“小子”的心来求问。
这就是我个人一种非常偏颇的看法,我觉得是不是还是要在经验和超验中反复求问,可能我们还是要有一种超验的心理来处理当下的一些经验,让这些经验不至于成为一些非常主观的碎片。当然,我们也要让经验,让上面这些超验的东西不变得玄而又玄,要接地气,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注意到几本非常有意思的科幻小说,激起我很大的阅读兴趣,我觉得它们似乎是在超验和经验中进行一种切换。
我个人浅薄的一种观感就是,文学可能有三步,一种是我手写我口,第二个境界是我手写我心,第三种境界是我手写你心,把你心中所想的、表达不出来的表达出来。所有好的文学作品是不是在我心、你心和众人之心中进行来换的切换?
我们现在很多作者是不是在刻意回避一些问题?或者说他也没有把握到文字所应该真正触动的一些问题。换言之,作为一种学问,如果你提不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那么你可能也很难寻找一种真正的解决之道。
梁永安 :这个问题确实太大了,一个宏大叙事,或者一个整体性的思想,是需要一定的条件,不能强写的。一个青年,尤其在今天流速匆匆的时代,要想把握现实、洞察现实,历史条件是非常差的,我们观看人类历史也可以明显感觉到,你身处那个时代,往往很难认识它。
今天的青年文学,我总觉得他们是在观念的时代,观念的时代和思想的时代有太大的区别,观念的时代里面我们需要一种锐度,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维度上有自己的观念,这时候相互推移,可能构成我们时代的整体。我接触的很多青年作家,写的就是生活里很刺痛的东西,如果放大一点看觉得没什么,但是确实有生命的真切性。就像瞎子摸象,每个人摸到一块,这时候一个活生生的时代会被逐渐感触到。
刘铮 :文学跟现实之间的关系,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现代主义的顶峰卡夫卡的作品——《城堡》《审判》《诉讼》——他是在描写现实吗?其实并没有德国当时现实的直接的纪录片式的描写,但他把握到现实的精神,把握到那个时代人的思想困境。所以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并不一定说是一个照片式的,它可以通过隐喻的方式达成,像罗翔老师刚才说的,他读到很多科幻作品,反而觉得比那些直接描写当下现实的、貌似现实主义的作品更能把握到这个时代的精神。
我对年轻人的作品的期待也在这里,谁真正把握时代的精神,并且体现到作品里,那他就是成功了,而我们要推崇的也正是这一类的作品。如果他没有把握住,我们可能流露出失望,也是正常的。
我在今年年初写过一篇评论,里面提出一个概念,叫做走出怨恨文学。怨恨是我们对时代的一种情绪,我们对很多现象不满,这种负面的情绪表达到文学作品里就变成一种冲动。表达对现实失望是很容易的,但是,就像罗翔老师刚才提到的,文学不应该止步于此,你如果只是给别人带来失望,这个失望是我们共通的,我们有这个失望,不用你再来告诉我,所以我们希望看到的文学还是有一个别样的状态。至于怎么表现,那是交给年轻作家的任务,评论家不可能给你设想一个方式,但是我想不只是表达冲动、怨恨、不满才能成为好文学,一定是比它更高的、超越这个目标的才能成为好文学。
03
我们必须要预设某一种
擦肩而过的可能性
许子东 :你们有什么建议给现在的青年写作者?他们现在的写作,客观上面临着跟前面的作家的竞争关系,怎样挑战或者传承前面的作家?
王德威 :今天最怕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千万不能当青年导师,我们在这里所扮演的角色和参赛者的立场是针锋相对的,想象下,在网上或者在未来会有多少愤怒的参赛者说,你们这六个老东西,懂什么东西?
我先引用哲学家阿甘本的话,他说什么是此刻,什么是当代,当代的意思就是最不合时宜的,最没有办法能够响应时代的要求。所以我们必须要预设某一种擦肩而过的可能性,这种历史的偶然性,我们必须要预留一个空间。
退到中国的语境来说,我们的确认为在一个更悠远的传统里,这个传统已经是包罗万象,需要某一种客观的角度做判断,需要某一种声音作为衡量尺度,所以我们只能很谦虚地说,我们在扮演一种所谓的路标设置者,真的要给青年作家什么样的建议,我觉得是很惭愧的。晚清作家吴趼人,有一个笔名叫老少年,但愿我们都是老少年,倒不是倚老卖老,也许年纪大了但还有一个少年之心,尽量去想象、去配合时代的改变。
说到小说创作的当下此刻性,举两个例子,1980年代末期一个叫刘慈欣的青年,一边在水力发电厂工作一边写科幻小说,我想那时候他不会想象到多年以后《三体》会成为全世界的经典文学。2016年,韩松写了《医院》,在后疫情时代,看起来肃然起敬,这是惊人的一个巧合。这个时代精神要怎么抓,这其实是一个对象,但是我们不能没有这样一个指标或者路标。
我们要怎么样去期待青年作家的写作?我宁可说也许我们作为老少年一般的读者,尽量地阅读、提供思维的可能性,在文学传统脉络里,有些作品的确要经过时间的淘洗倏然出现,这是所谓时代精神的作品。一方面我们讲时代精神,一方面讲此刻,这两种对时间的命名所产生的张力,这是一个悖论,这是宝珀理想国设置这个奖的时候,也许想到的一个话题。
我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我们在思考这个话题的时候,必须预留一个空间,我们不知道在这一轮阅读里会不会错过文坛的彗星。所以我刻意要说一些比较倾向青年作者立场的话,青年作者不论能不能到入围阶段,我相信期许自己作为几亿光年之外的彗星,期待有另外一个时空交合的点,那个作品突然发出最大的光芒也不一定。
许子东 :我有一次问到王安忆他们,你们这些人怎么回事,从八十年代寻根文学开始,就是韩少功、余华、贾平凹、王安忆、莫言等等,到今天他们还是一线作家。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陈平原在旁边说,许子东,你为什么不反省一下,你写文章也写了四十年,八十年代就在写郁达夫了,为什么今天你还在写?
今天的整个文学界,基本还是八十年代起来的这个阶段,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我们讲的一些主流作家,他们从先锋已经变成了后卫,他们目前做的事情还是在守卫一条意识形态的底线,就是刚才刘铮说的怨恨文学。在我看来,由于时代背景的限制,如果进入新时代,不一定就是文学的进步,所以八十年代的主流文学为什么到今天还是主流文学?
这是大形势,但问题是,对于青年人,写作怎么办?我看到两种与时俱进的方法,一种方法就是像格非这样,《望春风》写一个村庄里几十年的风雨,但是这个村庄完蛋,不是在文革当中,而是在文革后,商人把这块地皮卖掉,当官的帮助商人,他找到一个叙述技巧,把对以前时代的愤恨延伸到九十年代。他这个小说获奖一百万,格非真是聪明,不仅不忘初心,而且与时俱进。
双雪涛也是怨恨文学,但是他怨恨的是九十年代下岗工人的命运,很真实,他跟八十年代不一样,他写出了他这一代的故事。我觉得文学奖能发掘到这样的作家就很好。更年轻的王占黑,写的是这些工人为什么被抛弃,以及他们以后每天的日子怎么过,写得跟契诃夫的小说一样,她这么一个小姑娘就能懂得上海的退休工人、下岗工人day to day的生活,所有的大时代都在后面。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我不应该发言,我是报幕的,因为我最近正好看他们的小说,所以我觉得这个奖办的有一点成色。
还有陈春成,文字非常精致,背后也有一个大时代。他写的《竹峰寺》里有一个石碑,想得到这个碑的是红卫兵和当委员的和尚,可这个碑被有心的和尚藏在一座桥上,什么意思呢?我们天天走,传统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陈春成这个也非常了不起。
04
给这个时代一个礼物
许子东 :最后一个问题,各位对这个奖有什么具体的意见?
梁永安 :希望获奖的年轻作者可以跟青年读者有一个互动,把这个奖的青春气息渲染起来,它的文化气质跟其他奖项是不一样的,它一定要符合当下年轻人心态,我觉得这是要有一定创新的。
林白 :本来我觉得当评委这种事情是最累人的,但是旁边人都说,这个奖太厉害了,我才知道现在青年编辑鼓励青年作家写作就说,好好写,争取拿到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这是鼓励青年作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奖。要不然青年作家写着写着,五年、十年,就会没劲了,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更好。有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这就一个大家可以看着的高地。这是我要说的。
刘铮 :这次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主题是“从此刻出发”,我想回应一下刚才王德威教授提出的为什么到此刻还有很多年轻人愿意写小说,这个问题也很重要。我想到的是,其实现在这个“此刻”就是后疫情时代的开始,的确历史翻开了很不一样的一页,对于这个时代的写作者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写的自传,叫做interesting times,他说引用了一句谚语,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我希望你活在一个有趣的时代里,在某种意义上讲,现在就是一个有趣的时代。
对于今天小说的写作者来说,我觉得他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去把后疫情时代的特殊的感性和经验都写进他们的作品里。事实上在我们评选的作品里面,已经露出这个头,已经有人把疫情的内容写到自己的作品里,虽然还不是很深刻,只是浅浅的掠过,但是从这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开始,后疫情时代的经验和感性就会在青年文学作品中有一个爆发式的体现。
所以我对未来文学新的增长点,是抱着很大的期待,而且也很乐观,在这里一定会有值得流传的作品。
许子东 :短短两个小时的论坛,刘铮老师从悲观的批评开始,现在变成乐观的祝福。
罗翔 :我们这个文学奖是从“此刻”出发,“此刻”在英文中也有礼物的意思,我时常想,也许我们这个奖能够评选出一种代表当下文学最高水准的作品,作为给这个时代的一个礼物。
正如柏拉图那个著名的走出洞穴的比喻,我们大部分人可能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洞穴之中,看到的都是各种影像,各种世界的现象,但是也许有一些伟大的作品可以带领我们走出洞穴,至少让我们有这样一个走出洞穴的冲动和动力,希望这个文学奖能够评选出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作为给这个时代的礼物,也作为带领我们走出洞穴的一种盼望。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地球,也许我们把这个文学奖作为一个支点,也撬动我们对于文字的尊重,也撬动文字本身对于德性的一种追求。
王德威 :我正好延伸罗翔教授所说的洞穴隐喻,汉娜·阿伦特在她的经典作品《人的境况》里讲到,一个古典的公民社会,最重要的公民之间相互沟通的方式,以及建立社会秩序和憧憬的方法,就是互相的说故事,说故事是启动文明的一个开端。
我们怎么去看待未来,怎么回想过去,端赖我们这个世代此时此刻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一起说故事、分享故事,这个故事越复杂、越不可思议、越有传承的历史意义,就越能够展现这个文明可长可久的潜力,所以从说故事开始,这是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终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