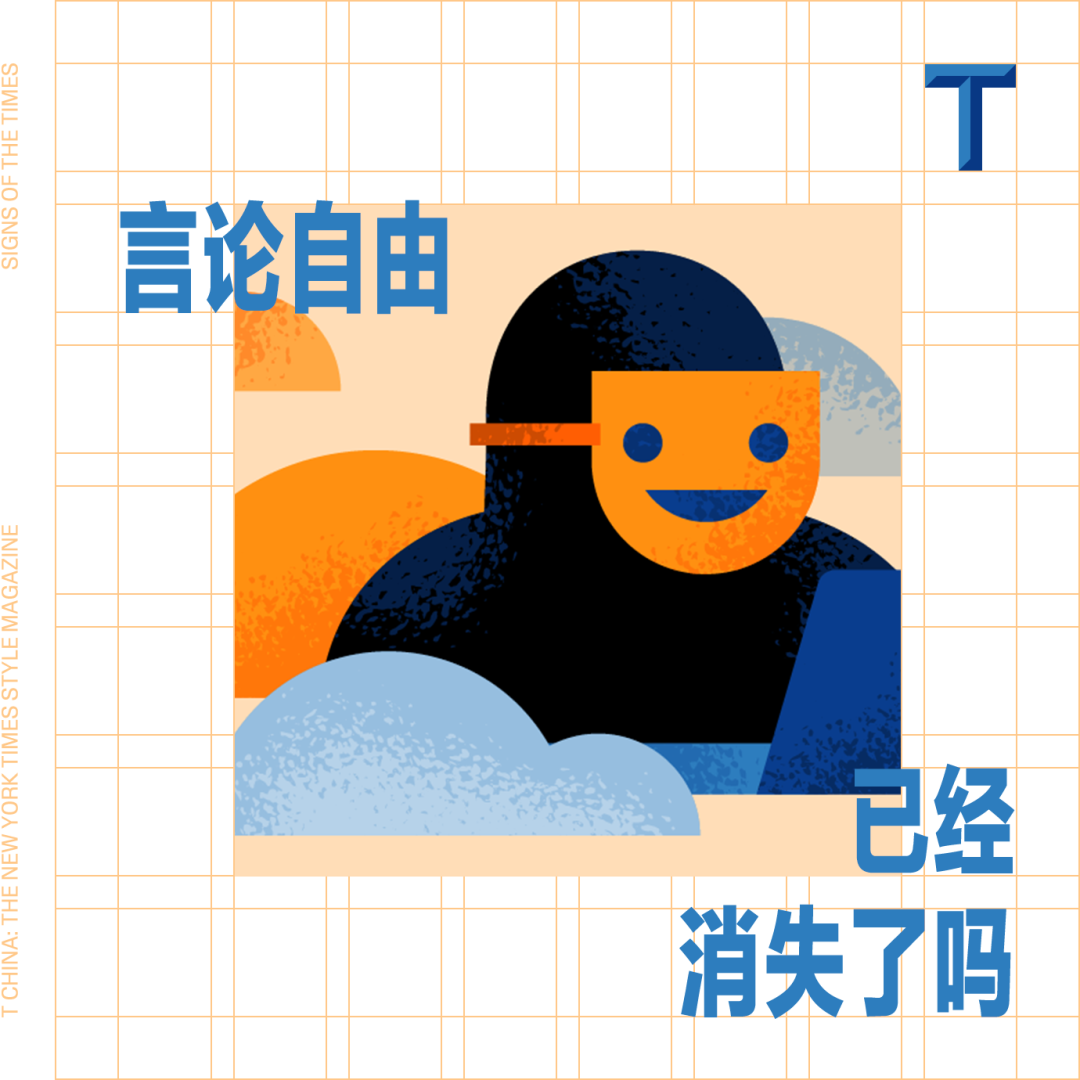
5 月 12 日,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教授张平发表了这样一条微博:「…… 学会三句话,走遍中国都不怕:1. 四大发明伟大。2. 台湾是中国的。3. 我不喜欢日本人。现在需要加一句,4. 国外没有支付宝。」这一言论引起我关注的原因有二:其一,他所提到的四大发明,让我想到 2019 年因评价「四大发明不是本质性创新」而被电子科技大学停课两年的郑文锋;其二是它的评论区,象征「免责」的表情符号层出不穷。
抛开言论本身的正确与否,在中国当下的互联网语境中,一个知识分子说出这样一段话,显然并不讨喜,一如「后浪」并不能获得所有追求个体独立的年轻人点赞一样。作为同时具有法律身份(自然人)和职业身份(社会人)的公民,我们在互联网发言表达的过程中,「求生欲」是否真的在增强?是谁在限制和威胁我们的表达与发声?网络中的个体如何在压力之下试图自由表达而又夹缝求生?
英文中,「传播」一词对应「Communicate」,有「沟通、交流」之意。对人类而言,无论是有声的语言还是静态的文字,它们从诞生初期就承载着沟通、交流的重要功能。而表达,恰恰是沟通交流的前提。按照传播学大师 Marshall McLuhan 的观点 —— 媒介即讯息 —— 表达,甚至构成了沟通与交流的核心。
人类的表达欲或许是与生俱来的。这自有其功能性的历史影响。在生产力低下的远古时代,经验的积累与传承、群体内部的维系与沟通、不同政治版块间的交涉与组合,都需要表达的具象化 —— 语言和文字 —— 的参与。自从物质与意识的二元对立出现,及至个体意识和群体观念伴随着宗教扩张、帝国战争、文明进步、商贸交流在不同地理空间内的扩散,我们表达的欲望也愈发强烈。无论是中国秦朝初年的「焚书坑儒」,还是欧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或是清朝统治下的「文字狱」,乃至西方新闻自由的先驱 John Milton —— 每一次政治运动和思想交锋的背后,都隐含着对表达权和解释权的激烈争夺。
实际上,表达权和解释权恰恰构成了所谓「言论自由」的一体两面。真正的言论自由,既需要个体意识的自由表达,更需要对自我表达拥有完整解释的权利。否则,每个平凡个体的表达就会遭受被误读、被代表和被湮没的威胁。这也正是「后浪」不受人欢迎的原因之一 —— 占据媒体资源的个人或机构,用部分的表达代替了整体的表达,将自身的意义建构强行安放在群体的肩头。因此,表达与对表达进行解释的权利,实际上是言论自由的真正核心要义。所谓钳制言论自由,要么是封闭了表达的途径,要么是切断了解释的渠道。而互联网时代的隐形媒介霸权,恰恰在于对表达解释权的牢牢掌控。
可以这么说,互联网时代的表达权本就是媒介进化史狂飙突进后非良性生长的产物。从印刷媒介到电报、广播、电视等媒介的各领风骚,它们在表达权方面的最主要贡献在于现代职业媒体人的成长与成熟。无论是报纸记者还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在大众传媒牢牢掌握媒介控制权的年代,这些传媒从业者无疑是最具表达权势的人。然而,情况在近 30 年间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互联网的发展在技术层面为个体的表达创造了理论上的无限可能,也「逼迫」操媒体权柄者不得不退居幕后,更加小心而隐秘地操纵意见表达的社会机器。这个借由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出现的全新场景,被国内传媒学者称作「全民记者」时代。
事实证明,「全民记者」时代确实为表达权的丰富带来了更多可能,却并没有从本质上解决解释权的最终掌控问题。甚至,在表达权虚拟繁荣的假象之下,我们作为个体表达者,正在进一步丧失解释权。换言之,如果你不能为你所说的话负责,如果你的话将被人冠以其他你无法左右的解释,这种情况下,即便发言的门槛降低,人们也不得不提高警惕,少说为宜。
是的,实现表达权的方式更多了,但这也让每个发言者承担的风险呈几何级数增加。而互联网的隐匿性、随机性和不可控性,又使得这种风险有可能降临在每个人身上,无怪乎「寒蝉效应」的扩散日益成为一种常态。
毕竟,网络的杀伤力与暴虐性已经无数次向我们展示过它的可怕獠牙和嗜血本色。
导演陈凯歌在 2012 年的电影《搜索》中讲述了女白领叶蓝秋因不给老人让座这一导火索引发连锁反应直至自杀身亡的故事。彼时,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方兴未艾,对互联网生态的冲击和影响也难以窥见全豹。只不过,《搜索》的预言很快应验:2016 年的「江歌案」,2018 年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故,2019 年大连 10 岁女童被杀案 —— 伴随社会热点和话题而来的,总有网络暴力、人肉搜索和口诛笔伐。
这些不问是非、不讲道理、不留底线的人身攻击与道德审判,迅速激起了网络草民强烈的求生欲。而与此同时,另一个尴尬而又悲哀的现实在于,对于为数众多的网民而言,他们既是网络暴力的潜在受害者,又是互联网空间法不责众思维下任意施暴的「乌合之众」。
事实上,2013 年发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就明确规定了网络诽谤入罪标准: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根据《刑法》规定,将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然而,实际情况是,互联网空间的隐匿性使得追责对象的确定依然困难,选择运用法律武器维权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心理成本却居高难下。
那么,网络暴力带来的恶果到底是谁之过?真正掌控互联网空间意见表达与解释权的到底是谁?
中国的网络使用者群体在近十年来以令人瞠目的速度疯狂增长。传媒资本市场的快速繁荣、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智能终端的低成本接入、网络空间治理的滞后性,无一不在参与着互联网生态的重构之路。
传统意义上,由政府规制和传媒资本市场共同左右的媒介控制权,已经随着市场化的深化和现代化治理的难度上升进一步向普通受众让渡。在此过程中,非精英化的意见领袖迅速崛起,给互联网良性生态构建带来了更多挑战与不确定性。与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意见领袖不同,互联网空间中的意见领袖,可能是美食博主、时尚达人、网红卖家,甚至可能是极端的宗教、民粹主义者。在 McLuhan 早已预言的这场「重新部落化」革命中,互联网空间被重新定义为众多亚文化圈层和部落化社区,每个圈层或社区的意见领袖都是掌握着网络空间杀伐利器的一方酋长,每个具体的网络参与者又往往同时身处多个圈层或社区之中,角色转换之快、种类之多同样令人眼花缭乱。
现实的情况是,一旦你作为「外来者」踏入某个网络部落,无论是物理意义上的接入,还是意识形态上的介入,都会快速引起反应,进而在「非我族类,其心可诛」的简单思维和行动逻辑下被审判。即便你在自己的网络空间发表涉及某个社群的话题或关键词,也不能避免被其攻击甚至消灭的可能性。「AO3」事件已经证明了一个网络社群的杀伤力可以有多大。
所以,或许应该这样说:当个体以某个网络社群中的身份和角色对他人的表达(尤其是他人来自社群之外)进行评判时,他们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而在这场媒介控制权的争夺战中,互联网空间并没有形成完备的权力竞争机制。说到底,表达权乱象的根源,在于快速发展过程中没有及时建立良性的互联网生态。
肉眼可见的现实是,互联网空间的表达权越来越开放,而解释权却进一步隐匿,成为媒体霸主和意见领袖的专利。前者控制流量,后者则在一定程度上创造着流量。因而,当我们探讨如何构建良性的互联网生态时,就绕不过这个主题。
媒介使用与媒介表达的进一步开放和获取,并不能带来媒介素养的天然提升。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互联网发言过程中如何正确认知自身的角色与定位,如何在施暴者与受害者之间找到自己。对大众传媒以及身后的控制者而言,政治、经济、社会效益的平衡,关乎传媒业的发展,关乎意识形态安全,更关乎每个传媒从业者的明天。毕竟,打卡下班后,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叶蓝秋。媒介伦理,无论是社会层面的,产业层面的,还是职业层面的,都是传媒人历久弥新的答卷。对新兴的网络意见领袖而言,刚刚获得的「贵族身份」着实在某种层面带来了全新的权力体验,但在媒介生态重构的进程中,今日的新贵也可能是明日的庶民,可以确定的是,权力透支的越快,偶像崩塌的也就越彻底。
人们在互联网空间发言的求生欲正在变强,这是不争的事实。假如这是由于互联网表达的误伤率正在增长,网民对承担责任的可能性丧失了信心,那么显然应引起互联网管理者和每个互联网参与者的担忧。如果有一天,求生欲不是因为担心自己受伤害,而是因为更加明确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以负责任的态度谨慎约束自我的言行,避免伤及无辜,我们或许才能认为,我们的成熟对得起互联网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