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协议是否签署,希姆莱仍坚持仅招募穆斯林的计划——3月3日,菲利普斯与党卫军同僚卡尔 冯 克雷普勒(Karl von Krempler)会面,后者将协同克罗地亚政府官员阿利亚 舒利亚克博士(Dr. Alija Šuljak)开展招募工作:此次招募行动始于20日,当时精通多国语言的冯 奥布沃泽与舒利亚克博士在其他几位要员陪同下开启了为期18天的招募巡行,并走访了波斯尼亚的11个地区——他们在各地举行了公众集会以敦促民众加入新师团——弗朗茨 约瑟夫皇帝旧波斯尼亚军团的模式显然在说服人们参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在一战中的英勇事迹在组建期间被反复提及。一份党卫军刊物宣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军团为自己赢得了不朽的荣耀。他们的英勇家喻户晓……如今,元首为他们提供了新的机会,使其能在党卫军行列中为欧洲大陆和他们祖国的美好未来而战。他们自愿响应‘国家领袖’(Poglavnik)的号召……其将作为德国士兵的一份子与其他(欧洲)民族并肩作战并配备相应武装。”
当然,除去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一名前志愿者于后来给出了他更现实的参战理由——他相信该师的存在“将彻底终结切特尼克(Četnik)组织在波斯尼亚东部对穆斯林的屠杀”。
当冯 奥布沃泽与舒利亚克两人着手招募志愿者时,德军于3月9日在柏林组建了该师的“组建参谋部”(Aufstellungssstab)——该部门负责组建师的各下属单位并训练其内人员——曾在东线指挥某团的赫伯特 冯 奥布沃泽(Herbert von Obwurzer)被任命为该师师长,而其奥地利同僚埃里希 布劳恩(Erich Braun)则担任起该师的作战参谋。布劳恩在日记中写道:
“3月9日——我终于接到通知,党卫军“北方师”(Nord)的冯 奥布沃泽和我将组建‘克罗地亚师’作为“欧根亲王师”的姊妹部队;只是目前尚无具体指令。从14点起,我一直在等冯 奥布沃泽。
3月10日——我在本日16点受邀与冯 奥布沃泽喝咖啡;他给人极佳的印象——一名典型的蒂罗尔人,前‘帝国猎兵’(Kaiserjäger)且在举手投足间尽显军官风范。得知我是奥地利人后,他颇为欣喜,我们随后讨论了局势。”
随后,冯 奥布沃泽前往了位于塞尔维亚的党卫军“欧根亲王师”以熟悉巴尔干军事政治形势,其最终于4月初与布劳恩在萨格勒布地区会合——而该师的“组建参谋部”也将设于此地——然而,二人起初能相处融洽却在后来关系恶化。希姆莱命令其驻克罗地亚私人代表康斯坦丁 卡默霍费尔(Konstantin Kammerhofer)也参与该师的招募工作之中。
显然,党卫军与克罗地亚政府在招募过程中都暗藏私心,两者均意图推进各自的议程。争议焦点自然是该师的族裔构成——希姆莱在初期谈判中已明确要求仅招募穆斯林,且立场未变;而克罗地亚政府官员则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助长穆斯林内的(独立)民族主义情绪/武装力量的行为。尽管帕韦利奇政权表面上支持该项目,但其却在暗中试图“破坏”招募行动。
毫无疑问,阿利亚 舒利亚克博士属于那一群“支持克罗地亚国家并自视为克罗地亚国民”的穆斯林精英之中的成员——到1943年,这群人反而在“在波斯尼亚大多数穆斯林中声望极低”,舒利亚克身着乌斯塔沙制服出席招募巡行中的公众集会,且其演讲仅宣扬乌斯塔沙的政治主张,这很快便导致他“遭到穆斯林民众的强烈抵制”。冯 奥布沃泽将此事报告给了菲利普斯,后者于4月6日在格莱斯 冯 霍斯特瑙将军的宅邸与多名要员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菲利普斯向弗拉尼契奇博士表达了对舒利亚克的不满(据菲利普斯描述,穆斯林认为舒利亚克是“公开反对穆斯林民族性的叛徒和煽动者”),并要求将其撤职。虽然弗拉尼契奇(据称他曾表示“绝不允许组建【任何】一支反乌斯塔沙的波斯尼亚师”)承诺配合并答应派遣两名克罗地亚军官接替,但这两人始终未到位。不过,德国人并未因此恼怒——此后其招募工作反而能减少克罗地亚方面的干预。
而舒利亚克本人激烈否认自己有任何过失。他后来辩称:“唯一的分歧源于(冯奥布沃泽)在公众集会上使用了塞尔维亚方言进行发言,这激怒了我的同胞。如果(他)闭口不言,事情会顺利得多。”
当冯 奥布沃泽不仅宣称柏林指令要求仅招募穆斯林,还试图在招募海报上印制绿色旗帜与伊斯兰新月标志时,舒利亚克强烈反对——其说法后来得到格莱斯 冯 霍斯特瑙的证实,后者写道:
“在波斯尼亚,(党卫军)招募者宣扬的自治愿景与奥匈帝国时期类似——这正是所有波斯尼亚人梦寐以求的。”
这位乌斯塔沙成员还报告了其党卫军同僚在巡行中的尴尬时刻:
“冯 奥布沃泽……曾在希腊生活过一段时间……我们途经斯拉沃尼亚布罗德地区时遇到了一列北上的塞萨洛尼基犹太人运输队;许多犹太人视奥布沃则为故交,热情招呼他,这令他在我面前颇为难堪。”
冯 奥布沃泽本人则早在向菲利普斯汇报前数日便已与舒利亚克分道扬镳——抵达图兹拉地区后,他会见了哈吉芬迪奇少校并与其于3月28日共同前往萨拉热窝。哈吉芬迪奇在此将这位德国人引荐给各个穆斯林自治派领袖,包括大穆夫提哈菲兹 穆罕默德 潘扎(Hafiz Muhamed Pandža)。自治派将这支师团视为受迫害穆斯林的救星,因此全力支持其招募工作。据记载,潘扎至少一次在萨拉热窝召集穆斯林学者并宣布:
“德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他们重提奥匈帝国与波斯尼亚的传奇友谊,我们必须挽救波斯尼亚尚存的一切。”
愤怒的克罗地亚政府官员向德国公使馆抗议,要求哈吉芬迪奇返回图兹拉的军团并罢免冯 奥布沃泽,但这无济于事——克罗地亚的小心思还体现在其司法部长帕沃 坎基博士(Dr. Pavao Canki)的行动中:他试图向萨格勒布政府提交一份被德国人称为“伪造报告”的文件,声称组建该师将引发波斯尼亚天主教徒和塞尔维亚东正教徒的骚乱。希姆莱还接到报告称,一些志愿加入该师的年轻人“在夜间被从床上拖走,送往克罗地亚军营或诺沃格勒迪斯卡(Novogradisca)和亚塞诺瓦茨(Jasenovac)集中营”——但后续调查证明这一指控不实;甚至有报告称,身着制服的乌斯塔沙成员在宵禁期间偷偷拆除了该师的招募海报。
克罗地亚官员的诡计并非党卫军行动中唯一的阻碍。德国外交部对希姆莱插手外交事务极为不满,尤其是公使卡舍(Kasche)强烈反对组建纯穆斯林师——作为克罗地亚政府的坚定支持者且与党卫军素来不睦【伯格尔(Berger)称卡舍“始终无法忘记1934年6月30日”——伯格尔暗指该日希特勒清洗冲锋队(SA)的“长刀之夜”事件,党卫队在此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作为冲锋队高官的卡舍则只是侥幸逃生】,卡舍逢人便称党卫军高层“在波斯尼亚自行其是地推行政治路线”,这对克罗地亚局势“极其危险”。他还批评冯 奥布沃泽公然无视3月5日的《弗拉尼契奇-登格尔协议》。另一名德国外交官则指责克罗地亚“既无理想也无能力解决民族问题”,而帕韦利奇的新国家“极可能因希姆莱对穆斯林自治运动的支持而覆灭”。
党卫队总部的负责人戈特洛布 伯格尔(Gottlob Berger)认为,流亡的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哈吉 阿明 侯赛尼(Haj Amin el-Husseini)可协助鼓励穆斯林加入新师团——这位曾领导巴勒斯坦阿拉伯高级委员会的反英穆夫提,当时居住在柏林采伦多夫(Zehlendorf)一栋豪华别墅中并同时接受德国外交部与党卫队的资助,其在推动德国与穆斯林世界关系方面发挥关键作用——3月24日,伯格尔,侯赛尼与菲利普斯在柏林召开会议讨论此事。穆夫提对波斯尼亚局势了如指掌,他在会议前几日的演讲中表示:
“所有穆斯林的心都必须与波斯尼亚的伊斯兰兄弟同在——他们正被迫承受悲惨命运。塞尔维亚匪帮和共产党匪徒在英苏支持下迫害他们……这些人遭到屠杀,财产被掠夺,村庄被焚毁——英国及其盟友负有重大责任,正如他们在阿拉伯地区和印度所为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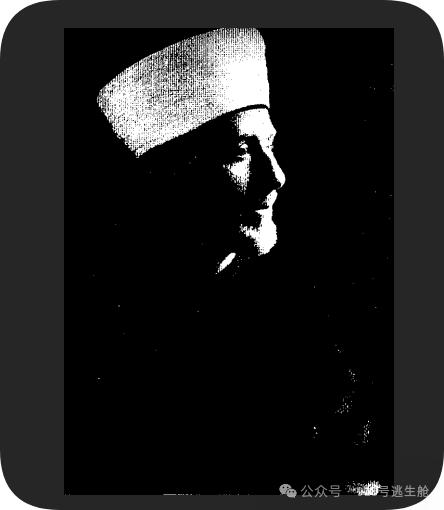
哈吉 阿明 侯赛尼(Haj Amin el-Husseini)
侯赛尼向德国人强调自己“在地中海沿岸乃至整个东方世界拥有巨大影响力”, 因此伯格尔安排他巡访该地区,会见穆斯林领袖、克罗地亚政府官员及当地德军指挥官——一名党卫军军官回忆道:“这次访问被寄予厚望——穆夫提将在波斯尼亚师的组建工作中发挥关键作用。”——就结果而言,这次于3月30日至4月14日进行的巡访确实成效显著,一位德国外交官写道:
“信徒们视他为真正的穆斯林;他作为先知的子孙而受到尊崇。他在开罗求学时的同窗与麦加朝觐时的故交纷纷前来迎接。人们向他赠送礼物——古兵器,刺绣等物。”
一名党卫军军官报告了穆夫提访问萨拉热窝的情形:
“菲利普斯派冯 奥布沃则与我前往萨拉热窝负责穆夫提访问期间的安保与住宿安排。他当时下榻于奥地利总督旧宫——1914年6月28日,遇刺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夫妇的遗体曾在此停灵。
穆夫提本人极具魅力。他蓄着红金色胡须,举止稳重,双目炯炯有神——面容充满领袖气质,其更像个哲人而非革命者。我因不会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或英语(这些他皆能流利使用)而未能与他交谈,但冯 奥布沃泽的土耳其语娴熟,二人有过一两次对话。
侯赛尼随行人员中唯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仆人。这位身着欧式服装,携带武器的贝都因人终日守在穆夫提房门前,确保主人礼拜时不受打扰。夜晚,他裹着毯子睡在门前,让穆夫提得以安眠——我始终未见他饮食或休息。”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穆夫提对于针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都表现得相当克制——他的主要敌人是巴勒斯坦的犹太定居者和英国人。然而,此次访问仍然取得了成功——作为伊斯兰世界公认的宗教与政治权威,他站在德国一方并呼吁建立对抗共同敌人的统一战线。
伊斯兰领袖们从远至阿尔巴尼亚的地方前来与穆夫提会面,他几乎接见了后斯帕霍时代波斯尼亚穆斯林政治舞台上所有派系的成员。人们向他控诉的不仅是克罗地亚政府对穆斯林福祉的漠视,还有部分穆斯林对德国人的怨恨,后者曾在1941年到来时被寄予给穆斯林群体带来和平与繁荣的厚望。他们还表达了对轴心国向其死敌——塞尔维亚切特尼克分子——提供军事援助的强烈不满;在萨拉热窝最大清真寺的布道中,侯赛尼关于波斯尼亚绝望处境的演讲令听众潸然泪下,他将当时的波斯尼亚穆斯林比作失去罗盘的迷途者并恳求他们支持轴心国。值得注意的是,一名在场的未来该师团成员回忆称,穆夫提曾敦促穆斯林“支持德国人并从他们手中获取武器”,但出于对克罗地亚方面的顾忌,他并未具体提及该师团具体是哪支单位。
在与萨拉热窝《曙光报》记者交谈时,侯赛尼称波斯尼亚穆斯林是“伊斯兰的精英”。他对另一群人说:
“整个穆斯林世界正团结一致对抗英国和苏维埃俄国。我已向元首保证过这一点……穆斯林世界与德国并肩而立,德国配得上并将赢得胜利。穆斯林世界的立场是明确的——那些饱受英国和布尔什维克枷锁压迫的土地正急切等待轴心国胜利的时刻。
我们必须投身于针对英国(这座民族监狱)的持续斗争,直至彻底摧毁大英帝国;我们必须投身于针对布尔什维克俄国的持续斗争,因为共产主义与伊斯兰水火不容。”
克罗地亚方面最初对穆夫提的到访感到意外,但深知其时机绝非偶然——这段时间正值党卫军招募“穆斯林”师团并拉拢自治主义者之际——于是,他们也展开了政治博弈,其内的政府官员试图阻止侯赛尼与穆斯林民族主义领袖会面,但这一阴谋被冯 奥布沃泽挫败,后者成功为这些重要穆斯林人士争取到了面见穆夫提的机会。坎基博士向特使卡舍抱怨称,随着穆夫提的访问以及“霍扎斯”(即伊玛目,负责师团伊斯兰宗教事务的穆斯林神职人员)的招募,该师团呈现出“泛伊斯兰战斗部队的特质”——特使本人则向柏林上级汇报:“克罗地亚人向我抗议,称党卫军军官自招募活动伊始就决定仅接纳穆斯林。”
返回德国后,侯赛尼就师团建设提交了系列提案:
“1. 该师的首要任务必须是保护(波斯尼亚志愿者的)家乡与亲人;严禁将该师调离波斯尼亚。
2. 该师军官团须由穆斯林组成,他们有大量曾服役于奥地利军队的人员可供遴选。
3. 应允许该师将武器保留至战争结束。
4. 不得从哈吉芬迪奇军团抽调兵员,该军团已承担本地区防务。”
最终,党卫军无视了穆夫提的建议——志愿者虽被允许保留武器至战争结束,但仅限服役期间。尽管伯格尔声称“不排除将(哈吉芬迪奇)军团成员编入党卫军部队的可能性”,但出于军事需要,在侯赛尼(Husseini)甚至尚未返回柏林之前,已有六千名士兵被征召。德国人还试图招募哈吉芬迪奇(Hadziefendić)少校本人,但这一计划未能实现:该少校及其55名部下于10月2日在图兹拉(Tuzla)附近被游击队击毙。
尽管穆夫提(Mufti)竭力推动,但截至4月14日也仅有8000人自愿加入该师, 这一数字远不足以填补编制。若伯格尔(Berger)向希姆莱(Himmler)的报告属实——他在4月最后一周声称“有20000名波斯尼亚人和8000名桑扎克(Sandjak)地区士兵可供服役”,那么这些人显然并未主动应征——最终,希姆莱于5月5日亲自访问萨格勒布(Zagreb)并宣布该师将接受所有信仰的士兵,但规定“天主教徒与穆斯林的比例不得超过1:10”。冯 奥布沃泽(Von Obwurzer)似乎比帝国领袖更热衷于招募天主教徒,后者对此批评道:
“冯 奥布沃泽的行为就像一头闯进瓷器店的大象……他公然违背我的命令,将宣传重点放在天主教徒身上。”
最终,约有2800名天主教徒被征召入该师,而这令希姆莱大为不满。
德国人最初决定满足洛尔科维奇的请求,在克罗地亚境内组建并训练该师。训练地点定在泽蒙(Zemun)的军营,但4月11日布劳恩(Braun)视察该地时发现此处仅能容纳8000人——另一问题是,第117猎兵师(117th Jäger Division)也计划同期在同一区域组建。布劳恩向菲利普斯(Phleps)汇报称,由于场地不足,只能考虑在德国境内寻找训练场地。
该师的通信营(signal battalion)被规定仅由德国人员组成以避免语言/沟通问题——该部队的组建于4月27日在党卫军“戈斯拉尔(Goslar)”军事训练场启动,其内士兵主要为1942年10月和11月征召的新兵——他们刚完成基础训练;而士官(NCOs)大多曾是新兵的教官。一名受训者回忆称:“许多年轻的通信兵很幸运,他们信任的班长和教官后来成为了电台排或电话排的排长。”;其内军官则于5月初从其他部队抽调而来。该部队指挥官是前神学院学生、东线战场授勋老兵汉斯 汉克(Hans Hanke)。一名士兵后来评价汉克“总能倾听士兵的问题,但要求铁一般的纪律和完全的作战准备。他将日常事务交给连队指挥官处理,而自己则大多退居幕后。”该部队驻扎在戈斯拉尔基地的旧战俘营房中直至6月底。由于德军决定不在克罗地亚进行师级训练,原定将部队转移至萨莫博尔(Samobor)的计划被取消。
1943年7月2日,在勒皮(Le Puy)的火车站中留影的波斯尼亚籍党卫军志愿山地师(13SS)的师内通信营营内的军官和士官们的留影——从左往右第二位看着镜头的那位便是该营营长汉斯 汉克(Hans Hanke)
1943年7月1日,正准备乘车离开党卫军“戈斯拉尔(Goslar)”军事训练场的该师师内通信营营内的军官和士官的留影——从左往右的第二位(露出侧脸的那位)军官还是该营营长汉斯 汉克。
招募活动结束后,波斯尼亚志愿者的实际征召工作随即展开,但这一过程并不顺利:在特拉夫尼克(Travnik)地区,德军闯入当地清真寺的祈祷仪式——其不仅带走了志愿者,还当场强征其他适龄青年入伍;次日清晨,部分被强征者逃亡。另一方面,也有克罗地亚军人主动逃离原部队加入该师,这一过激举动甚至导致萨格勒布街头发生了枪战。洛尔科维奇(Lorković)为此向冯 奥布沃泽提出抗议,德军最终同意将这些士兵遣返原驻地。关于志愿者本身,一名党卫军军官写道:
“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但大多数一贫如洗且目不识丁。这些男性抵达时需接受我方检查:其头发被剪成普鲁士样式并进行除虱——而记录他们的个人信息十分困难,因为许多人连自己的年龄都不清楚,我们只能进行估算;而有些人有多个妻子,这种情况下必须确定哪位妻子有权领取丈夫的军属津贴。”
另一位德国人评论道:
“我们在泽蒙的工作包括接收志愿者,体检,发放制服并(最终)将其移交至训练单位——但由于肺结核和癫痫等疾病盛行,大量候选者无法被接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