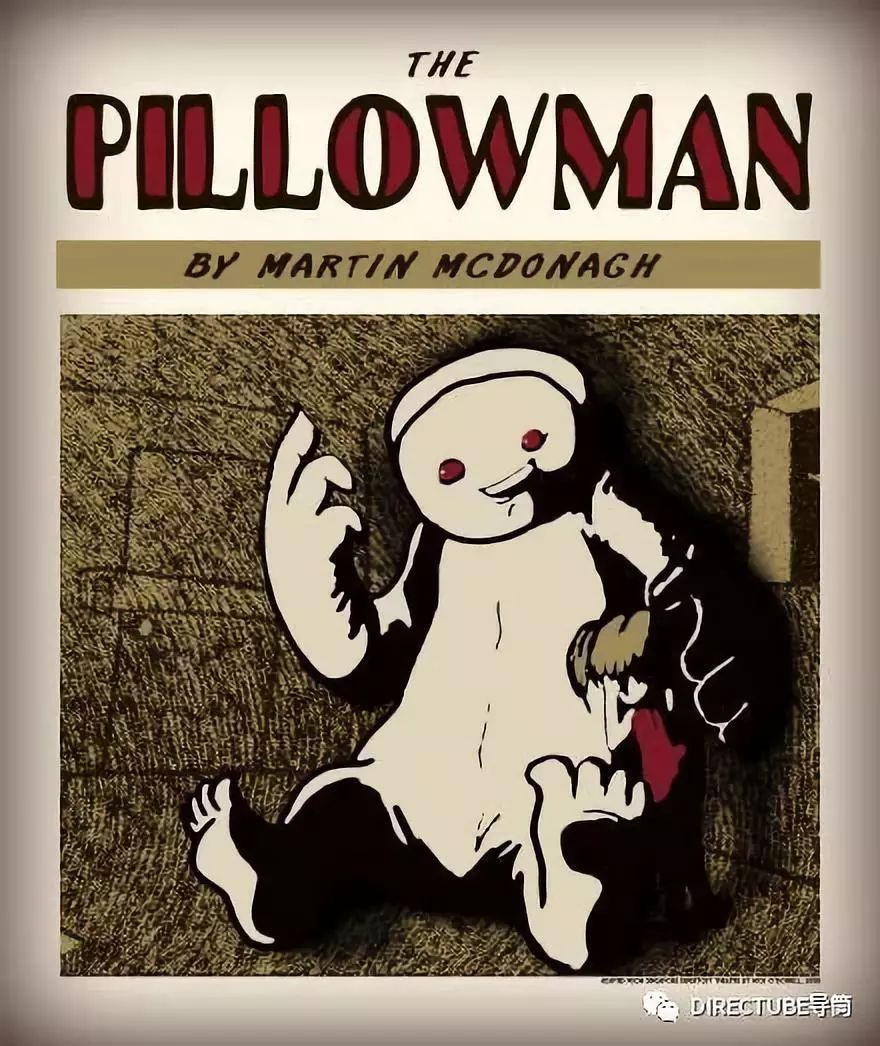2019年9月,由《三块广告牌》《杀手没有假期》导演/编剧马丁·麦克唐纳创作的话剧《枕头人》将来到上海,2003年,麦克唐纳编剧的《枕头人》在英国伦敦上演,引起巨大轰动。之后,《枕头人》又相继在纽约、巴黎等地掀起了一股黑色浪潮。
"我之所以行走于喜剧和残酷之间,是因为它们一个照亮了另一个。我们人都很残忍,不是吗?我们有时候不是处于这种极端就是那种极端,这就是希腊人所处理的戏剧。"
--马丁·麦克唐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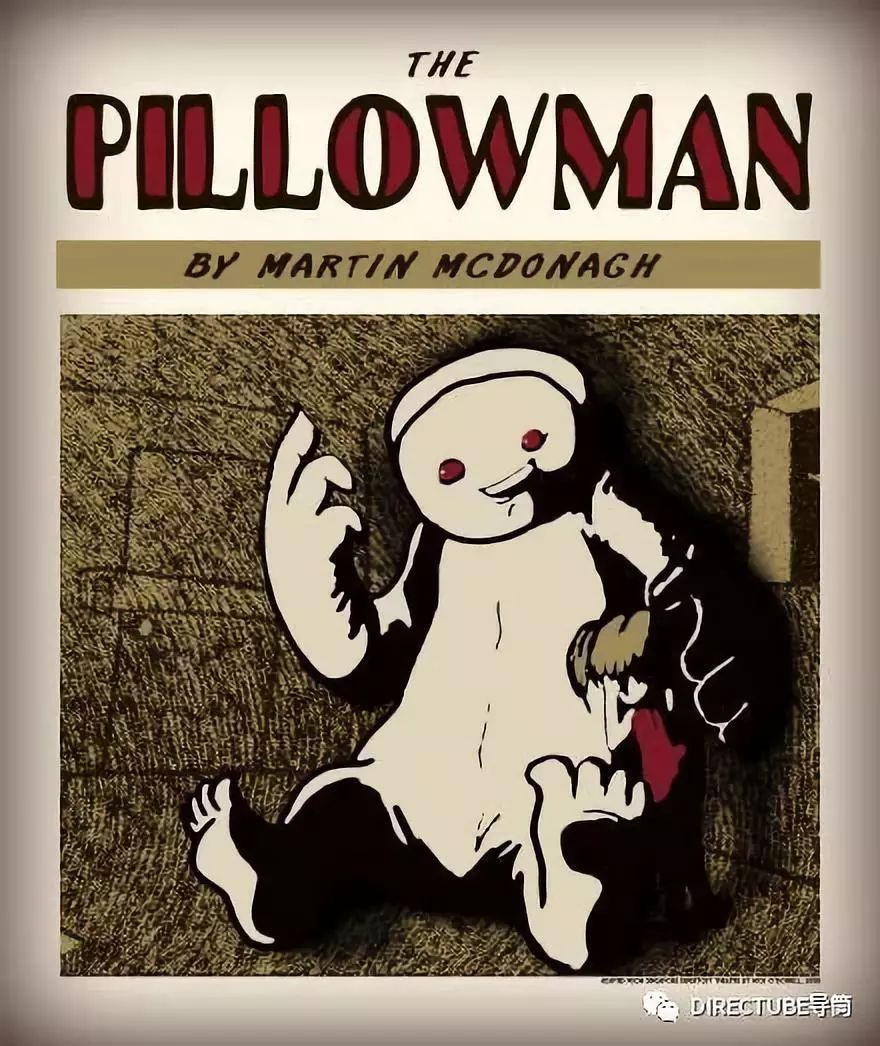
导筒专访来自上海戏剧学院导演戏导师、话剧《枕头人》导演周可,一起走进她在电影和话剧世界的思考与裂变。
剧情简介
一个小镇,三个儿童相继失踪。其中两人已被证实惨遭杀害,而第三个孩子至今下落不明。一连串的证据将怀疑指向了在小镇屠宰场工作的业余作家卡图兰。审讯室中,随着警探图波斯基和埃里尔的深入调查,卡图兰所写的一个个关于"虐杀儿童"的作品也呈现在了观众面前……第三个失踪儿童的命运究竟如何?作家和作家的弱智哥哥,谁才是真正的凶手?卡图兰的小说仅仅是一个个"暗黑童话"故事,还是对现实世界"精神本质"的真实记录?
周可简介
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导师、可-当代艺术中心创立人舞台剧作品:《圈子》《晚安,妈妈》《一根骨头四条狗》《谈谈情,说说谎》《情书》《青春禁忌游戏》《堂吉诃德之梦幻骑士》《婚姻风景》《浮生记》《情人》《爱情有什么道理》《怀疑》《枕头人》《王牌游戏》(中方导演)《邮差》《审查者》《奥利安娜》《妈妈,再爱我一次》《桃姐》《酒干倘卖无》(中方导演)《乱打莎士比亚》《拉贝日记》《啊!鼓岭》等;电影作品:《保持沉默》编剧/导演(周迅、吴镇宇、祖峰主演,2019年上映)。
采访正文
导筒:
这次话剧《枕头人》来到上海,和之前相比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之前看到的开场舞台设计视频很能引发观众的好奇。
周可:
我们的舞美是一个变化,档案盒从上面还是下面,左边还是右边,前面还是后面,这其实是由观众来打开的。观众可以从我们所呈现的这些碎片当中,自行组接成一个他想要的故事。我觉得它同时也像一面镜子,就是你心中藏有多少善和恶,可能就决定了你将如何去总结这个故事。
《枕头人》里卡图兰有句台词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小说家的首要职责是讲一个故事,或者更准确的说,一个小说家的唯一职责是讲一个故事。对此我深信不疑。讲好故事,我觉得其实并不一定要赋予它什么主题意义,或者即便有主题意义,作者并不想告诉你,我觉得更多的是在于你去思考的那个过程,那个是有趣的。我们这次还增加了一些盒盖的处理,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正去感受到空间的多维性。
另外就是音乐,我刚才说到了的张楚老师专门写了关于《枕头人》的主题曲叫《羽毛》。张楚是一个内心非常柔软的摇滚歌手,他自带一种苍凉的、迷茫的、永恒的少年气息,但这种忧郁的气息当中,又能感受到他内在的那种对阳光和温暖的渴望。我觉得他的气质和音乐的气质跟《枕头人》非常的吻合,莫名其妙特别吻合,所以我们会放在整个演出结束谢幕之后的一个彩蛋中出现。
张楚
另外我们这次的灯光设计是任东生老师,他是张艺谋的灯光师,他自己做过很多的好作品。这次对我们的灯光来讲,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升级。另外我们在文本上做了一些调整,我们把过去被拿掉的一些台词放了回来。所以这些台词可能演了五年都没有说过,但这次是第一次我们把它从过去的文本当中拿出来,以至于扮演米哈尔的演员拿到剧本后突然说:我怎么从来没有说过这些台词。我说这个就是原来剧本当中的,他说我知道,可是好像加了这几句台词以后,米哈尔的整个人物都变了。我说其实因为我们五年来都变了,所以可能我们也是逐渐的需要一些变化。
导筒:
您今年在话剧、电影两个领域都有作品问世,电影方面完成了第一个长片。自己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周可:
《保持沉默》其实是四年前的作品,那时我觉得也是机缘巧合,有机会去做这部长片。我个人觉得对于舞台剧导演来讲,尝试做电影长片,既是一个挑战,同时又是另一种愉悦,是痛并快乐着的一件事。在电影当中虽然会受到技术、资金各方面的限制,但是在有限的条件下,我觉得导演还是能够尽可能依照自己的想法去呈现和表达。
舞台剧毕竟是表演的艺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导演是要“死”在演员身上的,所以大部分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对象就是演员,就是你更多的,在80%以上的时间精力是在跟演员一起工作。这两种体验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对导演来讲电影的可能性和空间可能性更大。
导筒:
这两个作品都涉及到了悬疑或人性里的罪行展示,您觉得在电影剧本的创作上会有怎样的不同?比方说话剧更多区分在于演员,在不同城市公演还会对剧本做一些改变,但电影是一次性的。
周可:
我觉得,其实对于导演来讲,电影是两次创作。第一个是从文本到影像的创作,其实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也会受到各种条件的影响,不断地修改剧本,比如说《保持沉默》的结尾,其实当时我们希望在「挟持」以后,会有“车戏”,然后有追击,天亮之前,来到一个冰天雪地的地方。那其实会有场景的节奏变化,但是受到各种条件的影响,在拍摄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在房间的天台上完成这个部分。
第二次是在剪辑上的创作,比如说,其实在剧本中是直接从香港文化中心化妆间里的案件开始的,但实际上在后期剪辑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应该从十几年前把孩子送走的那个事件开始,本来那个画面是存在于回忆当中的,但是现在作为开篇以后,我觉得挺有趣的,这个开篇的送孩子走,种下了一个因,然后发生一系列事件,直到结尾,在酒吧里,端木兰律师(周迅饰)保留了那个孩子,成立了新家庭。其实这就是“得”,前面是“失”,后面是“得”,所以这其实也是两个女性完成了一头一尾的前后呼应。我觉得这是在二次创作,也就是在剪辑的时候才完成的。
导筒:
周迅的角色本身也有特殊性,她在北京与香港两地工作,这次选择庭审背景是香港,您是怎么决定的?
周可:
一开始,我们写了一个完全发生在北京的版本,但是因为涉及法律问题,所以没有被通过。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不一样,英美法系当中是有陪审团制度的,它遵循“疑罪从无,宁纵勿亡”。因此,在这个情况下才有可能用“保持沉默”这个辩护手法来脱罪,以迫使检方去寻找真相。但是在我们现行的大陆法体系当中,其实是不可能这么去操作的。
所以从故事性上来讲,或者说从整个文本空间来讲,以香港为背景可能会更广阔,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是,吴正为(吴镇宇饰)和端木兰一开始说好要留在香港,但这几年大陆的发展很快,香港其实是落伍了,所以当端木兰选择回到大陆以后,两人就渐行渐远了,直到后来端木兰再回去,当年两人分手的原因浮出水面,端木兰当年违背两人约定回到北京,但是吴正为出于知识分子特有的骄傲,选择不问,就把两个人的事搁置了,但实际上,当初两人只要多问一句或互相多关心一下(就好了),而且吴正为最后给出的原因是北京很冷,对香港人来讲,北京真的很冷,但是万文芳(周迅饰)就问他,你去过吗?
其实,人和人之间的误解、民族和民族之间的误解、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误解,不同的地方的人之间的误解,有时候是因为并不了解差异,然后又不想主动去解除误会的时候,那这个误会就放在那里了。虽然我们当时就是无心插柳的,但是拖了四年到今天再上映,突然发现它有着某种特别奇妙的映射。
导筒:
你们当时在香港拍摄的时候,有没有主动去看他们的案件审理,或进行相关法律咨询?
周可:
有,当时在写的时候有法律咨询和顾问。吴镇宇本身有很多香港的大律师朋友。所以在过程中我们也都有保持一些询问。其实有一些观众看完以后不太理解,说为什么连真凶都没有找到,就把男孩给放了。其实在英美法系当中,检方虽然说你可能是犯罪嫌疑人,但并不代表你有罪,你是否有罪不是由法官,是由陪审团来决定的,那检方和辩方都分别提供一些证据。那么在当时那个情况下,虽然端木兰提出了所谓的第三个人,那有些观众就会提问说她为什么不去查第三个人是谁,警察为什么反驳她没有第三个人。其实做辩方律师来讲,她不需要去查到真凶是谁,我只要证明有这个可能性,而且我只要把这个可能性就像“伊阿古种在奥赛罗耳朵里的种子”一样,让陪审团相信有这个可能性,剩下的问题应该是由警方、检方去解决的。
法庭上端木兰提出一个假设说第二刀有可能是田景程来刺的,只是一个假设,并没有说你一定有罪,但田景程在法庭上的过激行为,导致整个审理现场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这些其实都是律师的手段,这个手段就是要让我们的陪审团看到,你换一个角度去想,如果你们之中有一个人对这个小孩是真正的凶手存在着疑虑,你们就可以判他无罪。那么至于真正的凶手是谁,是判这个人无罪以后你们自己去查。让警方去查到底凶手是小孩还是田景程。我觉得是跟我们的办案体系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很多观众可能并没有这方面的了解,所以他在看的过程当中,他就会觉得怎么凶手也没有找到,就把这个人给放了,这个也是挺有趣的一件事儿。
导筒:
您的电影和话剧作品都有涉及到通过孩子身上的这种犯罪,或者一些因素来表现他们的变化,比如孤儿院里的一些身份互换。您是怎样来看待孩子,或者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观察。
周可:
我觉得大家一直都在说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其实完全就没有。后天给他什么,他就是什么。我个人觉得这个孩子的原生家庭占很大原因,对他的人格塑造有影响的,我认为至少对一个人在成年之前有70%的影响。他的童年如果遭遇了一些阴影,这个孩子其实要花很长的时间,甚至是一生的时间来治愈他的童年阴影。
如果孩子在童年是获得安全感的,是有爱的,那他长大以后也许会碰到很多的艰难,但是他在土壤时期,就是被培育时期,他拥有的爱和能量会让他在抵御这种黑暗时更有力,甚至于他可能会更加地从这个黑暗中挣脱出来。
但是如果孩子的性格形成时期,本身就生活在黑暗当中。如果他长大以后,再遇到黑暗,他很难有能力把自己从黑暗当中拔出来,很容易被黑暗吞噬。因为当我成为母亲后,我就觉得孩子生下来,你跟他有十个月的关联,他的命运跟你是真的紧密,虽然我们说你要把他当成一个独立个体来看待,他不是属于你的,他也不属于任何人。但这个独立个体他毕竟在成年之前,他是受到周围环境的很大影响的。
对一个妈妈来讲,其实她有责任来考虑他的温度,他的湿度,考虑他整个空间和整个的氛围,而且不停地观察这棵苗、这颗种子到底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去伸展,我觉得这是一个母亲的天性。但是我觉得很多父母可能自身都比较扭曲的,他自身都带着他原生家庭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父母看不到孩子身上的问题,也无暇顾及孩子身上的这些问题,甚至于他们把自己在这个社会当中所遭受的不幸困惑都发泄在更幼小的、更无力的孩子身上,于是就导致了进一步的被扭曲。这个是需要被终止的,它是需要有人来提醒。
导筒:
创作中您觉得和演员交流时,会花大量的时间与他们进行怎样的碰撞,会希望他们带来新的东西吗?
周可:
我觉得演员和我的沟通,其实是在进行价值观和世界观的碰撞。我们对善和恶、爱和恨的理解。我们经常在排练场吵做一团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大家对于善和恶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
比如你看到一条即将死去的狗夹在一个石缝里面,你会怎么选择?你是会想办法救它,还是会索性给它一下痛快,帮助它赶紧死掉。这里大家对善和恶不一样,就会选择不一样的行动。不一样的行动背后,看起来好像那个选择一板砖把它拍死的人很恶,但是那个恶的背后难道没有藏着一种怜悯之心吗?
想尽办法要救它的那个人,看起来是很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最后你如果救了它,也许它还是会死去,或者是没能把它从里面救出来,让它先抱有希望怀着希望,然后绝望地死去。这对它来讲,是不是更大的折磨?这里面有没有恶,还有就是你的出发点到底是为了证明你的善良才去救它,还是说你觉得善良的人都应该这么做。
所以这里面会带出很多问题,我们经常在一起会论论的是这些,就是我们会如何在舞台上行动,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行动。比如说子川来演卡图兰,他就一直在跟我讲,他说周老师我绝对不相信一个14岁杀了自己父母的人,会是一个健康的人,或者是你们所说的那种很纯净的、内心有大爱的人。他写了400多篇这么变态的故事,这个人的内在到底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每天都是在拷问着我们:怎样去撇掉我们被既定观念限制住的善恶观,从而重新发现人性。
导筒:
在今年欧洲大的电影节上,很多偏类型的犯罪电影,比如《寄生虫》《小丑》,在非常艺术化的评委系统里也受到了高关注,您对此怎么看?
周可:
《小丑》我还没来得及看,但是《寄生虫》我觉得其实挺高明的一个地方,就是它似乎是在写现实生活,但其实你通过它的表演和场景设置,会发现它其实是从现实生活中抽离出来的,我觉得它用了夸张甚至有一点点变形的方法来让你看到这些人。
奉俊昊《寄生虫》 (2019)
电影中上流社会的这一家人,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很聪明的有钱人,如果没有经过剥削,他们怎么可能成为有钱人,他们一定是很精明的。而往往是那些下层人民,他们是朴素的,他们相对来讲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所以他们其实是没有什么头脑的。但《寄生虫》呈现出来的是,整个上层精英那么单纯,每个人都很单纯,几乎就像白雪公主一样已经脱离了现实世界。而这些属于下层的人民,那么狡猾,那么工于心计,他们能够如此默契的配合,搞掉他们路上的一个个羁绊,对自己同阶层的人下手都非常得狠。
但是这个狠当中又是有底线的,比如到最后那一刻,过去那个管家回来,他们要不要把这个管家和她的丈夫给灭口?他们也有过纠结,而且就是在这些同阶层的人心中,其实反而朴社长是他们需要感激的一个人,因为他给了他们吃的,所以他们两个人都同时对朴社长的照片鞠躬。所以这些我觉得他本身已经有了一些变形了,已经有了抽离出来的部分。
导筒:
在大陆,很多影迷会觉得《寄生虫》里面的一些人物或者情节写实性存在问题,似乎有话剧的影子,而产生质疑,您又怎么看待?
周可:
说它更接近舞台剧,可能是因为很多看惯电影的观众觉得它场景比较少、比较集中。但实际上我觉得以此来划分舞台剧和电影,是不公平的。比如说在昆汀《无耻混蛋》的开场,德国军官审问法国农民那场戏,那就是典型的戏剧性,是很完整的一场舞台剧,那你怎么来划分?因为它是电影,所以它就是电影吗?不是的。其实你会发现姜文《让子弹飞》里,三个人在一起吃饭的那场戏,也非常完整,戏剧性很强,很像舞台剧,只不过他用镜头去把它展现了。那如果没有了戏剧性,镜头语言要呈现什么?它也不是只有一种可能性。所以我觉得那样的观点是比较狭隘的,但是确实在犯罪题材当中,我觉得我们能更多的关注人性。
昆汀·塔伦蒂诺《无耻混蛋》 Inglourious Basterds (2009)
包括去年的《小偷家族》,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所谓的犯罪题材还是家庭伦理题材,其实究其根本到最后好的电影都是关注人性的深处,像好的戏剧一样,我们看到的行为只是一个表象,我们不在这个表象的基础上急于贴标签,急于判断它的正确和错误,而是要去关注表象背后,到底是什么促使他有这样的行为,那是人性根本所在,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艺术探究的最有价值的地方。
是枝裕和《小偷家族》(2018)
导筒:
根据您最近的一些观看经历,有没有一些作品可以推荐给观众,话剧和电影都可以。
周可:
话剧的话,立陶宛的《伪君子》,这个话剧很有趣的。改编传统的戏剧,其实对所有的导演来讲都是有难度的,特别是几百年前的作品,今天再来上演它的时候,它于当代的意义何在。我觉得这版的《伪君子》改编得非常好,实际上它紧贴我们现在的网络时代。它不但贬斥所谓的伪君子这一个人,而且是让人人都看到,其实是我们在纵容这样的人,打着宗教的旗号来迷惑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伪君子。
它用了凡尔赛宫的花园布景,在那个布景下,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在看上去很美的场景下,肮脏的交易在进行着。它用了多媒体让你能够看到在绿色宫殿里面,当多媒体跟随着演员到了幕后,然后就产生了剧烈的变形,所有在台侧发生的对白行为都是变形扭曲的。
这些其实都很有趣,我觉得都是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一面和那一面。就像《罗生门》里面其实最根本的一个哲学观点,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其实是由看上去貌似完全截然相反的一些观点组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但是前提是,你必须要接受那个跟你看上去完全不一致的观点。
黑泽明《罗生门》 (1950)
另外还要推荐给大家的是NTlive放映的戏剧影像,由英国国家剧院与布里斯托老维克剧院联合出品的《简爱》以及阿尔梅达剧院出品的《理查二世》。
《理查二世》(2019)
导筒:
您后面有什么样的创作计划吗?
周可:
后面的计划,我觉得可能还是在话剧,在舞台剧、音乐剧还有电影之间。因为对我来讲,其实目前这些事情还没有做够,但是我不知道哪一天做够了,也许就不想做了。目前是这样,有一些音乐剧、话剧和电影都在谈。
《三块广告牌》《杀手没有假期》导演/编剧
暗黑童话领域的恶趣味大师
继昆汀·塔伦蒂诺之后,最有才华的编剧
《枕头人》编剧:马丁·麦克唐纳Martin McDonagh
"我之所以行走于喜剧和残酷之间,是因为它们一个照亮了另一个。我们人都很残忍,不是吗?我们有时候不是处于这种极端就是那种极端,这就是希腊人所处理的戏剧。"
--马丁·麦克唐纳
马丁·麦克唐纳生于1970年,是继昆汀·塔伦蒂诺之后,最有才华的编剧。2006年,他的《六个枪手》为他赢得了奥斯卡大奖,2008年他自编、自导的剧情长片《杀手没有假期》,因为独特的风格和优秀的品质赢得了众多好评,也为他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的提名。2017年,执导犯罪剧情片《三块广告牌》获得第74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第75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最佳编剧奖,以及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
同时,他也是当代戏剧的代表人物。作为英国"直面戏剧浪潮"代表作家,暗黑童话领域的恶趣味大师,他是继王尔德、叶芝、肖伯纳、贝克特之后爱尔兰又一位杰出的戏剧家。他以其荒诞的黑色幽默和挑衅性精神而闻名,他的残酷又幽默的作品为他赢得了无数知名奖项,其中包括三项劳伦斯·奥利弗奖,以及多项托尼奖提名。2003年,马丁·麦克唐纳编剧的《枕头人》在英国伦敦上演,引起巨大轰动。之后,《枕头人》又相继在纽约、巴黎等地掀起了一股黑色浪潮。
导演的话
周可
我童年时期最深的记忆之一,就是夏天的晚上,坐在屋外的"坝子"里乘凉。大人们坐在躺椅上,摇着蒲扇,跟围在周围的小朋友们讲故事。随着故事的展开,孩子们的想象力便突破了这个小山村,飞出了环绕的群山,飞向了另一个又远又大的不可知的世界。
"故事"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感到恐惧,感到期待,感到幸福,感到悲哀;故事也让我们体验到了丰富的情感。而编剧马丁-麦克唐纳是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人。他化身为"卡图兰",拿起了笔,写下了那些看起来是虚构,其实很真实的故事。于是有了《枕头人》这个剧本。
不知不觉,《枕头人》已经陪伴我们一起走过了五个年头。那个温暖的、忧郁的、带着一丝悲凉的诗意的枕头人,像一个谜一样,引导着我们走进人性世界那黑暗且光明的深处。五年的时间里,我们有过三个"卡图兰",三个"埃利尔",不变的是"警官图波斯基"和"傻哥哥麦克"。五年来,每一次的排练,都像是一次新的开始。我和演员们在排练厅各种争吵,挣扎,"互相伤害",听他们发誓说以后再也不演《枕头人》了。然后看见他们在舞台上那个小盒子里,越来越默契,也越来越成为人物自身,这或许就是"枕头人"的魅力所在。
今年,《枕头人》即将走进大剧场,作为导演,不会改变的是我们依然要跟观众们好好地讲故事。因为"小说家的唯一职责就是讲故事"(卡图兰)。如果说有什么和小剧场不同,当然会在视觉和听觉上做很大的变化。可以说从舞美、造型、多媒体、音乐各方面都在原有元素的基础上进行了升级和再创造。当然,我不会"剧透"太多,如果你想知道,就走进剧场自己来看吧。
《枕头人》获奖情况
2004年英国奥利弗最佳戏剧奖
2005年美国托尼奖六项提名
2005年纽约戏剧评论圈最佳戏剧奖
在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的发展潮流中,鼓楼西制造坚持着特殊的航向:相信"一剧之本"是演出成功的基石,相信真正的先锋是思想上的新锐。鼓楼西制造借取西方经典文本的力量,以实现思想品格与艺术品质的戏剧理想,出品并制作了一系列获得普利策、托尼、奥利弗等奖项的西方当代经典戏剧,其中多数剧目是在中国舞台上的"首秀",有着非凡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鼓楼西制造出品、制作和演出的话剧代表作品有:马丁o麦克唐纳《枕头人》[英](2014)、曹禺《雷雨》[中](2014)、尤金·奥尼尔《早餐之前》[美]、马丁o麦克唐纳《丽南山的美人》[英](2015)、波拉o沃格尔《那年,我学开车》[美](2015)、玛莎o诺曼《晚安,妈妈》[美](2016)、尼洛·克鲁斯《烟草花》(《安娜在热带》)(2017)[美]、英格玛·伯格曼《婚姻情境》[瑞典]、哈罗德·品特《背叛》(2018)[英]、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等。
鼓楼西不求高产,精耕细作,力求将"鼓楼西制造"打造成精品戏剧品牌。经过四年的积淀,鼓楼西已不再满足于向西方借取文本,改编自中国当代经典文学的大剧场剧目《一句顶一万句》,在著名导演牟森的带领下启航。这标志着"鼓楼西制造"走出小剧场,以更多元的作品面向观众。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