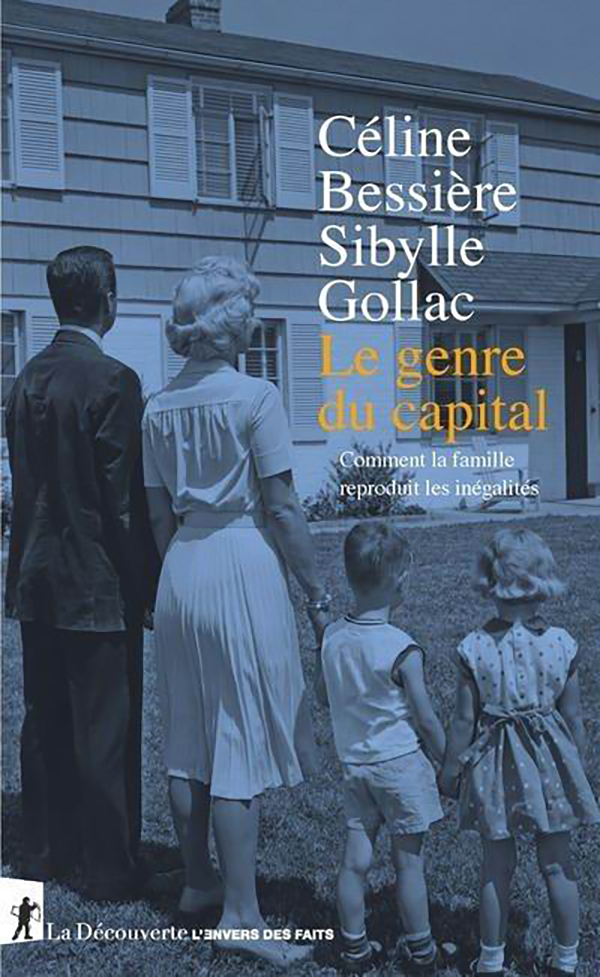
《资本的性别:家庭如何再生产不平等》,[法]贝斯尔、高拉克著,la Découverte出版社2020年2月出版,326页
越来越多的女性在职场上工作。在同等工作下,她们的工资虽然仍低于男性,但差距在减小。平等远没有达到,但其在各个领域都有进步。那么在家庭遗产方面呢?家庭经济资本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又是如何分配的呢?贝斯尔(Céline Bessière)和高拉克(Sibylle Gollac)提出的问题是重要的,因为,在读过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之后,每个人都知道,在二十一世纪,在一户家庭内部资本的积累,重新成为构成我们社会的阶级结构和财富差距的中心要素,比如对房产的占有。
“继承的回归”同时也是家庭机制的回归,这一家庭机制是经济和阶级建构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应该在这一点上寻求问题的答案。
我们意识到,今天的家庭,已经和二十世纪时多数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所描绘的理想图景完全不吻合了:今天的家庭完全不能还原成一个只有情感关系和无利害关系的地方,被动员起来仅仅是为了保证子女在学业上取得成功。家庭并不仅仅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上,也建立在物质基础上。家庭是一个产生财富的经济机制,并组织这些财富的流转和分配。
因此有必要打开黑盒子(这一黑盒子通常以“户”作为统计学单位来研究家庭遗产),更多了解在家庭内部分别流向丈夫和妻子、儿子和女儿的资本。
离异和分居、生者之间礼物的交换以及某位家庭成员死后遗产的继承,这些都是家庭生活的重要时刻,在这些时刻,我们能以最鲜活的方式来观察发生在家庭内部,以及更广泛的“大家庭”
(Maisonnée,见Florence Weber,
Penser la Parenté Aujourd’hui: La Force du Quotidien
, Éditions rue d’Ulm, Paris, 2013)
内部的“私密交易”
(transactions intimes,见Viviane Zelizer,
The Purchase of Intimacy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2005)
,衡量相关物品的价值,并分析这些物品传递到男性和女性的方式。
这时,我们就会出乎意料地发现,那些参与到这些交易中的法律职业人士——公证人、律师、法官,他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再生产甚至加剧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
当然,这些性别不平等根据社会阶层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在平民阶层,钱是女性的问题;而在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阶级,资本——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都是男性的事务。
目前缺失一种统计学调查,这种调查能够区分构成一户家庭的多个个体和分别流向每个个体的资本份额,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民族志的方法才能获得必要的数据。这个任务是艰巨的,因为在法国,人们并不是跟谁都能谈钱,更别说这些通常被认为是家庭秘密的经济协议。因此要和这些家庭建立很强的信任关系以便得知这些秘密,让他们愿意给调研者看私人文件、公证文书、信件和照片;调研者能被邀请参加婚礼或葬礼,能收集到各个家庭成员的不同观点,因为不同的兄弟姐妹,可以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描述他们父母的遗产继承的步骤,并不总是算入同样的物品,也不以同样的方式。因此完全不用惊讶这些民族志是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逐步完成的,更何况观察和访谈应该相互补充,重复,在长时间段里被实现。调研者因此在超过十五年的时间里追踪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房产策略。这些家庭轶事便是这本书的“血肉”,也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有原创性的、珍贵的文本。
贝斯尔(右)和高拉克
贝斯尔和高拉克也赢取了法律专业人士的信任,深入公证员的研究和律师事务所的幕后,参与家庭成员和这些法律人士的会议中,对这些法律人士做深入的访谈,使他们真诚地解释为什么以这样或那样的态度处理某个离婚案或继承案,所有这些都不容易。同样,被允许观察在法官办公室里所讨论的离婚或分居的家庭案件,并且相关夫妇也在场,也是不容易的。她们所观察的家庭成员、所采访的法律人士很快就成为读者所熟悉的人物。我们伴随着事件的进展在不同章节里读到他们,也因此了解了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家庭成员和法律人员的关系,和他们的配偶、他们的兄弟姐妹的关系,他们对和自身相关案件的理解。两位社会学家对受访者所展现出的强烈的同情心,从来都没有以销蚀客观性为代价,反而使本书的阅读显得更加生动。
除了这些民族志瑰宝,两位作者还发掘了一个司法数据库,这一数据库包括由2013年七个大审法院的三千个判决和两个上诉法庭的一千个判决所组成的抽样样本。每个案件都被标注了八百个到两千五百个变量,其中包括性别、年龄、职业。由国家统计局2004年到2015年实现的“遗产”调研也被恰如其分地并入分析中,成为本书调研的背景。伴随着时间,两位社会学家积累了大量的家庭案件仲裁中对男男女女处理的经验,这本书在两位作者的构思下,显然比其标题更具原创性。它从头到尾都被一股有力的女权主义精神所鼓舞,同时又结合了七十年代的“唯物主义”;在事实的基础上,它动摇了大量的原始表象;它生产出新的知识,同时也为社会学打开了新的道路。
涉及家庭案件的律师和法官这些职业在最近四十年里呈现出强烈的女性化趋势,公证员也一样:三个领薪公证员里有两个是女性。然而,这些法律从业人员常常在无意识中以损失女性利益为代价而优待男性。两位社会学家识别出了法官和公证员共同导致这一后果的一个职业行为:反向计算。在分居、离婚、遗产继承这些情况下,人们通常会对物品罗列并对其价值进行估算。最合理的方式无疑是对罗列物品的价值进行叠加,然后除以有权分享的人数,以使伴侣或继承人每个人都能被分配到平等的一份。贝斯尔和高拉克指出,在事实层面上,这一过程的顺序是如何反过来的。公证员一开始就在不同成员之间确立了一个对最终结果的共识,也就是如何对物品分配以及对不同成员的补偿。仅仅是在这一共识达成之后,人们才在考虑到市场行情和税收的情况下,对每件物品估值。这样一来,一栋房屋或一套公寓的价值就会根据不同情况而发生变化,比如所有成员都达成共识希望卖掉它,或是相反,即家庭成员中的某一个试图从其他成员手中买下它。在第一种情况下,所有人都希望估值越高越好。但在第二种情况下,那个购买者则希望估值越低越好,以便以最低价从其他人手中买下它;而其他人则相反,他们希望以最高价的估值卖出而获取最大的补偿金。公证员因此常常被定义成遗产医生和家庭和睦的担保人,他在达成共识——这一共识建立在“遗产协商”和构建等价物的基础上——的过程中扮演决定性角色。而这些反向计算加剧导致了男女财富的不平等。
无论在分居、离婚还是在遗产继承所涉及的财富中,总是有某些物品比其他物品更重要:这可以是一个公司、一栋房屋、一套公寓、一组证劵等等。这些“结构性物品”是公证员首先要分配给继承人或伴侣中的一个的。这些物品的价值能够帮助公证员来计算需要给其他家庭成员的补偿,而这一计算建立在通常和市场价有差距的经济估值上。
然而,统计数据表明,更多是独生子和长子获得这些“结构性物品”,而非次子或女儿。在家庭企业中,一个好的继承人在大部分情况下是男性长子是显然的,但在不动产和证劵的继承中这也很常见。公证员非常重视这一关于家庭的父系呈现,正如他们使用的遗产
(patri-moine, 译者注:patri来自于拉丁语pater,意为父亲)
这个词本身会让人联想到的那样。法国公证员官网上的配图呈现的就是父亲、儿子、孙子,甚至侄子。在公证员等候室里放置的小册子和印刷品都是用阳性来撰写的。
在分居或离异的情况下,无论夫妇是户主还是租户,女性通常都比男性更没有能力保留家庭居所。丈夫保留住宅占百分之四十三,妻子则只占百分之三十二。在有孩子要抚养的情况下,这一差距会减少,但分担看管孩子的情形非常不利于母亲:不得不离开夫妻居所的可能性对母亲而言高达百分之八十,而对父亲而言则低于百分之五十。至于丈夫向前妻支付的补偿金金额,它总是受限于不要威胁到男方的经济状况这一条件,无论男方是企业主还是工薪阶层,即便他是自己决定如何偿债的。
相较于公证员而言,女律师对其女客户的经济利益更加在意,也更加有女权意识,但她们的运作空间通常也是受限的,她们受迫于之前在公证员那里已经决定的遗产协商,同时也认为不应该让丈夫的社会地位或经济状况受到威胁。处理家庭案件的女法官也一样,其中一些法官以女性应该通过工作而得到解放的名义,在判决中拒绝过于优待“吃软饭的女性”。对法律从业人员的社会无意识——这常常是通过反向计算,考虑男性利益,以法律的名义表现出来——的细密分析是本书的主要成果之一。
除此之外,在这些家庭协商中关于交税的自由度是本书的另一个主要成果。正如作者所说,对税收的抗拒是一个有力的家庭凝合剂,即便关于个人税款的保密原则就社会层面上而言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富人就比穷人、男人就比女人更享受保密原则。
对基本生活补贴的征税情况也是不利于女性的。支付基本生活补贴的人(百分之九十七的情况下都是男性)可以在要交的税款中减免这部分补贴,而收取基本生活补贴的人则要在交税时申报并且支付这部分补贴所产生的税款。
同样的不平等还发生在补偿款这一政策上。补偿款是以月息的方式来补偿离婚夫妻中因离异而导致生活水平下降的那一方(大部分情况下是女性)。这个仅仅涉及结婚夫妻的政策,在2000年的一项法案中被大幅削弱。从此补偿款只需要在离婚之时一次付清,付款的债务人(百分之九十七的情况下是男性)在再婚后无需承担两个家庭的开销。更何况,男性通常比女性更多也更快地再次结识伴侣。
更广泛而言,这也是本书的重要结论之一,两位女作者通过确凿的证据指出,表面上看是平等的,家庭法和财产法却在每一社会阶层上利于男性而非女性、利于上层阶级而非下层阶级。
资本和遗产在今天的核心地位使两位作者重新审视了上世纪七十到九十年代研究家庭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这些著作都更注重家庭内部的情感联结,而无一例外地彻底忽视了两位作者提出的问题。由布迪厄和帕斯隆提出的文化资本,是作为遗产而在富裕家庭中传承的,这一带有经济维度、含义丰富的隐喻也对资本传递的经济问题保持了沉默。至于女权主义者,她们尤其把分析和调研集中在工作、劳动和薪资上的社会不平等上。
但是我们也能理解这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不得不承认,在紧随三十年繁荣期后的这一时期,的确是在劳动和文化这两点上形成了阶层之间和男女之间的最深的社会不平等。
本书最强有力的一点也正是以一种微妙而有说服力的方式连接起了阶层分析和性别分析。代际之间的经济传承加剧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遗产的个体化伴随着分居和离异的普遍化,这更削弱了妇女在关系破裂时的经济状况。妇女比他们的丈夫更常见“两手空空”地离开。
最终,家庭经济协商参与了社会阶层间界限的维持以及男女不平等的加剧。阶层的社会关系和男性统治是不可分割的。
经济、法律、社会学,这个调研的对象正是处于这三门学科的交叉口;没有任何一门学科单独就可以呈现所有维度。男性和女性之间家庭资本的分享无法化约成一个单纯的计算问题。要理解的话就要深入法律的奥秘中去,并且分析公证员、律师和法官各自的角色;每一类职业人士都会在法律的基础上加以协商,这些协商根据的是这些职业人士的客户利益,他们的职业原则,以及他们本身的价值体系。识别、解释、理解这些不同维度之间的多重互动,并提炼出这些互动对男女不平等所产生的影响,正是通过对这些私密交易的既同情又客观的观察实现的——而这恰恰是贝斯尔和高拉克所做的:为社会学打开了新的道路和富饶的多学科试验田。
(此文2020年3月23号发表于
La vie des idées
,得到原作者授权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