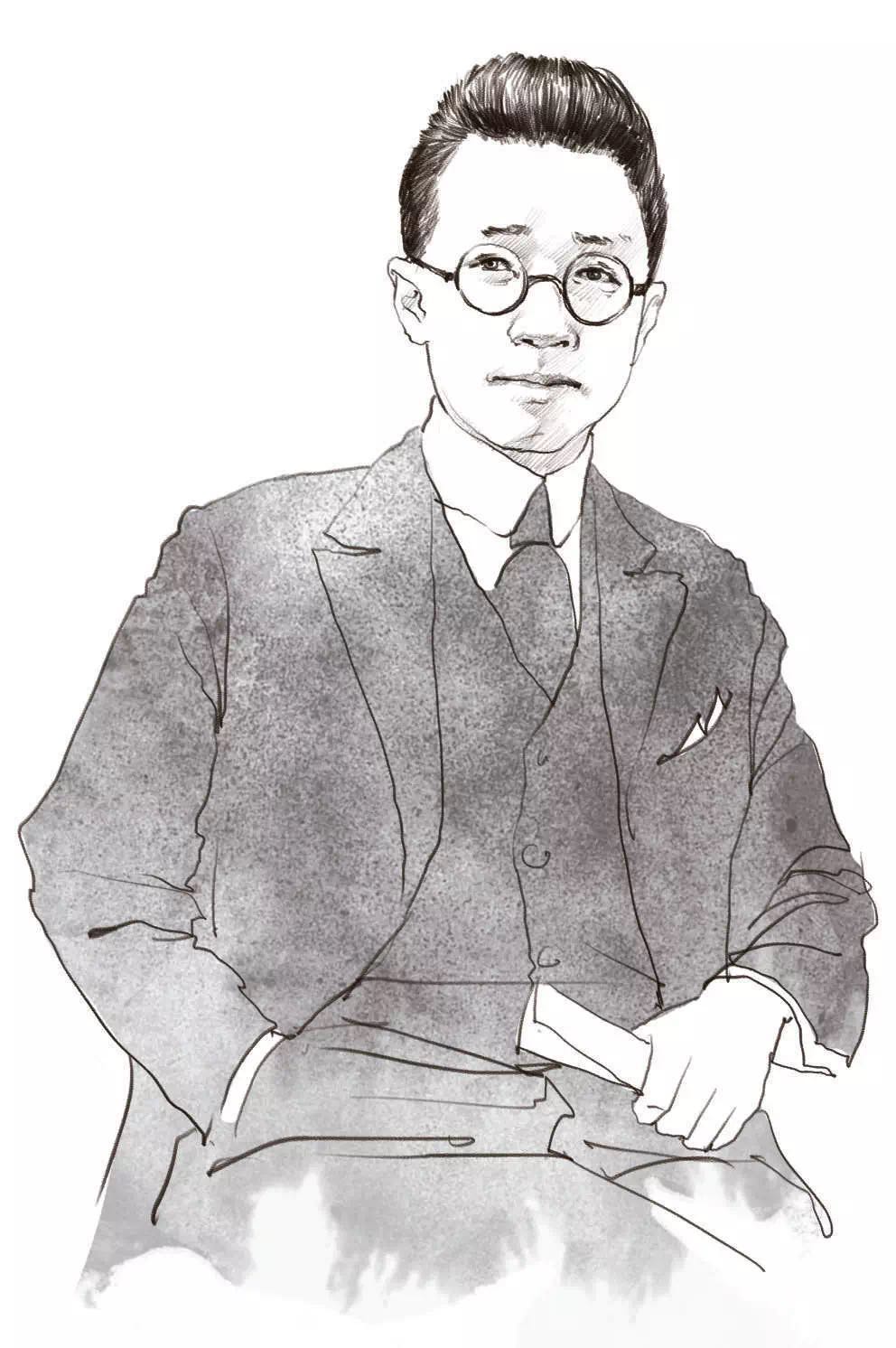很少有哪场历史事件,像1919年的“五四”运动那样,将历史如此清晰明澈地划为两个时代,它既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也是一个没落时代的终局。它蕴藏的巨大力量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更冲击了人们的心灵,以高声的呐喊让人们向过去告别,又以万丈激情将人们带向新的未来。它更给人以一种积极的信心,让人们相信新的、几乎触手可及的光明未来正在前方等待着这个国家的人们。
几乎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到这场为国家命运寻求答案的运动中。从公共知识界和学界,到工商界,再到工人。运动中的每一个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国家中的一员,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国家命运的共同关切也将每一个个人联系在一起。
在“五四100年”来临之际,我们特别策划了“我在,我见,我记得(1919-2019)”专题。当后世回望这场运动时,就会发现,“五四”运动带给这个国家最重要也是最深远的遗产,并不仅仅是那一时代的变革,而是一种历史的自觉:“五四”运动中的中国人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识到历史正把握在自己手中,中国人有能力也有必要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所谓的“历史自觉”正是“五四运动”创造出的大写的“我”。“我”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我”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我”感受到了时代的风云变化,“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正在创造“我们”的历史。
匡互生、梁启超、李大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陈独秀、胡适、顾维钧、陶孟和、孟宪彝、那桐、辜鸿铭、梁漱溟......这些名字,有的如雷贯耳,有的寂寂无闻。但他们都为我们一次次还原着历史的细节。从4月10日开始,我们将会每日在公号推送一位五四人物。今天是胡适——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
撰文 | 林建刚(重庆文理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教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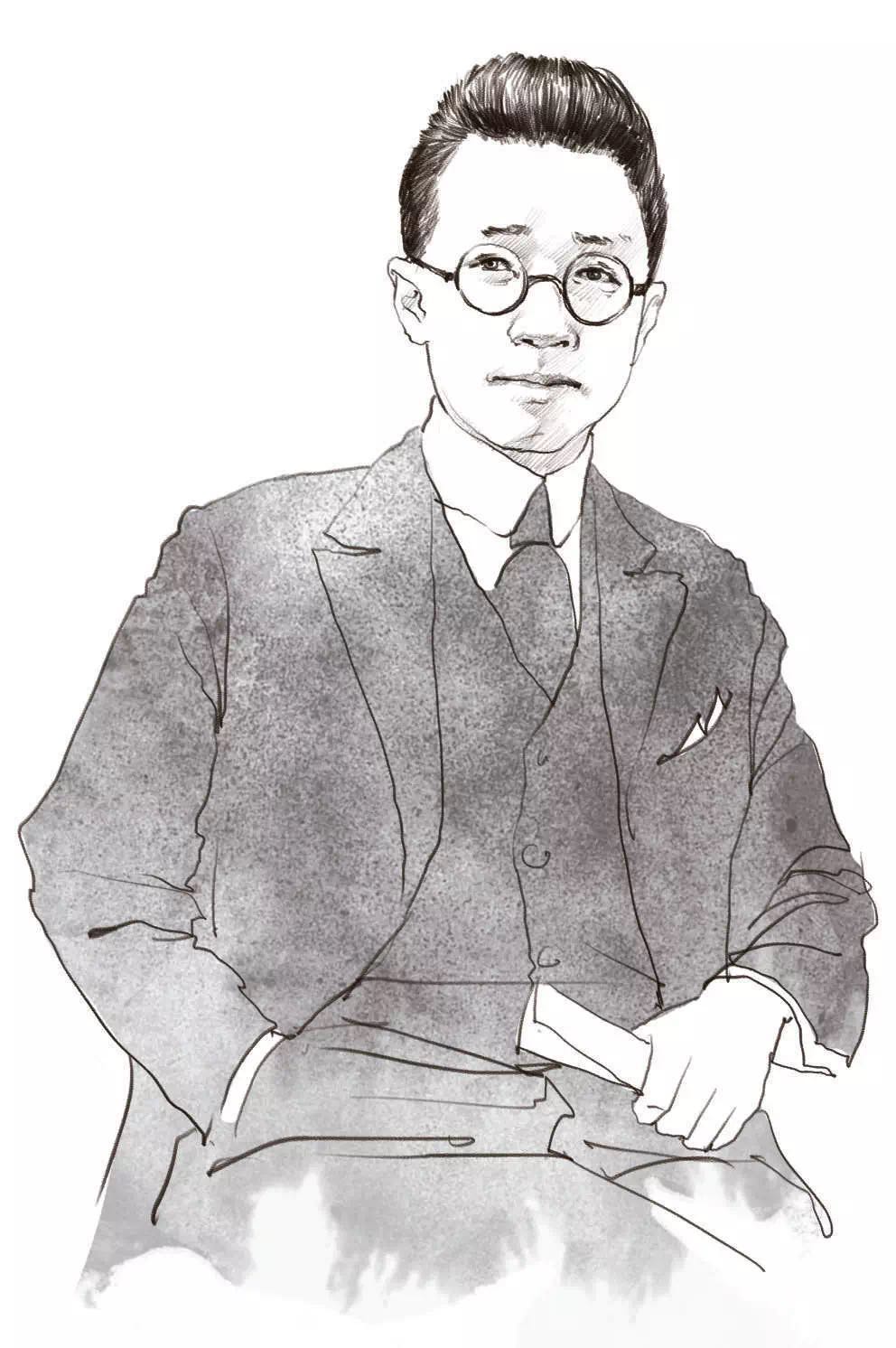
姓名:胡适
时年:28岁
身份:北京大学教授
地点:上海、北京
五四学生运动爆发时,胡适并不在北京,而是在上海给杜威做翻译。不过,此后不久,胡适很快离开上海回到北京,深度参与了五四运动后续的一系列活动。不特如此,五四学生运动中的学生领导者,傅斯年也好,罗家伦也罢,不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与胡适有密切往来。因此,未曾在北京亲历五四运动的胡适,也深度介入了这场运动,是毫无疑问的。
在中国整个现代史上,1919年无疑称得上奇迹迭出之年。从五月四日到最近几周的教师罢课,这一年发生了一系列值得纪念的事件,它们已为大家所熟知,所以我在这里也就无需再提了。但这一年的真正奇迹,应该是这个国家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这种转变的传播速度异常迅猛,连那些对其最后的胜利怀有最疯狂期待的人都感到震惊了。
——胡适《中国知识分子在1919年》
狭义的与广义的“五四”
狭义的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这场运动胡适并未亲身参与。至于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则是“首举义旗之急先锋”。
五四新文化运动,指的是从1917年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舆论阵地,以北京大学为思想场域掀起的思想文化运动。正是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为信号,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应运而生,尔后,这场语言革命进一步演变为思想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核心的三位思想领导者应该是陈独秀、胡适与蔡元培。这一点,陈独秀在悼念蔡元培的文章中说道: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再具体一点说,蔡元培是北大校长,他把北大改造成了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陈独秀是《新青年》主编,正是有了这一舆论阵地,新文化运动才会兴起,而胡适则凭借一系列的言论主张,尤其是首倡白话文运动而“暴得大名”,其成名之速,可谓奇迹。当是时也,属兔的胡适年仅26岁,陈独秀比他大一轮,是38岁,蔡元培又比陈独秀大一轮,是50岁。三人生肖都属兔。故而,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可谓是一只“老兔子”带领一只“中兔子”和一只“小兔子”掀起的思想文化上的革命。
本文以1919年这一年胡适的相关活动为线索,通过分析新旧派及新派之间的分歧、胡适与《新潮》、五四学生运动中的胡适、胡适论五四的是非功过等问题,来论述胡适与广义及狭义的五四运动的关系。
新旧派之间的冲突
五四新文化运动自1917年开始后,遭到了旧派文人的反对。这本是思想主张上的冲突,但在有些旧派文人看来,文学革命乃是动摇国本之举。因此,个别旧派文人利用谣传,寄希望于政治势力来驱逐新派文人。这一思想冲突在1919年达到顶峰。1919年2月,林纾发表影射小说《荆生》与《妖梦》。此外还有一个半真半假的谣言说: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公然去妓院嫖娼。这则谣言,其实是在给北大校长蔡元培施压。当时蔡元培正提倡“进德会”,进德会的会员相约不嫖不赌。如今,被蔡元培举荐成为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公然嫖娼,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应该如何处理陈独秀呢?
于是也就有了1919年3月26日之夜的会议,蔡元培召集相关教授,讨论处理陈独秀的问题。最终,在马叙伦、沈尹默、汤尔和的影响下,陈独秀被迫离开北大。
此后不久,五四学生运动爆发,这场学生运动最终使白话文运动成为主流,新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不过,在这场胜利前后,陈独秀因为旧派的攻击离开了北大,并将他主编的《新青年》带到了上海。
1923 年1月,胡适(右)与陈独秀(左)在上海合影。
胡适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在他看来,陈独秀离开北大,使留在北京的新派知识分子失去了最重要的思想阵地《新青年》,并导致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新派之间的分歧
1919年初,不仅新旧两派之间的思想冲突尖锐化,在新派内部,也有了分歧。这里的新派,指的就是《新青年》同仁内部之间的分歧。具体而言,指的就是胡适与陈独秀、钱玄同在一些议题上的分歧。
胡适与陈独秀的分歧主要体现在“谈不谈政治”这一问题上。1917年胡适回国时,恰逢国内张勋复辟,深受刺激的胡适立誓“二十年不谈政治”,希望从思想文化方面为新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胡适与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曾达成共识。到了1918年年底,一向关注政治的陈独秀忍不住要谈政治了。两人妥协的结果就是1918年12月《每周评论》的创办。一方面,胡适等人可以在《新青年》杂志上继续新文化运动;另一方面,陈独秀也可以在《每周评论》谈政治。《每周评论》创办初期,陈独秀多次向胡适约稿。胡适发表在这份刊物上的文字,大多都是翻译外国文学家的作品。陈独秀对此行径不以为然。
胡适与钱玄同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待论敌的态度方面。胡适认为应该让论敌畅所欲言;不赞同的地方写文章反驳,进一步商讨。钱玄同则是不理睬,痛骂之。胡适对待论敌的姿态,让钱玄同很不满意。
钱玄同与陈独秀是留日派,胡适与陶孟和是英美派。《新青年》内部留日派与英美派的分歧,可能很大程度上源于所受教育的不同,这也是导致《新青年》同仁分裂的重要诱因。
胡适与《新潮》
《新青年》内部同仁的分歧,胡适作为当事人之一,再清楚不过。因此,当1918年年底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俞平伯等人计划创办一份刊物并请他做顾问时,胡适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并建议将刊物的名称定为《新潮》。《新潮》的英文名是TheRenaissance,指的是文艺复兴。胡适在论断五四新文化运动时,都指出这是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
《新潮》杂志于1919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成为当时推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可以说,《新潮》杂志最能体现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具体设计。因此,晚年胡适在回顾这一时期的活动时说:
这封《新潮》月刊表现得甚为特出,编写俱佳。互比之下,我们教授们所办的《新青年》的编排和内容,实在相形见绌。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胡适明确将这场文化运动定义为新潮,并于1919年12月发表了鸿文《新思潮的意义》。他给这场文化运动设置了路线图:“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重铸文明。”
以傅斯年、顾颉刚、俞平伯等人为代表的《新潮》杂志的北大学生们,可谓胡适这一主张的忠实实践者。这一时期,《新潮》杂志提出了妇女解放问题、贞节问题、女子求学问题、青年读书问题等等,都是对胡适呼吁“研究问题”的响应。此后俞平伯研究《红楼梦》,乃是对胡适《红楼梦考证》的深化;顾颉刚的“古史辨”,乃是直接受胡适疑古思潮的启发;傅斯年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学术实践,也都是对胡适呼吁“整理国故”的响应。
胡适评价甚高的《新潮》杂志。
更耐人寻味的是,《新潮》杂志社的核心成员,在五四学生运动中都是领导者。其中最知名的两位,莫过于傅斯年与罗家伦。按照预先设计的示威游行的路线图,他们是要向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提交意见书,并希望美国总统威尔逊来为中国主持公道的。这里涉及当时知识界天真的理想主义情怀。伴随着巴黎和会的召开,坏消息纷至沓来,这种大期望一下子变成大失望。巨大的心理落差是导致五四运动爆发的心理诱因。经历过五四运动后,胡适就多次说过“不存大希望,就没有大失望”的言论。
“火烧赵家楼”并不在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既定计划之内。后来的罗家伦意识到仅仅靠标语口号是不能救国的。救国之道,教育与外交,才是其中关键。此后的岁月中,教育家与外交官,成为罗家伦一生的关键词。
傅斯年与罗家伦的命运,其实也是胡适人生的一种写照。20世纪的中国,读书与救国,自五四运动开启,成为相反相成的一种矛盾。在胡适看来,救国之关键,乃在人才之培养。而人才之培养,关键在教育,故而他在《易卜生主义》中大声疾呼:“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重要的莫过于把你自己铸造成器。”
某种程度上,五四运动乃是20世纪初期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某种隐喻。以胡适为例,他希望居住在象牙塔中,通过文艺复兴与思想启蒙的学院派之路,来为百年中国奠定通往未来之路,但是现实中国的处境,要求他必须离开象牙之塔,来到十字街头。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关键时刻,为了国家的生存荣辱,胡适放弃教育家之身份,去从事外交官的工作。
胡适为五四运动做了什么?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时,胡适在上海陪同杜威来华演讲,“完全不知五四的发生”。
5月7日,胡适在上海参加国民大会游行,声援学生运动。第二天,北上北京,到北大后,因北大校长蔡元培已离校,胡适全力协助当时的工科学长温宗禹处理校务。
6月初,政府进一步逮捕学生,北大的部分校舍也成为关押学生的监狱。其中,北大法科一地,成为关押学生的第一监狱。第二天,胡适借得一张执照,得以进入北大法科,探望被关押在这里的学生。这时,胡适做了三件事。第一,通过交涉,给关押的学生送去了三十多个铺盖,不过关押的学生多达176人,肯定不够用。第二,学生被关押后,长时间没吃饭,胡适探监知晓情况后,立即委托北大的教职员工买了一些面包送进去,以免学生挨饿。第三,忙完这一切后,立刻给报社主笔张东荪写了一封长信,将详细情形报告给了上海的新闻媒体。收到胡适这封长信后,张东荪以《北京学生受辱记-大学教授胡适之先生来函》的标题将此信全文发表在6月8日的《时事新报》上。
6月11日,陈独秀写了《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并委托胡适将这封传单翻译成了英文。当天下午,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入狱。当晚后半夜知晓这一消息的胡适,立刻开始营救陈独秀。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跟陈独秀、胡适都是安徽老乡,胡适希望借乡谊来打动吴,并由自己出名作保,将陈独秀保释出狱。为此,他还邀约安徽旧派文人马其昶与姚永概出名营救陈独秀。此二人是陈胡掀起的白话文运动的反对者,但是,当陈独秀被捕之时,两人却签名保释陈独秀。这种旧派文人风范,也算是久违了。
7月,在营救陈独秀之余,胡适还为傅斯年、罗家伦辩冤白谤。由于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领导者在五四学生运动中不够激进,两人逐渐被激进的青年学生所抛弃。就在此时,出现了一种谣言,说傅斯年、罗家伦已经被安福俱乐部所收买。为此,胡适专门致信《申报》记者,澄清了事实,为傅斯年与罗家伦做了人格证人。
处理北大校务、保护入狱的青年学生、营救陈独秀、为傅斯年罗家伦两人辩护,这四件事,可谓胡适在五四学生运动中的主要活动。
胡适看“五四”
对当时的新派知识分子而言,不论是狭义的五四,还是广义的五四,这场运动可谓取得了双重胜利。
狭义的五四运动,追求的是“外争主权,内惩国贼”,最终的结果是,一方面,被认为是国贼的曹汝霖等人被免职;另一方面,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也没在巴黎和会签字。
广义的五四运动,指向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的推广以及由此而来的新文学、新思想与新观念的变革。在这方面,狭义的五四运动的发生,最终将这场广义的五四思想革命推向了纵深与高潮。
1919年底,身在历史现场的胡适在当时就意识到了五四运动在未来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他用英文撰写的《中国知识分子在1919年》,是比较早向西方世界宣传五四运动在中国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地位的重要文献。
在胡适看来,狭义的五四运动导致的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推动了白话文运动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同样在这篇英文文章中,他写道:
1918年,几乎只有《新青年》一家在为新文学和新思想运动而摇旗呐喊;1919年6月刚过,全国各地众多期刊如雨后春笋纷纷涌出。这些刊物的主编,基本上都是些受新思想影响的青年学生;它们仿效我们8月份被北洋政府封禁的《每周评论》,多为周刊,并且几乎都是用白话文写成。据估计,这样的期刊目前已逾四百种,而据上海的《星期评论》报道,仅在江苏、浙江两省,新期刊就超过两百种;在湖南长沙,曾经有十种思想激进、敢于说话的周刊,它们同样处在张敬尧将军的军事统治下。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颇具影响力的杂志《新青年》。
新文化运动不可阻挡的前进势头,迫使许多老牌日报发生了彻底改变。上海和北京的一些重要日报,尤其是《晨报》和《民国日报》,已经加入了这场新运动,不但它们的社论是用白话文写的,而且,那些重要的新闻通讯也是用白话文写的。然而,最重要的变化还在于多数日报“增补”的版面。一年前,日报副刊刊登的都是男女演员以及歌女的八卦新闻;但去年,占据这些版面的实际上都是对教育和哲学演讲的报道,以及翻译的契诃夫、高尔基、莫泊桑、斯特林堡等现代作家的短篇小说。即使是那些保守党派的报纸,也会在他们的专栏里登一些自由派作者的文章,因为他们发现这样做有利可图。
由此可见,具体到1919年,胡适对狭义的五四运动还是高度评价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胡适对狭义的五四运动,也有了很多的反思。在他看来,狭义的五四运动,主要有以下几个缺陷:
第一,五四学生运动之后,学生得到了胜利之后,动不动就罢课,往昔那种潜心求学的宁静精神一去不复返了。第二,学生运动的成功,让政界认识到学生的力量。国民党、研究系等政党纷纷介入学校,于是政潮与学潮,相互作用。第三,对狭义的五四运动,胡适的态度是暧昧的。一方面,这场运动推动了白话文的推广,但另一方面,却也使他设置的新文化运动路线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
对胡适而言,他最关注的无疑还是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一直对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持高度赞扬的态度。他个人将这场运动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当西方媒体将他赞誉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时,胡适自己不仅欣然接受,而且以此为最大的荣誉。晚年的胡适,在听到蒋介石批评五四的口吻后,要当场反驳蒋介石,要立即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辩护。在他看来,他一生最大的功绩,无疑就是这场由他以北大为阵地而掀起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死后,覆盖其身躯的,也正是北大的校旗。
1962年,胡适之在台湾逝世。临死之际,在演讲中,他念念不忘的乃是科学在中国生根的问题。死神降临之前的胡适,魂归五四。五四五四,魂兮归来。
作者:林建刚(重庆文理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教师);编辑:宫照华 西西 沈河西;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