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艺术》(Chinese Art)是西方早期研究中国艺术的重要文献,1958年在纽约出版,上下两卷。作者William Willetts(魏礼泽)(汉学家、西方艺术史家)从中国的地理特色着手,系统梳理了玉器、青铜器、漆器、丝绸、雕塑、陶瓷、绘画、书法、建筑等中国艺术的各个门类。他坚持客观描述作品的方法,“并不对所讨论器物给予美学价值论断,而是让器物自己说话”。
“让器物自己说话”,与观复博物馆“以物证史”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我们选择翻译此书的原因。此次我们邀请到美国CCR(Chinese Cultural Relics《文物》英文版)翻译大奖获得者对此书进行正式专业的翻译,译者也是MLA(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国际索引数据库)和AATA(国际艺术品保护文献摘要)收录的美国出版期刊Chinese CulturalRelics的翻译团队成员。
本着尊重原著的原则,此次翻译将存疑处一一译出,其后附有译者注。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本书,在绚烂璀璨的器物中,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辉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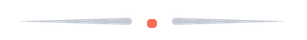
但不管是在欧洲还是中国,真正阻碍风景画和山水画受欢迎的,在于自然风景没有边界这个事实,自然风景也没有有机结构。一匹马,一棵树,一个人或者任何一个独立实体,都是和周围环境隔绝开来的,因为其有形边界。但乡村风光的特性,在于无边界;如Friedlander所说,物体有边界,但风景没有界限。一个有边界的东西可以被当成图像概念象征,用轮廓线勾勒就可以表示出来,而风景不能被如此象征化。对于风景来说,唯一的界限只存在于画框的边缘;所以风景不能被当作是概念象征。
直到社会也赋予自然以象征意义,画家才会赋予无秩序的风景以有机结构,为风景找到共识性的边界。当自然失去了其恐怖感,人能够一点一点地与自然同频共振,能够在自然中投射情感,人逐渐学会容纳自然作为概念象征的状态,而后者本来是不能有任何有限边界的。过渡是有帮助的,甚至是必要的。欧洲风景画的早期历史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案例。自然本身无边无际。对于人的介入有天然的敌意。人总是想在自然的寂寞中找到逃避和心灵的抚慰,而这种避难所是有边界的,这种边界与人的模式有关联。一座封闭的花园,可以呈现出概念象征的模样。其围墙可以在画框内完整地或部分地展现。而花园外,人们可以窥见野生自然,人在这样的自然中只能自己摸索开辟。14和15世纪的天堂乐园画中,中世纪风格的神圣爱场景,通过诗意的想象弥合自然的广阔和事物有限之间的鸿沟。
乐园(paradise)一词来自波斯语,新的符号以及许多相关的符号可能是在十字军东征时期由远东传入欧洲的。所以我们必须注意,远东的乐园场景的想象对欧洲的影响。这种影响传播是通过波斯细密画途径传播的。比如,Kenneth Clark爵士在《玫瑰园的麦当娜》这个作品中就发现了波斯画的影响,该作品藏于Verona的Castello, 属于Stefano da Zervio私人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