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在课堂上说,蔡鸿生先生是一位真正的智者,他不仅学识渊博,具有“全景式的历史思维”,而且还有十分高超的语言艺术,因此阅读蔡先生的著作是一种享受,从未觉得文字有滞涩之感。蔡先生的作品既妙语连珠、诙谐幽默,又切中肯綮。当然,像这样一位充满睿智的学者,他有关治学经验与方法的论述,不啻对初学者,对即便像我这样已厕身学界有年的人也极富教益。因此通常我在课堂上推荐给学生阅读的蔡先生的著作,除了《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广州海事录》等经典作品外,更多的是他有关治学经验与方法的论著,诸如《学境》《学理与方法》《仰望陈演恪》《读史求识录》等均一一推介。当然,我也与学生一起学习,并将学习札记与学生分享。
在蔡先生所有有关方法论的论著中,《读史求识录》(以下简称《求识录》)是最晚出的一种,也是有关方法论的讨论最为集中的一种,因此值得特别重视。《求识录》内容分上、下辑,上辑由蔡先生给研究生开设的“学理与方法”课程的授课记录整合而成,核心之义是为了加深学生对“读史求识”的理解;下辑则是与之相关的讲谈和文稿,其中涉及的部分问题的探讨具有研究示范意义。因该书比较“薄”(按:“薄”是蔡先生著作的普遍特点,与现在有些人追求论著的“厚”形成鲜明对比),便于携带,一度成为我出差时的“机上读物”,因此札记的有些内容是在飞机上完成的。
《求识录》第一篇开宗明义“历史研究要以人为本”。其中蔡先生说:“历史学的功能就是帮助我们知人论世。‘知人’的‘人’,包括个体和群体;‘论世’的‘世’,包括时势和时代。对历史一窍不通,没有间接经验为借鉴,是知不了人,更论不了世的。”(9页)可谓的论,而知人论世的最终目的是尽可能正确地探究历史真像。
在此我想补充的是,“历史研究”与“知人论世”其实也存在辩证关系:一方面,历史研究能帮助我们提高知人论世的能力,另一方面,历史研究者也必须懂得“人情世故”,必须“接地气”,也就是说,不具备知人论世能力的人是做不好历史研究的。后一层面的问题涉及历史学的认识论问题。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认为,史料本身不会说话,使史料说话的,只能是历史学家的学识水平或认识水平,水平越高,就越具有创造性,所阐释的历史事实也就越深刻;史学家不是被动地接受史料,而是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创造性阐释史料。这与兰克史学的认识论有根本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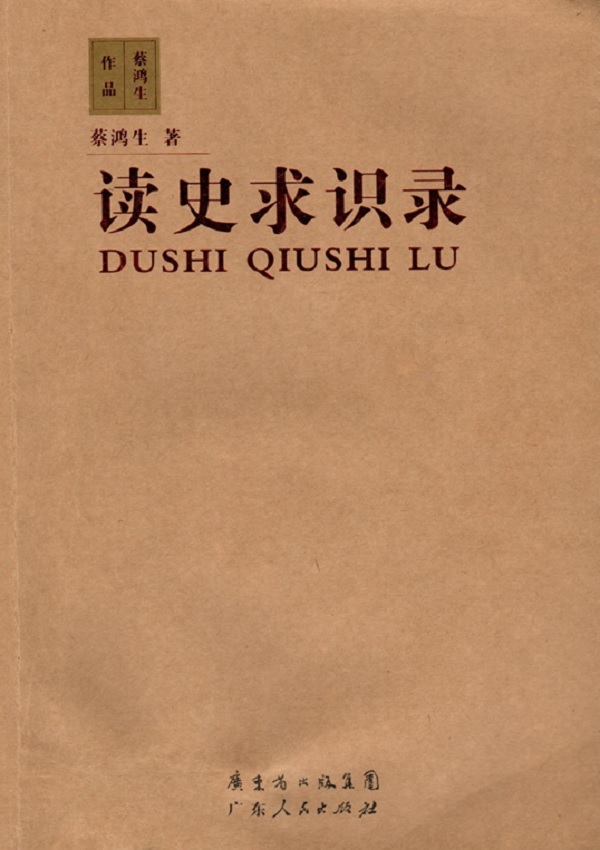
蔡鸿生著《读史求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
在我看来,史料本身还是能说一部分话的,但更多的话、更深刻的话,需要历史学家替它发声,这主要仰赖于历史学家的认识水平和主观能动性。那么,如何提高历史学家的认识水平和主观能动性呢?从现实社会获取“间接经验”至关重要。换句话说,历史学家仍然要通过“现实”这扇窗口来认识“历史”。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如克罗齐所言,历史是以现实生活作为参照系,过去只有与当前的视域相重合时才能被人所理解。这主要源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从人类思维运动的基本规律来看,今人与古人虽然有不同,但也有相同和不变东西,因而现实与历史始终存在密切的联系,现实与历史总有“相重合”的地方。因此,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目的并不是强调实用主义的历史观,而是在强调认识历史的基本路径,即必须通过当下、通过现在来认知历史。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不了解当下,不了解现在,就无法认识过去。而史学家想要通过“现实”这扇窗口来认识“历史”,就必须熟谙“现实”、“知人论世”,即既要懂得“知”现实中的“人”,也要会“论”现实中的“世”。
王学典先生说,“历史的洞察力更重要的是来自对现实生活的参与程度、深度。一个人连自己生活的社会都认识不清楚,你怎么能指望他能认识清楚2000多年前的先秦社会呢?……希望大家不要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当……保持对现实生活的高度关注,首先要当历史的创造者,才能当好历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人性的复杂,你如何研究历史人物?对人性观察的广度、深度,影响你对历史判断的广度、深度。古今中外人性是相通的,这是历史研究得以进行的假定。没有这个假定,我们就没法研究先秦史、美国史。没有比对人性的观察、比对现实的观察更能训练洞察力的了。” (王学典《治学的功力与见识》,《中国研究生》2009年第8期)王先生是从训练历史洞察力的角度切入的,表达的其实是同样的意思。
在《求识录》“史与思”一篇中,蔡先生谈到论文选题问题,他说:“选题应在学术史中去寻找。只有通过学术史的回顾,才能知道既往研究遗留的问题,包括没有解决,或认识不足以至误解的问题。选择这些问题来研究,才有‘拾遗补缺’之功,不致完全重复或部分重复前人的劳动。……现在写学位论文,按规定学术史回顾是不可或缺的,但要注意,是为选题而回顾,不是为回顾而回顾。徒具形式,于事无补。选题来自对学术史的回顾,才是有根之学。”(11页)
这段话十分清晰简洁地阐明了研究史回顾与论文选题之间关系,现实指导意义非常强,我以为初学者可以奉为圭臬。从目前我们系我所在专业的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的写作情况看,很多学生搞不清选题与学术史回顾之间的关系,以至于“为回顾而回顾”的情况普遍存在;同时,由于搞不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回顾的内容十分枝蔓,不能紧紧围绕自己拟要研究问题展开回顾,因而这样的研究史回顾基本上是无意义的。本人十分赞赏蔡先生把二者之间的关系梳理得如此清楚,这里唯一需要补充的是,在我看来,由学术史回顾进行学术研究不仅仅是“拾遗补缺”,更重要的是,它也是学术创新的起点,同时也是创造新知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正确的学术史回顾对于学术研究异常重要。这一点必须引起在读研究生的足够重视。
在《求识录》“我们不提倡‘速成’”一篇中,蔡先生谈到了“通”的问题,他说:“各个学科都要防止‘专而不通’的偏向,读专门史的人‘作法自毙’。以前有人批评牛角尖式的学科分类是‘马尾巴的功能’,但是我们不要画地为牢,不能栽在‘专’上,要有通识的眼光。”(80页)
“通识的眼光”,这马上让人想到陈寅恪先生“国人治学,罕具通识”的警示,看来蔡先生对这一警示的确是念兹在兹的。陈寅恪的通识观,蔡先生理解为“全景式的历史思维”。他在“中国学术三名著”这篇中谈练内功时说,所谓“内练”,“用陈先生的概念来讲,就是要有‘通识’。不只是‘识’,而且是‘通识’。所谓‘通识’,假如译成现代概念,也许就是要有‘历史感’,要有‘全景式的历史思维’,不是抽象地、孤立地来讲一件事情。……‘历史感’就是要把‘历史过程化’。”(59页)在蔡先生看来,陈寅恪先生的通识、精思和发覆之功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有全部呈现 (蔡鸿生《仰望陈寅恪》,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25页)。
在我看来,这是目前对陈寅恪通识观最透彻的理解。从陈寅恪先生到蔡鸿生先生,“通识”早已成为他们的“共识”。在蔡先生看来,要“具通识”首先要有“通”的意识,这个“通”指专业领域的“贯通”。这涉及到“通识”与“贯通”之间的辩证关系。关于二者的辩证关系,我在《学理与方法的另一种呈现》(《上海书评》2018年12月14日)一文中已有所提示,这里还想再重申一下:
“贯通”是“具通识”的前提,“贯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具通识”,不具备“贯通”能力则难以“具通识”;而“具通识”与提高史家的“识见”又是正相关的,只有“具通识”才能提高史家的“识见”。因此,优秀的历史学家往往既具有强烈的“贯通”意识,更具有强烈的“识见”意识。“独断之学”是邓广铭先生终生追求的目标,“独断之学”即指史家要有“独到的见解”,史家要有“识见”。他认为一个学者如果“不能抒一独得之见,标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为乡愿”, (邓广铭《邓广铭治史丛稿》自序,《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那就不足取了,应力求避免。
在《求识录》“精神产品和精神家园”一篇中,蔡先生谈到了“为文”的重要性,他说:“由于重道轻文……现在一些人写文章或著书,不是没有‘道’,但因为‘文’不行,表达不好,令人难以卒读……今天,有必要适当强调 ‘文’的重要性。‘道’固然重要,但‘道’要‘文’来载。”他在《精神生产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再次强调“文字”必须“下很功夫”:“从心上到纸上的整个过程,表现为逐层减弱的趋势,即想比说好,说比写好……因此,文字表述必须下狠功夫,才有希望把思维所得的新意挤逼出来。” (蔡鸿生《学境》,香港博士苑出版社,2001年,1页)
事实上,蔡先生的确是“为文”的典范,即如前文所说,他的语言艺术十分高超。不止蔡先生如此,很多前辈学者都十分注意“文字功夫”的锤炼。
这相当于“道”与“器”的关系,不能只重“道”而不重“器”,须知“器”是“道”的表现形式,无“器”则无以显“道”。换句话说,“文字功夫”不过关最终会影响学术产品的质量。在我看来,学术产品的文字表达的基本要求是:准确、严谨、简练。正是意识到“为文”的重要性,本人在平时训练学生时也颇留意于此。实际情况是,写作技巧缺乏和文字表达能力弱是普遍存在于在读研究生身上的“能力短板”,“行文枝蔓”、“言不达意”、“夹叙夹议”、“杂乱无章”、“偏题跑题”等情况比比皆是,因而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我的具体做法,一是推荐一些文字功夫上乘的前辈学者的学术产品让学生阅读,通过阅读揣摩他们的语言表达技巧,并进而让他们试图去模仿,我推荐的学者包括宿白、蔡鸿生、张广达、荣新江等;二是跟大家一起分享前辈学者“为文”的经验,如缪鉞先生的经验。现将缪先生的经验撮要介绍如次,与初学者共勉之!
蔡鸿生
缪鉞先生常说,“作文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将学术写作形容为“惨淡经营”。他曾引陆机《文赋序》“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晋陆机《陆士衡文集》卷一《赋一》,清嘉庆《宛委别藏》本)一语,指出“文事益进,则运思愈精;运思愈精,则求达益难”。可见其对自己的写作要求之高。缪先生行文的基本原则是:简明清畅,要言不烦。犹忌枝蔓芜杂,为此必下“惨淡经营”的工夫。他又说,作文章最讲究得体,即在一定的题目要求之下,哪些应当说,哪些不应当说,哪些应该多说,哪些应该少说,都需要斟酌,不能信笔乱写。如果斟酌得好,则“轻重疏密,各得体宜”,就是好文章;如果信笔而写,杂乱无章,繁简有无都不合适,就是坏作品。为此他强调,作文之前一定要事先构思好 (这段文字主要参考了罗志田《要言不烦:缪钺先生论表述》,《读书》2015年第2期)。
陆机所说的“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言不达意”、“言不尽意”,可见这一点自古至今都是“为文者”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从“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一句中,我们能感受到古人眼中“为文”的难度究竟有多大。陆机的说法似乎有些超出我们的想象,但这的确是古人“为文”的态度,也是事实。之所以有些超出我们的想象,说到底,是因为今天我们很多忙于制作“学术产品”的人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文”的重要性(即没有搞清“文”与“道”或“器”与“道”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严重低估“为文”的难度。缪鉞先生因对陆机的话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因此才有“惨淡经营”、“文事益进,则运思愈精;运思愈精,则求达益难”的感叹,这也正是他“为文”实践的真实写照。缪鉞先生通过自己的“为文”实践,反过来又加深了他对陆机所言的体认。
对照缪、蔡二位先生的“为文”,可以发现有不少共性,首先,都简明流畅、要言不烦;其次,他们的著作都很“薄”。由此看来,“坏作品”各有各的“坏”法,而“好作品”的“好”法则基本一致。
《求识录》“仰望陈寅恪铜像”一篇,是蔡先生在陈寅恪铜像揭幕仪式上的致辞,其中第二段话,读之为之动容:“面对着陈寅恪先生的宗师伟业,道德文章,我自知差距巨大,矮了半截,只有仰望又仰望。他生前授课,我坐在学生凳上仰望;他作古多年后,我写《仰望陈寅恪》一书追念;今天在这个仪式上致辞,依然守‘仰望’之旧义,不敢哼‘走近’的时调。时时仰望,似乎比烧柱香更能表达对金明馆主人的感念之情。”(95页)
每次读到这一段,不知为什么,我的眼睛总会湿润,且如鲠在喉,总想说点儿什么。按照我的理解,这段话,一方面,是蔡先生在恪守“师道尊严”之旧义,是一个“弟子”向“先师”的最崇高的致敬,这一层意思无须多说;但另一方面,“仰望”一词足以引起我们更多的思考。在这篇不足千字的致辞中,“仰望”一词出现达十次之多,因此“仰望”绝对是这篇文字的要义所在。在先师面前,蔡先生的心迹展露无遗。我们看到的是,博学如蔡先生者,对陈寅恪先生仍始终抱持“仰望”之旧义,从不敢奢谈“走近”的时调。因此我相信,蔡先生说“自知差距巨大,矮了半截”,绝对不是自我谦虚,而是肺腑之言,真正是一位智者的“自知之明”。蔡先生作为真正的智者,此时此刻再次展现出他的大智慧。因此我认为,蔡先生对陈寅恪先生的态度可以成为时下一些学者的警醒剂,因为在他们身上缺少的正是“自知之明”。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早已不知道自己究竟“几斤几两”了。
蔡先生说,“学人更要抑制浮躁,‘浮躁’是学术上的‘幼稚病’”(80页)。这句话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事实上,当下学术界这种“幼稚病”颇为流行。蔡先生在另外的场合对“浮躁”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说,“浮躁就是轻浮加急躁,一浮躁就不可能踏实……只有‘潜’下去,才能进行脚踏实地的研究” (蔡鸿生《仰望陈寅恪》,219―220页)。又说,“浮躁是对心灵的践踏和背叛……任何短、平、快的登龙术,都与精神生产的历史经验不相干” (蔡鸿生《精神生产的历史经验》,《学境》,1页)。看来“浮躁”的确是为学者的大忌。在此我还想补充的是,当下学术界还有另一种病,也很严重,那就是“狂妄症”。他们往往在某个领域小有成绩辄“信心爆棚”,以为已“高处不胜寒”,于是“鸢飞戾天”之心日重,把自己当做待价而沽的“奇货”,在学术市场“吊起来卖”,这都是“狂妄症”的具体症候。
在严肃的学者眼中,著书立说是一件非常艰辛的工作,但在这些学者眼中似乎不需要那么艰辛。但坦率地说,这些学者靠印刷“等身”的著作而取得的“巨大成就”,如果与那些“具通识”的前辈学者相比较,其间的差距,套用章炳麟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的一句话就是,“不可以道里计”!为什么“不可以道里计”呢?陈垣先生《致蔡尚思函》中作了回答:“欲成一专门学者,似尚需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动国际而垂永远。不然,虽日书万言,可以得名,可以噉饭,终成为讲义的教科书的,三五年间即归消灭,无当于名山之业也。” (《陈垣全集》第23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174―175页)陈垣先生这句话仍有现实意义,因为现如今仍确有不少学者真如其后半句话所说这般操作,其与“具通识”者的差距自然“不可以道里计”了。“具通识”对人文学科的意义,钱锺书先生归纳得很到位,他说,“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由于人类智力和生命的严峻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愈来愈窄,把专门学科分得愈来愈细。此外没有办法。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 (钱锺书《诗可以怨》,《钱锺书集·七缀集》,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129―130页)存在上述两种病症的人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因而很容易把自己的学问从“专家级”自动升格为“通识级”。
当然,这两种病症存在内在联系,因此很多人往往一身患二病。说到底,患这两种病症的人主要是被眼前利益和功利心迷失了心智,即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古生物学家周忠和所言,“功利主义让我们远离了科学精神” (李艳《功利主义让我们远离了科学精神》,《科技日报》2018年6月21日),因而忘记了学问其实是“无底深渊”,不仅“学”无止境,“问”也无止境,因而他们已丧失对学问必须抱持的“敬畏之心”,必须抱持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态度。看来,不仅人文社科界有人染病,自然科学界也有人病得不轻。
患病或与环境有关,如学者所言,“如今的学术环境,使得学人一味在争夺生存空间,校园政治大行其道,欲以小人之术谋君子之相,非但心术不正而已,学术上也只好横溢斜出,凿空蹈隙” (桑兵《桂子山从学琐记》,原载《近代中国研究网》,此据《桂子先导》微信公众号,2019年9月)。患病固然与环境有关,但也不能成为自甘堕落的理由。
说实在的,那些“信心爆棚”的学者的学问和识见,跟陈寅恪先生的相比,真的算不了什么,用“几分之一”来形容,实不为过。“信心爆棚”者与陈寅恪先生之间的差距,可以从陈寅恪的“贯通”能力,“发覆”能力以及“工具”的掌握能力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陈寅恪先生的“发覆”能力,蔡鸿生先生有透彻的解析 (蔡鸿生《发覆的魅力》,《仰望陈寅恪》,66―74页)。何炳棣先生对陈寅恪先生的评价可谓公允之论:“陈寅恪师国学根基之深厚、欧亚古代语言之具有阅读之能力、中古史实制度考订之精辟、诗文与社会史相互阐发之清新深广,世罕其匹,自有公论。”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322页)何炳棣先生也是当今海内外公认的成就卓著的史学家。学识渊博如何、蔡二先生者,尚且有如此清醒的认识,尚且始终抱守“仰望”之旧义,况我辈乎?!
“陈寅恪”就坐在那里一直默默地注视着我们,不知那些每天行色匆匆地从他身边走过的“鸢飞戾天者”,何时才会“望峰息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