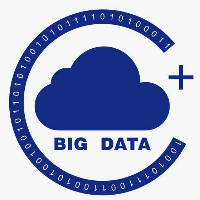山川网:今天是10月9号,为期8天的国庆长假已经结束,全国多数地区业已进入深秋,冬天已经不远了。
而根据昨天文化和旅游部的相关数据显示:八天长假期间,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6.37亿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恢复79.0%;实现国内旅游收入4665.6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恢复69.9%。
另据国家电影专资办初步统计,2020年国庆档期(10月1日至8日),全国电影票房共产出39.52亿元,吸引近1亿人次观影,去年的国庆档票房为44.66亿元。
一如网络上一些朋友说的那样,今年的国庆节,更像是个迟来的春节。经济与社会秩序正在迅速得以恢复,这无疑是相比其他任何消息,都更值得大家感到欣慰。
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是国庆期间我就已经在思考的,只不过假期大家都在放松愉悦,并不太适合安排推送相对严肃的一些话题,所以我也就一直没写,正好今天假期结束了,各方面的社会经济数据,也能够印证疫情直到当下,才算真正的即将结束了。
一、返贫隐患
国庆期间,一条来自世界银行的信息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新冠肺炎大流行正在进一步拖慢减贫进程,预计2020年全球极端贫困率将出现20年来的首次增长。今年世界极贫人口可能增加8800万-1.15亿人,明年可能增至1.5亿人。
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极端贫困是指每天生活费不足1.90美元(约12.77元)。世界银行在《贫困与共享繁荣》的报告中称,假如全球大流行没有发生,预计贫困率在2020年会降至7.9%,但现在贫困率可能达到9.1%-9.4%,这意味着倒退至2017年的水平。
报告指出,大量新穷人将集中在贫困率已经很高的国家,而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将出现大量人口掉到极端贫困线之下。据世界银行估算,约有82%的新穷人集中在中等收入国家。此外,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将陷入极端贫困,而过去受极端贫困影响的主要是农村居民。
除了每天1.90美元(约12.77元)的国际贫困线外,世界银行还将中低收入国家的贫困线定义为每天3.20美元(约21.51元),将中高收入国家的贫困线定义为每天5.50美元(约36.98元)。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虽然目前全球只有不到1/10的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1.90美元(约12.77元),但有近1/4的人口生活水平低于每天3.20美元(约21.51元),有40%以上的人口(将近33亿人)的生活水平低于每天5.50美元(约36.98元)。
这条信息为什么如此值得注意呢?甚至它对于我的吸引力,还远超过了本文开篇时我讲到的由文化和旅游部和国家电影专资办发布了国庆期间旅游和电影消费数据呢?
因为它真的和你我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假期结束了,该玩的玩了,该看的看了,但接下来会怎么样,显然才更值得大家关注。世界银行估算的“约有82%的新穷人集中在中等收入国家”,而中国目前可以说就是世界上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双最大的中等收入国家。
更重要则是下面的这一句:“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将陷入极端贫困,而过去受极端贫困影响的主要是农村居民”。而众所周知,在2019年我国的整体城镇化率刚刚超过60%,迈入了城镇化进程的新阶段,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城乡收入差异,对于未来中国的影响无疑将是十分巨大的。
中国经济从来不是孤立的,所以并不存在一些人幻想中的无论世界经济如何衰退,中国照样吃香喝辣这种情形。在此前的相关推文中,我曾介绍过关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绩中,受益于全球化良多,截至目前我国也依旧还保有并不低的外贸依存度。
而大量的中小外贸企业,所能够生产的产品流向,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占比同样颇高,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在今年受到重创,且恢复进度远落后于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值得开心和欣慰的事情,这将在接下来几年间深刻影响中国沿海地区中低端制造业的发展动向。
二、失地失业
无论是这一次的新冠疫情,还是此前的禽流感、非典等历次疫情,当我们一次次战胜这些疫情,生活秩序得以恢复后,往往会很快将其忘记。那么,如果没能战胜疫情,又会怎么样?
比如像新冠病毒这样的疫情,如果发生在医疗条件十分落后的中国古代,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在中国古代,对于恶性传染病有一个统称——瘟疫。非典、鼠疫、天花、流感、霍乱、疟疾等等,都曾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给无数百姓带来苦难。
这里,我们举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
明末鼠疫,又称明末华北鼠疫、京师大瘟疫、明末大鼠疫、疙瘩瘟,是指明朝崇祯帝在位期间中国北方出现的大鼠疫。
明末大鼠疫开始于崇祯六年(1633年),最早爆发地点是山西。崇祯十四年传到河北,并随着李自成和清朝的军队传到更多的地区。崇祯十四年(1641年),鼠疫传到北京,造成北京人口的大批死亡。
相关史料记载,明末鼠疫这场大鼠疫使得“街坊间小儿为之绝影,有棺、无棺,九门计数已二十余万。”北京在1643年的8月到12月间,保守估计死亡人数已高达全城的五分之一。所以当次年的4月,李自成攻进大明帝国的都城北京时,他面对的是一座“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的死城。
太平天国中后期,一场瘟疫在江南地带的太平军和湘军交战区里迅速蔓延。当时人们称这种流行病叫“吊脚痧”、“子午痧”、“瘪螺痧”或“吐泻病”。当时江苏常熟地区有记载称:“时疫流行,名字午痧,朝发夕死。上海极重,渐延太(仓)境,吾方间亦有之。”这种疫病还有个专门的名称:霍乱。
1860-1861年时,安徽、浙江和江苏等地已经出现了大面积染病和死亡的现象。而此时曾国藩的湘军正在和太平军正在安庆鏖战。战争和瘟疫从来是紧密相连的。湘军虽然攻下了安庆,但得到的是一座空城,数万太平军全部被杀,城内城外死尸成堆,第二年夏天,随着高温,新一波瘟疫开始大面积蔓延。
而事实上,相比疫情中庞大的死亡人群相比,还有另外一个群体,他们的情况同样值得大家高度重视。
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是战争、旱灾、洪灾还是瘟疫,事实上都必然伴随着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灾民逃荒。而对于逃荒的灾民而言,无论是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还是从事个体工商业的商贩匠人,失地与失业,同样必然伴随逃荒这件事并发。
作为农耕国家,中国古代绝大多数灾民都是农民。土地,是农民赖以安身立命的最基本要素。这一点,和当下整体城镇化率已经超过六成,逐步完成国家支柱产业向工商业转换的中国完全不同。
对当下而言,失地农民是指农民的土地被依法征收后,农业户口的家庭人均耕种面积少于0.3亩的统称为失地农民。这被视作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尤其是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农用土地转为非农用地,全国每年至少有300万农民成为失地农民。不断累计的失地农民至少超过5000万,已成为很庞大的社会群体,其中完全失去土地、没有工作的农民至少在1000万人以上,占失地农民的20%。
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去工作的市民,如果无法得到妥善安置的话,又会朝着什么方向演变呢?
三、城乡流民
要想读懂中国历史,首先要读懂中国农民。而千百年来与中国“农民”一词联系最为紧密的,其实应该是“流民”。有一种历史观点甚至认为,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史,本质上就是一部流民史。
所谓流民,即因土地兼并、租税徭役、天灾人祸、战争破坏等多重因素,被迫而逃往外地谋生的农民,又名棚民(山上搭棚居住的流民,无家可居之人)。
而流民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普遍存在的一种人口现象和社会现象。约在公元前21世纪,中国建立起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一一夏朝,流民亦随之在中国大地上出现。
随着岁月的流逝与社会的演进,流民问题不仅未能消除,反而变得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复杂,并对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产和生活诸方面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纵观中国历史,历朝历代的流民现象均十分突出——
汉末献帝时,关中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
唐安史之乱后,土地兼并盛行,不断有农民因失去土地成为佃农或者流民,甚至加入盗贼集团;
宋熙宁七年(1074年),北方大旱,郑侠曾作《流民图》,图中流民或身背枷锁,或口食草根;
明弘治二年报告,当年四川流民、饥民有八十七万余口;
清乾隆末年,“广、黔、楚、川、陕之无业者,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
近现代时期,在中国文革时期发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结束后,大批的返乡但却无法获得工作的情况,事实上又造成了当时社会的另外一种形式的“城市流民”。
新中国建立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两次大规模失业潮,即70年代末的返乡知青失业潮和90年代末的下岗工人失业潮。历次的失业潮之后,必然产生流民潮。
纵观上述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任何一次的社会秩序动荡变化,都有可能衍生出规模庞大的城乡流民,进而深刻影响此后至少十余年的社会机构与秩序。
言及于此,我不介意再次向大家推荐一部非常难得的关于“游民”主题的纪录片,徐童导演的“游民三部曲”:《麦收》、《算命》、《和老唐头》。
这可能是当代社会,为数不多、十分珍贵的,聚焦本身数量庞大,但是从来游离在主流社会视线外中国当代“游民群体”的视频资料。
四、犯罪启示
从历史上来看,数量不断增加后的流民群体,大致上会走上两条路——其一是揭竿而起,其二是打家劫舍。
而在当下的和平年代,法制社会大背景下,大规模的传统流民现象已不易发生,革命与起义自然极难发生。但个体的流民现象仍旧会长期存在,而之于个体流民或个体流浪,有一种行为几乎也会长期与之共存而难以割舍——犯罪。
老朋友们应该有所了解,近一年时间来,山川网的更新频率被我不断降低了,从早些时候的日更,几经调整后,变为目前的每周更新一到三篇左右的推文。一方面是中国城镇化已经进入了全新阶段,区域经济领域的大变化越来越少,可谈的大话题也在随之减少;另一方面,就是我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研究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变革历史与大案要案纪实。
在写这篇推文时,我看了一眼自己正在更新的“90年代刑侦大案纪实”音频节目,已经有了超过50多集的内容,前前后后汇总整理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数十个具有符号性意义的大案要案。阶段性的犯罪行为频发所折射的,表层是人性的丑恶与扭曲,但本质则是深刻反映对应时代的社会变革状况。
一个纯粹的无地、无业、无牵挂的城乡流民,能够对既有的社会秩序形成怎样的潜在破坏性呢?这里,我们不妨举几个上世纪90年代的代表性大案——
韩振营案:1974年生,出生6个月时就被生父母过继给本乡农民收养,8岁就开始流浪,数次拘留入狱。于1995年至1996年间流窜河南、湖北、湖南多省市流窜杀人抢劫。被捕后,韩振英自称作案67起,杀死63人。最终经警方查证案件33起,其中杀人案17起,总共杀死22人,杀伤10人。
王强案:1975年生,8岁时父母离婚,十几岁开始流浪。自1995年至2003年,流窜开原、铁岭、沈阳等多地,杀人、强奸、抢劫的犯罪34起,其中杀死45人,强奸10人。
彭妙计案:1966年生,从小随父母逃荒投靠姨母,12岁时被人拐卖,曾长期在关中、渭北一带流浪。1992年至1998年间,彭妙计团伙在河南、陕西、安徽、江苏四省抢劫、强奸、杀人,疯狂作案数十起,共杀死77人。
上世纪60、70年代,中国社会正处十年文革时期,社会混乱失序,经济停滞落后,贫困地区未成年人失学流浪情况突出。而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很快即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社会经济体制发生变化,城镇化进程开始加速,贫富差距不断被拉开。
此后,一大批出生于文革时期,幼而失学、继而流浪,并无其它一技之长,甚至早早失去了家庭关爱的未成年人,开始有相当比例的人群成为所谓的城乡流民。
受制于人口、资源、地理位置和产业布局经济政策等诸多因素,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并不均衡,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中西部地区要远远落后于东南沿海和北上广等地。
城乡差距、地域差距使以犯罪来平衡被剥夺感甚至具备了某种“正当性”,高危地区及人群以这样极端的方式“融入”社会分工,强行对收入进行再分配,争夺生存资源。
在疫情期间,由于经济形势空前严峻,在区域经济圈内,曾一度流传过这样一种观点:一些人认为东部发达省市的财政压力巨大,却还要每年向中西部地区进行相当规模的财政转移,甚至还计算出了东部某些省市每年,具体到每个人身上,承担了多少向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由此直呼压力山大、力不从心。
类似的观点,其实并不是个案。比如过去历次我们讲到东北振兴、西部开发等相关问题时,有一种观点认为对于上述地区的持续性支持是没有必要的,应该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式,任由各地区贫富差距发展。而人往高处走,届时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会不断主动流入经济发达地区,最终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共同富裕”。
这样的观点,显然过于理想化,是对中国地域差异之大,人口规模之巨,客观国情之复杂缺乏基本的了解。现阶段能够称得上是较为发达的中国地区依旧是极少数,而所谓欠发达地区人口规模至少数以亿计。
不通过提升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均衡性,进而使得上述数以亿计的百姓就地实现城镇化,能够有地可安身,有业可立命,而是对于地区间贫富差距与发展水平完全市场化操作,任由其自行拉大差距的话,那么必然会出现的情况就是:大量无以糊口的欠发达地区人口扎堆涌入发达地区,而这些所谓流动人口的本质,与今天我们全文中讲到的“流民”,又有什么区别。
所以我们始终强调“共同富裕”和“地区均衡”,哪怕心知肚明永远不可能实现所谓的完全均等,但是这依旧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从本质上来讲,这并不是在保护穷人和经济落后地区;恰恰相反,这是在保护富人和经济发达地区。因为无论到了何时何地,穷人和经济落后地区永远都是大多数,而当大多数人无法通过“合法”方式安身立命的话,那么必然会通过“非法”方式获得利益,首选的受侵害对象又会是谁?
而更关键的是,界定“合法”与“非法”行为的,还是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