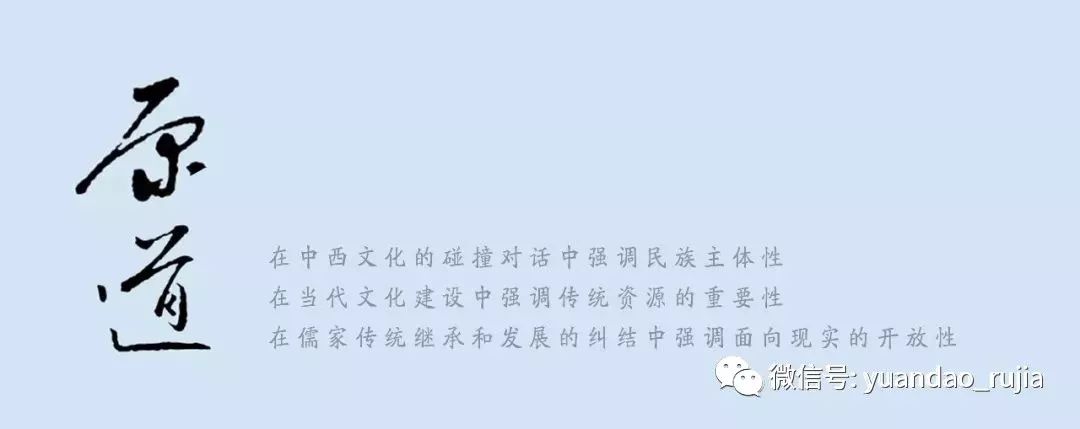
工夫、历史与政教:“学庸章句序”中的道统说
白发红
内容摘要:《学庸章句序》是朱子道统说最基本的文献。在《中庸章句序》中,道统即是道学,道学的内容为舜传禹之十六字心法,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其中”。
(《学庸章句》)
其实质为一种工夫理论,道统的传承不绝有赖于心性工夫的保证。在《大学章句序》中,道统即是大学,道统体现为学统为体、治统与教统为用的结构。因道统在历史中的表现,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
上古从伏羲到二帝,此阶段道统表现为学、治、教三统合一;孔孟时期,三统合一之道统解体,治统、教统在制度层面崩溃,而收缩于学统之中,学统赖孔孟而传;孔孟之后,学统亦不传,到宋代二程才重新接续孔孟之学统。
在朱子看来,学统本质上是一种全体大用的结构,它的重新发明,意味着治统、教统复建的可能性。宋儒复建治统的努力失败了,而社会层面的教统则是成功的。
关键词:道统;工夫;学统;治统;教统
朱子的道统说是晚近朱子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大学章句序》和《中庸章句序》两篇序文(合称“学庸章句序”)则是朱子道统说重要的基本文献,也是研究朱子道统说不得不征引的文献。两序均作于淳熙己酉(1189),前后相差仅一月。
是年朱子60岁,两序可视为朱子道统说的成熟作品。两序一方面从道统的角度提供给《大学》和《中庸》以核心经典的地位,另一方面则反过来受到《大学》和《中庸》原有文本的制约,表现出一定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又反过来丰富了道统的内容。
《中庸章句序》拈出“道统”一词,阐述以道学为核心的道统之传,道学以道心人心之辨为内容,主要是一种工夫论。《大学章句序》以“大学”之“学”为主要论述内容,以一种历史性的理路展现“学”的传承与失落,以及在宋代全新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更多的是一种落实为政教的可能性。本文即拟围绕“学庸章句序”,从工夫、历史与政教的不同维度探究朱子道统说。
一、道统含义之衡定
(一)道统即道学
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区分道统与道学,此后朱子道统说的研究便不得不面对这一问题。余英时认为,朱子将历史分为两期,即内圣与外王合一的上古时期和以孔子为开端的专门讲求内圣的时期,道统与道学恰好分别对应这两个阶段。
(朱熹)
三代与后世的历史区划无疑是朱子承认的,问题在于《中庸章句序》中,道统与道学的提法,是否就有历史分期的意味?
《中庸章句序》云:“《中庸》何为而作业?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其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其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
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加于此乎哉?
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
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
“其曰‘天命率性’,则道心之谓也;其曰‘择善固执’,则精一之谓也;其曰‘君子时中’,则执中之谓也。世之相后,千有余年,而其言之不异,如合符节。”《中庸》一书是子思忧虑道学失传而著,也就是说,《中庸》一书在于保存道学。
道统之传为“上古圣神”“圣圣相承”而来,其内容则是见诸《论语·尧曰》的“允执其中”,和见诸《尚书·大禹谟》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其中”十六字,后者为前者的扩展版。
(《论语》)
上古圣神道统的传承,实质上就是《大禹谟》十六字的传承。而此十六字在朱子学的论域中很显然是心性论的语言,亦即属于内圣。时至孔子,孔子不得位。依余英时,此时道统断裂,孔子开创道学,而后又有颜曾、子思传承孔子开创的道学。
而子思《中庸》一书的内容“天命率性”“择善固执”“君子时中”,在朱子看来,则与上古圣神道统之传的十六字若合符节。因此,《中庸》一书的内容亦即道学,就是指道统之传的内容。也就是说,道统的实质就是道学,道统的传承就是道学的传承。进而言之,道统即是道学。
反观余英时之说,我们无法否认,他的历史阶段之区划确实是朱子历史哲学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在《中庸章句序》中,毋宁说朱子更为强调了历史的连续性,以道学为核心内容的道统之传是从尧舜一贯而下至孔曾思孟的。
孔子在道统历史上的地位不是“开创道学”,而是通过“述而不作”和“集大成”使得道统得以承续。因此,余英时道统道学的区分,至少就《中庸章句序》这篇文章的脉络来看,恐怕还大可有商榷之处。
(二)道统的工夫义
在《中庸章句序》中,朱子一方面以道统—道学之传构筑了从尧舜至孔孟、再至二程的道统谱系,另一方面则对道学之含义进行了深度挖掘,道学之“学”不仅是学问体统,更是一种达道的工夫论。
朱子以《中庸》为“孔门传授心法”,此心法的实质就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其中”。《中庸章句序》云:“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
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
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在朱子看来,心很容易因其所知所觉不同而分裂为道心、人心。道心即是《中庸》首句所讲“天命率性”,因此也就具有形而上的性格,人心则倾向于形而下而时时有流于人欲的危险。
(《中庸》)
在心的这种危险处境中,只有通过“惟精惟一”的工夫,才能够做到“允执其中”。尧、舜、禹作为上古圣神,“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其终极内容只不过是这一套工夫论。因此朱子所谓“心法”涵具本体、工夫二义,而尤重工夫,工夫的终极境界在于保证天理之公(本体)胜人欲之私。
由此,道统的承续与失落,也因工夫论得到了说明。惟有做到“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道统的承续才能够得到保证;而道统的失落,则是由于工夫懈怠或者工夫缺失,使得道心人心“微者愈微,危者愈危”而导致的。
以工夫言道统不限于《中庸》,也与《大学》相关。在朱子的经典世界中,《大学》毋宁就是工夫论本位的。他在著名的《壬午应诏封事》中说:“盖‘致知格物’者,尧舜所谓精、一也。‘正心诚意’者,尧舜所谓执中也。自古圣人口授心传而见于行事者,惟此而已。”
可见,朱子不仅把《中庸》中的“天命率性”“择善固执”“君子时中”诠释为十六字的工夫论,而且他还把《大学》八条目中的前四目同十六字的工夫论等同起来。因此,朱子以工夫言道统,是其道统说最为核心的内容。
二、道统与历史分期
《中庸章句序》中的道统论说以“道学”为核心,因此可称为学统。在这种学统的视域下,突出了尧舜至孔孟道统传承的连续性。
而在《大学章句序》中,朱子则以学统、教统、治统三统并重的角度,全面讨论了道统在现实历史中的断裂与承续。依着《大学章句序》的文本脉络,历史可分为上古(伏羲、神农、黄帝、二帝三王)时期,孔孟(孔曾孟)时期,宋代(二程)时期。
(一)上古时期
《大学章句序》云:“《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
(《大学》)
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属、典乐之官所由设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备,然后王宫、国度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
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由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夫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教之之术,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则有皆无不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勉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
《大学》一书不是对上古学校制度的记述,而是对学校“教人之法”的阐明。在朱子看来,上古治教合一,政教的目的在于人人都能“复其性”,恢复被气质遮蔽的原本就固有的仁义礼智之性。
在这个历史时期,不仅治统、教统、学统三者为一。朱子详细地描述了三代的学校制度,三代的学校制度保证了每个社会阶层都能够受到教育,圣王的教化因学校制度的保证也能够普及民间,而以“民生日用彝伦”而内容的教化又保证了人人都有学,学因而也具有普遍性。
上古三代之治在《大学》的视域中,就是以治、教、学的统一为根本特性的。学有小学、大学之分,上古时期的特性,以学的角度来看,则体现在小学与大学的完备与实施。这是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也是后世治、教、学的最高的可能性。
(二)孔孟时期
《大学章句序》说:“及周之衰,圣贤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
若《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故小学之支流余裔,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著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广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
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周的衰落意味着历史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从道统角度来说,则到了孔孟时期。
(孟子和孔子)
周的衰落有四个方面的表现:“圣贤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这四点从政教的角度来说,亦即是治、教层面的。而学则赖有孔子才得以传承。
因此,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在于道统的分裂,治统、教统的失败,导致道统收缩为学统。道统即是学统(即道学之统),这是分析《中庸章句序》时得出的结论,同样也是《大学章句序》表达的内容。
此中有一问题,即以孔子之圣何以“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毕竟上文说“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到孔子之时则何以不“必”?
朱子的学生对此也曾感到困惑,《朱子语类》记载:“问:‘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天如何命之?’曰:‘只人心归之,便是命。’问:‘孔子如何不得命?’曰:‘《中庸》云:大德必得其位。孔子却不得。气数之差至此极,故不能反。’”
(《朱子语类》)
朱子把孔子不得其位的原因归结为气数,是从理气论的角度阐明现实历史中道统断续的原因。从理上讲,道统之道亘古亘今,无所谓失落或者断裂。但从气上讲,道坠入气中,处处受气的制约而无法得到完全的呈现,道统也就有了承续与断裂。
在现实历史中,理气是一种“气强理弱”的关系,道统能否得到传承,便取决于气数。但这不意味着,人便可以无所作为。面对“气数之差至此极”的时代,孔子无法“得君师之位以行政教”,但他“独取先王之法”,将道统以学统的形式传承下来。
位有君位、臣位之别,这在《中庸章句序》的道统谱系有所体现:成汤、文、武得君位道统之传,皋陶、伊、傅、周、召得臣位道统之传。孔子不得其位,是不得圣君之位,还是不得贤臣之位?
面对尧舜之后家天下的事实,孔子如果得位,那也只能是得臣位。上古时期的历史还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前三代”时期的官天下与三代的家天下。因而,朱子在《中庸章句序》中提出臣位的道统传承谱系,实有极深的现实意味,因为三代之后的历史,圣贤之君不作,道统的传承就只能依靠得臣位而实现治统。
(三)宋代时期
孟子之后的历史时期,道统的彻底断裂。不仅治统、道统中断,由孔孟传承的学统也彻底失落。这一局面要到宋代才得到改观。《大学章句》云:“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
其他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有纷然杂出于其间。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晦盲否塞,反覆沉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坏乱极矣!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休明。
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此处的小学与大学不是上古学校制度,而是教人之法。
(程颢、程颐)
在宽泛的意义上,俗儒之学、异端之学乃至权谋术数之学、功名之学、百家众技之学都是学,但这些学比之小学、大学则无用、无实。学统的中断便是由于这诸种之学的充塞。
学统中断,也就意味着,治统、教统的彻底无望,导致的结果则是“闻大道之要”、“蒙至治之泽”之可能性的彻底丧失。这种无学的历史局面在五代达到了极限,五代在宋人眼中是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
然而,“天运循环,无往不复”,气数行至宋代,宋代却能奋起一代之治。“宋德隆盛,治教休明”,这是朱子对本朝的评价。然而,宋代的治、教是在何种意义上能够称为“休明”,从而作为二程接续道统(学统)的前提或者原因?
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态势表现为一治一乱的循环,朱子认为“一治一乱,气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寻,理之常也”。一治一乱是从气化(气数)的角度说的。孔孟时期的历史态势也是乱世,彼时气数较差,而至宋代气数较好,因此有宋一代之治才有可能。
宋代之治首先表现为对五代之乱的拨乱反正,在这个层面上说“治教休明”是完全合理的,问题是“治教休明”是否还能指治统、教统的“休明”?答案是否定的,宋代的“治教休明”只能是气化层次上“一治一乱”之“治”,如果治统、教统皆能显明,那宋代便是三代之治在历史中的重现,而这只是包括朱子在内的宋人回向三代的政治理想。
但是,恰恰是气化层次上的“一治一乱”之“治”,却保证了二程有重新接续学统的可能性。朱子说:“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但说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说的透。”
“崇礼义,尊经术”是“宋德隆盛”的表现,也是二程接续、阐明学统的文化基础。“一治一乱”保证接续学统的可能性,学统的接续则是“善治”的基础和根本原因。《语类》记载:“才卿问:‘秦汉以下,无一人知讲学明理,所以无善治。’曰‘然。’因泛论历代以及本朝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为而不为。
‘太宗每日看《太平广记》数卷,若能推此心去讲学,那里得来!不过写字作诗,君臣之间以此度日而已。’”当学生把历代无善治的原因归结为“无一人知讲学明理”时,朱子同意了。
(《太平广记》)
朱子还论及本朝皇帝的“好学”,显然他们所学非《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学。如此,二程接续学统而讲明之的重大意义就凸显了出来,与同样以学统为道统之传的孔孟时期相比,首先宋代是治世,其次宋代有由治达善治的可能性。
三、道统与政教的关系
上文中曾屡次指出,道统即学统。学统之学依《中庸章句序》为道学,依《大学》则是大学,道学、大学实质上为一。大学的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大学》一书的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明明德即是内圣,亲民即是外王,二者是一种体用关系,用朱子的话来表述,就是全体大用,而“体用元不相离”。朱子认为:“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齐家以下,新民之事也。”
因此,学统的内容不止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还包含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孟时期道统的命运表现为上古圣神之政治、教化制度的全面衰落,而其精义则作为治统、教统的本质保留于学统之中。
《大学》作为保存道统内容的根本经典,其内容本质上涵学统、治统、教统三者于其内。学统、治统、教统并举而言时,学统指涉明明德之事,治统、教统指涉新民之事。而只言学统时,则治统、教统收摄于学统。
学统之学是全体大用之学,学统为体,治统、教统为用。从而,我们可以说,学统的传承不仅仅是内圣之学的承续,也是外王之学的赓续。上古政治制度的崩溃是必然的,也是合乎气运流行的。
朱子明确地指出,在宋代“封建实是不可行”。气运不息,时异势殊,合乎治统的政治制度只能通过对之前制度的损益来实现。
(一)学统与治统
既然学统与治统是一种体用关系,那么二者本质上是必然相关的。孔孟以学统为道统之传必然关涉着治统,同样二程接续发明孔孟的学统也就必然意味着合乎治统的政治制度复建的可能性。
朱子说:“治国平天下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只是一理,所谓格物致知,亦曰知此而已矣。此《大学》一书之本指也。今必以治国平天下为君相之事,而学者无与焉,则内外之道,异本殊归,与经之本指正相南北矣。”
可见,只要以《大学》之学、学统之学为学,则治统必然地被包含在内,治国平天下不仅是有位的君相之事,也是学者的分内之事。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能理解,《中庸章句序》中所说的,孔子“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
但严格来说,治统之事只能依靠在位君相,学者的治平之事属于教统。理学家“致君行道”的理想,只有在前者的层面才能得到更为充分的理解。朱子著名的几篇《封事》无不是这一理想驱动下的产物。
其中的思路是这样的:讲明学统,促使帝王能够学、且能以正心为学,由此便可复建治统,达乎三代之善治。治统能否落实为善治,关键在于“人君之学与不学、所学之正与不正”。
一般来说,朱子承认宋代的帝王都是学的,上文所引宋真宗每日对《太平广记》就是一例,但显然其所学不正。宋孝宗亦好学,但他认为“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显然是以佛学为体、儒学为用,学统之全体大用分成了两截,因此其学亦不正。
(宋孝宗)
朱子对孝宗之学是了然于心的,但在《壬午应诏封事》中提出:“记诵华藻,非所以探渊源而出治道;虚无寂灭,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这不是无的放矢。朱子在《大学章句序》描述学统中断的历史时,恰恰突出了不正之学的兴盛。
因此,辨异学、辟佛老,不仅仅是在学统的层面为儒学争取“正学”的地位,也直接关系到善治能否实现,亦即在治统层面有着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
当然,宋人意欲帝王正学为本、复建治统、达乎善治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朱子在《大学章句序》中所谓“以俟后之君子”,很可能是就治统层面而言。
然而,学统之学本质上是一种全体大用之学,治统的复建失败后,“大用”如何实现?如果无法“大用”实现,那么学便是体用隔截之学,便是异学而非正学了。
(二)学统与教统
学统与教统亦是一种体用之关系。上古时期的历史特征在于政教合一、君师合一。到孔孟时期,上古制度全面解体,“教化”的权力便下落至“士”的阶层。到了宋代,二程接续学统而讲明之,教统也就有了复兴的可能性。
实际上,这是一条比治统更为可靠可信的道路。治统与教统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政治层面的,后者是社会层面的;前者是一种上行路线,后者是一种下行路线。
朱子在评价宋神宗、王安石时说:“神宗极聪明,于天下事无不通晓,真不世出之主,只是头头做得不中节拍。如王介甫为相,亦是不世出之资,只缘学术不正当,遂悮天下。”
在朱子看来,神宗与王安石都是不世出之人,他们的相遇则是千载一时,这反映出了治统落实的艰难性。
因此,对于一个有着善治抱负的儒者来说,最为理性的安排莫过于,一方面不放弃得道行君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则要汲汲于社会层面秩序的重建。后者便是教统层面之事,也是全体大用之学的体现。
朱人求把朱子的社会关怀和社会实践总结为:书院教育的推广,《朱子家礼》的实践,社仓制度的社会关怀三个方面。其实不仅此也,朱子的注释经典、聚徒讲学都可包括在内。而所有这些,只有在道统(治统)的视域下,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朱子家礼》)
而且,不论对当时来说,还是对后世的影响来说,朱子的这些实践都是相当成功的。书院制度的建立,意味着古代大学“教人之法”在宋代的实现,古代大学学校制度与宋代书院制度均为大学“教人之法”在不同时空的实现形式。
仅就教统着眼,古代学校制度所教不过为“民生日用彝伦”,这在三代之前则由“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承担,而司徒之职在于“敬敷五教”(《尚书·舜典》),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别,朋友有信”。
宋代书院制度的核心精神亦在于此,朱子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讲:“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
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
开篇即称引五教的具体内容,可见书院的精神是对古代教育制度之精神的遥契。换言之,就是说教统在制度层面落实为书院制度,书院制度也也意味着教统的实现。书院制度首先是作为学统的制度现实化而存在的,但教统已然寓于其中。
学统与教统关系之密切,由此可见一斑。虽然宋代儒者积极地参与治统的复建,但治统能否复建则非他们所能决定。教统则不然,教统的复建一定程度上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他们也的确成功地落实了教统。
这种落实不仅意味着社会教化的成功,同时也意味着保证了学统全体大用之结构的完整性。
因此,朱子(宋儒)以道学之传承为核心的道统说,首先是一种理论的建构,但这种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全体大用的结构,即以学统为体、治统教统为用。故而学统的承续讲明,必然要求治统层面的政治实践和教统层面的社会实践,而这表现在宋代社会中,则是复建治统的失败和教统的成功。
因为篇幅原因,将注释删除,详情请参阅《原道》期刊纸质版
白发红,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本文载《原道》第39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
主编:陈明
选题:任重
编辑:陆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