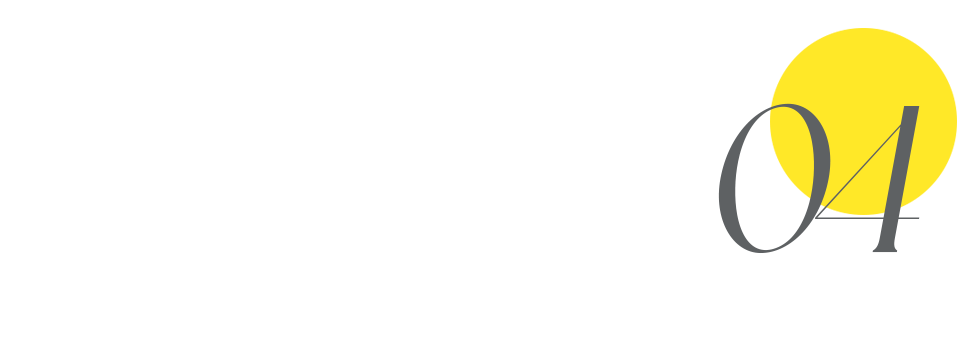莎士比亚曾说:
再深的记忆,也有淡忘的一天。再爱的人,也有远走的一天。再美的梦,也有苏醒的一天。
失去,本就是命运轮回的一环,如同人们在日落时感叹时光飞逝一样寻常。
当太阳照常升起,我们会发现:失去的,已成过往;留下的,都是经历。
就像李碧华小说《霸王别姬》里程蝶衣所经历的那样:
戏台上,他是强颜欢笑的虞姬,是酒入愁肠的贵妃,是分不清梦境与现实的杜丽娘。
然而,抹去脂粉,卸下行头,他却是个不断失去的可怜人。
为了活命,年幼的他被母亲留在戏班,吃尽了苦头;
好不容易熬成名角儿,却与从小搭档的师兄分道扬镳;
而他竟也因痴心太重,连自己都迷失在了戏中,辨不清戏里戏外,更不知今夕何夕。
不过幸运的是,虽然几经沉浮,经历从台前到幕后的转变,却能一直守护着自己最钟爱的戏曲。
待一切风平浪静,回首过去时,他才发现,失去或许是生活的刁难,但更是命运留给他的一线生机。
我们永远不要害怕失去。
因为:
留不住的,注定不属于你;
属于你的,终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你身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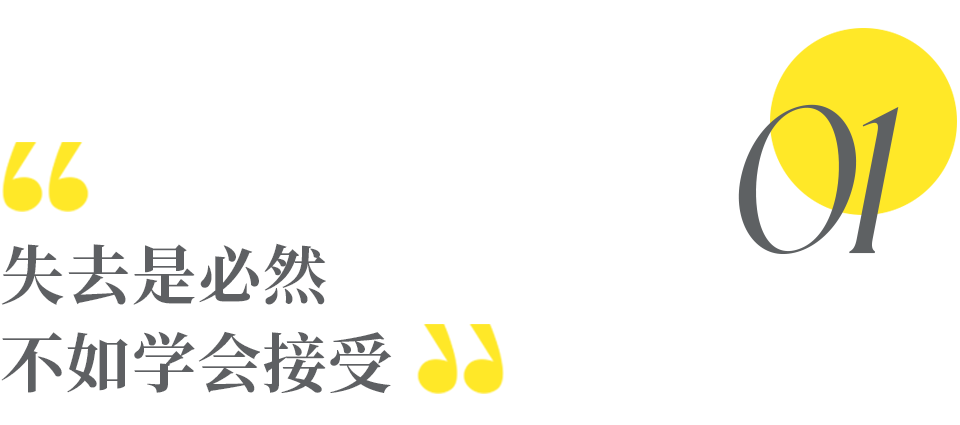
1929年的程蝶衣,还是被娘唤作“小豆子”的九岁小孩。
那年冬天,走投无路的娘将他送到戏班,想给他谋条生路。
班主关师父一眼就相中了他,可又瞬间变了脸色。
原来,小豆子身条样貌都合关师父的意,只是右手大拇指旁多长了一节指头。
任娘磨破嘴皮,关师父仍是拒绝,只不耐烦地说道:“你看他的手,天生就不行!”
听闻这话,娘一咬牙将小豆子拽到灶台旁,狠心剁掉了他那节多余的指头。
这一剁,却也阴差阳错为他剁开了一条生路。
从此,小豆子拜入关师父门下学戏,也才有了日后红极一时的京剧名伶程蝶衣。
只一个冬天,小豆子就习惯了没有娘的日子,京戏也学得有模有样。
开春,要“分行”了,每个人都将会有自己在舞台上的角色。
大师兄小石头是关师父一早就定好的大花脸,还有师兄弟被安排去唱小生,更有不少人只能跑龙套。
与众师兄弟不同,小豆子入门较晚,很多东西没有学熟练,因此经常出错。
比如他总是将戏词里的“女娇娥”错唱成“男儿郎”,因此遭到师父的多次训斥。
大师兄小石头看他总也唱不对,便给他出主意说:“你就想着自己是个女的。”
在戏里扮女人,就把自己当女人,肯定不会错,可小豆子做不到。
不出意料,等到下次轮到他时,还是出错了。
随着一句“我本是男儿郎”出口,关师父手中的铜烟锅就狠狠地捣进了他嘴里,一通乱搅。
血,顺着小豆子嘴角流了下来。
只听关师父又喝到:“重唱!”
只一瞬,小豆子就想到了大师兄的话,决意将自己从男儿身中剥离,进入戏里的美人角色。
和着嘴角的血,伴着眼角的泪,他开口唱道:“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
眼波流转,水袖轻颤。轻轻翘起兰花指时,他已然是颇具神韵的“女娇娥”。
这一瞬,连关师父看向他的眼神都添了几分慈爱。
从此,小豆子有了自己的角色,成了师兄弟中独一份的旦角。
在人生这出大戏中,无论是生旦净末丑,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角。
剧情如何推进,我们无法预知,却无不取决于自我内心的抉择。
有选择,必然会有失去,可以是权衡利弊后的取舍,也可能是走到山穷水尽时的无奈。
如果无法阻止失去,不如坦然接受。
就像有句话说的那样:
“所有的选择都有遗憾,但也都是我们成为自己的过程。”
分行以后,关师父教得更加细致,小豆子也学得格外用心。
很快,关师父就为他们师兄弟争取到了登台演出的机会。
开场前,关师父只给每个人半边脸上了油彩,让他们自己照着样子补全另外半边。
这也是小豆子第一次扮演美人,在自己上妆时心里紧张得很。小石头看见,一时兴起,想要替师弟描上几笔。
关师父登时恼火,大声喝止,反问小石头说:“以后你照应他一辈子吗?”
小石头不情不愿地放下手中的油彩刷子,小声嘀咕说:“一辈子就一辈子!”
少年人的赌气话,算不得承诺,因为彼时他们还不知道一辈子有多长。
可小豆子却当了真。
这次演出反响不错,众人因此得到了更多登台的机会,渐渐就到小戏园子里唱戏了。
只要有戏唱,他们就可以在后台吃一顿管饱的“保命饭”。
作为科班里唯一的旦角,小豆子自然也不用再担心活不下去。
可也因为这角色,他时常被师兄弟们揶揄嘲笑。
每每这时,小石头都护在他前面,甚至有一次还和师兄弟们动了手,伤了眉骨,自然少不了关师父的一顿数落。
伴着关师父的训斥,十年一晃而过。
小豆子和小石头学成出科,离开了关师父,也有了自己正式的名字——程蝶衣和段小楼。
他们从乡野的草台班子唱起,带着行头,拖着戏箱,走乡过户,一路相携。
不久,他们的名字便出现在了城里一家戏园子门口的大水牌上。
大水牌上还有当晚压轴大戏的剧目预告——《霸王别姬》。
这是他们最上座的一出戏。
他们也合作了一场又一场。
戏里的虞姬和霸王,戏外的师弟与师兄,亲密无间,容不得外人介入。
程蝶衣心存执念,认定大师兄是比娘更亲的亲人,台上台下只护着他一个人,就像是在心照不宣地践行年少时的承诺。
可突然有一天,大师兄却毫无预兆地说他要结婚了。
程蝶衣只觉自己被背叛、被抛弃,原来“一辈子”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他心里慌乱又刺痛,比娘离开的那晚更无助,什么祝福的话都说不出,只淡淡地自言自语道:“往后我也得唱唱独角戏了”。
作家马尔克斯曾写过这样一句话:
人生的本质,就是一个人活着,不要对别人心存太多期待。
如果总是将希望寄托于别人,留给自己的只会是失望。
凡事不要太依赖别人,这世上,只有自己,才是你永远的靠山。
离了大师兄,程蝶衣更红了。
他一人唱《洛神》,唱《拾玉镯》,唱《贵妃醉酒》……无论唱什么,都是场场爆满。
有不少阔绰的戏迷捧他,给他置办戏箱、行头,甚至有金丝银线的戏衣,还有点翠镶钻的头面。
连戏园经理也尊他一声“程老板”。
可程蝶衣对这些都不甚在意,他的感情几乎全部投入到了戏里。
好像除了唱戏,根本没有什么需要他上心的事情。
俗世纷纷乱乱,他的日子却过得很慢,但时光易逝,转眼他也到了不惑之年。
这一年,即使再不问世事,程蝶衣也能感觉到,他的戏好像也快唱不成了。
不仅是他,戏园子里也不再唱戏,而是用作放电影、演话剧。
戏班子改成了剧团,他倒是还可以演戏,不过剧里已经没有了英雄美人,他只能演配角。
那些整箱整箱的戏衣行头自然也成了累赘,他不得不含泪一把火将它们都烧掉。
此后的几年,程蝶衣不再唱戏,他的精力都被迫用来和过去划清界线。
段小楼也是。结婚后,他虽然没有将唱戏当做活命的唯一营生,却也一样需要坦白交代自己的过去。
在这段特殊时期,他们一同接受批判,一同写检讨,却也私下里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
相同的境遇,让二人仿佛又成了心无芥蒂的师兄弟。
可他们不知道是,有些刺扎在心里太久,不动不疼,一动便致命。
而所有的刺,都在迫不得已互相批斗的那一晚,穿心而过。
一开始,二人都不知道怎么开口,但一开了口,又不知道是谁的哪句话,触到了那根刺。
瞬间,场面失控,他们发了疯似的,争着抢着将对方最见不得光的事情,摊到众人面前。
在围观者的震惊和鄙夷中,二人回过神时,再看对方,中间仿佛已隔了楚河汉界。
原来真的只有最亲近的人,才知道扎哪里最要命。
那晚之后,程蝶衣懊悔不已,自觉没有脸面再见大师兄,学虞姬自刎,可又被救了回来。
在那场风波里,他没有失去性命,却终于失去了大师兄,还有一截小指。
多年后,一切都归于平静,他作为“四十年代名旦”,被邀请回京剧团,做了艺术指导。
他不再登台演出,只是换了一种身份,依旧做着他最喜欢的事情。
恰如小说《许愿树》里写的那样:
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没有不可结束的沉沦。
所有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
与电影结局不同的是,小说《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没有在舞台上自刎。
平反后,他有了在茶叶店工作的爱人。
六十多岁,随团访港演出时,他又见到了大师兄。
二人短暂相聚,简单叙旧,然后又长久地分开。
离别似乎才是人间常态。
分分合合,起起伏伏,人们总是在一边失去一边得到中度过一生。
如果失去的痛苦必不可免,不如错过的,就让他错过;得不到的,也不必强求。
终有一天,你会发现:以往的失去,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得到回馈。
或许,这些生命中的缺憾,正是你收获的独特经历。
也正是因为这些经历,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你。
作者 | 穆穆良朝
主播 | 云湾,暖心宝哥,每晚用声音伴你入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