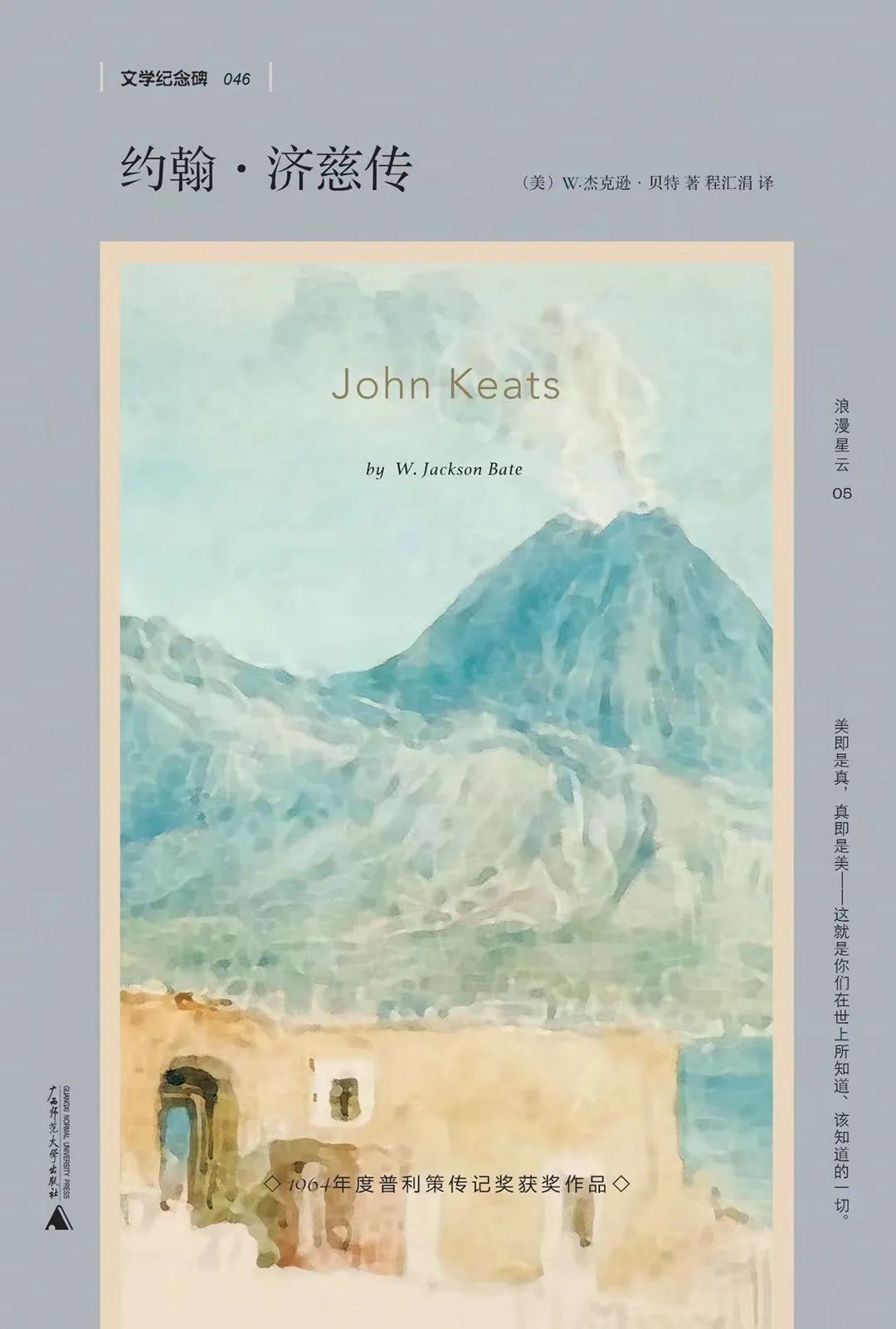
《约翰·济慈传》,[美]沃尔特·杰克逊·贝特著,程汇涓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1000页,198.00元
2023年12月6日英国《卫报》上刊登了书评人埃拉·克里默(Ella Creamer)的文章,标题是“济慈学者发现罗马警方调查了去世前的诗人”(Keats scholar finds that Roman Police investigated poet before death)。这位“济慈学者”名为亚历山德罗·格兰奇(Alessandro Gallenzi),是伦敦的一位出版商,同时也是诗人、剧作家、小说家和翻译家。文章说,格兰奇在查阅十九世纪罗马警察局的档案文献时发现一项有关济慈病情的记录,济慈的名字被误拼成John Xeats。记录中写道:济慈接受了警方调查,女房东要求他搬离她的房子,因为他没有向女房东说明自己身患结核病的情况。在当时的罗马,结核病被认为是一种触染性疾病,济慈如果不隐瞒病情就无法找到住处,即使找到了住处,昂贵的房租他也支付不起。
济慈在1820年年初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同时伴有肺部出血,医生们建议他离开英国前往意大利疗养。济慈在朋友约瑟夫·塞文(Joseph Severn)的帮助下,乘坐“玛利亚·克劳瑟号”轮船,克服途中恶劣天气、晕船和食物稀少等困难,于1820年11月15日抵达罗马。济慈和塞文随即与罗马的一位年轻苏格兰医生詹姆斯·克拉克取得联系,希望他帮助寻找住处。克拉克医生帮助他们找到了位于罗马西班牙广场26号的一处公寓,是两间狭小但舒适的房间。顺带一提,这位克拉克医生于1826年回到伦敦,后来成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御医,还被女王封为准男爵。
看了《卫报》上的这篇文章,我并没有觉得惊奇,因为哈佛大学已故教授沃尔特·杰克逊·贝特早在1963年出版的经典著作《济慈传》中就披露了类似信息:“女房东安娜·安吉莱蒂夫人已经猜到济慈得的是什么病,并按照规定通知了警方。”(《约翰·济慈传》,878页,以下引用此书仅标注页码)这应该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秘密。我猜想,《卫报》的这位专栏记者之所以写这篇文章,也许是因为她觉得济慈这位弥尔顿之后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天才诗人,去世之前居然受到了罗马警方的调查,这有些让人难以接受。
其实,罗马警方的介入是出于济慈的结核病可能在罗马造成广泛传染的忧虑,女房东也怕自己受到牵连,所以报了警。这是当时意大利和英国医学界及民众对结核病认知上的差异所致,英国医学界仍在怀疑肺结核的传染性,意大利的医生却不这样认为。早在济慈一行乘坐的船只到达那不勒斯湾时,他们不得不接受那不勒斯官方的命令:船只必须隔离十天,因为官方听说伦敦部分地区出现了小型斑疹伤寒瘟疫,来自伦敦的这艘船必须接受监视和审查(855页)。可见意大利人对触染性疾病持有高度警惕性。记得米歇尔·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说过:同样是对待麻风病,法国采取的手段要比英国约克郡采取的手段凶残得多。看来,欧洲大陆对触染性疾病的防范要比英国严格。而且,当时在罗马乃至意大利境内的绝大部分地区,结核病患者居住过的房间里的所有物品必须在他去世后用火烧掉。
塞文大概知道意大利政府或罗马警方的这一规定。他们租住的房间实在过于逼仄,济慈非常想换个环境,搬到隔壁较为宽敞的那个大房间里去住。大房间里“摆放着新租来的钢琴、塞文的绘画材料、他们买的书、一张沙发以及其他家具”(879页)。如果有人知道济慈搬进了这间房子,那些东西在他去世以后就都要烧掉,这些东西值一百五十英镑左右,对经济拮据的他们来说是一笔价钱不菲的损失。如何瞒着女房东搬进这间房间?塞文为人老实温和,对济慈极为忠实,他是济慈临终前最为可靠、最可依赖的朋友,用贝特教授的话来说,“约瑟夫·塞文正是在这个阶段占据了济慈人生故事里的突出位置”。为了济慈,塞文不得不使出了巧诈。贝特是这样写的:塞文心生一计。……济慈待在大房间里时,不能让安吉莱蒂夫人和她的仆人进入。他满脑子都是恐惧和对未来的不可预料,他自己在罗马身无分文,且深陷从未预想过的处境。绝望的塞文首先搬动家具,接着把家具一件件堆起来,堵住了门。为了不引起任何人(包括济慈)的好奇心,这事只能悄悄地做。假如济慈知道这一切蒙蔽手段是为了逃过女房东的注意,甚至罗马警方的调查,以及他死后塞文面临的处境,那么济慈一定会痛不欲生的。“最大的困难是向他隐瞒一切。”塞文觉得济慈对他所做的事“半信半疑”,但不管到底有怎样的怀疑和想法,济慈此时缄默不言(879页)。济慈是诗人,在生活中不乏诗人的敏感,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只是不想让好友感到难堪罢了。
济慈曾经学过医,对自己病情的凶险程度是有所了解的。还在他第一次肺部出血时(时在1820年2月3日),据他的另一个朋友查尔斯·布朗在《约翰·济慈生平》一书中记载:我听见他说:“那是我嘴里的血。”我走过去;他正好仔细端详床单上的一滴血。“布朗,把蜡烛拿来,让我看看这滴血。”他认真地凝视了许久,抬头看着我的脸,脸上平静的表情我永远无法忘记,他说道:“我知道那种血的颜色;——是动脉血;——颜色骗不了我;——这滴血是我的死亡通知书,我肯定要死了。”(819页)当时医生们对结核病的治疗方法肯定会让今天的人们感到可怕:每当济慈失血,他们就割开他手臂上的一条静脉,放出更多的血。放血治疗各种疾病是英国几百年来的普遍做法,我们在读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时也见识过同样的治疗手段。另外,就是限制病人的饮食,这在济慈那个时代也是常用的治疗手段,其结果是病人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疗法,苏东坡在惠州时痔疮发作,当地缺医少药,在痛苦不堪中辗转呻吟达一百多天。后来采纳一位道士的建议,用控制饮食的方法来治病,苏东坡总结为“主人枯槁,则客自弃去”。当然这是万不得已时采用的治疗方法:用“主人枯槁”的代价换取疾病的“自弃去”。
更令人奇怪的是,医生们居然不认为济慈患的是结核病,有一位呼吸系统疾病权威罗伯特·布里医生认为,济慈的病从根本上来说是神经性的,治疗的关键在于休息,避免情绪激动,建议济慈少费心思写诗。济慈知道自己曾与患有结核病的家人(他的弟弟汤姆患结核病去世)朝夕相处,自然有理由怀疑自己也染上了同样的病。但此时的他宁愿选择相信医生的话,“毕竟,他的确遵照布里医生的叮嘱,放弃了创作乃至思考诗歌的努力。从此刻到其人生尽头,即便他那么热爱诗歌,也把它完全放下了”(820页)。
据塞文后来回忆,济慈即便在生命最后时刻,也“从未完全失去他那令人愉快且灵活的头脑”。那些时刻在塞文的记忆里永不磨灭,济慈努力迸发出来的机智和欢乐,是为了他这位尽心竭力、不离不弃照顾他的挚友。最终,在去世前一两个星期,济慈告诉塞文,他不想在坟墓上留下名字,也不要墓志铭,只写一句话:“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但是济慈一生中最要好的两位朋友:塞文和布朗,却并没有完全兑现济慈的遗愿,对墓志铭做了润饰,其语言“不仅背叛了济慈临终要求所隐含的精神,而且其改动方式恐怕会令济慈感到痛苦不堪”(889页)。他们只是略去了济慈的名字,因为济慈对此的意愿十分强烈。但他们在墓碑上刻上了这样的话:“坟墓里埋着一位年轻英国诗人的遗体,他临终前,为同胞的怠慢感到极度痛苦,他希望墓碑上刻下这句话:‘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889页)其他朋友反对在墓碑上刻上“任何超出济慈本人要求的文字”。最终版墓志铭的措辞里,塞文将“为同胞的怠慢感到极度痛苦”改为“因敌人恶意的伤害,而内心痛苦”。
塞文为什么要这样改呢?当时英国许多人将济慈的早逝归罪于保守派在报刊上对他的人品和诗歌的恶毒攻击,比如拜伦就认为济慈是“被一篇文章杀害的”(snuffed out by an article)。在拜伦看来,保守派刊物《布莱克伍德爱丁堡杂志》和《季刊》上两个批评家的恶毒攻击,把济慈给活活气死了。这两个批评家是约翰·吉布森·洛克哈特(即不久成为著名小说家司各特乘龙快婿的那位有才气而傲慢的人)和约翰·威尔逊·克罗克。拜伦还写了一首四行小诗来讽刺《季刊》:Who killed John Keats? / “I”said the Quarterly./ So cruel and tartarly./ "'Twas one of my feats."(是谁杀害了济慈?/“我”,《季刊》回答说。/如此残忍而凶恶。/“那是我的杰作之一。”)雪莱也在济慈去世三个月后写成一首挽诗《阿都内伊斯》(Adonais),控诉《季刊》(Quarterly Review)是毁灭济慈的罪魁祸首。雪莱认为,“《季刊》对他的《恩狄米昂》所做的野蛮批评,对他的敏感的心灵产生了极强烈的影响;这一刺激导致了他肺部血管的破裂,肺痨现象立即发生,以后较为开明的批评家虽然承认他的伟大的天才,但已无法疗治他惨遭攻击的伤势”。
精神刺激是否会导致肺部血管破裂,这是一个医学问题,那么,济慈的健康状况事实上究竟如何呢?王尔德在1877年跟一位名叫亨特·布莱尔的朋友结伴前往罗马,他谒见了教皇庇护九世,也拜谒了济慈墓。据布莱尔说:王尔德对济慈的恭敬程度超过了教皇(参见《都柏林文学四杰》,[美]理查德·艾尔曼著,吴其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版,30页)。王尔德还为济慈写了一首诗,开头几句写道:“他终于摆脱尘世的不公和痛苦,/长眠在上帝的蓝色帷幔下;/在生命和爱情还鲜嫩时被剥夺了生命/殉道者中最年轻的在这里被杀。/他和塞巴斯蒂安一样美,一样被卑鄙地害死,……”(《济慈墓》,谈瀛洲译,《王尔德全集》第四卷,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王尔德在诗中所表达的意思是:济慈死于“尘世的不公”,“被卑鄙地害死”,因为塞巴斯蒂安“被邪恶的敌人绑在树上;尽管身中数箭,他仍抬起他的眼睛,用圣洁、热切的目光,凝视着正向他敞开的天国的永恒的美”(同上)。这样看来,济慈的死似乎与肺结核没有直接关系。布朗也为自己建议改变墓志铭措辞的行为感到后悔,他写信给塞文:“若一位垂危的朋友,一个好人,对其墓志铭的措辞留下过严格的嘱托,那人们就该听从他的要求——假如这世间仍有真诚善意的话。我为自己的错误忏悔,也必须重复我在罗马对你说的话,‘除了他自己规定的墓志铭,我希望政府准许抹去其余每一个字’。”(890页)遗憾的是,塞文并未听从布朗的建议。
需要指出的是,报刊上针对济慈诗歌《恩狄米昂》的这些攻击,“不论多么令人不快,其实并不危险。因为它太针对个人了”(476页)。济慈本人对这首诗也不满意。他之所以写这首诗,是因为要考验自己,看自己是否能有足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来完成一首长达四千零五十行的叙事诗。他在写给弟弟乔治的一封信中说:“……何况一首长诗还可以考验创造力,而我认为创造力是诗歌的北极星,犹如幻想是它的帆,想象是它的舵一样——近年来人们已经忘记创造力是诗歌的一个优点了。”他自己承认《恩狄米昂》是失败之作。
1821年2月23日,济慈病逝于罗马,仅得年二十五岁。济慈与雪莱、拜伦齐名,同为浪漫派诗人,在英国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王佐良先生论及包括济慈在内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诗歌创作成就时,说:“他(济慈——引者注)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上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是浪漫主义的创始人,拜伦使浪漫主义的影响遍及世界,雪莱透过浪漫主义前瞻大同世界,但他们在吸收前人精华和影响后人诗艺上,作用都不及济慈。”(《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版,334页)这应该是对诗人济慈的最高评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