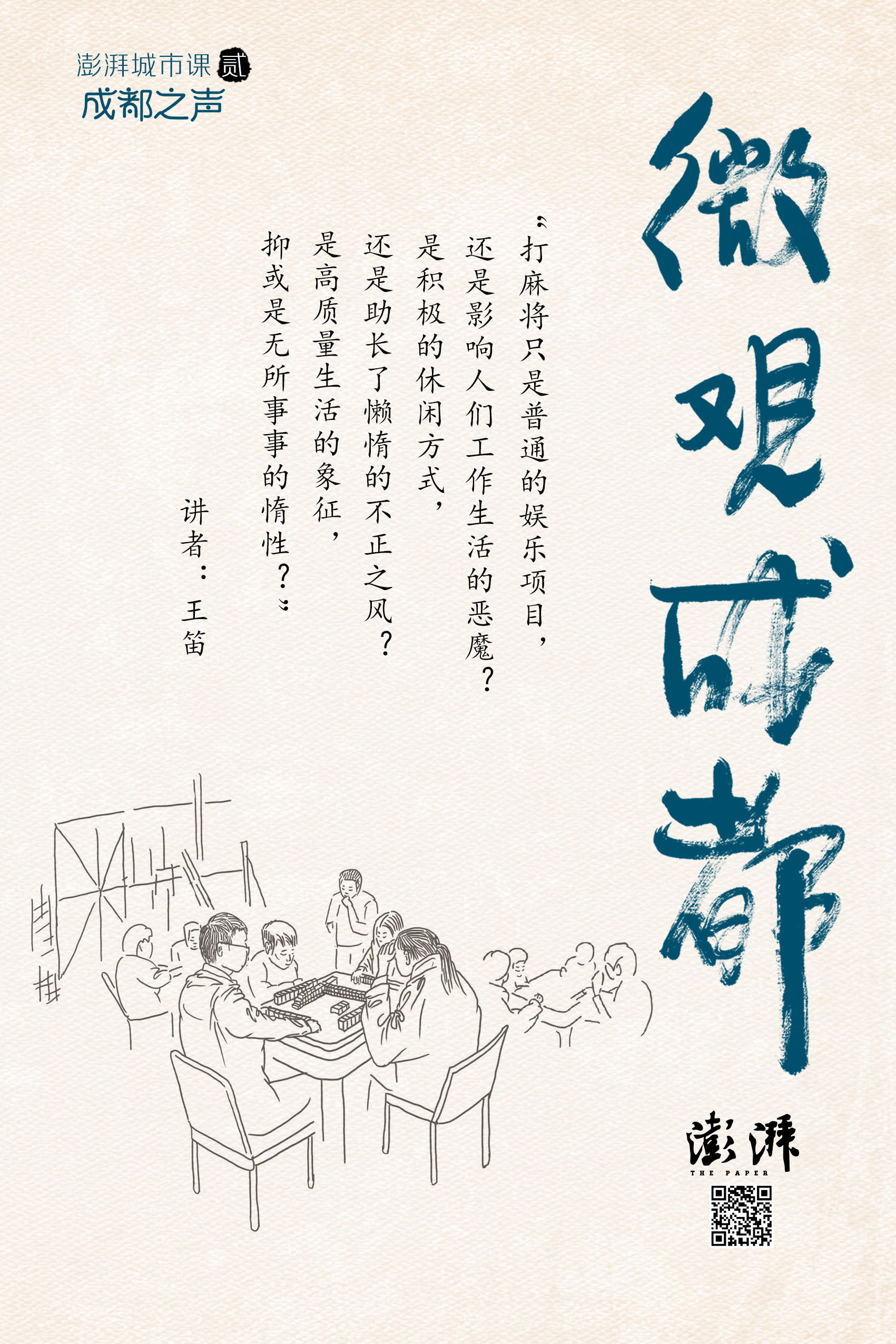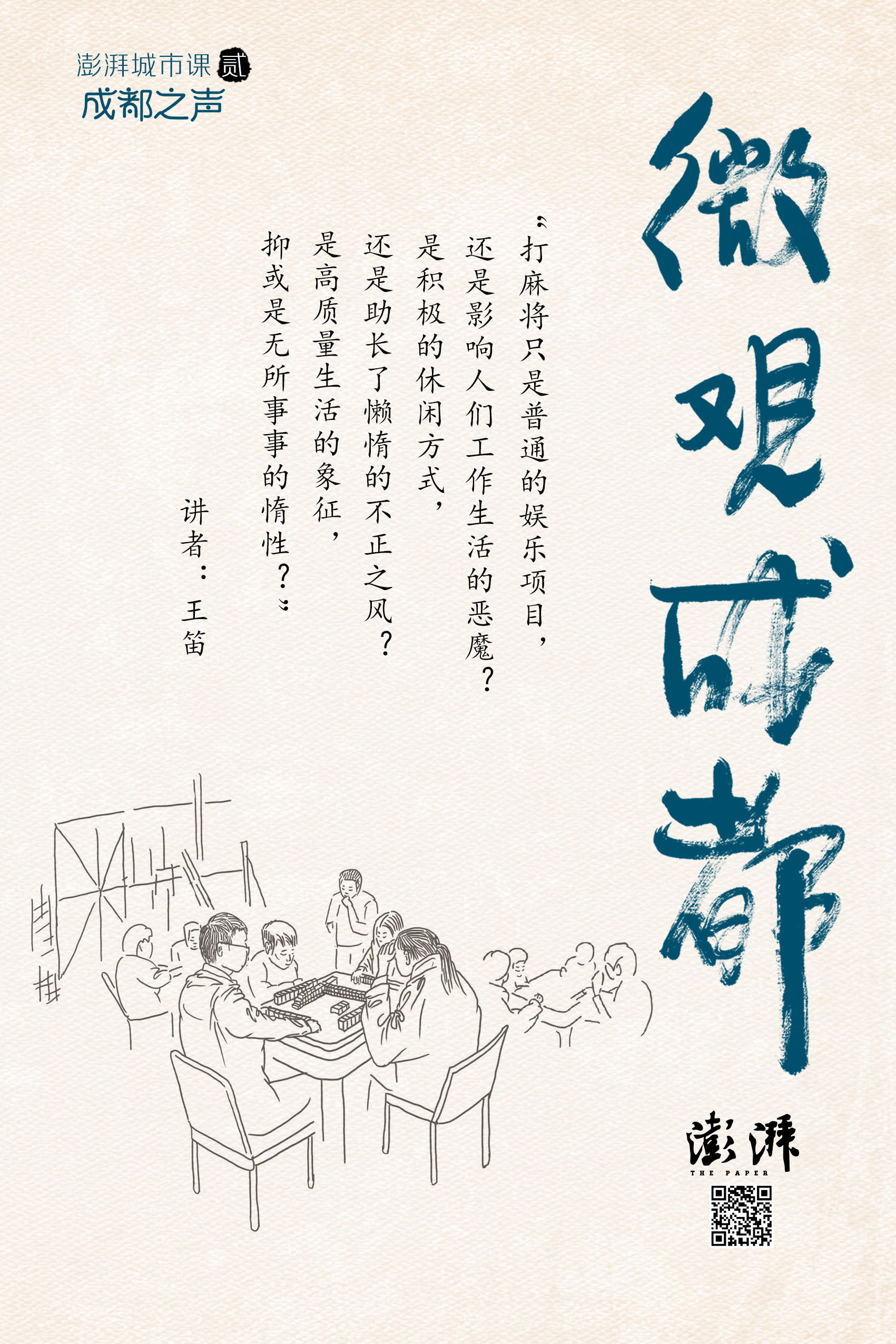
中国老百姓酷爱打麻将,长期以来不同的地方传承了一套独具当地特色的游戏规则。倘若在外地碰到家乡人,只要两人对一对麻将的打法,便能迅速辨认出到底是不是来自同一个地方。
在成都,无论是去茶馆、公园,还是老旧居民区,找一处打麻将的地方绝不是什么难事。成都人打的“川麻”叫“血战到底”,搓麻将发出搅动风云般的“哗啦”声,搭配牌桌上中老年大妈大爷们紧锁眉头的认真神情,颇像一场正处于千钧一发的战斗。
在《微观成都》第四集中,历史学家王笛将从成都一场因打麻将引发的官司谈起,说一说这座城市和麻将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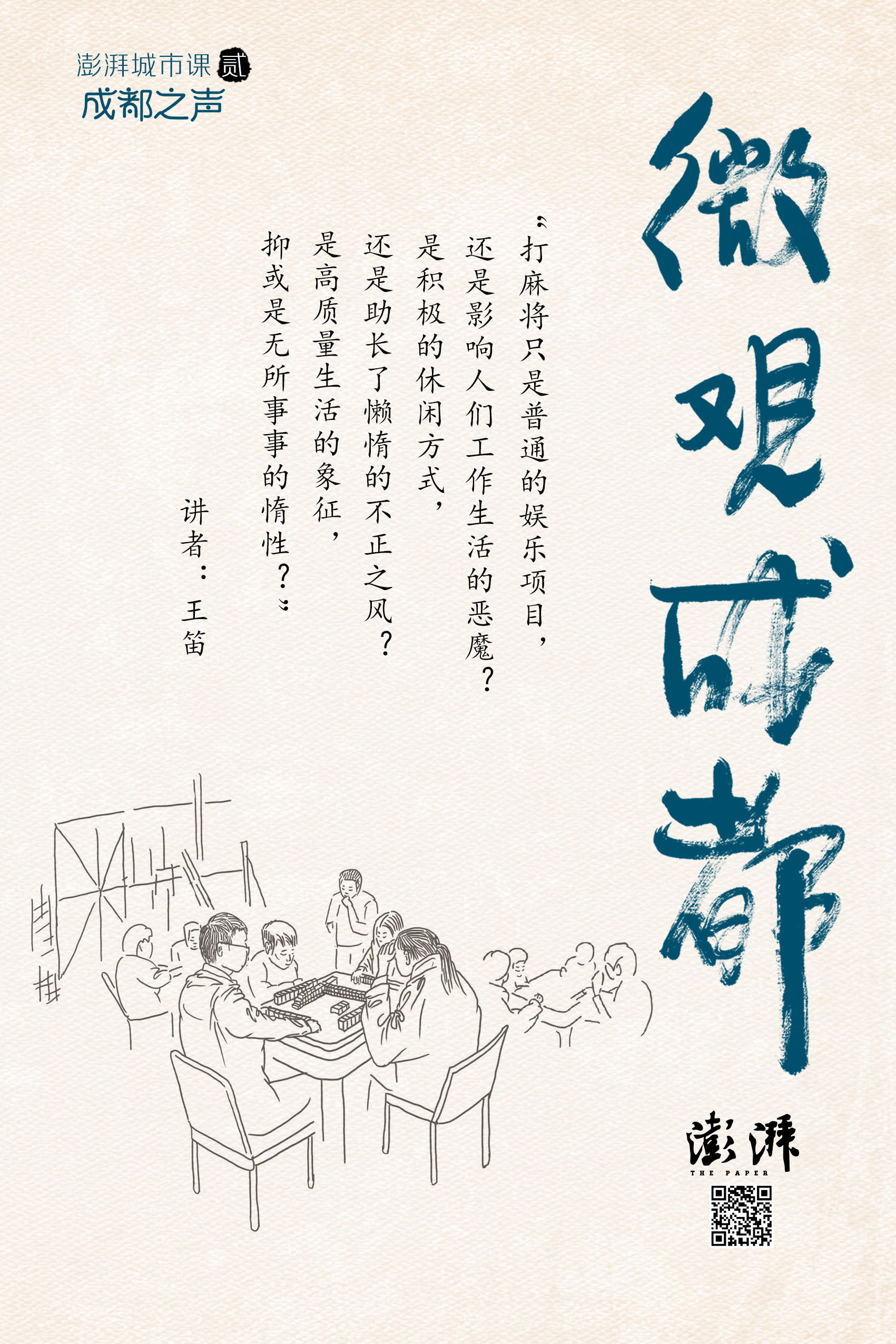
插画&海报制作:陈鑫培 题字:孙鉴 策划:康宁
欢迎收听本集音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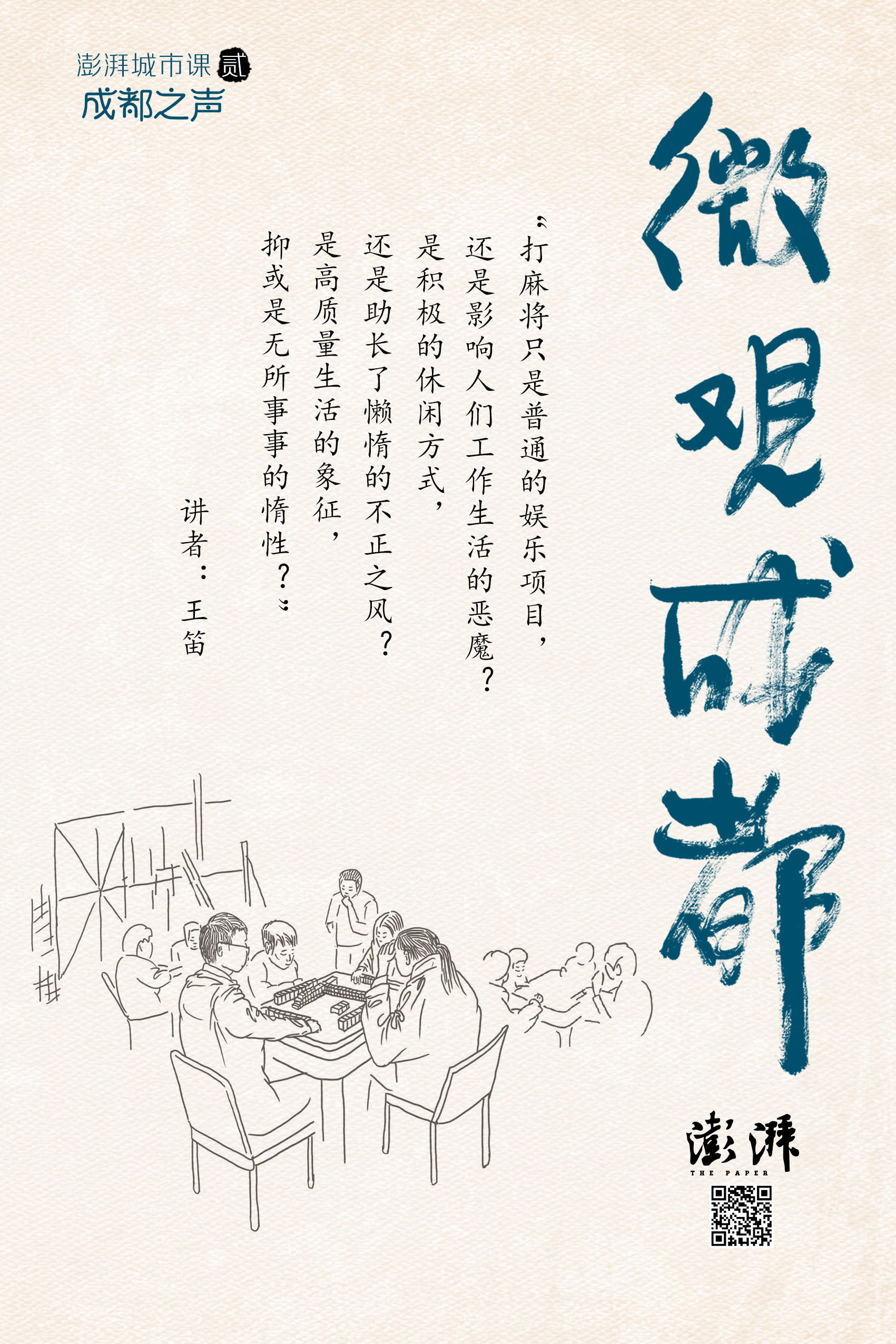
讲者:王笛 音频制作:康宁本集文稿如下:
2000年10月,成都发生了中国第一例因打麻将导致的法律纠纷,受到了全国范围的关注,并引发了一场关于个人权利、集体利益和城市形象的大讨论。
故事的主角是28岁的余女士,她住在一处居民小区内一幢普通公寓的二楼,房间的窗户正对着楼下居民委员会设立的居民活动室。那是小区居民——尤其是退休的老年人不分昼夜打麻将的主要场所。
从早到晚,麻将声令余女士辗转反侧。老人们打麻将发出的噪音使她和她的孩子夜里难以入睡,她甚至患上了神经衰弱,不得不依赖服用安眠药物以助休息。就此问题,余女士不断地向居委会投诉,甚至几番报警,但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视觉中国 资料图2000年11月16日,关于此事进行的第一次法庭听证为我们提供了不少这场纠纷的细节:2000年10月7日晚10点20分,该小区的居民们在活动室中打麻将的吵闹声使余女士和她的儿子难以入睡。余女士下楼劝阻,希望邻居停止打麻将,但没有人理会她,她一怒之下便剪了活动室的电线。
第二天早上,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将余女士拦截在小区门口,要求她对前一晚发生的事进行解释,解释清楚才能去上班。面对此种情形,余女士再次报警,前来解决争端的民警建议居委会另择新址设立活动室。随后,居委会决定为此召开一次居民全体会议,商讨解决办法,投票决定晚上是否能在活动室打麻将,什么时候活动室关闭等问题。
一共有近70位居民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年人。会议开始时,居委会主任首先讲述了这起因打麻将引起的纠纷的经过,并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条款,接着便请居民们自由发言。不难想见,参会的绝大多数人都支持打麻将。
一位72岁的老人说:“老年活动室应该开!老年人打点麻将娱乐一下是应该的!”接下来,参会者争相发言,异口同声认为活动室应该继续开下去,不过关于活动室的开放时间,他们同意可以稍作限制。在场的一位老人说:“不能为了她一人的利益,牺牲我们大家的利益。”
在会上,余女士不断重申自己的处境,希望得到别人的理解,并且反复强调:“老年人可以有很多娱乐活动,为什么不搞点别的?难道只有打麻将才是娱乐?打麻将也行,但是不能影响别人休息。”她抱怨说,有些人从早上8点就开始打麻将,中午吃饭后接着打,并一直“战斗”到深夜。“难道我们也得陪着等到深夜才能休息吗?”她要求将麻将室的开放时间限制为早上10点至中午,以及下午2点到6点,中午午休时间和晚间关闭,以保证她和孩子有足够的休息和学习时间。
听了余女士的说法,有人抱怨道:“全院300多户人都不反对打麻将,就你一户闹得凶,你太霸道了!”一位老人生气地嚷嚷道:“你想清静可以,就不要在这里住,就不要在成都住!”余女士微弱的抗争声逐渐被淹没在了批评与质疑中。
会议将近尾声时,居委会负责人提出投票进行决议,结果是67票支持晚上打麻将,1票弃权,只有余女士1票反对。作为妥协,居民们同意活动室冬天和夏天的关闭时间分别设在晚上10点和11点,而过于吵闹的人则将被请出麻将室。
面对这样的结果,余女士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唯有将居委会告上法庭。“这样的结局早在意料之中!”余女士说,“在这个异常酷爱打麻将的大环境里,从一开始我就是孤立无援的。但我认为,这样的事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决定。我决心诉诸法律来讨回自己的权利。这官司我打定了!”
这起诉讼引起了成都当地居民和各路媒体的强烈反响。超过300位居民和20家以上的媒体出席了11月16日举行的第一次听证会。
这个诉讼案之所以能够吸引如此大规模的关注,归根结底是因为麻将对百姓生活的影响非同小可。麻将是中国最为流行的娱乐方式之一,人们都关注着这个案子会如何影响到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此外,这个案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打麻将是否损害了成都慢节奏“休闲之都”的声誉?麻将的价值和意义是否需要重新评估?在现代生活中是否应当保留它的一席之地?健康的娱乐和生活方式又该如何定义呢?最重要的一点是,社会该如何在集体利益和个人权利间寻得平衡?
在这个案例中,集体利益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冲突彰显无疑。在中国,人们总是被告诫应该“个人服从集体”,但余女士的行动明显违背了这一原则。虽然,社会主义国家一向对“集体利益”赋以更多的强调,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亦愈发注重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可以说,这个诉讼给了世人一个思考以上问题的机会。
因原告、被告均无法对打麻将发出的声音是否构成噪音污染进行举证,因此法庭决定安排成都市环境监测局对噪音指数进行测定,并在具体测量数据公布之前暂时休庭,择日再审。

小镇上的老人在简陋的社区活动中心打麻将。2019年7月,王笛摄于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郪江镇。这个案子实际上把居委会置于了两难之境。居委会是管控社区最基层的组织,作为城市管理的有效工具而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将居委会定义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全中国有119000个这样的组织。
同时,因为居委会的主任和成员多是在退休居民中直接遴选,所以他们通常与其他居民私交甚笃。作为连接国家和社会的准官方组织,居委会起着维系政府机构和民众之间关系的作用,其功能包括调解邻里纠纷、维持社区治安、保障公众福利等,它是城市管理体系的最基层结构,而为人数不断增长的老年退休人员组织业余休闲活动则往往成为其重要的任务之一。

成都退休大妈在茶馆里打麻将。2003 年5 月,王笛摄于成都一家茶馆。到茶馆中打麻将的人越来越多,一些居委会也顺应这个潮流,提供空间供市民——尤其是老年人娱乐,在余女士的案例中,活动室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它俨然成了整个社区的交流中心。
打麻将作为休闲由来已久,对打麻将的批评,包括其浪费时间、牵涉腐败、有损城市形象等,从来就不绝于耳。从晚清开始,茶馆以及麻将便一直是社会改良者和政府执意批判和锐意改革的对象。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便将麻将视为“国戏”,并通过写作《麻将》一文加入了“反麻运动”。他在文中强调,过去中国的三个恶魔:鸦片、八股和裹小脚都已不存在了,麻将是第四个恶魔,它发展得异常兴盛,却没有人批评它对于国家民族的损害。
胡适算了下人们浪费在打麻将上的时间:“麻将平均每四圈费时约两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一百万桌麻将,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费四百万点钟,就是损失十六点七万日的光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都还在外。”
但是,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激进的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发生半个世纪之后,麻将不但没有消亡,反而愈加欣欣向荣,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虽然“反麻运动”声势浩大,但不少人仍对打麻将持积极态度。一些人认为,麻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对社会稳定有利。他们认为,既然麻将被体育总局认证为一项正规的体育活动,那么它便应该作为传统文化精粹,尤其是老年人的消闲活动被推广。
在一次关于成都旅游发展的会议上,一位国家旅游局的官员建议推广“麻将文化”来打造成都“休闲之都”的声名。他甚至建议,干脆建一条“麻将街”,办一份《麻将报》。
2004年,《新周刊》就将成都列为继北京、上海和广州之后的中国第四城市,认为其“城市魅力”最有特色。相对于上海的“小资文化”、广州的“商业文化”,成都因其“市民文化”而为人所熟知。在成都,不论贫富,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娱乐方式,这造就了一座“非常祥和”的城市。在大部分中国城市疲于奔命地追求经济增长之时,成都却不紧不慢地乐享休闲愉悦的生活方式。正如易中天对成都的评论所述:“如果说广东人敢于生活,成都人则善于生活。”《新周刊》称:“这些对成都的评论,都显示出成都是一个注重生活品质的城市,并没有因为经济建设而忽视精神生活,这是成都的品牌打造和城市运营最为成功的地方。”
从这起麻将的官司中,我们可以看出今日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如何和传统的生活方式融为一体的。现代化的确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并非如人们所设想的那般翻天覆地,文化的连续性于此体现。
打麻将的社会大环境从二十世纪早期便开始变化了,但这项游戏的核心属性——娱乐、赌博和社交——却并未发生什么变化。
人们就怎样看待打麻将长期争论不休。它只是普通的娱乐项目,还是影响人们工作生活的恶魔?是积极的休闲方式,还是助长了懒惰的不正之风?是高质量生活的象征,抑或是无所事事的惰性?是应该先关注集体利益,还是个人权利?
关于打麻将的争论反映了人们如何对社会变化进行反应,他们如何在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现代社会道德准则之间寻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