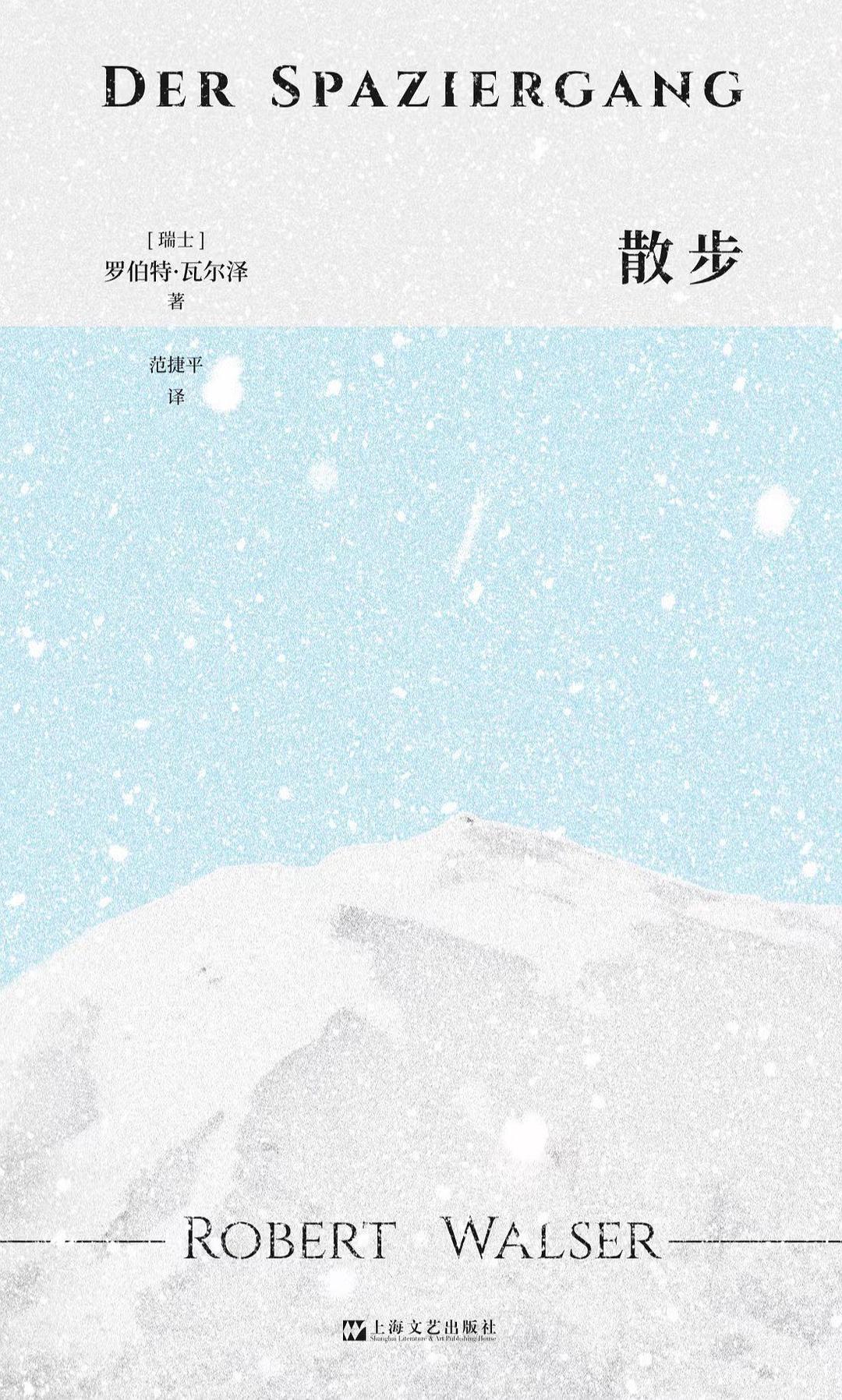本文为“出去散步吧,这是生命之光——与瓦尔泽一起散步:罗伯特·瓦尔泽《散步》新书分享会”文字整理稿。
苏远:各位老师,各位读者朋友们下午好。非常高兴在刺鱼书店举行罗伯特·瓦尔泽的《散步》(范捷平老师译本)新书发布会。大家可能已经看了我们的简介,我一看嘉宾的名字就备受震撼。因为我们知道王炳钧老师是《德语人文研究》的主编,也是《文学与认识》的编撰者。虽然我之前就是对德语文学了解没那么多,但是我一想到我以前有可能还读过他编的德语教程,就觉得这是特别难得的一次机会。范捷平老师曾获得过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杰出贡献的银质奖章,虽然我做他的编辑也有一两年的时间,但今天是第一次见面。任卫东老师是翻译、研究卡夫卡的专家,也是彼得·汉德克的译者。王正浩是范老师的学生,也是研究这个德语文学和文化学的专家,他翻译了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以及茨威格的《一个女生一生中的24小时》,所以今天是一个很好的了解德语文学的一个机会。
接下来我们先了解一下《散步》这本书。首先,虽然在书的扉页上有关于瓦尔泽的简介,但是我们还是很想听一听范老师和各位老师们来介绍一下这位作者。首先就有请范老师。

对谈现场
范捷平:这场活动是一个与大家见面的好机会啊,因为我们今天来的都是中国现在研究德语文学的非常杰出的学者、老师,也很年轻,我很开心跟我的朋友们在一起来聊德语文学,也特别感谢苏远。
我在德国生活过很多年了,我研究德国文学大概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现在,主要是研究罗伯特·瓦尔泽,那另外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德国大作家,马丁·瓦尔泽。我今天讲的罗伯特·瓦尔泽在德语文学中就像掩埋在雪地里面的这样的一块瑰宝。如果太阳不出来,天气不热,咱们就不知道他是谁。要是像今天这样一个夏至日,它把雪都融化开,就会露出这么一块宝石,我们就会知道这块宝石是多么珍贵。所以罗伯特·瓦尔泽是德语文学当中被人遗忘的、了解不太多的一个作家。我认为他的价值也正是因为他鲜有人知,因为如果他被众人熟知,就可能会被商业化或者不那么艺术了,瓦尔泽恰恰是一个没有被消费透的作家。
瓦尔泽的一生其实活得很长。他的生卒年是从1878年到1956年,他在1956年去世的时候特别伟大。他死的时候是一个精神病院里的病人,他可能是因为贫困潦倒,没什么钱,然后就躲进了精神病院,我甚至怀疑他的精神病是装出来的,因为没有办法证明他是否真的患有精神疾病。瑞士是一个福利非常好的国家,那个国家的人百分之百都是有保障的,有精神病也有保障。他出生在比尔,所以他就回到他的原籍,在那里可以吃住免费。那天好像是1956的圣诞节,那就应该是12月25号,他吃完饭跟往常一样去散步,在雪地里走,当时积雪非常厚。我去过那个地方,走过他去世的那条路,但我是夏天去的,那里正好是绿茵茵的草地。我走到那个地方,它有很多栏杆,因为瑞士有很多牛,牛在脖子上要挂个铃铛,叮叮当当的,夏天的时候是这样。冬天的时候,栏杆上有很厚的雪,但罗伯特·瓦尔泽没有去扶那栏杆,他觉得好像扶了以后就会碰掉这些栏杆上非常自然的东西,于是他往前走,走到一个地方就倒下了,倒下以后就死去了。这里有一张照片把它记录下来,当时没有人发现他,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被几个小孩发现,然后告诉给附近的农民,后来慢慢地被人知道了,也被全世界知道了,这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
瓦尔泽出生在比尔这个地方,1878年他出生在一个小镇子里,他父亲一共生了大概有五个孩子,他关系比较好的就是他最小的一个哥哥和他的一个姐姐丽莎。他从小与别的小孩子一样有梦想,有一天,据说是有一个剧团到他们那个地方演戏,演出席勒的一个戏剧:Die Räuber(《强盗》),他看了以后觉得特别好,就想当一个演员。但是我们都知道,瑞士人说的瑞士德语,特别难听懂,然后瑞士德语需要演戏的话必须要会Hochdeutsch,也就是所谓的标准德语,但瓦尔泽说不来。而且因为他像阿尔卑斯山上的农民,接触的世界比较小,非常腼腆,不太会说话,因此到他青年的时候这个少年时代的梦想一直没有实现。
瑞士人都喜欢出去闯荡,而且许多瑞士作家都不在瑞士奋斗,所以瓦尔泽很年轻的时候就去苏黎世一家小公司里去工作,后来他开始写一点诗。好像是在1899年的时候,他写了第一首诗,写了诗以后给别人看,大家觉得诗写得还不错。正好借一些朋友的关系,他认识了Victor Widmann(约瑟夫·维克多·威德曼,瑞士记者和作家),这个人当时在苏黎世有一份文学杂志。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个特点:文学开始有了新媒体,即文学杂志、文学刊物,还有一些日报,到周末的时候还有一个副刊。这样的新媒体对于当时的作家来说就有了一个新的机会,大家可以去发表,或者写点东西。瓦尔泽就把自己写的一些诗歌寄给了Victor Widmann,他看后觉得很好,就在《联盟》杂志上发表了,大概这是瓦尔泽出道的开始。所以瓦尔泽一开始写的是诗歌,后来他又认识一个叫Franz Blei的人。当时有很多文人,他们既是作家又是文学批评家,同时还是杂志的主编。所以Blei也是一本杂志的主编,他当时在杂志上也会刊登瓦尔泽的一些作品。瓦尔泽就这样开始了文学工作。
1905年前后,瓦尔泽觉得自己应该成为一个专业作家,于是他就去了柏林投奔他的哥哥,他哥哥卡尔·瓦尔泽(Karl Walser)在柏林画画,也是柏林现代派的一个著名画家。当时柏林有很多艺术家,所以罗伯特·瓦尔泽到了柏林以后就进入了这个圈子。柏林有一个出版商布鲁诺·卡西尔(Bruno Cassirer)给瓦尔泽预支稿费让他来写小说,于是就有小说《唐纳兄妹》(Geschwister Tanner),《助手》(Der Gehülfe),以及《雅各布·冯·贡腾》(Jakob von Gunten)等作品。但写完了以后没人读,卖不出去,之后出版商就不再给他预支了。这样他在柏林大概待了七年的时间,之后又重新回到了瑞士,这也就标志着他这一段文学生涯的失败。
后来他回到瑞士后又不断地给这些杂志社、报社写一些小东西,开始时发表比较容易,渐渐就没人要他的东西了。按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写的东西也许过于先锋,一般人不习惯,当时就有人说他连德语都不会,怎么能写文章呢,他收到很多读者的批评。这样到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他的发表越来越困难,于是他留下了很多手稿。他用铅笔小字写了很多文学草稿,而且字越写越小,把字写在香烟盒、车票、日历本上等等,但写完了以后也发表不了。到了1933年,他就进了赫里绍精神病院,那家精神病院开始时给他一间有桌子的房间,说他是一个著名的诗人,也会写小说,就请他来写小说。但瓦尔泽就是坚决地予以拒绝,他认为他来这里就是发疯的,同时还能吃免费的饭,但作品呢他是再也不写了。他写下的那些手稿有一天就被一个叫卡尔·塞里希(Carl Seelig)的人发现了,他之前在柏林期间就关注到了瓦尔泽,但突然发现找不到这个人了,之后在赫里绍发现了他。于是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拜访他,一直到瓦尔泽1956年去世,塞里希后来写了《与瓦尔泽一起散步》这部作品,记载了他跟瓦尔泽的一些经历,对研究瓦尔泽也特别有价值。
《散步》
苏远:谢谢范老师,讲了很多细节。其实刚才范老师也讲了瓦尔泽的作品在德国的出版及再发现。后面我们请王炳钧老师,来评价一下瓦尔泽。
王炳钧:谢谢苏远。其实我对瓦尔泽没有什么研究,零星地读到过他的一些文字。刚才范老师讲的这个小字,对它的破解在德国是一件比较轰动的事情。另外就是“散步”这个主题——他死在雪地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主题,在今天似乎可以把它理解为能够反映现代性悖论的东西。你看瓦尔泽《散步》这篇文章,看似是一个通常意义的休闲活动,但你看他在其中讲的故事,就会发现是与他的散步并行,且时间节奏非常紧张的东西。这实际上就是现代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所说的“现代性加速度”这样的问题。这里还关涉到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如果说时间就是金钱,那这也是19世纪才开始的一个口号式的东西,时间在文化学上就成了衡量现代的一个标准。比如,如果说我有闲暇,那我就是个无所事事的人;但我说我总没时间,就好像我是一个忙碌的人;所以谈到散步,就是说我既能谋生,也有时间才会去散步。另外一点,是本雅明讲的游荡者的问题,实际上一方面也是无所事事,但同时又是商品经济带来的社会分化现象的反映。这就像是在讨论群体中的人,说大都市的人精神或感知的麻木,尤其是坐在公共交通里面,两眼相对但半天不讲一句话,所以散步能体现现代性的一个悖论的问题。那另外一方面是散步这个体验,之前我们说这是一个放松的、休闲的活动,现在又多了一层所谓的强迫症似的、受健康意识驱动的内涵。还有一个可能是我感觉好玩的地方在于瓦尔泽对观察到的人其中的姿势的描写,就是他对这个不同的人群的观察带有一些自嘲式的和反讽式的表现。
范捷平:就散步这个活动,我想说这是工业化带来的一个概念,我们德语中叫Spaziergang,我觉得这和Wandern、Flanieren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区分。我们说wandern这件事情是德国人的最爱,这个词的意思是比如说在森林里面走很远的路,从甲走到乙这样一个很美好的事情。但走路到了这个工业化以后,我发现就是Spazieren,这件事情在法国是需要撑伞的,在中国夏天的时候也因为太阳晒去撑伞,这是一个工业化有了马路后开始的一个活动。而Wandern是在一个松软的森林里,冬天是那种雪地里走路。刚才说的Flanieren是毫无目标的,是在大城市里的一种观望,会看到许多汽车、橱窗等等。但瓦尔泽的《散步》,它是混杂的,既有一些都市的,也有一些乡间的,既是Wandern也是Spazieren,同时还有一些本雅明所说的无所事事,但他又有职业,他是作家,他不散步就写不出东西来,所以我想这也是工业社会、现代社会带给我们的一个文学想象。
苏远:好,谢谢王老师,也谢谢范老师,对我们理解散步又有了新的一个视域。之前我读《散步》的时候也感觉好像并没有什么田园风光,也没有那么诗情画意,就是它时间节点特别明确,虽然他不是为了工作去忙,但也会有事物在不停地推动他,所以我觉得现代性悖论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瓦尔泽的作品。
还有范老师讲的散步的内涵兼具漫游与散步两种特性,其实我之前备选的一个问题也提到,作家散步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当然卡夫卡是个例外,像托尔斯泰、黑塞都会在森林里散步、漫游,然后有奇遇,我想问的是,为何单单只是瓦尔泽与散步紧密连在一起,他在“散步界”是如何有一席之地的?我们来听听老师们的看法。
罗伯特·瓦尔泽
任卫东:我觉得瓦尔泽的散步可能不是一个纯粹的散步,散步对他来说是有特别意义的,它可能更像是生命或生存,或者是像写作一样的意义。刚才提到的卡夫卡,他之前也在朋友的强迫下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但他发出来后就被别人视为瓦尔泽的笔名,觉得两人很像,我是从这里了解到瓦尔泽的。之前说瓦尔泽因精神疾病到精神病院,我先开始认为他的文字会有一些阴郁,但读完后我却发现这些文字很轻盈、很俏皮,好像还有一些自嘲反讽在其中,这完全颠覆了我对他的想象。然后我看范老师把本雅明的文字翻译出来,我很认同其中的内容,尤其他说瓦尔泽所有的书、所有的写作,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文学写作本身,这在我读《散步》第一句话时就感受到了:“我现在开讲……”这似乎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的节奏。就像王老师所讲,散步和散步其间发生的事情的矛盾性,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本雅明说瓦尔泽的文字有一种随意性,他在《散步》中也说到“我不确定几点,因为我散步的热情油然而生”,这件事是突然发生的,但我们看到之后的内容似乎又是安排好的。既然是安排好的,又是一个写作的过程,我们是否应该考虑这几件事之间的关联性,但仔细想想又会发现没有,就是很随意的,这是我觉得瓦尔泽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他这样的写法放置在一个长篇小说中,比方说《雅各布·冯·贡腾》《唐纳兄妹》,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在我的想象中他可能是特别典型的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倾向。
王炳钧:那我补充一下。就刚才说的文学写作本身而言,我们从文学进程的角度来说,或者从德语文学的发展角度来看,虽然越来越走向一个,用系统论的话语来说,自我指涉的问题。也就是说,我写的可能不是我在外界观察到的,而是写作本身的一个世界,压缩到文学系统内部的一种反思、回馈,是对写作本身这一问题的指涉。
王正浩:那我就这点继续补充一下。瓦尔泽的文字和表达确实是有一种挑战性。我十几年前上范老师课时读的这些作品,如今再读是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最大的感受可能就是任老师的观点,瓦尔泽好像会把这个问题设定好,然后用文字游戏展开。第一句“我现在开讲”就很像佛经里的“如是我闻”,就通过这样一种表述让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信的,但不一定完全可信,因为他后面的表述还有很多,比方说他邀请读者参与,或者写着写着发现有些事情没有解决,那我就一会儿再来说。他就不断在这一文字游戏中展示出这样的一种随意性,一种散步时的感受。
所以对读者来讲,你不太会抓住他的点,如果只是纯欣赏情节,就会觉得平平常常、普普通通,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但是其中会感觉到生命的快乐。前些日子我在镇江的金山寺看到有一个牌匾,上面写着“心生欢喜”四个字,我觉得瓦尔泽在这样一种文字的游戏里表达出生命的这样一种喜悦在。这是最近在读《散步》时的一种感受,用一种从现代或后现代的观点来解释,感觉不仅在启发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对下一代来说依然是一个象征,是一种隐喻。
范捷平:那我再补充一点本雅明的观点。本雅明对瓦尔泽的评论只有序言里的这一篇,他主要讨论了什么是瓦尔泽文学写作的目的,它的目的就存在于无目的性当中。这篇评论对瓦尔泽文学的解读有指导性的意义。
我觉得今天我们读瓦尔泽的作品,有点像滚雪球一样,比方说我先声明我是一个作家,我写书写累了就出去走走,那么走的过程其实也是我写作的过程,这就是很小的一个雪球,然后越滚越大的结果。我们看瓦尔泽在作品中都是Ich-Roman(我-小说),Ich-Text(我-文本),Ich-Literatur(我-文学),都是Ich(我),而且大部分都是第一人称。有时他可能会带一个Maske(面具)把自己掩饰掉,或取个新名字,但其实写来写去还是在写他自己,所以我认同他将写作与生命、人生结合得非常紧密。他的写作方式我们今天看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如果倒退100年,当时的读者是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那里走出来的,他们会很难接受这样的写法,恰恰是这样一种文学叙事方式,使他具有一种先锋的特点。
另外,瓦尔泽的《散步》有两个版本,我选了第一个版本,我觉得这版他是真的想放下笔出去走路,是一种毫无目的的方式。后面瓦尔泽修订的版本反倒加了一些目的,这就很难体现瓦尔泽的随意性这个特点了。我们看他的Aus dem Bleistiftgebiet(《来自铅笔领域》),解读出来后都没有给他加一个题目,因为这个特点就在于原始性。这就好像秋天落叶铺满大道是很漂亮的,扫干净之后反倒会有一些遗憾在,所以这是我坚定地选用第一版的原因。
苏远:范老师讲完后我更清楚了范老师选用第一版做翻译的原因。随着我对瓦尔泽了解的深入,他的作品好像那种白玉未经雕琢的状态,而他本人也更像是横空出世的文学坐标。
关于瓦尔泽的写作没有目的这点,我找到一篇贝尔富斯的评论,他说“在他的故事里,唯一的栖息地就是语言本身,他们无处可去,我想这就是把他称为‘诗人中的诗人’的原因。作家们梦想写出没有内容的文本,而罗伯特瓦尔泽就非常接近这一目标”。对,通俗一点讲,瓦尔泽的文字里虽然有一些小事情发生,但都非常细微,没有太多的情节性,就只是当时的瞬间,描写一些场景,这是我的一个感觉。他虽然有时像卡夫卡一样,有一点神经质,但你读起来还是有一个愉悦的情绪在。那接下来想请各位老师谈谈,卡夫卡和瓦尔泽的异同。
任卫东:我想到卡夫卡有一篇叫《突然的散步》,篇幅很短,但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想象。我带着对那篇的印象来读瓦尔泽的《散步》,我发现这篇要丰富很多,但我会思考:瓦尔泽真散步了吗?书里写从上午出去到晚上回家,我是在想他真的出去散步了,还是他也是在写字台和精神世界里进行的一场散步。
范捷平:他写的时候一定没去散步,这点我想与卡夫卡是一样的,都是一场文学的散步,在纸面上的散步。但表现的手法不一样,卡夫卡在德国文学或文学评论史上受到了布拉格学派的影响,从卡夫卡的日记当中也是有佐证的。那位马克斯·布罗德(Max Brod)是卡夫卡与瓦尔泽共同的朋友,他们交情不一样,马克斯·布罗德与瓦尔泽未曾谋面,只有一些书信来往。卡夫卡会读一些瓦尔泽的作品,还会嘱托布罗德要及时告诉他有关瓦尔泽新作的消息,他读瓦尔泽《雅各布·冯·贡腾》还是《唐纳兄妹》后非常兴奋,所以他们之间是有一些密切关系的,而且他俩的风格也有些像。
任卫东:我看到这里有几个短篇讲述得特别完整,其中都在探讨写作和文学的问题。卡夫卡的短篇像《判决》《变形记》是能看到一个完整的故事,但他的长篇里似乎是在努力写一个完整的故事。瓦尔泽我看他在短篇里也是有很完整的故事在,他要讨论的问题也在,那他在长篇小说里是什么样呢?是不是也有一个完整的结构在?
范捷平:这个我简单比较一下。我们刚才说他的随意性,但在提的时候,我们说ja(是)时也要带一个nein(不),说他是随意的,他一定是不随意的,反之也是这样,他大概是这样一个矛盾体。我在研究瓦尔泽的时候发现他特别的“做作”,我曾经评论“他经常喜欢翘起兰花指说话”,我们说这在中国戏剧里是表现女性特点时的一个手势,罗伯特·瓦尔泽就是喜欢这样编故事的,他编造的都特别不真实、特别奇异,但他始终都在表现自己,因为他经常不成功嘛!这又涉及刚才我们讨论的躺平问题,罗伯特·瓦尔泽是特别不愿躺平的,他是很想成功的,只是人们不看他写的东西,他会说我拼命地想让你们知道我是多么的厉害,但是你们不让我成功,我能怎么办?所以,这个点就成了他文学作品中的反讽,让你们觉得好笑。
我经常认为瓦尔泽和卡夫卡写的东西不一样。卡夫卡是非常悲的一个人,是一个被伤害的人,是非常苦恼的一个人,他老是在想这个世界怎么这么对我,这是我们读卡夫卡时的那种经验。瓦尔泽不一样,你读完后总觉得有手指在你心头挠你,痒痒的。他是一种喜,这种喜是蕴含着一种悲的,但他用喜剧的方式来表达悲。他作品中的价值观和我们不一样,和德语小说中修养小说、成长小说、教育小说也不一样,他是反过来讲的,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反教育小说”,是非常现代的,所以从情节上讲,他和卡夫卡的理念还不太一样。他塑造一个完整的故事,但又把这个故事彻底颠覆成一个毫无意义的东西。他的《强盗》变成了一种完全漫游性的,没有目标、没有故事的东西,一点情节都没有。有人认为这与他患精神病有关系,我认为可能不是这样,因为这是一篇写在草稿上的文字,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说。
王炳钧:就瓦尔泽与卡夫卡之间的差异来看,我认同你说卡夫卡是对自身遭遇的一个强烈反应,而瓦尔泽似乎有一种更为“欢快”的东西在,这一方面是一个自我指涉、自我反省的过程,他没有明确涉及生存这种更严峻的指涉,而更多的是具体的书写过程。康德在谈美学时认为问题首先是一个美的感受,这也是一种无目的性,我更多的感觉是这样的。他们实际上反映的问题都是通过文本的表述让你去感受,但实际上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全貌”让你去把握。这就类似我们不是拿地图去看城市上的明确坐标的,当你进入城市中行走,你没有办法做到这样一种概览式的转换,而是必须身体在场去感受这个瞬间,是一种探索。就《散步》而言,其实更多是一个跟主体体验紧密相关的东西,我想可能两个作家在用不同的方式来演绎现代性的问题,因为我记得有学者说过“卡夫卡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范捷平:是的,卡夫卡好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荒谬,或者是怪异,有点像表现主义后的绘画,像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作品一样,认为这个世界很怪异,我透过这个视角看见这个世界都是不准确的;反过来,罗伯特·瓦尔泽在他作品里描写的世界都是准确的,但自己不准确。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差异。
苏远:我认为他们俩的相同点都在写小,是很小、很弱的人物,而卡夫卡在写小的时候好像在削减自己,削减且异化自己作为一个主体的人。此外,我认为瓦尔泽是在真散步,他几乎每天可能都要出去散步,而且有时候夜里还会出去散步。就是在他可能精神病发作之前,他也保持着这种散步,散步好似跟他是融为一体的,他是一个散步中的人,他必须要散步才能维持自己正常的活动。还有他其实是没有自己的朋友的,他总是一个人,甚至都不像卡夫卡还有女朋友,是之后出现的监护人卡尔·泽里希(Carl Seelig)一直陪伴他。有篇德语文章写到他从伯尔尼到日内瓦,大概720公里,几天几夜的时间在路上。我在看《与瓦尔泽一起散步》时发现他俩有时的散步更像是旅行,也是一起跳上一趟火车,然后就出门好几天。现代大家会有City Walk这样一个很时尚的说法,我想这可能是不同时代的散步不同称呼吧,但大家都是在用双脚丈量土地。
王正浩:那我就苏远老师的论述做一些强调。散步对瓦尔泽来讲是一个Beruf(职业),有点类似于他的职业,换句话来讲是演变成Schicksal(天命,命运)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他要去打发这样大段的时间,这是他如何去解决的问题。卡夫卡的生活还是很多彩的,这一点他们俩还是很不同的。那如果了解他们的家庭背景,或许会有一点新的角度。
瓦尔泽的家庭是阿尔卑斯山上的一个农户,而卡夫卡的家庭虽然算不上富家子弟,但至少生活还是不一样的,他上过大学,而瓦尔泽只做了一个培训,所以他们的人生境遇、他们的人生感悟,以及他们身处的环境,会影响他们对世界的认知与把握。所以,我们如果站在Heim(家)的概念来讲,当现代人失去这样一种Heim之后产生的一种unheimlich(令人害怕的)情绪,这时的侧重面就会不一样。所以我在想,为何卡夫卡的长篇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而瓦尔泽还能写完,因为就像本雅明所说,瓦尔泽在作品里是被治愈的,不论是Angst(恐惧)还是Freude(欢快)都会在作品中被治愈,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而卡夫卡这种Angst是无法被解决的,他没法把这个情绪处理掉。这是我的一点感想。
丁君君:我提个问题。其实也是我刚才在思考瓦尔泽在写《散步》时,其中所有的这些事件它不是一个人的真实体验,它是有一个后续的加工,包括里面人物的一种长篇大论。所以我想问,瓦尔泽是不是在散步时,把他所有看到的人或事当成一个像催化剂一样的瞬间,这个瞬间激发他以往类似的思考,然后合成一个完整的文本,所以散步对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然在此之前以及在此之后他整个人格的某种东西是通过散步在文学上彻底散发出来。就是这是我一个猜想,所以也想听听范老师的意见。
范捷平:这个是对的。散步作为一种表现形式,它或多或少地贯穿在罗伯特·瓦尔泽的所有作品当中,我们看到其中的故事几乎全部发生在行进中,那些故事非常日常,他把这种日常生活的东西拼凑起来,我们用现代主义文学讲就是拼贴、装置和蒙太奇,他的拼贴性很强,是一种精心策划的东西,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inszieniren(组织编排)或Theater(戏剧),因为瓦尔泽本身就喜欢成为一个演员,但他不善于言说,而是善于书写,所以瓦尔泽本身的书写能力就是一种表演能力,也有人称它为“述行”。还有一点,我们说瓦尔泽经常出去有几天几夜的散步,有一次他接受一个邀请,去一个很远地方,他也是散步(漫游)过去,但去了之后,别人认为他口音太重,说不清楚,就让另一个人去代替他在台上朗读他的作品,他在下面鼓掌。这种情况也经常发生。
苏远:谢谢丁君君老师的提问和范老师的回复。那我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苏珊·桑塔格会评论说“瓦尔泽是一个错过时间的散步者”,黑塞也说“如果瓦尔泽有千万个读者,这个世界会平和很多”?我想听听老师们对这些评论的看法。
范捷平:赫尔曼·黑塞受东方思想的影响,让他变得不那么热血沸腾,所以他希望文学不是那么吓唬人的,瓦尔泽的文学就是心平气和,小小的一本书,这样世界会变得平和很多。这句话好像是1929年黑塞在《苏黎世日报》上发表的,他似乎已经看到这个工业社会,这种卷的状态。卷是后现代社会带给我们的,瓦尔泽是想克服这个卷,但事实上他也必须去卷,我想“世界平和很多”可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苏珊·桑塔格对瓦尔泽的接受是比较晚的,因为我们对瓦尔泽的接受本身是分两个阶段的,在20世纪初,有一批精英对他的评价很高,然后上个世纪80年代后也有一批,桑塔格是后面这一批的。而“错过时间”这种慢半拍,我想这可以从本雅明的思考中解读出来,本雅明经常说Scham(羞耻)这个词,评论卡夫卡的时候也用到这个概念,在我看来,Scham都是要克服的那种现象,人在感到羞愧的时候,都像挖个地洞钻进去,要掩饰自己,让自己消失,所以瓦尔泽的躲避Scham的方法是掩饰自己,让自己戴上面具,采用一种自虐、自嘲式的反讽,他会把自己视为一种没有价值的东西,然后从中让我们看到价值,而卡夫卡的Scham是更直接的表达,就此我认为瓦尔泽要比卡夫卡更加委婉一点。
王炳钧:我认同你说的文学作用这样的一个思考。文学不是灵丹妙药,我们在进入一种虚构的审美世界时,他会让你忘掉现实世界,转而获得一份“安宁”。还有Scham这个词,我们把他叫做耻感或羞耻感,以此作为一个基本的道德观念,那谈论卡夫卡和瓦尔泽更多的是呈现我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我所面临的世界,这个姿态是什么样的,我感觉更多是在区别对待世界的感知模式。瓦尔泽的《散步》一个是在行径中对外界的感知,有一种不确定性在;还有一个是反映视觉占主导地位的东西,更多的是看而不是交流,尤其身体基本上是不在场的,或者语言也是不在场的,然后去尝试怎么确定我与外界的关系,这样的距离一旦拉开,想象力就会变得更加丰富,或者说回到“我”,我用文字来描述“我”与世界的联系。
王正浩:就苏老师引用的黑塞的原话,我想我们读完瓦尔泽会得到一定的内心的平和,但并不是说读完就会完全放松。黑塞对瓦尔泽还有一句评价:我们可以爱他,我们可以笑他,我们可以恨他,接着可以马上跟他和解,我们能够与多少著名的诗人做到这样的?这就是说,你读瓦尔泽不会期待其中有什么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因为它里面描写的小人物,描写主体消解的过程,是为渺小者书写的。他不是把自己展现出来,而是歌颂,或者是为一种失败的、自卑的人提供一种与自己和解的过程,呈现一种失败是正常的,不是每个人都要展现自己的价值观。
苏远:还有一个问题,就“保持渺小”而言,在当今的话语体系来说是“躺平”,其实躺平也不是很消极的,它其实是对“卷”的一个抗拒和拒绝。这与瓦尔泽内在的哲学精神是否有一致性呢?或者说,在当今竞争过于激烈的社会环境中,有没有可能通过保持渺小来生存呢?
范捷平:我认为“躺平”与瓦尔泽是没有关系的。瓦尔泽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或者作为一种文本表达,这是一种艺术。如果在现实中,他是最不想躺平的,他的创作是在工业化社会中,在20世纪初的语境中形成的一种写作方式,或生活方式,我觉得瓦尔泽是真实的,他会通过语言的在场找到一种自我救赎。如今的躺平现在我认为是社会对人生存方式的反射,这背后有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在,而不是直接来评判躺平这个词。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负责。
王炳钧:我认为躺平是一个最表层的现象,是对外界规矩的反应。人们都想追求一个有意义的东西,但当出现看不透或摸不清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态。
王正浩:我同意范老师的解读,就是这是两个概念。瓦尔泽的文字是一种表达,一种艺术,他其中提到的渺小不是孤立人们躺平,而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态度,而他在文字中依然在游戏、在创作。而且我在现实中也发现其实不存在真正的躺平,他总会找些事情做,这就像瓦尔泽所说“人总得就这样活下去”,因为无所事事也是一种事情。躺平这可能是年轻人的一种口头禅,但真正躺平的几乎没有。
任卫东:我也认为任何一个躺平的问题针对一个作家而言都是不成立的,如果他们躺平了就不会在搞创作了。